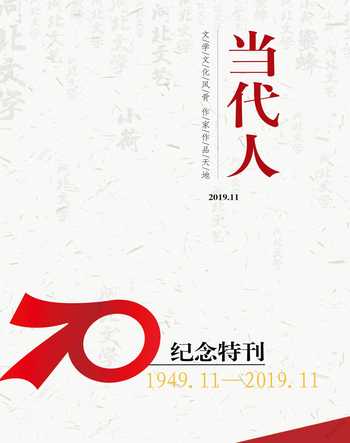栗乡的风(外一篇)
燕山南麓、滦水之滨的迁西,一到春夏,便有百花的香气氤氲弥漫开来。但这只是花事的序幕。端午节,一场真正盛大的花事才正式上演。
七十万亩栗林的四千万株板栗树一同开花了,队伍雄壮,声势浩大,仿佛是替自己的迟来致歉,又仿佛是一个永远不言败的人,攒尽全力露出嫩黄色的笑容,将原本单调的绿色海洋翻转,将全部的芬芳馥郁祭出,奉献给供养自己的这方水土和这方水土上的人们。
她的模样,仅是一簇簇、一穗穗布满嫩黄花蕊的小绒条,不美、不艳、不媚,平淡无奇,像极了那不争不抢很容易被人忽略的邻家小妹。
这样的邻家小妹,自然是无牡丹之国色天香千娇百媚的,然而却有牡丹所不及的韵味。她不挑高枝低枝,若是一朵两朵,就在黧黑的树干上摇曳,风吹过,亦生楚楚可怜之态;若是一团一簇,便商量着把一整条树枝、一整棵大树、一整片山林都开满。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是她芬芳的气息,甜蜜蜜、缠绵绵,一层一层把人包裹,却是再香也不觉得腻。因为,她对你的那般拼了命的疼和爱。
《诗经》云:“山有嘉卉,候栗候梅。”吹开漫漫光阴的浮尘,一路追溯到古孤竹国时期,迁西境内已有人类繁衍生息。不知是哪位勤劳的先民种下了第一棵板栗树,在这块土地上,它斗风霜战雨雪,年复一年,历尽苦寒,一点一点生长,终于伸出了铜墙铁壁般的枝干,长出了翡翠般的枝叶,开出了状如银链的花,结出了形如紫玉鲜美无比的珍果,并漫山遍野生息繁衍。它们就如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一样,朴实、顽强、坚韧。
循着历史的金戈铁马和狼烟峰火,仍依稀可见李广北击匈奴、曹操东征乌桓、戚继光十六年镇守蓟镇的身影;可见长城抗战爆发,宋哲元、张自忠、赵登禹等抗战名将在喜峰口一带以白刃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
生于斯,长于斯,我是多么幸运。一年一年,栗乡的风吹过我的发,栗林中留下过我的影,栗花香浸润过我的眉,我的眼……
小时候,常常挎着篮子去山里捡拾栗花。风从林间吹来,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栗花一根根扑簌簌落地。山间雾气氤氲,栗花香气馥郁,把正在成长的女儿心熏染得似水一样柔软。回到家,将篮子交给奶奶,看她盘腿坐在炕上编织。巧手的奶奶总是变戏法似的,一会儿变出一只活灵活现的小老虎,一会儿又捧出一只栩栩如生的小狗,一会儿又蹦出一个京剧里的小生……空闲时,还会编织一条长长的驱蚊的“火绳”。
虽然打马扬鞭去过许多地方,但从未与故乡长久远离。走在这香透了的县城中,感受上苍对迁西的眷顾,感受百姓在这寻常日子里得到的这份特别惊喜和安慰,我更加知道,自己命定是属于这一方山水的,一如栗树,一如栗花。
虫眼儿栗
秋日的正午,我和父母、姐姐一起去打板栗。
“秋老虎”肆虐,栗树遮不到的地方炙热无比。父亲笨拙地爬上七八米高的百年老树,挥着四五米长沉重的竹竿,对着高悬于树梢的数百个栗篷逐个敲打。
一个实实在在的苦力活,其中有很大的技术含量,必须准确判断出老树的枝杆健硕与否。如否,则有枝干折断摔下树来的危险,敲打时的用力方向也必须正确,如果不对把树码打落,则会影响来年的产量;栗篷浑身是刺,扎进肉里钻心地疼,如果砸中眼睛特别是眼球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我们母女三人齐刷刷一个姿势仰起头,盯着栗篷落地的方位,唯恐落下一个。
待父亲敲打完半边树,转过身去面向另一边时,我们就赶紧左手提着篮子,右手拿着栗夹子跑过去捡。炎炎烈日之下,又渴又累,却必须弯腰曲脊,将弓样的身影从一个山坡移到另一个山坡上,从一棵树移到另一棵树下。
母亲个性好强,过日子仔细,山坡上、草丛里、石缝里、未收完的庄稼地里,凡是可能落到的地方,母亲都逼我们一遍一遍地搜寻,一个栗子也舍不得丢下。
最后,我们将各自篮子里的栗果栗篷一同倒在编篓或是麻袋里,由父亲用独轮车推回家。
拖着被汗水湿透的身体跟在父亲后面,一步也懒得走了,直想着家就在眼前多好。有一次,我累极了,感觉身体早已不是自己的了,与母亲商量休息一会儿,没想到刚坐在地上头一歪倒地就睡着了。
每年,父亲将板栗用自行车驮到供销社去卖。回来时,车把上总会挂上几斤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或是金灿灿的泛着油光的油炸饼,有时还会买来几尺好看的花布给我们做衣服,家里充斥着欢声笑语。当日晚上,更是过年过节一般,母亲会炖一锅喷香的猪肉粉条,让我们吃个够。
入夜,母亲将洗干净的栗子哗啦啦倒入锅里翻炒,灶堂里红色的火舌一舔一舔地吞吐着,配合着屋内炕上爷爷旱烟锅的忽明忽灭。很快,板栗炒熟了,一股甜甜糯糯的香气回旋在夜的上空,打破夜的寂静,直穿过鼻孔冲了脏腑而来。趁热剥开一颗,一颗金黄的栗仁就跳了出来,放到嘴里,不用怎么嚼,就化了,满口生香,甜蜜绕舌。吃完一颗,再剥另一颗时,口水便会顺着嘴角流出来。肚子饱了圆了,嘴瘾还没过够,恨不得一个人能够长出两个胃。那香、甜、糯的独特味道,终生在我的大脑中萦绕,在我的舌尖上转动。
只是,第二天早晨,家中的灶台上总会出现一盆特殊的板栗——炒“虫眼”板栗。那是母亲在我们吃饱睡去后的后续工作。一颗颗原本完好的板栗,可能由于太甜了,又不打农药,在生长和储存的过程中,会有一种白色的小肉虫来咬,多的咬去半个栗子,少的也要咬掉一个小豁口。这样的栗子,是没法卖掉的。但我的母亲一个也舍不得扔,用水洗了,泡了,一条条虫子便会自动爬走。
多次和母亲抗议,倒掉这些“虫眼儿栗”。母亲不依,说从来“卖凉席的睡土炕”,总比挨饿强。我不解。终于趁母亲不注意,偷偷地倒在猪槽里好大一部分,被母亲发现了,狠狠骂了我一顿。我委屈地大哭,眼泪混着鼻涕直哭得要背过气去。
待我哭得没了力气,母亲将一个用缝纫机新缝的花布书包挂在我肩上,拍着我的肩膀说,别哭了,走吧,跟着你姐上学去吧,学习好了,考上大学自己挣钱,就不用像媽这样过日子了!
我成了全村上学年龄最早的孩子,也是学习最好的孩子。
再后来,全家都搬到城里,童年历经的一切都似乎远去。我开始暗自庆幸,终于成为了城里人,终于逃离了“虫眼板栗”及一切我不喜欢的有关农村的东西。
逃离这一切的我,开始无师自通地追求时尚,喝咖啡,吃西餐,涂稀有颜色的口红,穿多少也要带点牌子的衣服,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目光直视而不是左顾右盼,试图表明,我是地道的城里人。
但不是。
与朋友们一起,同喝上等乌龙,同吃法宴牛排,同用小勺舀起秘制鱼翅汤,慢慢地送到嘴边,不带任何声响地喝下去。朋友们吃得喝得轻松惬意,谈笑风生,我却经常沉默不语。我的目光总是透过眼前的饕餮盛宴看到童年的“虫眼板栗”,那些密密麻麻的白色的小虫子在啮咬我。
我试图把它们清除,试图把它们彻底消灭,但它们固执地蛰居在我的体内,仿佛宿命般无法摆脱。
我终于明白,我们的童年本身,我们不完美的肉身心身,其实也是带了虫眼儿的。你无法拒绝更无须摒弃。
(马蕙,本名马惠,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