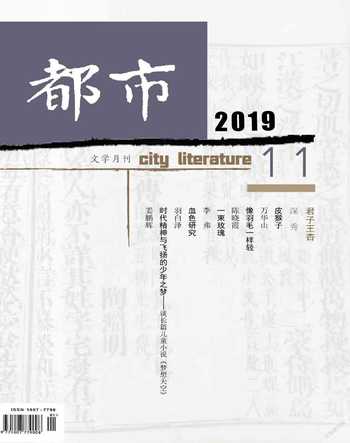不一样的苏二花
刘媛媛
二花很厚实。
斟酌了很久,我还是固执地用了这个开头。用厚实形容一个女子,显然会让她着恼,但是我想二花会明白我的意思。
当然,二花绝不是苗条的女子,但我说的,是她的文字。
第一次被二花的文字惊艳,是她的散文《海燕不哭》,这篇怀人之作,完全打破了常规的写法,既不悲戚缅怀,亦不历数逝者功德,是一种痛到极处的愤怒,一种因为无法释然无法放下的暴戾。因此在这篇本应柔肠百转的文字里,我看到了一种杀气腾腾的力道。这种力道让我且惊且喜,山西文坛又有新的亮光!
在《海燕不哭》这篇文章里,她在写海燕这样一位至亲离去的前后她们的关系和各自的成长过程中,二花有对自己的记述,这样一种遥相对应的写法,不仅加深了离去的人与自己的深厚关系,也用自身的变化给读者深刻的感世忧时之思,那种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的感觉不着一字尽在眼前。她在文章里有两段关于自己的描述:“瘦,眼里有恨,双腿似刀,骑女式木兰,迎风开足100迈,穿过边靖楼的城门洞上下班。那时我还无法想象,文学在我的身体里,是怎样的一个存在,也无法想象,张发老师在山西作家协会,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真的,我已经没有了恨,我是觉得,人只有把自己吃圆了,才能有效规避这世界所有的历练和伤害。我已经不骑100迈的木兰,我出行只步走,那是我唯一信任的。”由是我知道,二花从前很苗条的,由瘦到胖,由眼里有恨双腿如刀到一个圆润无恨的胖子,由代县到娄烦,我不知道二花经历了什么,我更愿意通过文字去臆想,通过文字间传达的气息,去构筑我文学空间里的那个叫苏二花的女人。
她应该是那种能长歌当哭,能把苦难嚼碎咽下去,让你看着像吃提拉米苏,还会笑着跟你说俏皮话的人。这样的女人,恐怕没有什么可以降服了,她的体量就是她的能量,也只有这样体量的人,配得上那些热腾腾力道十足的文字。相比之下,当下流行的审美过于脆弱和苍白。
《安格尔大宫女》这篇小说应该是苏二花目前为止影响最大的一篇。这篇小说2019年在《都市》第1期发表后,很快被选登在《小说选刊》2019年第2期,这篇小说以一种别致的视角和新鲜的表述让读者眼前一亮。这是一篇类似《城南旧事》式的散点视角小说,没有贯穿全篇的人物和故事,以一个小女孩的眼睛和心理活动,反映一个小县城的人情风貌。但它抛开了童真的单纯清澈,处处体现一个处于童年与少年交界发育时期女孩的敏感,她毫不隐讳地刻画出一个小少女混乱蒙昧又充满狂野幻想的成长心理。诚实,应该是这部作品的一大亮点。作者大胆地突破了作为女性作者的某种禁忌,真实刻画了一个小女孩成长中“不洁”的各种心理变化。“我说过我是个十三岁的不洁女孩了。我的不洁,来自我对异性的不良感知,这不良包括内心的波折以及身体上微妙的变化,这令我深感羞耻。”性心理的羞耻感,一直是很多作家自觉规避的“禁区”,在大众的接受心理中,儿童应该是纯洁无邪天真烂漫的,就像《城南旧事》里的小英子。小英子是一个客体的存在,她是作为一个没有主观意志的观察者出现的。在苏二花这里,角度完全变了,“我”是一个主体,我的感知和思想成为外在世界的倒影,我的存在感成为叙述的主题。
小说中的小女孩名叫小树,是个生长在小县城的底层工人家庭的孩子,虽然生活环境单调乏味,但不妨碍“我”内心充满幻想———向往远方,向往流浪,向往着能过一种从影视剧中看来的快意恩仇的江湖游侠生活。周围熟悉的人让小树感受到生活的压抑和压抑中的变化,而真正掀起她内心波澜的是大院儿对面新开饭馆的两个老板,他们一个叫黄平,一个叫小易,这两个人的出场带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在水映蓝天的背景下,仿佛是梦想的出现,无论他们的服装还是他们的语言,都是“我”梦想中的样子,“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和糊在门头上的安格尔大宫女一样,是我们这个县城最新鲜的异数。”这两个学美术的人,在饭馆的门头上用黄泥糊出了一个女人的形象,并将其命名为安格尔大宫女,于是这样一个偏远、闭塞的小城,与遥远的世界有了某种神秘的对接,安格尔大宮女和塑造她的黄平、小易成了县城里“小树”们梦想的载体。但现实世界却是乏味的,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老一代浑浑噩噩,年青一代想努力挣脱,但又不知道方向。小树的二哥是一个乡村邮递员,但他不安于现状,总是梦想着能从家里挖到金银,以此告别这个寂寞乏味的工作,他的寻宝行动终归一无所获,但却在某一天因为单位配发的一辆新摩托车而变得意气风发起来。摩托车这一现代交通工具,让他变得自信潇洒,连久违的爱情也光顾了他。除了二哥,这个大院里还有许多年轻人,一心要考上大学远走高飞的孙家姑娘,随时准备返城的遗留知青,最早觉醒的个体户乡村摄影师,甚至小偷李旦,也吐露他内心深处的愿望,离开这里,离开这个灰色的小城。“只要能离开这个县城,离开这讨厌的边靖楼,离开我们院儿,让我到哪都行,哪怕是杳无人迹的西藏,哪怕是草浸天边的内蒙。我以为我已经足够决绝,却没想到,李旦哥连劳改场都愿意,我输了。”然而安格尔大宫女终不过是一个粗糙的黄泥糊的形象,时间久了没人再关注她,就如同那两个当初让“我”惊为天人的年轻人,最终敌不过生活的洗磨,一个成了犯罪分子,一个“还是把县城里任何一个开饭馆的老马或老刘们的相带了出来。如你所知,老马或老刘们,永远佝着腰,永远谢着顶,永远冒油光,永远把浑身挂满狡黠和市侩。”那个门上有着安格尔大宫女的饭店最终以倒闭为结局,曾经让“我”以为是梦想一般存在的那些人风流云散,消失在现实生活这样一个吞噬一切的巨大黑洞里。小说的结尾,小树走在铺着厚厚积雪的县城街道上,内心充满莫名的忧伤,忧伤里又藏着莫名的甜蜜,那种惆怅恍惚的伤感是每一个成长中的人都曾经体会过的吧,爱与恨的交织,去与留的无奈,小树此时流出来的眼泪包含了人类从童年时代就特有的莫名伤感,也让这部小说有了诗的柔软味道。
如果说《安格尔大宫女》带有某种诗意,是天荒地老中人类的寂寞忧伤,那么《祈雨》就是活生生的人世间了,如果我主观地将其看作是主人公小树成年后的人生,不知道作家会不会同意。文学的一大好处是,作品一旦出版发表,如何解读就成了读者的权利,作为一个批评者,我当然有权利按自己的理解解读作品。在这部烟熏火燎的作品中,作者延续了她一贯的文字风格,那是一种在俏皮戏谑天真实诚中又透着聪慧狡黠的可爱,正是这样的文字风格,让她的作品从众多的同类题材中脱颖而出,给人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说实在的,在信息泛滥的当下,网红们博流量各出招数,比来比去卖点无非是新鲜感,文学也一样,这门古老的艺术尽管皇冠巍峨,受尽世人的敬仰崇拜,更不乏群星熠熠光耀千古,但是,你指望现在的读者静下心来看《追忆逝水年华》恐怕有点难度,甚至如果放在今天,这样的作品能不能出版都是一个问题。因此,文学同样需要与时俱进,需要创新,更需要探求新的表达方法。也许,人性中许多共性的东西古今不变,但是不同时代的人们需要看到不同方式的表述,这也是合情合理的。作家需要探求的是如何符合当下人们口味的叙述方式,也就是如何把类似的故事讲给当下的人听,讲出新意,讲出水平,讲出个人风格,而不是一味埋怨世风日下,埋怨读者的阅读品味。好的作品永远带有强烈的个人标识,就如所有能够流传下来的品牌。
在《祈雨》这个故事里,苏二花非常传神地汲取了张爱玲的精髓———假如苏二花自己不承认读过张爱玲,只能说她也是个张氏般的天才了。她有本事将一个农村女性的人生,编织得如《沉香屑———第一炉香》抑或《金锁记》一般迷彩斑斓,而其中更是有许多亦真亦幻难以琢磨的看似与正在叙述的故事不搭界的旁语,这一点才是真正的张氏风格,平凡中的传奇,庸常的人生偏要用了暗中窥视的角度,看出不一样的机巧来。
问题是,苏二花确是个“奇葩”,她给我看的《祈雨》是未经删改发表前的,而正式发表的稿子,抽去了原稿中重要的两个人物:水秋和婆婆,情节变成了单线,锁澜进城的原因不是奸情败露在村里无法立足,而是变成了夫妻理念不同。对比两稿,我个人更偏爱原稿,结构上更丰满,人物行为的推进更合理,发表的版本情节上可能更利索,但削弱了人物精神上的叛逆和心理层次的丰富,于是下面的评论是基于原稿之上的。
拆开来看,《祈雨》写了一个很平常的故事,农村媳妇锁澜爱上了下乡干部水秋,水秋对她是逢场作戏而已,她与水秋的绯闻让她与丈夫建功无颜在乡间继续生活,各自去城里求生,进城的锁澜做起生意,苦打苦拼维持自己和儿子的生存,期间,双井村被拆,婆婆离世,二十年后夫妻在给婆婆送终时再次相见,正式离婚,锁澜的儿子也考入大学,在送儿子上学回来的火车上,锁澜回顾自己的一生,泪下如雨。
这篇只有两万多字的小说,道尽了一个女性所有的酸甜苦辣。她想追求爱情,向往外面的世界,她遇到了下乡干部水秋,“下乡干部水秋见到锁澜第一眼,就朝锁澜笑,脸如水中一汪月。那一年,水秋就是大城市。”水秋是逢场作戏,在得到她后拒绝带她离开,并让她成为全村笑柄。锁澜被丈夫偷走了买衣服的钱,就进城买了1065毒药,毒死了婆家的猪,埋在树下的猪成了丈夫的替身。但是,和所有成为母亲的女性一样,锁澜有一个稚嫩的儿子,“婆婆说那你就试试吧,反正你是远近闻名的巧媳妇,说不定你能做到靠墙墙不倒靠鬼鬼不跑。月亮地里,婆婆又说,乐平可还没吃饭呢,我答应给你看孩子,我就只管看孩子,孩子吃不吃饭我可不管。”
“月亮这种东西,前半夜是水,后半夜就成了铁。铁一样的月亮,给锁澜和婆婆的周身都镀了一层铁。”婆婆用自己三十年守寡的清白,不仅为双井村祈来了大雨,也将不守贞操与人偷情沦为全村笑话的锁澜逼到绝处。为了儿子,锁澜进城,经受各种委屈坚强地生存下来,但她倔强地靠自己,没有依傍任何男人,无论是在生意上帮助他的老许,还是对她生活上关照的李驰,都被她一一拒绝,儿子看穿了她的心思:“妈你人是离开了双井村,但你所有的神经触角都还留在双井村;妈你最恨奶奶,但你所做的每一件,都是做給奶奶看的。”她所有的努力和克制都朝向一个目标,就是要证明给双井村和她婆婆看,她不是一个靠姿色的坏女人。“一盘惨白的吸顶灯下,锁澜瘫在椅子上,她太累了。累了好,累了就不会做噩梦,就不会梦到被狼追。那狼总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刻,对着锁澜的耳朵突然大喊一声,哇———”她用劳累控制自己的欲望,与自己搏斗,就是证明当全村人嘲笑她,背后叫她“仙人洞”时,婆婆那双看她的眼睛暗示的一切,锁澜最终报复了婆婆,婆婆临终时,“锁澜把饭盛在碗里,碗上放了筷子,放在婆婆跟前。婆婆能看见碗里的饭,也能闻到饭的香,但就是够不着碗。锁澜说,饭我是给你做熟了,能不能吃到嘴里,是你的事。当年,婆婆在这个屋子里,曾经对锁澜说过一句话,她说我答应给你带孩子,但我没答应给孩子做饭吃。那时候,可怜的乐平也是用这样清汪汪一双眼睛看锁澜的。”两个女人的对峙,惊心动魄,分别都用了自己的一生。
这篇小说里,有许多值得称道的语言,与张爱玲神似,但又绝不是模仿,如她写焦急等雨的农人:
“所有人都不说话。七郎庙里,双井村的农民把自己坐成罗汉。大家罗汉一般不说话,但又罗汉一般表情各异,绝望的和期冀的、目瞪口呆的和深恶痛绝的。”
写一个搬迁时打电话的男人:
“这突然的一笑,暴露了他生在双井村的印记。只有出生农村的人,才在笑容里泄露掩饰良久的山梁和水洼。这也是大部分人共有的特征,身体里流淌的血是农村人该有的淳朴与融洽,表现的却是城市人必备的精明与尖刻,但这两者都因为没有很好的用武之地,所以精明得捉襟见肘,也淳朴得让人疑窦丛生。”
我个人觉得有些遗憾的是,正式发表的版本中,将故事情节设置为夫妻二人因为进城与否发生争执,锁澜孤身带孩子进城,删去了锁澜与水秋的偷情,婆婆与锁澜的对峙,故事线索变得单一,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人物的形象。
我没有和二花交流过,不知道她的阅读倾向,我相信她是有语言天分的人。期待着她的新作,也期待一颗新星冉冉升起。
责任编辑高璟
——重读《安格尔论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