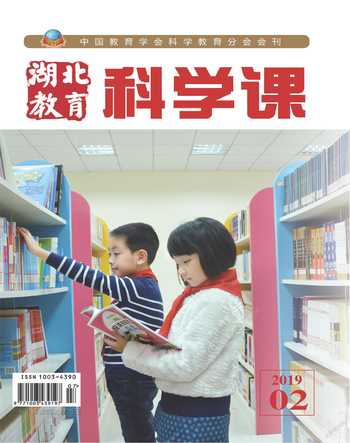特有的默契巨大的分歧
段文娟
笔者曾任高中化学教师,现任小学科学教师,把小学科学与高中化学前面的限定语拿掉,剩下科学与化学,它们之间是相互包容的关系,其实意识中距离远的应该是小学与高中,然而远吗?实则中间有若干条紧紧相连的线,其中一条是实验。
学生在十年寒窗苦读后,知识、智力在增长,思考的深度在加深,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是否丢失了什么呢?为了對比,笔者特意选取了2个实验样本:高中部分,选的是人教版《化学》(必修2)第四章第一节,是高中化学必修部分的最后一章,这一节可以充分代表高中阶段学生的化学实验水平;小学部分,选择的是《观察叶》一课,经过近一个月的学习,学生已经基本适应了小学的生活节奏,初步领会了学习科学的基本方法。令人意外的是,在实验这件事上,小学教师和高中教师呈现出了特有的默契。
特有的默契
默契一:“在未说开始之前请勿动手实验”
从小学进实验室一直到高中,“在未说开始之前请勿动手实验”这句话是每一个教师都在强调的,而这句话唯一的目的就是维持课堂秩序。以至于到了大学直至研究生,当教师给学生独立的课题研究时,他们通常迟迟不敢下手,一直在等待指令,但此时已没有人告诉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从哪儿开始。从小学到高中,教师对学生的种种干预渐渐地抹杀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强化了他们对教师的依赖性。独立思考的能力是教师培养出来的吗?不是,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只是慢慢地被抑制了。
默契二:“表现不好,下节课就不许进实验室”
“表现不好,下节课就不许进实验室”这是常规威胁,什么时候有用?一直能用,而且很好用。
为什么能用?对于小学生,他们对未知的事物充满了极强的探究欲,在他们的概念里,只有科学家才能进实验室,进实验室是一种荣耀。有一次下课后,有一个性格内向的小男孩走过来:“老师……”
他站在那儿似乎有话要说,但欲言又止。
“怎么了?”
“我……,我喜欢科学。”他想了想,小声地说。
“是吗,老师觉得你一定能成为科学家。”
“嗯,我一定能成为科学家。”他小小的脸上写满了严肃和认真,目光坚定。
在他眼里科学是伟大的,成为科学家是神圣的,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我们小的时候,当被问起有什么样的梦想时,有多少人想成为科学家?当我们有幸进入科学领域的时候,又有多少人成了科学家呢?我们来看看高中生吧。
进实验室对于高中生来说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我们可以从几件常见的事情看出来:其一,进实验室想要让他们听见教师的声音,需要用扩音器;其二,需要教师不断强调整理好实验室之后才能离开;其三,“请勿随意离开自己的座位”,这句话教师总是挂在嘴边。
也许有人会说,学生对做实验充满了热情,正说明潜在的研究人才储备非常丰富。这句话对了一半,学生只是对做实验这件事充满了热情,但是并没有把他们的热情用在思考上,他们只是机械地完成了实验步骤,这一点从他们的实验报告中可以看出来。进实验室对他们最大的吸引力在于,终于不用一直坐在教室被灌输一节又一节的知识了,终于可以“玩”了。
而对于高中教师来说,带学生进实验室做实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政策有规定“要考”,进实验室总能顺便熟悉操作步骤,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加强知识的记忆,不然,在教学时间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进实验室是何等的奢侈。
对比之下我们发现,从小学到高中,学生被抑制的何止是独立思考的能力,还有极强的求知欲。
巨大的分歧
分歧一:意外
“取1滴管碘水于试管中,向其中滴加3滴淀粉溶液;取1滴管海带浸泡液于试管中,向其中滴加3滴淀粉溶液。”
这是一段选自高中实验的操作步骤,当学案上有这样的操作步骤时,学生会怎么做呢?当然是严格按照操作步骤来。没有人会问老师为什么是3滴,那他们有疑问吗?有,他们会小声地议论,旁边的同学会立马给他答案:“书上这么说,那就这么做吧”。如果不小心加多了,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会选择在教师过来之前将它放到试管架上,重新再做。整个实验只有一个目标:按照教师示范的步骤进行操作,“验证”自己的猜想。实验中出现的任何“意外”都是错的。而教师只会关注时间是不是到了?这节课能不能完成教学任务?
“还记得阿伏伽德罗常数吗?”高中同学聚会上,我问一位目前在北理工工作的同学。答案是很明显的——那是什么?然而在高中阶段,为了攻克这个难点,我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如果我们给一点时间交给“意外”呢,结果又会怎样呢?
回到小学课堂,我们会发现小学课堂就是由“意外”构成的,我们允许且鼓励每一个“意外”的发生。课堂快结束时,我问学生:“对于叶子,你还想知道什么?”
很多小手举起来了,其中一个学生问:“叶子离开树上的时候为什么会落到地上,而不是飞到空中呢?”“非常好的问题,那是不是每一片叶子都会落到地上呢?”我问道。下午经过教室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学生都在盯着树看。他们在看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此时他们的眼睛在“发光”,我看到了希望。
请多给学生一点时间,允许课堂上“意外”的发生。
分歧二:答案
当我拿到小学《科学》课本的时候,感到很茫然,因为没有什么知识点,一节课的内容似乎几句话就可以完成,在40分钟的课堂上,我们到底要做些什么?例如《观察叶》一课,课题很明显说明了这节课的内容:一片叶子放在了投影上,问学生,你们看到了什么?“叶子”“叶子在往下掉”“它已经老了”“它有漂亮的花纹”“叶子上有锯齿”“它是黄色的”“它像小水滴”……
就这样10分钟过去了,依旧有很多的小手不断地举起来。“你们看到了吗?”“我们都看到了,而且习以为常了。”换句话说,我们依旧不会“看”,更不会把看到的说出来。
回到高中实验室。“请你描述一下实验现象。”“溶液变蓝了。”“还有其他的答案吗?”没有了。没有其他的答案不代表没有观察到其他的现象。那么教师需要做的是引导,将问题具体化、细致化:首先是选择观察目标;其次是有目的、有计划地指导观察;接着是提示有序观察,区分观察的细节,形成生动的表象,学习在观察中思考等;最后,就如曾宝俊等科学名师在《小学科学教材教法与教学设计》一书中说到的,要把观察研讨和表达结合起来使用,这样可以通过学生和学生、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相互研讨,提供给学生充分质疑的机会。
这一套流程在小学科学学习的过程不断地强化,但是很快会被繁重的知识点冲淡,直至到了高中,教师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学生都会。但其实,学生会过但已经忘了,或者不愿意耗费精力去思考,因此需要不断地强化,去除思维的惰性。
“你的回答很有思考性,非常棒!”这句只有在小学课堂才能听到的评论,请还给高中生。同时请呵护那双会观察的眼睛,一起用小学生的眼睛去观察。
作为教师,我们到底需要做什么呢?不是抑制,是呵护,细心呵护学生的求知欲,以及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