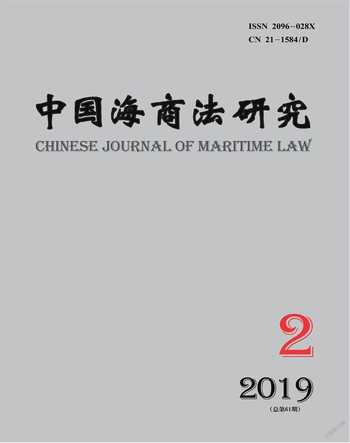跨界破产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侯国彬 王德岭 杨运福
摘要:由于航运市场萧条,国际航运公司破产事件接踵而至。中国缺乏跨国航运企业破产处理的国际合作实践,同时相应的跨界破产立法处于空白状态,这些问题将严重制约中国的国际海事司法中心建设。针对中国司法实践在处理近期国际航运巨头韩进海运有限公司破产案中出现的困境,通过对主流国家与中国对跨界破产的域外效力以及破产程序与船舶扣押程序的冲突相关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进行比较研究,提出适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环境且与国际接轨的相关立法建议,为优化中国国际航运中心软环境,改善“一带一路”法律服务环境提供帮助。
关键词:韩进海运破产案;跨界破产合作;互惠原则
中图分类号:D996.19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28X(2019)02-0081-07
Discussion on several legal issues of cross-border insolvency—based on the bankruptcy case of Hanjin ShippingHOU Guo-bin1,2,WANG De-ling3,YANG Yun-fu2
(1.International Law School,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0042,China;
2.Yang&Lin Law Firm,Guangzhou 510220,China;
3.Merchant Marine College,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Shanghai 201306,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recent on-going depression of shipping market, bankruptcies of international shipping companies come one after another. China does not have sufficient experience in the field of cooperation handling international shipping industry’s bankruptcy, and the legislation vacancy of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is another concern. This current condition will restrain the constructing of global maritime judicial center in China. As this paper’s main conclusion, The legislation proposal is drawn by discussion of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recent case of Hanjin Shipping bankruptcy, and reviewing other major shipping economies’ legislation.
Key words:the bankruptcy case of Hanjin Shipping;cooperation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reciprocity
2016年8月31日,世界排名前十的航運巨头——韩进海运有限公司(简称韩进海运)决定向韩国首尔中区地方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同年9月1日法院裁定接受其申请。9月2日,韩进海运启动破产重整程序,9月20日到10月25日进行债权人登记和申报。韩进海运在该年的11月11日举行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原计划12月23日提交重整计划,后因案情复杂重大推迟提交日期。2017年2月17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宣布,鉴于韩进海运的清算价值超过继续经营价值,韩进海运正式破产,至此,全球航运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航运企业破产案成为现实。
自韩进海运申请破产以来,债权人纷纷向各国法院申请船舶扣押及其他财产保全,继而启动诉讼程序。涉及到中国管辖法院的,据不完全统计,相关案件上海海事法院受理16起,涉案标的总额超2亿;宁波海事法院受理11起,涉案标的总额超8亿;厦门海事法院受理11起,等等。除了在韩国境外采取救济措施外,部分债权人也选择到韩国向韩进海运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参与韩进海运破产财产分配,据悉全球范围内有四千多家债权人在韩国境内申报针对韩进海运的债权,其中包括三百多家中国债权人。[1]34针对债权人在世界各地采取的救济行动,韩进海运在破产程序启动之时,即采取了应对措施,一方面向其境外财产、船舶挂靠国申请破产保护,另一方面,为配合在外国的破产保护程序,命令船舶减速,延时待外国法院批准其申请后挂靠该国港口。因韩国已于2006年采纳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跨界破产示范法》(简称《示范法》),给予韩进破产保护措施的多为《示范法》采纳国,其中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于9月5日承认了韩进海运的重整程序,接受了其提出的禁止扣押申请。9月6日,美国法院也批准了韩进海运的请求,韩进海运获得了临时破产保护令,该公司船只得以在美国港口靠岸。9月9日,美国法院同意韩进海运申请的破产保护,扩大了司法保护范围并延长了保护期限。除《示范法》采纳国外,没采纳《示范法》的国家,比如新加坡、德国也给予韩进海运破产保护。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韩进海运在中国有十几家分公司及办事处,且韩进船舶挂靠中国港口较多,但并未发现韩进海运的破产管理人向中国法院提交破产保护申请。
韩进海运破产案自正式公布至今,给国际航运市场造成巨大冲击,全球范围的供应链中断,市场一片混乱,引发了大量商业纠纷。由于该案波及数十个海运国家,各个国家给予的破产保护方式及保护程度各有不同,尤其当破产保护措施与船舶扣押制度冲突时,各国法院的态度更为混乱,因此破产国际合作、破产案中破产程序与船舶扣押程序冲突等问题引起国内外破产、航运方面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笔者拟就跨界破产的域外效力以及破产保护与船舶扣押程序的冲突进行论述。
一、跨界破产程序的域外效力
(一)域外效力的簡介
跨界破产程序的承认是破产案件国际合作存在的前提条件,简言之,是一国境内进行的破产程序开始后破产人境外财产的法律后果以及相应的境外破产程序对外国债务人位于本国之财产的效力。具体而言,包括破产公司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法院启动破产程序后,外国针对破产财产的普通诉讼程序、执行程序是否中止,保全程序是否解除,破产财产的管理人是否可对债务人在国外的财产行使收回权,破产案件受理后或宣告前债务人对未到期债务的提前清偿或者对债务提供担保的效力等。
(二)国际上通行做法
涉及跨界破产程序的域外效力,国际上存在两种对立的基本原则,[2]其一是普遍主义,也称为“单一破产制”,即主张一国的破产程序具有完全的国际效力,而对其他国家的破产程序不予承认,其理论来源于“破产之上无破产”的法律格言。单一破产制有利于全世界范围内合理分配债务人财产,公平对待所有债权人,有效管理债务人的财产。从各国实践来看,普遍主义已经成为主流趋势,美国、英国是采用普遍主义的典型国家。欧洲大陆法系原本采用属地主义,但现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德国以前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均坚持本国破产程序的域外效力,但否定外国破产程序的域内效力,而1999年生效的《德国破产条例施行法》贯彻了普遍主义原则。当然,由于普遍主义原则要求财产所在地国家放弃其对债务人在其境内财产的控制,使得本国债权人丧失对当地财产优先受偿的机会,因此采用绝对普遍主义的国家并不多。其二是属地主义,即主张一国进行的破产程序仅在本国领域内产生效力,而不及于域外财产。属地主义的理论基础是破产程序的公法性质,反映了国家对本国债权人的保护和本国经济利益的维护。但属地主义否定了所有债权人的平等性,会导致债权人之间的不公平及破产财产的混乱,也不利于国际商事交往,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绝对的属地主义思想遭到广泛批判。由于绝对普遍主义和绝对属地主义存在的缺陷,目前国际上采用较多的是“折中主义”,包括“修正的普遍主义”和“合作的属地主义”,此原则为韩进海运救济过程中所援引的《示范法》所采纳,《示范法》采用“复合破产制”,允许对同一债务人在两个以上国家提起多重破产程序:《示范法》第2条(b)款规定了主破产程序,第2条(c)款规定了非主要破产程序。该法第20条、第21条又分别对两种不同程序的效力进一步作出规定:对于外国主要程序,承认的后果通常包括停止个人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诉讼或停止有关债务人资产的强制执行程序,并终止债务人转让或抵押其资产的权利。而对于外国非主要程序,则给予“酌情”救济,即由法院自由裁量是否中止在本国进行的破产程序或者对相关财产予以冻结。考虑到《示范法》采纳国家对上述程序的接受程度不同,《示范法》采用了较为灵活的方式,将是否采纳上述规定的权利交由采纳国本国法律规定。这也是韩进海运在《示范法》采纳国家所享受的破产保护程度不一致的主要原因。
(三)中国在此方面的立法、实践现状
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简称《企业破产法》)颁布之前,中国在跨界破产领域的立法长期处于空白状态,在实务操作中也经历了从绝对的属地主义到有限制地承认外国破产程序的漫长过程。早期案例中,较为典型的是1992年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申请宣告国际商业信贷银行深圳分行破产案,该案中中国债权人仅参加对该银行深圳分行的清算,而不参加对该行的全球清算,可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该案中采纳绝对属地主义。[3]在稍后的破产案件审理中,针对中国法院破产案件的域外效力,多采用绝对普遍主义,而对外国法院的破产程序效力问题,多采纳属地主义。然而进入中国入世阶段,法院态度有所改变,比如2001年的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B&T Ceramic Group s.r.1.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意大利法院破产判决案中,法院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意大利共和国关于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承认了意大利法院作出的破产判决在中国的法律效力。可见中国法院在对待外国破产程序在中国的效力方面正逐步接受有限制的普遍主义。
在总结跨界破产司法实践的基础上,2006年新颁布的《企业破产法》对跨界破产效力问题进行了原则性规定。根据该法第5条,中国坚持本国破产程序的域外效力,同时在公约优先、互惠原则且对公共秩序做出保留的基础上承认域外破产程序。可见在此方面中国立法采用的原则已经逐渐趋向于与国际通行做法一致,即“有条件的普遍原则”。笔者认为该条既体现国际私法领域的国际礼让、公约优先等原则,也体现了对中国主权、法律原则的维护,相对而言对境内债权人的保护也是比较有力的。但是该条也存在诸多问题:互惠原则是国际礼让在国际私法领域的延伸,也称“对等原则”,曾一度被认为是国际法的独立支柱之一。[4]具体到跨界破产领域,如甲国法院对乙国的破产程序不予承认,或者虽然没有不承认的事实,但推定其不会对乙国的破产程序承认,则乙国对甲国的破产程序的效力相应不予承认,其本质是“国际报复”。[5]当今国际社会对互惠原则多有批评之声:首先,本国对外国破产程序不予承认的措施损害的并不是不承认本国法院裁判的该国家,而是在该国裁判中获胜的当事人,而当事人甚至可能不是该国公民,同时在本国针对境外破产企业的财产采取法律行动的债权人也有可能不是本国境内主体。从实际操作角度来看,在两国均采取“互惠原则”且都相对保守谨慎的情况下,“互惠原则”可能成为假命题,比如采取“事实互惠”的国家,两国均坚持以本国破产程序得到对方实际承认为条件,在此情况下,双方均不可能成为第一个承认对方破产程序的国家,也永远不会出现承认的事实。
鉴于“互惠原则”的缺陷,再考虑到《企业破产法》第5条比较概括,法院在实务中很难据此判断是否应该承认境外破产程序的效力,实践中法院往往持保守态度:比如在较早期的日本公民五味晃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并执行日本法院生效判决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出具了《关于我国人民法院应否承认和执行日本国法院具有债权债务内容裁判的复函》,根据该复函,由于中国与日本国之间没有缔结或者参加相互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国际条约,亦未建立相应的互惠关系,故中国法院对日本法院的裁判应不予承认和执行。依照该复函可以得出结论,当时中国法院采纳的“互惠原则”是以“事实互惠”为标准的,即外国法院实际承认并执行了中国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裁定,是中国法院按照互惠原则承认执行外国判决裁定的前提和基础。如前所述,事实互惠在其逻辑上存在不可补正的瑕疵,如两国的破产法律同样适用该原则,则两国均需等待对方承认本国破产程序的先例,恐怕永远不会有互惠原则适用的案件发生。再者,外国法院未先给予承认和执行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该国未发生过此类案件,而非根据该国法律,对中国生效判决裁定一概不予承认,如因此认为双方无互惠关系,难言公平。
相对“事实互惠”标准,“法律互惠”是一種更为积极的互惠标准。该标准要求,法院在审理适用“互惠原则”的案件时,需要审查外国法律是否规定该国法院可以按照互惠原则承认执行别国判决。如该国法律存在此类规定,则比较该国承认条件与本国法院承认条件,如果该国条件与本国相同或更为宽松,则可以认定为符合互惠原则的要求。“法律互惠”相对于“事实互惠”更为开放及宽松,但是该原则在中国以往司法实践中采用不多。
(四)“一带一路”背景下互惠原则的发展
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的经济格局和国际经济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引进外资促进发展模式,到今天招商引资与对外投资双引擎促发展模式,招商引资多元化,对外投资形式也逐渐多样化。联合国贸发组织和中国商务部贸易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增长44%,达到1 83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聚焦到航运领域,以中远海运为例,自国内两大航运巨头中远集团与中国海运集团重组以来,在全球现投资经营码头共四十多个,泊位两百多个,集团远洋航线覆盖了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 500多个港口,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业务涵盖集装箱代理、物流、港口、燃供等领域。[6]可见当前的中国经济主体已经逐步融入世界经济共同体,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引领全球经济的发展。为适应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变化,中国破产司法实践需要积极参与国际范围内的破产合作。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背景下,司法实务中对于外国法院作出的判决效力也逐渐开始持开放包容态度。比如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简称《2015年最高院意见》)中提及为了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司法协助,“要在沿线一些国家尚未与我国缔结司法协助协定的情况下,根据国际司法合作交流意向、对方国家承诺将给予我国司法互惠等情况,可以考虑由我国法院先行给予对方国家当事人司法协助,积极促成形成互惠关系,积极倡导并逐步扩大国际司法协助范围。”该意见采纳的“互惠原则”的标准符合“法律互惠”的本意,比司法实践中长期坚持的“事实互惠”相对开放包容。另外,2017年6月8日,第二届中国—东盟大法官论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举行并通过了《南宁声明》。该声明包括八项共识,其中第七项为:“区域内的跨境交易和投资需要以各国适当的判决的相互承认和执行机制作为其司法保障。在本国国内法允许的范围内,与会各国法院将善意解释国内法,减少不必要的平行诉讼,考虑适当促进各国民商事判决的相互承认和执行。尚未缔结有关外国民商事判决承认和执行国际条约的国家,在承认与执行对方国家民商事判决的司法程序中,如对方国家的法院不存在以互惠为理由拒绝承认和执行本国民商事判决的先例,在本国国内法允许的范围内,即可推定与对方国家之间存在互惠关系。”相对于《2015年最高院意见》,《南宁声明》在表述上采纳了更为包容的“推定互惠”原则,[7]即只要该国没有拒绝承认和执行本国民商事判决的先例,即可推定与该国存在互惠关系,而该国相关法律是否有“互惠原则”的规定在所不论。当然如果该国采纳了过于保守的态度,比如绝对的“属地原则”,则《南宁声明》中的“推定互惠”恐没有适用的余地。由上述可见,中国的司法机关在司法协助及合作领域正沿着更开放更自信的方向前行。回到破产法领域,尽管尚无典型案例对《2015年最高院意见》和《南宁声明》支撑,不过在上述环境下,加之中国自2015年供给侧改革中提及“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等改革要求,跨界破产的“互惠原则”亦需符合当前国内经济、国际环境,采用更为开放及宽松的“推定互惠”。
(五)韩进破产程序在中国取得破产保护的可能性
虽然韩进海运在中国存在十几家分公司、办事处,其所运营船舶频繁挂靠中国港口,但其并未向中国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导致此情况的发生,很可能是韩进海运破产管理人对中国跨界破产司法实践有所顾虑,同时从中国立法、司法实践角度分析,确实存在较大障碍。
首先,中国未采纳《示范法》,韩进海运无法在《示范法》框架下要求中国法院承认其本国破产程序,提供救济;同时中国也并没有与韩国缔结破产国际合作方面的条约。民商事司法协助领域仅有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但在该条约中所约定的司法协助范围不包括法院裁决的承认与协助,因此中国无对韩进海运在中国的财产提供破产保护措施的国际义务。
其次,韩国并无对中国破产裁判承认以及对中国债务人予以破产保护的先例,基于中国此前较为保守的“事实互惠”原则的法律实践,中国法院恐不会对韩国首尔中区地方法院的破产程序予以承认。另外需要说明的是,韩进破产事件发生在《2015年最高院意见》之后,尽管该意见中提及的互惠原则采纳“法定互惠”标准,但该意见仅限于“一带一路”参与国家之间的司法合作,而“一带一路”仅为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并不是一个国际法意义上的实体组织,韩国对“一带一路”的倡议参与度不大,因此该意见对韩进海运破产案不具参考意义。
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与跨界破产程序的冲突与衔接
(一)问题产生概述
韩进破产案中,尽管韩进海运的破产管理人在多个国家申请破产保护救济措施,但承认并协助韩进海运的破产程序的国家所给予的救济措施各有不同,尤其是在船舶、其他财产诉讼/诉前扣押保全与韩进海运在外国申请的破产保护措施冲突时,这种混乱表现尤为突出。限于篇幅,笔者仅讨论船舶诉前扣押程序与跨界破产程序之间的冲突。
(二)各国在船舶扣押程序与破产保护程序冲突时的不同做法
大部分海运国家认识到跨界破产程序的重要意义,对境外的破产程序予以不同程度的保护,但是鉴于船舶扣押程序的相对独立性,尤其在英美法下,诉前的船舶扣押程序被认为是典型的对物诉讼制度,[8]因此在外国破产程序得到本国法院承认的前提下,当船舶扣押程序与境外的破产程序相冲突时,各国对外国破产财产保护的程度各有不同,即便同样采纳对物诉讼制度的英美法国家,其态度也可能截然相反。根据笔者对跨界破产若干案件的整理和分析,主要可分为“破产保护程序优先说”及“破产保护与船舶扣押折中说”两种立法和实践。
关于“破产保护程序优先说”的实践,主要包括美国、日本、南非等国家。当外国破产保护程序在本国内提起申请,则申请时间之前的船舶扣押或其他保全行为均归于中止,申请时间之后将不接受扣船申请。以美国为例,本次韩进海运破产案中,韩进海运外国代表依据《美国破产法典》第十五章向美国新泽西地区破产法院提交了破产承认申请,美国新泽西州联邦破产法院正式承认韩进程序为外国主要程序后,启动自动中止机制对韩进海运位于美国境内的资产予以救济,其中包括对担保债权的救济,美国法院在给予韩进海运在美资产救济措施时,特别强调享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人也不得通过扣押韩进海运船舶等形式实现其担保债权。
关于“破产保护与船舶扣押折中说”,不同国家对二者之间的妥协程度有不同态度,笔者拟就船舶扣押程序发生在境外破产保护申请得到本国批准之前,以及本国船舶扣押程序发生在外国破产保护申请被本国批准之后两种不同情况进行讨论。
当扣船程序发生在境外破产保护申请在本国被批准之前,在英美法国家的对物诉讼制度下,船舶扣押往往被认为是债权人对船舶本身(而不是船舶所有人或其他利益方)所负债务采取的救济手段。无论是基于船舶优先权的船舶扣押,还是针对普通债权而产生的船舶扣押,破产程序都可能对船舶扣押程序让步:[9]在存在船舶优先权的情况下,尽管船舶优先权概念存在债权、物权之争,但主流观点对海事优先权属于债权担保并无争议,[10]且该担保的产生时间与主债权产生时间一致。因此,如果破产保护申请获得本国法院批准之前,本国已经开始了基于船舶优先权启动的扣船程序,且本国法律规定认可有担保债权的诉讼程序不受破产保护程序影响,则已经开始的船舶扣押程序不予中止、解除;即便是基于普通债权的船舶扣押,在承认对物诉讼制度的国家仍然坚持以对物诉讼为基础的船舶扣押程序是优先于境外破产程序的,根据对物诉讼理论,不附海事优先权的普通债权人在船舶被扣押的瞬间即取得一个法定优先权,该法定优先权使得债权人的此项债权成为有担保的债权。该理论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In re Aro Co Ltd \ Ch 196案,该案的审判法官Brightman先生解释:“通常对物诉讼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擔保。原告对扣留和扣押的标的物形成了一个诉,并且有权在获得胜诉判决时要求从拍卖价款中受偿,除非还有其他更优先或者同等受偿顺序的索赔请求。因此,原告的对物诉讼权类似于一个普通法或者衡平法下的抵押权人的权利或者押记。”在本次韩进破产系列案件中采纳本判例观点的比较多见,比如新加坡法院于2016年9月14日承认了韩进破产程序,并发布了禁止扣押令,但新加坡法院的承认效力不涉及到其已扣押的船只韩进“罗马号”。同样,根据《英国跨界破产条例》的规定,自动中止的救济并不影响享有担保权益的债权人在债务人财产上实现债权。根据个案情况,英国法院可以修改或扩大自动中止的救济范围,以中止享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实现债权,即所谓的额外救济。本案中,英国法院给予的救济措施并没有影响到债权人担保债权的实现。加拿大法院对于该问题的立场与英国法院类似,对韩进海运在加境内资产的救济措施并不及于债务人设定了担保物权的特定资产。[1]39当扣船程序发生在境外破产保护申请在本国批准之后,大部分国家通常不予准许再行启动船舶扣押程序。但是同样是对于“对物诉讼”的英美法国家,基于船舶优先权的扣船程序仍然可以在对物诉讼中得以优先适用。比如在Yu v.STX Pan Ocean Co Ltd案中,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法院Buchanan J法官认为,“目前来看没有理由限制根据《示范法》所承认的权利,然而具有海事优先权的债权人在债权产生之时便对该船具有了担保利益,我在本案情况中找不到任何原因拒绝在破产程序外批准扣船①。”本案被告STX Pan Ocean Co Ltd于2013年向首尔地方法院提出破产重整申请。此后该公司旗下的一艘船在澳大利亚被扣。破产管理人基于《示范法》向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提出承认外国破产程序的申请及申请额外救济,额外救济申请中部分内容被指可能是为了防止船舶在澳大利亚扣押。笔者认为本案判决与In re Aro Co Ltd \ Ch 196案的判决并不矛盾,前案中债权的担保(海事优先权)产生于债权形成之时,而后案中,普通债权是通过扣押船舶得以成为担保债权的,而一旦破产保护申请获得批准,扣船申请将不予批准,因此普通债权将无法转变为担保债权。
韩进破产案中,给予保护措施的国家中大部分的观点与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在Yu v.STX Pan Ocean Co Ltd案中的观点是一致的。
(三)中国扣船程序与破产程序的冲突与实践
首先,中国的船舶扣押制度在性质上属于诉讼财产保全制度。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三章第二节关于船舶的扣押与拍卖的规定借鉴了英美法的对物诉讼制度,对船舶扣押程序进行专门规定,但是该节的规定与普通民事诉讼财产保全程序在本质上区别不大,因此中国的船舶扣押仍然从属于本案诉讼程序的辅助性保全措施。[11]其次,根据《企业破产法》第19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本条并未规定任何例外情况。综合考虑上述两点,在境外破产程序获得中国法院的承认之后,船舶扣押程序与普通诉讼保全程序一样,均应予以解除,至于扣船是否基于优先权在所不论。
当外国破产程序被中国法院承认之后,船舶扣押是否被准许?笔者认为该问题涉及到破产法律的适用问题。中国对破产法的适用并无具体法律规定,国际上普遍接受的观点是破产法适用受理法院所在地法。进一步分析,如果破产所在地所属国法律规定应就破产船舶的扣押适用财产所在地法律,船舶扣押是否又适用《企业破产法》第19条?笔者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9条之规定,中国适用的涉外法律不包括外国的法律适用法,据此可以得知中国不接受反致,因此无论破产法律的规定如何,当外国破产程序被中国法院承认以后,中国的法院将不再受理针对该破产债务人的船舶扣押申请。
尽管通过上述讨论可明确得出,中国的船舶扣押程序应让位于破产程序,但问题在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简称《海商法》)第28条,在基于船舶优先权担保的债权中,船舶优先权的实现只能通过船舶扣押,而破产法又在程序上剥夺了此类债权人的船舶扣押的权利,使得他们在破产程序中降格为普通债权人的法律地位,笔者认为尽管船舶优先权法律属性尚有争议,但仅因为破产程序这种与债权保护优先等级无关的事实的出现,而使得作为实体权利的船舶优先权丧失,这并不符合法律应有之意,而是立法技术导致的不足与缺陷。
(四)中国船舶优先权在破产法中的受偿地位
本标题看似不属于破产域外效力的议题,但它是破产程序能够被大部分国家承认和协助的关键,因此笔者一并进行讨论。跨界破产案件中,大部分国家对外国破产程序予以协助的条件是要求在外国的破产程序不能有损本国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比如,韩进破产案中新加坡高等法院予以司法协助的条件之一便是考虑“破产重组程序对境外债权人的公平公正性”。[12]美国、日本等国家在本案中也提出类似的条件。予以承认和提供破产保护的国家在程序方面并不以其本国程序为准,其重要目的仍然是为保护本国债权人对破产人的财产应享有的权益。国际上普遍认为具有船舶优先权的债权是一种担保债权,因此船舶优先权在破产所在地国家中的破产受偿地位是破产国的破产程序能否获得别国承认和协助的關键。中国在此问题上争议相对较大,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船舶优先权具有破产法上别除权性质,[13]根据《海商法》第25条第1款规定船舶优先权优先于留置权和抵押权受偿,而留置权和抵押权属于破产法上的别除权,对特定的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根据法理学中当然解释原理,[14]应该推定船舶优先权所附债权属担保债权。第二种观点认为破产法上的有担保的债权不包括船舶优先权,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3条将“有担保的债权”限定为“已依法设定担保物权”的债权,而船舶优先权为法定的优先权,并无债务人依法设定,同时船舶优先权是否具有物权属性并无明确法律规定,因此船舶优先权应在别除权之外。笔者较为认同第一种观点,从破产国际合作的角度讲,如船舶优先权担保债权的优先受偿性因破产受理而归于消灭,则该破产程序很可能被外国法院认为此程序不能平等保护该国债权人,因此不能得到外国法院的承认和协助。
三、结论及立法建议
自2008年以来,国际航运市场发生了断崖式下跌,航运大鳄的破产事件接踵而至,先后发生了韩国的STX PAN OCEAN破产重整案,丹麦的OW BUNKER破产案、笔者论及的韩进破产案。中国在法律上并未做好充分应对跨国航运企业破产的准备,跨界破产法律制度以及国际合作成为制约中国跻身航运强国的短板。因此,建立完善跨界破产国际合作法律制度,平衡海事程序与破产程序的冲突,在司法实践中树立中国公平保护中外债权债务人的良好国际形象,将有利于中国国际海事司法中心的建设,同时也为中国航运法律工作人员提出了挑战,提供了契机。笔者综合以上论述,提供如下立法建议。
第一,关于国际海运企业跨国破产:从立法角度来说,《企业破产法》已经明确了“互惠原则”,且在当前立法条件和经济环境下,对境外破产程序采取“普遍原则”的可能性不大,这也不符合国际主流经济体的立法趋势,因此宜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在跨国航运企业破产案件处理中应采用较为开放的“法律互惠”原则。笔者之所以在《南宁声明》以及《2015年最高院意见》之后仍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皆因前述“声明”和“意见”均为“法律互惠”设定了适用对象限定条件,前者为“东盟国家”,后者为“一带一路”国家,同时此类“声明”或“意见”在中国司法实践中法律效力较差,适用主体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在《企业破产法》的基础上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给出明确性意见,有助于提高法律预见性,更是为国内法院处理国际航运企业破产合作提供指导。
第二,关于船舶扣押程序与破产程序之冲突解决以及船舶优先权在破产案件中出现的问题:从破产法的统一性及完整性考虑,无论扣船程序是否基于担保物权、船舶优先权,均不应将船舶扣押解释为优先于破产的程序,因此应在《海商法》修改中将船舶优先权的实现条件加以调整,避免因破产程序优先性导致债权人船舶优先权的丧失;同时建议对船舶优先权的法律属性予以确认,以进一步明确具有船舶优先权担保的债权在破产程序中的优先效力。
参考文献:
[1]石静霞,黄圆圆.跨界破产中的承认与救济制度——基于“韩进破产案”的观察与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31(2).
[2]杜涛,陈力.国际私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234.
[3]石静霞.中国的跨界破产法:现状、问题及发展[J].中国法学,2002(1):114-126.
[4]杜涛.互惠原则与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J].环球法律评论,2007,29(1):110-119.
[5]林倩.再论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中的互惠原则[J].法制与社会,2007(11):774-775.
[6]刘瑾.中远海运:“深改”“快改”奔向世界一流[EB/OL].(2017-06-30)[2018-05-01].http://www.ce.cn/cysc/jtys/haiyun/201706/30/t20170630_23944666.shtml.
[7]张勇健.“一带一路”背景下互惠原则实践发展的新动向[N].人民法院报,2017-06-29(2).
[8]向明华.对物诉讼与我国的船舶扣押法律制度[J].河北法学,2006,24(4):121.
[9]DAVIES M.Cross-border insolvency and admiralty:a middle path[EB/OL].(2017-03-26)[2017-06-01].https://comitemaritime.org/work/cross-border-insolvencies.
[10]田田.船舶优先权的法律特征及属性分析──从一则案例谈起[J].学术界,1999(1):50-55.
[11]向明华.船舶扣押程序的独立性及其程序保障[J].中国海商法研究,2007,18(1):230-241.
[12]刘瑶.中国跨境破产国际合作的法律问题研究——以韩进破产案为例[J].中国海商法研究,2018,29(3):107-114.
[13]吴胜顺.冲突与衔接:当海事诉讼与破产程序并行[J].中国海商法研究,2017,28(2):85-93.
[14]孙笑侠.法理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