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凌坡的村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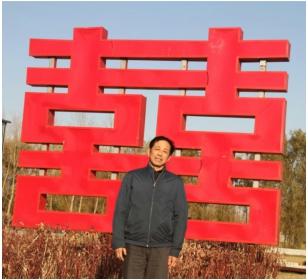
作者简介:顾文显,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吉林省首批“德艺双馨”优秀称号获得者。1987年发表小说处女作,迄今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各类作品1100余万字,诗歌500余首,剧本被拍摄成电影4部,在全国各类作品大赛中获奖500余次,其中微型小说《精神》《英雄》《家仇 国恨》《纸条儿,纸条儿》等分别获得《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年度奖或大赛奖。20世纪90年代始在《野草》发表小说、散文近20篇,并获得两次征文奖。
一
康惠友的胸口正慌乱地扑腾着,森林警察就找上门来。老康恨不能拿锤子砸自己脑袋,睁开眼就左一遍右一遍地嘱咐自己,别想别想,想啥会来啥,可这倒霉的脑袋偏偏就往警察那方面出溜,这不真他媽的给想了来。
警察是屯官李唐全领来的。李唐全说,老康,这是吴警官、杜警官,找你问点事儿。
完了完了。康惠友两眼霎时像蒙了层纱布,几乎看不清来人的脸。平时大叔长、大叔短地叫得甘甜,这回改成老康了,必是警察跟他透露了啥,难道是坐实了案子,要抓他走?
头一回跟警察打照面,康惠友热情不是,冷淡更不敢,两眼直勾勾地瞪着对方,连水也不知道倒。心里叮嘱自己别怕别怕,没事怕啥,可丁点儿用也不管。
吴警官盯着康惠友的眼睛看了半天,问:“老康,昨天过半晌,你干啥去了?”
完了。康惠友脑袋嗡的一声。但他又一遍叮嘱自己,稳当点儿,没做你怕啥,就答:“我上山割点架条,地里的秋芸豆爬蔓老高了。”
声音有些颤。
“割指头粗细的架条,你带锯干啥?”
果然叫那个该剜眼带割舌头的朱踮脚给卖了!康惠友觉得脑门发潮:“警官,我腰里……别把锯就是个习惯,我可没敢打那松树的主意。”
“我说过你打松树的主意了吗?心里没病,你哗哗淌汗干啥?”
康惠友的汗淌进了眼睛里,辣得眼珠子好不难受,他抬起胳膊抹了一下,没抹干净,却感觉不能再抹第二下:“你你你……警官,那松树叫人砍了,我也心疼。你为什么不带警犬来闻一下,罪犯肯定有脚印、有气味。我把话撂这儿,我若是跟那松树沾一点点边儿,把我们全家四口都枪毙!”
警察冷冷地说:“我们怎么破案,还得你教吗?你是高法,说枪毙四口就枪毙四口?废话少说,仔细看下笔录,签字。”
警察和屯官走了半天,康惠友心口依然咚咚咚地跳。警官没带他走,可也没说不带他走,这事有完还是没完?真是人倒霉了放屁也砸脚后跟。昨天下午他去李家沟带着把锯不假,他是瞅准了那儿有一棵病死的枯树,扔着也是烂掉,扛回来不是还可以修房子啥的派个用场?咋就那么巧,偏偏当晚赶上有贼盗伐松树。早知道,还不如承认锯了棵枯树,爱咋罚咋罚呗,现如今他有理也说不清了……是哪个嘴欠告的密?踮脚朱长山。昨天就朱长山看见他进山,还跟他打过招呼!
冰凌坡再往南就是没有人烟的原始森林。过去是个小队,现在成为尚余百十口人的小屯,行政上归十里外的村管辖。站在小屯朝南望,那片三角形的山林里长着三棵松树,冬天松叶翠绿不必说,就是树叶子关门的盛夏,那三棵树也是骆驼站进羊群,打眼一看就分辨得出。它们哪年生的没人知道,据专家说,是稀有树种,得几百上千年才能长到水桶粗细,这样的宝物全地球也就此三棵!松树成了神树,成了小山沟人的骄傲。于是,冰凌坡的村民每天清早开门头件事,就是仰脸望一眼那神树。
可昨夜连风加雨折腾到天明,几十条狗居然没听到咬几声,冰凌坡的村民一开门,那三棵神树没了,再揉眼睛,那神树千真万确地没了!
李唐全下令,哪个也不准到现场,其实不下令也没谁敢靠前。李屯官立即报警。
干屎抹不到人身上。康惠友把这句老话反复念叨,可心里还是不托底,究竟能不能把他给带到局子里去,天知道。如今风传那些警察黑着呢,有事没事挖个坑让你跳,目的就是弄你的钱,可他康惠友缺的就是钱!
昨天下午去李家沟,只遇上那个在垦萝卜地的朱踮脚,两个人还搭了话。除了他没别人。这个朱踮脚那张破嘴给个老娘们儿也不换,连老丛家的闺女处对象怀上了孩子这等事,他也敢造谣,何况他康惠友腰带后真就别了把锯。
康惠友土豆也不抠了,往炕上一仰,他妈的,犯相。姓康的挨上了姓朱的,这糠(康)迟早叫猪(朱)给吃了!
老婆柳絮领着俩闺女进山抠药材,让一阵小雨撵了回来。见男人躺在炕上,灶间没发现新抠的土豆,以为又是打麻将去了,刚要吼骂,男人先开了口。
柳絮那张嘴比刀子还锋利:“什么人玩什么鸟,疤瘌眼嫁了个朱踮脚。这老死头儿打了多半辈子光棍,临老了才娶上个疤癞眼老婆,这样的命,咋就不知道积个善终!”两口子怒冲冲直奔朱踮脚家。
朱踮脚死不认账:“哎呀惠友,你们两口子可冤枉煞我了,我撞见你拿锯不假,可这么大的事,我哪敢随便瞎嘞嘞!”
老康回忆那警察看他的眼神儿,分明是掌握了情况:“对。你哪敢瞎嘞嘞?这山沟里的是非你从来不掺和。”
一句话把朱踮脚噎住了。那回造老丛家闺女怀孩子的谣言差点闹出人命,结果让屯长当众扇了耳光!
柳絮也逼上一句:“嘴巴子是不是扇轻了?”
朱踮脚把手里的茶缸子使劲儿往地上一蹾,磕掉好几块碎瓷片:“康惠友,咱打盆论盆,打罐论罐,少拉三扯四。咱俩冲灯说话,我姓朱的今天大门没出,更没见到警察的面,谁要是对任何喘气的提到你带锯进山半个字,那就天落石头瓦块砸死他!”
“谁死谁命短,谁告状谁心虚!”柳絮才不信赌咒发誓那一套,她扔下这句话,拉着男人气哼哼地走了,那扇破门被摔得呱嗒嗒响了好几声。
老话说靠山吃山。冰凌坡的村民挨着原始森林居住,尽管上面这不让那不让,可看不见偷点摸点儿的事儿哪家没有,就是林业站也睁只眼闭只眼。平时若遇上哪个敢向上级汇报,那就是得罪了冰凌坡全屯村民,这主儿往后别打算在这儿待下去。换别的事,朱踮脚不敢,可如今不同,那神树让人偷了,那全地球只三棵的绝品让人偷走,警察为破案,奖金能少给吗,人为了钱,啥良心不能卖?
回到家,康惠友两口子琢磨来琢磨去,还是觉得除了朱踮脚那个贱嘴子没别人。这么大的事,判多少年可不一定,沾谁身上谁受得了哇。唉,这叫暗算无常死不知呀。
二
第二天,村东头张歪嘴子家盖新屋上瓦。
山沟人心齐刷,哪家有事,尤其是娶亲、盖屋、发送死人,哪怕有天大的仇口,若敢不到场,你人品就跌了下去,往后有事你就自己来吧。
康惠友当然要去帮忙。来到现场,见踮脚朱长山也在,昨天那股火还憋着呢,俩人谁也没跟对方搭腔。老康不须推让就第一个上了房,凭他那手绝活儿。朱踮脚年纪大又啥啥不会,就被安排在房子下角和泥。
上午很快就把架子拉了起来,傍晚上瓦。上完瓦,也就是把房盖整好了,只剩下喝酒吃饭。
本屯子无论哪家新屋上瓦,就是老康和胡大爪子俩搭档大显身手的时候:普通人苫瓦,三人一组,师傅身后坐一接瓦的,地面上有一递瓦的,双手平端起一块瓦,往上一扔,这接瓦人接住,堆在身后,供苫瓦师傅取用。老康身边却省了那接瓦工,自己身兼二任,几乎不用回头,用瓦了,只喊一声:瓦。他的搭档胡大爪子拿起瓦往上一撇,这老康回手刷地接住,瓦不须往身后摞,借惯力往前一送,那叫一个准,严丝合缝地苫在了应该苫的位置,接着回身再要再接。老胡扔瓦不用瞄,老康接瓦不用看,俩人配合得用小学校长谷老师的话说,那叫一个珠联璧合。
今天在屋顶上,老康自然“故伎重演”。不过往下一瞅,那个昨天告状的朱长山踮着一只脚,哼哧哼哧地和泥,老康那股气就又上来了。哼,你妈的,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的废物,就告状有能耐。此时要照腚后一脚踹趴下,你那贱嘴插稀泥里去才过瘾。这样一想,他每接住一块瓦,先借惯力夸张地往后一甩,瞄着在房下和泥的朱踮脚脑袋比画一下,心里说,把你的脑袋开了瓢,看你还敢逮谁诬陷谁。挑衅一下之后,再将这块瓦苫上,康惠友认为不这样就出不来憋在他心口窝的气。
那朱踮脚哪里知道房子上有人冲他恶意比画呢,只顾低头和泥,越这样老康越觉得自己白比画了,心里越堵;胡大爪子知道他俩昨天的疙瘩,也就迎合着老康媚笑,这瓦一块接一块地扔,康惠友赌着气呢,那瓦就越苫越快。
老话说:“人欢没好事,狗欢抢屎吃。”康惠友只觉得这种挑衅解气,没想到却惹出塌天大祸。眼看瓦苫到屋顶了,他回手接过老胡扔上来的一块瓦,这块瓦有道小裂缝,就在老康顺手一抓一甩的工夫,它突然断掉,老康手中只抓住一个小角,剩下的大半块借惯力飞了出去,直奔屋下方和泥的朱踮脚!
康惠友刚才还想象着某块瓦砸中朱踮脚的脑袋,砸得他脑浆崩流才解恨,却不料那瓦当真出了手,并且直瞄着朱踮脚的脑袋去了。康惠友知道要坏事,脑袋赶紧使劲儿往一边歪,可那瓦不受遥控,老康吓麻了爪,大张着嘴出声不得……
老胡当然也看到了瓦片失手,下意识地喊了一声:“三叔……”本意是提醒对方小心,哪知不喊这声,断瓦可能从头顶上越过,这一喊,朱踮脚听到声音一抬头,那飞瓦不偏不倚,恰削在他的额角上。朱踮脚闷哼了一声就倒在地上放出一個闷屁,人竟然死了!
康惠友一下子瘫在了屋顶上。刚才活蹦乱跳的一个人,昨天还一口一个“惠友”,指天画地发毒誓,今天居然死了,死在他康惠友的手里。人命关天,这天塌了下来!
盖屋是大事,屯长李唐全当然在场,他急忙打电话报警,一边安慰傻在一边的康惠友:“老康大叔,这事就算比天大,也不是你特意干的,在场的人都能证明。”
“证明个啥呀?”老康吼道,“就是把我姓康的枪毙八回,能换回这条命来?让警察把我抓去,该咋判咋判吧。”
这时已有人飞也似的跑去朱家给老太太报信。可是,老朱太太没在家,估计是进山采五味子去了,房主张歪嘴子等一干人只急得捶胸顿足,叫苦连天!
三
康惠友的老婆领着九岁的小女儿红玉,各挎着满满一筐五味子,兴高采烈地往家奔。今年真是收了山,大女儿朝思暮想要买个随身听学英语,这回用不了的用!
刚从山坡上下来,却看到本屯的老孙婆子牵着牛往树上拴。这老孙婆子外号“小广播”,左邻右舍的事没有她不知道的,大老远见了柳絮,粗声大气地嚷上了:“如今天矮了,发下毒誓马上报应。快下去看吧,朱踮脚果真就让天落石头瓦块给砸死了,刚才有人跑去找疤瘌眼儿,她没在家。”
也在为告状的事闷着气,见小广播神情不像是乱说,柳絮心头一片乌云豁然开朗,嘴上辟谣,其实是把事实往铁里定:“啊?不能吧。他没跟警察下舌,怎么可能砸他?”嘴里说着,同时回头,望见半山腰有人影一晃,躲进了树丛中,她立即闭了嘴。这也算冤家路窄,那人影正是朱踮脚的老伴儿疤瘌眼儿!
朱踮脚的老伴儿当年是城里人,据说念过不少书,就因为右眼下长着个拇指肚般的大疤癞,活像沙子迷眼翻起来的眼皮,红鲜鲜得吓煞个人,长到三十多岁,没人肯娶,这才下嫁到冰凌坡。过了几年,没生出一男半女,老头子忽然得了急病死了。当时有位跳大神的葛老太太提醒她,就是眼底下那块疤癞位置不好,把老汉给妨死了;如果不治好再嫁,嫁谁妨谁。这样的主儿哪有人敢搭茬?好不容易遇上了老汉朱踮脚,说你不嫌弃我残废,咱俩对付着过吧,只当旧社会的搭伙。咱拼命攒钱,无论如何也得去北京上海把那疤癞弄了去。
真正是瘸驴拉豁磨,老两口和睦相处,日子居然好起来,谁能预测到老汉死在了飞瓦下?
朱踮脚排行老三,山沟人当面三婶子三大娘三奶奶地称呼,背后都叫她疤瘌眼儿。小广播跟柳絮说的话,被她一字不落地听进了耳朵里,她如何肯信这些无聊女人瞎掰,早晨起来老汉还乐呵呵地跟她合计做美容的事呢。然而,两只脚却不由自主地错过自家门前小道,直奔了张歪嘴子的新屋。
走近了,疤瘌眼儿见现场围着一大堆人,谁都不说话,只是默默地给她让开路。定神一瞅,门板上躺着的可不就是她那老头子!老太太两眼一黑,左右晃个不停……然后跪下,两手抱着尸体左晃右摇,半天,哇地哭出来半声,突然停住了,现场静得人汗毛倒竖!
“三奶奶,您别憋着。哭,哭出来就好啦。”李唐全怕老太太再出事,硬着头皮上前哄劝。
又是好一阵子死寂,老太太终于开了口,说话声音像梦呓:“他没告状,咋就死了……”
“三婶子,”康惠友一咬牙,“怨我。我没拿住那瓦,掉三叔脑袋上了。让警察把我抓起来吧。”康惠友感觉这么熬着,还不如麻溜将他枪毙了好受!
“我不跟你说。”老太太站起身,再瞅了一眼躺在木板上的老汉,“要是真告了黑状,那他砸死就活该。可昨天一天他没离我的眼,又没电话,拿啥去告诉警察有人拿锯的事?没告状他一定活得过来。人,先放这儿吧!”老太太扔下这话,转身颠颠地回了家,房门摔得咣咣响!
遇上这等事,事主若是大哭大闹,虽然有些麻烦,却还算好解决。然而,朱老太太只哭了半声,居然要让老伴儿自己活转来,这简直是甩给屯长个天大的难题!李唐全吩咐屋子先停了吧。山沟没实行火化,马上做棺材。这边康惠友的家人守灵烧纸,又派几个跟老太太说得来的女人去陪着她,千万别再出事。
但老太太不发话,哪个敢挪动尸体?大热天放在这里,是绝对不行的!屯长一转念,那老太太别看长相吓人,可平时挺说理呀,如果康惠友给她下个跪,杀人不过头点地,她不会死纠缠的。
“下跪?”康惠友头一昂,“跪天跪地跪父母,你还见我跪过哪个?把我枪毙吧,一命抵一命。”这倔种硬上了!
“屁话!”屯长说,“人家活蹦乱跳的老伴儿嘎嘣一下死了,死在你那片瓦下,换成你会咋样?按法律,你属于过失误伤,判不到枪毙。电视上讲法律的节目没看过吗,你就是马上吊死,也还得负赔偿责任。说吧,从经济上赔偿老太太,你认不认?”
张歪嘴子哆哆嗦嗦地接过话头:“给我盖屋出的事,我也……拿一份。”
康惠友一跺脚:“咋不认?屯长你跟她说,她要多少就是多少,我姓康的今年还不上,明年;这辈子还不上,来世。”
说罢,老康晃晃悠悠回了家。一进门,老婆对他说:“那朱踮脚是不是真告黑状了?不然他咋偏偏让瓦给砸死了?”
啪!康惠友一个耳光,打得老婆滚倒在地上:“操你祖宗。人都死了,你还敢说风凉话,麻溜领着红玉给人烧纸守灵去!”柳絮捂着腮帮子爬起来,屁没敢放,领着闺女跑出了门。
四
出了人命,屯长李唐全再难也得出头哇。他带上几个在山沟算是有头有脸的,硬着头皮去见老疤癞眼儿。
“三奶奶,三爷人是走了,您看有啥要求……”
“他必是跟警察下了舌应誓呢,活该吧。”
“三奶奶,您可不兴这么想,咱们人类都上太空了,还信那个。”屯官急得抓耳挠腮,恨自己话递不上去,“要是发个誓就应了,那还要法院干啥。”
“就是就是。”随员们七嘴八舌帮腔,冰凌坡村民们嘴拙,况且头回遇上出人命的事。
就那么僵坐了个把钟头,老太太终于吐了口:“我知道,就算把老康弄进去,死人还是活不转来。他害我一口,我不能再害他一家。你看我眼瞅六十岁了,活到这窝囊份上,为什么?老葛太太多年前就提醒我,我這个疤癞窝是个凶相,真后悔不早治了它去。你看,妨死了俩男人,我满身是嘴也抖落不清了。”
“三奶奶,咱商量着来。您给个话儿,缺多少吧。”
“我去过市医院。大夫告诉我,到北京上海,有十万块钱做个美容手术,就能整得跟没疤时差不离。死鬼帮我攒下五万,他这条命再给换五万,去大医院给这疤癞弄掉。我这把子年纪,不是图美图浪,就图个不再倒霉,不再把别人吓着,从此搬出这伤心地儿,哪死哪埋,跌进壕沟当棺材,谁个也不拖累。”
李唐全做梦也没想到老太太会如此开通。按说,赔一百万也换不回人来,五万块钱这才到哪儿。可康家实在困难……这样吧,由康惠友和张歪嘴子共同负责赔偿老太太五万元,歪嘴子一万,老康赔四万。
老太太没吱声,算默许了。李唐全在悼词上把死者说得跟雷锋相似,并警告,老人家根本没见到警察,哪个敢背后嚼舌,就是缺了八辈子德,死了也没人抬去。死者得以顺顺当当地入了土。康惠友的小女儿红玉披麻戴孝,给朱爷爷摔的丧盆,出殡时,康惠友与张歪嘴子抬的前杠……棺材一起步,朱老太太又昏死过去……
五
朱踮脚出殡第二天,盗伐珍贵木材的案犯落网。一个外地盗伐团伙早就打定了神树的主意,趁雨夜把它们砍倒,抬过一道山岗,从另一条道上运到了外地,跟本屯人一点关系也没有。警方其实已经掌握了些线索,由于一些特殊原因,需要制造假象麻痹嫌疑人,所以,派一名退休警察带一协警来冰凌坡,就是那么随便一问,问哪个都是带锯了没有。就是这么一个过场,却搭上了一条人命!
康惠友直拿脑袋往墙上撞。千刀万剐的盗木贼,不叫你偷了神树,这人命能出吗?骂过贼人又骂自己,都是他自己做贼心虚,还固执地认定是朱长山告的密!有心想跟老太太赔个罪,可一撞上对方那冷冰冰的眼神,康惠友魂都没了,人家搭上一条命,这罪咋个赔?
知道对不起老朱太太,康惠友立即把家中老母牛连同它的双胞胎牛犊儿低价卖掉,惹得女儿红玉好一顿哭,她舍不得亲手放养的牛哇。家中刮尽箱底,凑了一万五千元,托屯长先给老太太送去。
疤瘌眼儿一张脸拉得老长:“说好了的立马兑现,这哄得死鬼入了土,想耍赖是不是?那我去他门口吊死,大家谁也别想好了!”屯长好说歹劝,说这是表示个态度,明天后天催促老康家尽快把剩下的三万五还完。
李唐全清楚,康惠友砸锅卖铁也凑不齐这么多钱,但他作为屯官,只能是推一天算一天。
这边老康也百爪挠心。朱老太太不追究,等于是天大的恩惠,这钱再不还人家,没天理了。他一边张罗借钱,一边打电话通知念高中的大女儿娟子停学,回来帮助家里。一家人没白带黑地长在了山上,采野果,抠药材,挣一个是一个吧……
这天柳絮领着小女儿红玉上山,发现悬崖上生长着一种叫卷柏的药材,挺值钱的。红玉灵巧,小心翼翼地攀过去,大把地采摘起来……正采得起劲,没提防脚下一块风化石松动,女孩连人带筐摔了下去。
悬崖不高,小红玉人没摔坏,可人砸在枯枝上,枯枝树梢断了,根部一截断枝弹起来,差一点点就戳到眼睛,眼皮下划出一道很深的伤口,那血就淌了满脸……柳絮再也顾不得药材,背起女儿就往家跑……回到家,红玉仍然疼得不住声地哭叫,当妈的嘴里哄劝安慰着,拿盐水洗了消毒,又向邻居借了点云南白药敷上,直到煎两只鸡蛋给女儿吃,算是止住了哭声。
天黑,老康和大女儿也回来了,两口子抱着小闺女放声大哭:“苦命的孩子,你咋偏赶在这当口出事。咱那边欠着人命钱,若是上医院治疗,明摆着的是有钱不还账,你想老太太能善罢甘休吗。”红玉这孩子特别懂事,“爸妈,不碍事的。我小心点不让它感染。就是不能跟你们上山了。”
第二天,老康把红玉留在家,嘱咐闺女定时吃饭吃消炎药,他带着柳絮、娟子进了老林子。赶上季节,成片的蘑菇能绊倒人,但刚采摘的水分多,往家倒腾不起,办法是就地搭间小屋,垒两铺石板炕,摆上蘑菇,炕底下架柴火猛烧,烘干了再换。夜里山外望不着冒烟,就架火猛烧,清早停火,这石板已滚烫,白天照样烘蘑菇,傍晚,再点火……要是让森林警察逮着,不但没收蘑菇,还得蹲拘留所。事到如今,老康两口子啥也顾不得了,他们心里只有一个“钱”字。
冰凌坡的村民没人去跟康惠友家抢蘑菇,个个眼睛瞪得圆,耳朵竖得倍儿直,一旦有警察嗅着味儿过来,就立马去人送信……
六
“一更里呀,黑咕又隆咚,家家户户点上油灯。自个儿打着火,自个儿点着灯,自个儿“拉呱儿自个儿”听……”
天黑透了,老朱太太灯也不点,冲着黑屋子把这首半拉磕唧的老歌哼了一遍又一遍,哼着哼着就变成了呜呜的哭声。
她本来不是个迷信人,不相信那块疤癞能改变她的人生,就算改变她自己,活蹦乱跳的两个男人,哪会都为这块疤癞说送命就送命?假设阎王存在,那么,俩男人的命运是前世定了的,娶了个疤癞女人,阎王就命令秘书给改过来?可这话跟谁辩论去,有人听吗?
老太太叹了一口气,感觉胸口还是堵得慌,就使劲再叹一口,胸口还是堵。她眼前輪番出现俩男人的样子,都是影影绰绰看不真亮。唉,一铺炕睡了多少个年头,其实俩男人真说不上待她好还是待她不好,他们就跟商量好了一般,平时能不说话,就绝不开口;实在有啥事必须跟她说时,脸冲着墙说。她是有名字的,叫高淑芳,可俩男人一律把她叫作了“哎”,就是夜里要她,也是紧闭着俩眼像跟仇人较劲似的,从来没正眼瞅她一下……
洗衣裳时,她也在河水里照过,确实是越瞅越烦。这疤最好是长在脚后跟上,扩大个两三倍也不碍啥,可它……上小学时,同学们都是俩人同桌,她却孤零零地在最后排独占一桌,没人愿意靠着她。她流了多少泪呀,老师总在课堂上一遍遍地讲心灵美心灵美,可到了真格时,怎么连帮她安排个同桌都不肯?老师太虚伪。上到初二,她再也没勇气面对那些异样的眼光,干脆躲在家里自学。邻居有位退休的高中老校长检查了她的成绩,点头又摇头:“怎么不去上学呢,你这天资要是考不上大学,我这双眼睛就算瞎了。”
然而又能怎么样呢,她不敢出现在课堂上,也没有地方参加高考,最后像捡了多大便宜似的嫁到这冰凌坡,跟那个大字不识一筐的半大老头儿睡到一铺炕上,老头儿死了,还被讹成她给妨死的……
眼下老朱头儿走了,倒像是卸掉一副重重的担子。从此夜里不必再憋憋屈屈地应付他,真是不乐意不是,装成乐意更不是。老汉临死给她做了点贡献,可以把这个害她一辈子的疤癞除掉了,往后,往城里一搬,离开这伤心之地,或许可以开始她真正的生活。若是再嫁个老头儿,她可要认真地挑挑,起码也要找个识文断字的。对,一定要找个老头儿,除掉这该诅咒的疤癞,她高淑芳绝对是名副其实的资深美女!
老康家钱准备得咋样了?老康不比她老太太,不愁没人借贷。两口子年轻又有俩女儿,有还债的指望,就是挨家磕头,难道凑不上那笔钱?惹了事别装土鳖呀。这样一想,老朱太太就打着电棒去了康惠友家,催他们赶紧想辙,她脸上的疤癞一刻也容不得!
怎么狗没咬,窗户也是黑着?细听,屋里有女孩轻声哭泣,挨打了这是?姓康的心情不好怪你自己惹事,拿孩子撒什么气?老太太想借机会把老康骂一通,她拉开虚掩着的房门。
屋里好像没别人。拉亮电灯,是红玉仰躺在炕上,眼泪鼻涕抹得一塌糊涂,孩子右眼上蒙着块口罩布,上面压着一个手绢包……伸手一摸,小脸烧得烫手,忙问:“丫头,你这是咋了?”
“三奶奶,我前天抠药从砬子上跌下来,把眼睛下面戳破了皮,我疼啊。”红玉泪如雨下。
朱老太太细瞅,手绢里包着是鸡蛋清和白矾,民间传下来的消炎偏方;掀开口罩布,红玉的伤口转圈发红,已有化脓的迹象!
“你爹妈呢?他们把你自己扔在家里,咋不去医院?”孩子的伤口一下子转移到了朱老太太心口上!
“三奶奶,爸妈进老林子烘蘑菇去了。我不能去医院。俺家还欠您钱呢,欠钱不还就去医院,那成啥人啦。”
老朱太太一下子杵在了原地,半晌不动也无语。突然,她疯也似的跑回家扎了一头,又快步奔屯官李唐全家院子:“出来,给我看住狗!”
李唐全魂都飞了,老太太杀上门来,这回咋应付吧。赶紧跑出来把那狂吠着的大黑狗喝住:“三奶奶……”
“李唐全,你还好意思当这个队长吗!”山沟人仍旧习惯称屯官是队长。
大李知道这是逼债来了,如同小鬼见了阎王,话都说不囫囵了:“三奶奶,我前天还把老康好一通骂,他紧着想法子呢……”
“放你妈的屁!”老太太进屋,把一只塑料袋拍在屯长的炕上,“红玉那张脸眼瞅要毁了你不知道吗?冰凌坡有一个不够,还要变成疤癞眼屯!你麻溜给我找人连夜往医院抬。我这里总共七万五,都拿去。再不够,砸你的骨头,也得保住红玉那张脸。我把话撂这儿,孩子有个闪失,咱谁也别想好了,我这么个年纪,我怕谁?你快呀!”
李唐全以为是做梦。老太太冒火窜烟才讨得一万五,这一下子却连老本也舍出来,不会是讨不到钱说赌气话吧?
“三奶奶,这钱是您治疤癞的……”
“我眼瞅要死的人了,疤癞了一辈子,就不差这几天了,可绝不能再耽误孩子,不能让俺孩子走我这条路!”老太太说罢,扭头就走!
李唐全瞅一眼炕上的钱,对着小广播喊上了:“屯子里会喘气的,赶紧帮我去抢救老康家的红玉……”
很快涌来一大帮村民。李唐全掏出一沓钱:“这是我自个儿家的,每人一张拿去当工钱,医疗费三奶奶出了七万五,剩下的我全包。”
“抢救个孩子还给工钱?队长,不带这么骂人的。冰凌沟村民人穷不假,可没龌龊到那地步。”
几个壮汉轮番背起烧得半昏迷的孩子,连夜送出了山沟。
朱老太太回到自己家,打了半盆清水,对着盆子里的自己骂上了:“你这个倒霉透顶的疤癞眼儿,你接连妨死俩老头儿,临死你差点害了俺红玉,那花骨朵般的年纪呀!”老太太嗚咽了,“你咋这么个命呀,倒霉事全让你摊上了?老葛太太,你整个就是活神仙呀……”哭够了,老太太一头栽倒在炕上,昏睡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朱老太太昏昏沉沉听到有人喊她。睁开眼,天大亮了,喊醒她的是屯长李唐全:“三奶奶,告诉你个好消息,红玉那伤不碍大事,现在她妈陪她住院,一礼拜就拆线回家了……”
“啊?不能落疤癞?”
“大夫说,多亏治疗及时,不然可就毁了容。这回好了,过两个伏天就看不出来了。三奶奶,您起来出去看看。”
李唐全搀起老朱太太,开门一看,老太太呆了:小院外挤满冰凌坡的村民,那个倔种老康跪在当前,身后跪着他大闺女娟子,见老太太开门,齐声叫:“妈!”“奶奶!”
老康的头叩在石板上,磕得咚咚响:“我的亲妈,儿子跪天跪地也跪了您,您就是我亲妈!您得跟我回家,明天咱去北京美容。大家伙儿作证,今后我一家四口全是您的亲骨肉,康惠友有半点虚情假意,就不是冰凌坡的村民。您若是不答应,俺爷儿俩就多咱跪死多咱算!”
老朱太太一阵晕眩,几乎又是站立不住:那个老葛太太看得到底是灵还是不灵呀?还是这张疤癞脸……她虚指着老康的脑袋点了好几下,突然就冒出一个从来就没说过的词儿:“小鳖羔子!”
编后语:
像一块石头掉入平静的湖泊,三棵神树的“失踪”打破了冰凌坡原有的宁静,悲剧和苦难接连上演。可就在这个小小的山沟里,无论何时都能人心齐聚。共患难的次数多了,邻里间的猜忌与嫌隙也随之烟消云散。他们或许不是亲人,却是最亲的人。案件的真相最终水落石出,真正的坏人被绳之以法,冰凌坡恢复了它原有的样子,宁静的背后,又多了一份温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