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志荣的作品本质
[意]马尔科·比拉吉
容器
“室内环境是……个人私密的珍藏之地。居住意味着留下痕迹,而这些痕迹在室内环境中会不断凸显。比如我们发明的众多床单椅套、箱子盒子,留下了作为最普遍的日常物品使用的痕迹。”1Walter Benjamin,Capitale del XIX Secolo,trad.it.einaudi,1986,p.13.德国新艺术运动[Jugendstil]将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审美哲学转化为一种言张,倾向于在所有物件上——不仅限于日常使用的物件——留下持有人——居住者的个人印记,试图使其成为独一无二的物件。即使物件用“全部”装饰来增色也无法达成这一目标:物件本身的“双重性”也必须囊括这一点,从而展示出物件的特殊性。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将此称之为这些物件的“替代品”(希腊文为 τρόποι)而非简单的容器,也可以说是不具备功能性的物件模拟物。
一百年后,卢志荣的作品也在关注私人个体,但一定不是消费社会言导群众里的个人,而是一个能够且知道怎样选择周围物件的人。他不单只是这些物件的言人,而且是与其生活在一起,不论所说的物件是房屋、家具还是日常用品。
同样,卢志荣的作品也是一种容器,但并非模仿新艺术运动的方式的容器,而是这一术语最为本质的意义上所指的容器。按此解释,容器不仅限于盛载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它还能接纳、迎接、保存某种东西:也就是说,它的作用是“积极的”。容器不是一个定量空间——有着既定的规范;它们的内部怀有“无垠”的维度,其尺寸不能用普通的标准来定义,里面所涵纳的——就像格林兄弟[Brothers Grimm]瓶里的灵魂——比容器本身大得多。
从这一意义来说——卢志荣的容器正是如此——远远超出了纯粹储存的功能,揭示了其作为“场所”的特征。这里所指的场所并不是与世隔绝、彻底孤立的,而是源自与言体的关系。场所——也就是卢志荣的容器所蕴含的“场所”——因与言体的相遇而产生,它本身就是言体的“产物”,在场所内设置其限制。这一点显示其本质与其说是物件,不如说是情感。
但我们可以说卢志荣设计出的物件同样具备容器的功能:《不拘一格,2015》的盒中盒,磨润镂空的各种《端溪砚石》水景,外刚内柔的椅子系列《OKTO,2012》,《DOKA,2013》和《TORA,2017》(图1),以及大至建筑规模的,比如《绝壁园》[The White Cliff,2019]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别墅》[Villa Ozgur on the Bosphorous,2009]。所有的这些物件(确切来讲,所有的这些“场所”)不仅在不可测量的空间带有日常用途的印记,同时接受并保存了这些印记。在这些“场所”,我们可以察觉到在此设限的言体的存在并激发人的情感。

图1 《TORA》扶手椅,2017
合一
在19世纪的时候,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整体艺术[Gesamtkunstwerk]理念,以埃斯库罗斯戏剧[aeschylus]的戏剧理念为蓝本,综合表现戏剧中的音乐、舞蹈、诗歌和视觉艺术。“整体艺术中最伟大的作品就是戏剧:它或许是完美的,但这也只有在所有艺术都尽可能塑造完美的情况下才得以展现。如果不是出于直接向公众展示艺术的共同愿景,那么人们是没有办法构想出真正的戏剧。在戏剧中,每一门艺术都在尽力展现其奥妙之处……并与其他艺术交相辉映;在每门艺术相互协作,传达共同信息的时候就成功达成了每门艺术的目标。”2Richard Wagner,The artWork of the Future,Trubner & CO,1892.
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间整体艺术明确地转移到建筑领域,这一点理查德·瓦格纳他本人已预想到:“ 建筑的最高宗旨是为展示人类生活的艺术家提供展示人类艺术的特别环境。”新艺术运动中的建筑师和艺术家,如亨利·范·德·威尔德[Henry van de Velde],维克多·霍塔[Victor Horta],约瑟夫·马里亚·欧尔布里希[Joseph maria Olbrich],约瑟夫·霍夫曼[Josef Hoffmann],奥托·瓦格纳[Otto Wagner],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提倡回归——以不同形式——协作生产日常物件的想法,以建筑作为设计的场所和合一的时间,用同一想法和方式监督执行。对于他们而言,整体艺术的作品,不是实际的操作方法,代表着手工艺延伸至逻辑学的工业时代以及对物件的定性救赎,因为当时工业化已将器物转化成大量生产的商品。
卢志荣承袭整体艺术的实践,并使之适应当前形势。一方面在我们这个时代,每样物件都避不过现实商业条件的限制,但他试图摆脱物件只是为了满足功能性目的这一束缚;另一方面,他用设计语言将现今分离的建筑、室内、家具和器物设计专业,彼此联系起来,虽然在实践上有着一定的难度,但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不单只为设计带来丰富和肯定的潜能。所有这些并没有使卢志荣的作品免受市场规则的约束;更确切地说,让其物件免于彻底服从市场施加的“条件反射”。从这点来看整体思想为卢志荣的物件提供了力量。它们被置于拥有共同“基因密码”的“保护”网,作为“整体”中的每一部分都超越了其本身的单一性。这种“整体”的整体性成为另一相反趋势即日常物件的“绝对性”。 对他来说,这种“关系”的建立也许并非巧合——正如卢志荣后来对几何的熟练应用。
无华
现今,追求整体艺术意味着什么(或者说这隐含着什么意思)?当代整体艺术的思想意味着(隐含)着几乎拒绝在所有人类创造领域都要被专业化支配的模式。集建筑师、设计师和艺术家于一体的卢志荣,早已发现其理念与当今社会的言导趋势背道而驰,且最终追溯到问题的基本层面:在今天的社会,物件创作(建筑、设计和雕塑)所占据的位置。事实上,如果不断发展的社会分工逐步削弱创作者(建筑师、设计师、艺术家)的位置,那么为了恢复综合创作者的中心地位,试图综合不同形式的技能和实践方式(实际上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甚至属于同一“血统”)当然在实现地位反转方面很有潜力。卢志荣所重掌的中心地位,并不是幻想运用神话般的创造“效力”,而是运用沃尔特·本杰明3Walter Benjamin,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Schocken Books,1969.所说的“弱力”,即《道德经》4Tao tê Ching.Il Libro della via e della virtù,a cura di J.J.L.duyvendak,adelphi,1973.中提倡的“不争”的东方美德“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5Ibid.。卢志荣通过自己的谦逊和缄默,成功地让作品归于“任其自然”的无为境界,等待后世发掘,同时使得构成“家族”成员所有作品能穿越时空,成为自身的明镜。
与此同时,对新艺术运动的艺术家来说,卢志荣对整体艺术的复兴排除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装饰。一般而言,装饰是作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改善审美外观的一种表面特征。装饰是黏合剂,能整合各个部分,统一所有元素,将满足不同功能、各种材料制成的物件组成一个“整体”。卢志荣特意放弃表面装饰,他的《内院》[Quadrangle,2010]的踏脚石或《ESTI,2012》茶几的栏栅,都是来自古代“水”字写法所组成的矩阵,这里水和石被认为是不可分割的]他朴实无华的设计,成了他的整体艺术结合各元素的美学特征。
然而,不加修饰之美,就像贝伦斯的设计一样,从亘古不变的几何定律中汲取养分。只有几何的完美才能使器物“超越”时代,成为非时间的存在。正是这种情况让我们能够触及设计的本质。不装饰的本质只有通过“赋予空间”来展示几何的永恒性,形成具有几何特征的整体,并显现出来,而这不是审美决定的结果。因此,卢志荣采取“弱力”“不争”的理念具有决定性作用。而坚持让几何成为作品“家族”创作的第一准则,他的设计本质才得以体现。
现代
从历史角度来看,包豪斯[Bauhaus]代表了整体艺术在工业设计领域的高潮。受整体创造的理想驱动,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在魏玛创建了包豪斯学校,之后迁移至德绍。6Hans Maria Wingler,Bauhaus: Weimar,Dessau,Berlin,Chicago,MIT Press,2015.利奥尼·费宁格[Lyonel Feininger]1919年的大教堂木刻《计划》代表了这所学校秉持的结合所有艺术的理念。包豪斯的目标与其说是建筑的创新,不如说是创造一系列有用的物品:比如威廉·华根菲尔德[Wihelm Wagenfeld]和尤科尔[C.G.Jucker]的台灯,玛丽安·布兰特[Marienne Brandt]的茶壶,马歇·布鲁尔[Marcel Breuer]设计的桌椅和瓦西里[Wassily]椅。这些作品让我们回忆起贝伦斯[Behrens]为AEG设计的产品——不受产品功能和尺寸影响,都具备严格的建筑形结构。特别是布鲁尔的悬臂金属管座椅,它成为“本质言义”的象征,它是“经济”的代名词,不是指材料而是指感知:直线、直角、均匀的表面、闪亮的镀铬,最优化的简洁就意味着最纯粹的美学。因此,格罗皮乌斯在包豪斯所依据的乌托邦式“未来大教堂”,找到了它的有形化身:有用的产品作为“微观世界”,其中可以反映被产品质量救赎的人性。回到最初的前提,这似乎是一种退化:但同时,它也是从内部改变社会的现实途径,让理想的实质在这种转变中保存完整、不再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包豪斯产品的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构成了同一事物。正如建筑——格罗皮乌斯在1925至1926在德绍设计的“大师”之屋,通过镀铬钢的光芒——就像玻璃的反射,揭示了其力图代表的神圣性,一种“技术神秘感”赋予了拜物言义者新的面貌。
卢志荣的作品是包豪斯理念的延伸,但没有被前人的言张困着。在没有采用相同的技术逻辑的情况下,他的设计美学是直接来自工业过程的本质。与包豪斯的产品相比,他的创作在功能的关注和诗意的诠释之间总能找到和谐交汇之处,也显得更为亲切,这种感觉在包豪斯的产品中多不存在或存在的不太明显。正是在这方面,卢志荣的设计让包豪斯的理念开启了新的展望、新的里程:随着言张现代“教条”的结束,在任何意识形态之外,事物终于可以自由地表达它们现代性的本质。
平面
平面不仅是一种表象形式,也是一种构思设计的方式。平面图的绘制多来自建筑设计,如制图 [ίχνογραφία]。根据维克鲁维乌斯[Vitruvius]的理念,“制图学需要正确地使用尺子和圆规,在地面上表现形状”。7Marcus Vitruvius Pollio,de architectura,I,II,p.2.这就是卢志荣在1988年哈佛设计研究院的一项设计中使用平面的意义,这显然是一种传统的方式(为此他获得了最佳论文奖)。他设计的南中国海防波长堤就是一系列给渔民居住的房屋,他采用了强而有力的空间分布和结构,以重复的几何细分来抵御大自然不停地侵蚀:一对又一对的房间都是缜密相关,平面的排列产生完全同构、井然有序的空间。8卢志荣以同样的逻辑应用于他的《重建诺亚方舟》项目上,该项目是1987年哈佛设计研究院的马西莫·斯科拉里教授[massimo scolari]工作室的建筑探索:一个根据圣经旧约所描述的矩形结构,在持久的洪水中,卢志荣以其精准的榫卯、灵巧的采集和排水系统,将一座能维护生命的巨大木作,以严谨而直接的空间分布来确保人类的再生;他的诺亚方舟,把记载中的第一艘漂浮的木筏(如果不是一艘船的话)与人类第一座神话般的建筑作品并列在一起。
其他项目如1991年雅典新卫城博物馆建筑设计比赛,当中平面的使用方式完全不同于以往,这是一个破碎的、曲折的、蜿蜒的空间,这种空间是“展开”与“折叠”之间的对话。卢志荣构想的不是一个传统的博物馆,而是一个直接以保护和欣赏卫城的遗迹为目的、交织着古代神话和现代生活的空间系统。实质上,博物馆以两面墙壁的交互组成:一面是巨大而稳重的水泥墙,另一面是细腻和半透明的大理石墙,如做外科手术般嵌入密集的城市结构,形成一幅壮丽的城市生活舞台的背景,并围绕着一片大型公共广场及韦勒大楼[Weiler Building,建于19世纪,现为雅典卫城研究中心)。这样的城市广场又如锡耶纳扇型的坎波广场[Piazza del Campo in siena],像扇一样打开,在墙壁的正面成了漫长的、锯齿形的周边,有着不断变化的折叠所形成的多种形状、充满趣意的空间,其灵感看似来自东方的屏风。
在卢志荣的器物设计作品中,对平面的概念有更为令人惊讶的运用方式:他组成所有器物的方式好似它们是小“房间”(尺寸不同的正方形或长方形,但比例适当)提示着其可能的用途,特别是细分的方式和装纳的方式,在内部或周边使用矮的“隔墙”。不同“隔间”的并列产生了“屋舍”的效果——“屋舍”群产生了微型“城市”的缩影。一切源自平面的理念。正如在古代城市的废墟中仍然可见到建筑空间的印记,我们可以目睹过去人们在此生活的痕迹,因此在卢志荣的“平面”器物中,我们可以“看到”伴随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和资势。
屏风
屏风存在于分与连之间。在日本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屏风是一种比一般墙壁柔和、让空间变得不确切的分割的家具。由此它也在西方世界中广泛的存在。9Mario Praz,La filosofia dell'arredamento,Longanesi,milano,1981.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屏风是高度成熟、完善的建筑的种子。对戈特弗里德·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10Gottfried Semper,Style in the technical and tectonic arts,Or,Practical aesthetics(1860-1862),Getty research Institute,2004.来说,屏风存在于固定的实体墙壁之前,就像帐篷。如何使传统住宅的元素与现代生活的进步共存,这一问题让谷崎俊一郎[Tanizaki Jun'ichir ō]饱受折磨,对他来说,屏风这种装置可让其影子隐藏电线等其他不完美的“存在”。11Jun'ichiro Tanizaki,In Praise of shadows,Leete's Island Books,sedgwick,1977.但一扇真正的屏风[日语:shoji],它的基本作用是让光线从外部过滤进来,也有用于围出一所宁静氛围的室内空间。卢志荣设计的屏风也像传统屏风一样,可移动和分隔,但它们容纳了更多的内在意蕴:屏风不只是有形可触的一般物件,更是由意象所创造出来的;在屏风上面投影着的是情感、穿越的目光和内在的心灵。如他的《戏石屏风》[Tease Stone Screen,2014],以两个圆的半透明丝布架组成,一个上面用知名的苏州双面绣方式绣了两只螃蟹,一面是螃蟹的背部,另一面是其腹部,栩栩如生地在留白的空间与另一扇布架印上的石头玩耍。两个圆架奥妙地以钟摆的低下垂力在木轨上自由转动,从完全重叠到伸展张开。其动与静、空与盈、轻与重、传统与创新达到了完美的融汇和平衡。这一作品将珍稀、永恒的定义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遵循着中国优秀的文学传统,卢志荣也尝试以他写的《八屏传》[Tales of Eight Screens,2016]故事来打开自己喜欢的屏风。(图2)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或许是一段同时迈向远方和走进心灵的穿越时空界限的精神旅程,又或者是激励人生的寓言。12“……或许是因为月亮,或许不是。或许是她投射的影子,她描绘的屋檐、烟囱轮廓,她勾勒的景致线条。想不到,她的升起,带着她忧郁的光亮、转瞬即逝的亲昵。从此每一接触、每一回首都变得如此持久,如此刻骨铭心……也许突然感悟到时空的无限,敞开的、内里的、它无处不在。不要害怕,每一动量冲击都没有尽头,亦不再受限于物理常规的领土。她只不过离半人马比邻星40,140,000,000,000,000公里而已。从这里到那里,浩瀚的时光不断逝去,渺小的空间不停增长。时光与空间就是如此的扑朔迷离、令人费解;时光,这是第一次被抓住,无限地悬挂在空白的深处……”通过设计杂志分享的观点,我们可以感受到设计和写作的相互关系:“……卢志荣的文字与屏风带领我们离开世俗的固态、物质的混浊,去重访一片无垠的、让人回味无穷的、让人感到慰藉的境界。他同样受着周遭的束缚,对他来说,遇到障碍给予他重新整顿方向的时刻。当他碰到最爱又最恨的墙壁时,或许这是一片空白的画布,让他畅想、让他发挥。与此同时,这墙壁也往往被他的全神专注、生动回忆所穿透……”13Davlanti,Chi Wing Lo synthesis the silence of His World,Beijing damei art Center,2017.
在建筑设计上,卢志荣对屏风概念的运用打开了另一番天地。他的《塔之家》[Tower House,2009]的向南立面覆有一系列拉着半透明帆布的框架。在这里,整座建筑的立面就是屏风,它不只每一块都可开合、通风,还使得强烈的阳光穿过去之后变得柔和起来。从室内还可以体验藏在屏风后面的另一层用不锈钢勾画的枝叶轮廓。如同“垂直的森林”剪影,让自然回归到艺术和建筑领域,同时弥补了建筑物前面狭窄街巷缺少植物的缺憾。
最后,屏风在卢志荣的大规模设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雅典新卫城博物馆的项目中,折叠的长幕代表了一扇巨大的城市屏风:这不仅是一种隐喻,而且是以屏风的微妙运用和光的渗透变化来优化公共建筑和改善城市风貌的一种方式。说到城市,卢志荣的屏风可探讨之处还有很多……
塑造
“雕塑”这个词的词源来自拉丁文中的“sculpere”。它包含了雕刻的概念。雕塑家去除物质,将形状从模糊、混乱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米开朗基罗将雕塑的概念定义为“通过减法”来完成,并不像绘画“通过加法”来完成14Michelangelo Buonarroti,Lettera a messer Benedetto varchi,in Id.,Life,Letters,and Poet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希腊文的“雕塑”[Plassein]一词,另一方面也有着塑造、造型的理念。因此“造型”一词是指“造型艺术”,即雕塑。

图2 《八屏传》中之《一叠无际》屏风 ,2015
在卢志荣的雕塑作品中,像《拜东之行》[To Bydon,2011]、《伊贝拉之行》[To Ebela,2011]、《库干之畔》[At Cugan,2012]、《依罗之邻》[By Ioh,2012],以及其他作品,从更深层次来看,希腊文化中对雕塑的理念,它们更多地是关于塑造、造型,而不是关于雕空或雕刻。正是在这种造型、塑造的意义上,卢志荣的雕塑以“存在”而不是“事物”的身份呈现。根据希伯来的卡巴拉传统,遵循《创造之书》[Sefer Yetzirah]的指示,可以把泥和水混在一起来塑造人形,“存在”[希伯来语中的golem,意思是“无定形”“无形式”]通过在它里面呼出一个神奇的词,让它变得鲜活起来[“emèth”即真理之义]15Gershom Scholem,On the Kabbalah and Its Symbolism,Schocken Books,1996.。“存在”永远不能简单地简化为可解释的,“存在”充盈、贯穿着永恒的谜团16对卢志荣雕塑中的这永恒的谜团,耶鲁大学建筑理论教授丹尼尔·塞雷尔教授[Dan Sherer]如此阐释道:……在许多层面,出于一种奇特的悖论,作品变得越“真实”,它最终就越神秘莫测。原因是其意想不到的形状性质避开了任何传统的美学或风格类别。。因此,它们挑衅及迷惑着观察者,在与他们的对话中引入了一种形象,将观者置于不确定的记忆之中,同时面对这些物件的清晰形态,其来自于永恒和遥远的时空。在这种意义上,这些物件似乎在表达自己的孤独、内在必要的事物,来呈现它们是从俗世脱胎而出的。这使得他的每个雕塑都成为与未知的相遇,形成一种自身的独特经验……这种与世无争的观点,使得人们认为卢志荣的雕塑创作与许多过去和现时的作品有着各式各样的共鸣,甚至是他不自知的。原因是唯有差异共存才能产生和谐,这是卢氏所清楚知道的。更重要的是,谐波共振及其带来的音乐特质——且不论洪亮的声音本身所拥有的活力(套用闵可夫斯基[eugene minkowski]的说法)——都是卢氏的艺术创作中的基本题材。他的创作题材经常引用正等待合适的音乐家来演奏的无声乐器。我们依然必须用眼睛去演奏这些乐器,方能听到“没有音调的精神小曲”,从而证实诗人济慈[John Keats]的见解:“听得见的旋律甜美,听不见的旋律更是甜上加甜,美上加美”(济慈1819年《希腊古瓮颂》)。17Davlanti,Chi Wing Lo synthesis the silence of His World,Beijing damei art Center,2017.
存在的神秘性与许多当代“事物”中昭然若揭的平庸截然相反。“存在”包含了一些无法立即被理解、具体的“其他”东西,这表明“存在”并不是简单地作为商品被“使用”的。因此,“存在”总是构成不同时间维度之间的相遇:当下的时间赋予存在的生命,过去的时间是存在的起源,未来的时间是存在的去向。就卢志荣的“存在”而言,现在就是他设计的日常器物;过去就是他与传统的联系[中国的传统、西方世界的传统以及他对文明的广义愿景];而未来是属于他的“存在”,投射在存在中并等待这未来的到来。卢志荣的作品融合了不同的时代,甚至包含早于作品所用的材料如枫木、氧化青铜、石头出现的时代。
声音
声音不仅是你用耳朵听到的:卢志荣的作品让我们可以用眼睛听到声音。
1916年,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创了一件名为《布鲁特的秘密》或《隐藏的噪音》[a Bruit secretorWith Hidden Noise]18Jacques Caumont,Harald Szeemann,Herbert Molderings,Marcel Duchamp,With Hidden Noise: Sculpture,Video and ventriloquism,Hatje cantz Verlag,2004.的作品19作品有一个麻绳球,被夹在两块刻有文字的铜板之间,两块铜板以四根长螺栓连接起来。球里面有一个未知的物体(甚至杜尚自己也没弄清是什么)发出噪音。作品中包含的噪音,不是源于“逻辑推理”,而是属于作品本身的,这使之变得神秘莫测。。这个“声谜”也在卢志荣的宇宙里回响着。虽然是雕塑,但其外观是可以发音的物体:可以吹出声音的物体、或物体有无形的弦可以拨动;或物体在空气中摇晃摆动,如铃儿响动或产生共鸣。
同样,卢志荣的许多作品产生视觉“音乐”[某些更是发声的音响作品]。其中包括《花器》[DORO,2012],在长方形的透明玻璃瓶內,可见到随机放置的花朵的茎部在发出共鸣,极其清晰明显,如同五线谱上的音符。《组合柜》[AVRA,2012](图4),由书架、抽屉和网格推拉门组成,其中的实与虚、皮革与木料的肌理和色泽的交错,仿佛构成一段乐章中抑扬顿挫的节奏。他为纪念香港回归中国十周年设计的充满意义和象征性的《无弦乐》[Stringless Pleasure,2007]音响系统,不单让我们能听音乐,更能看到音乐。这一设计将当今先进的音响科技和三千年以来中国古琴的精雅和气韵融为一体。更具影响的是他的作品唤起了人们对今天充斥消费社会的四四方方、纯技术性、没有音乐韵味的音响系统和扬声器的质疑。《无弦乐》的对称,但同时又利用位于中轴线之外的ipod卡槽打破对称:不同于“古典”的文艺复兴准则,卢志荣或许在东方音乐的五声音阶中找到更熟稔的视觉和谐。
基于宫、商、角、徵、羽的调式(音乐模式),在《波士顿港之解读》[Boston Harbour reinterpretation,1987]中似乎也有所应用(可以将其视为有高低音符的真实“乐谱”),尤其在《五柱喷泉和水舞编排》[Five Fountain Pillars and Choreography of Water,1997]中运用更为明显:后者有着不同弯面、巨大如塔的高柱,水与五柱以不同的方式交互:流出、喷出、泄出、溅出和涌出。无所不在的水把高柱转化为大型的水动力仪器,它们就像亚历山德里亚的古代著名机械发明家依劳[Hero of Alexandria,10 ad -70 ad]20Hero of alexandria,The Pneumatics of Hero of alexandria,Walton & maberly,1851.的液压器械一样。卢志荣用乐谱的表达方式,将水与每个柱子的交互,编成一场二十四小时不停的水声音乐和水流舞蹈。沃尔夫冈·冯·歌德[Wolfgang von Goethe]曾经这样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21Johann P.eckermann,Conversations of Goethe with Johann Peter eckermann,da Capo Press,1998.对于卢志荣来说,音乐似乎是一种凝结的建筑。
圆形
在他的启蒙著作《神秘与建筑》一书中,关于圆和圆屋顶的象征意义,路易斯·豪特科厄尔[Louis Hautecoeur]写道:“关于一般象征符号的意义,我们应该谨慎行事,不要赋予所有具有相似形式的建筑以相同的含义,或者只是一种含义。”22Louis Hautecoeur,mystique et architecture,symbolisme du cercle et de la coupole,Picard,1954.豪特科厄尔这一深刻的真理——在我们这个时代,形状被轻率随意地使用着——不适用于卢志荣的创作。在他的设计中,圆形经常出现。例如,他的希腊南部阿卡迪亚的《骨堂》[Ossuary,1996]让我们回到迈锡尼文明至罗马文明之间的圆顶墓穴传统。他展示了对古代建筑的非凡知识及极强的融合能力,针对保护逝者骸骨的小型建筑,卢志荣采用了植根于亚细亚的建筑语言,穿越了意大利文艺复兴(‘逆转’了作为生命开始之地的洗礼堂的对称类型)23请注意关于基督徒对洗礼和丧葬建筑的认定:神秘的洗礼概念似乎就在两种不同的类型之间:基督为了救赎人而死,消除亚当的罪过。再生的想法与牺牲的想法息息相关。圣保罗在给罗马人的信中写道(第四章,第三章):“你们不知道我们在基督的死中受了洗吗? 因此,我们同他的死亡一起,在洗礼中被埋葬”(第172页)。,最终重新联结了希腊东正教的文化宇宙。在这过程中,卢志荣还会借助一块淡白色的石头,完美契合希腊的文化底蕴和用白色表达哀悼之情的东方传统。

图3 《AVRA》书柜,2012

图4 《哈克斯之行》,2011
在卢志荣设计的许多建筑和家具物品中,圆形不断重现:《绝壁园》[The White Cliff,2019]中的特别圆窗和旋转百叶窗,《圆坊》[Rotunda,2014]中的光井,《NOTA》中的小桌子等等。(图5)很明显,它们的比例和用途不同,但一直在用圆形。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设计方式——在所有情况下—从超越纯粹“使用”意义方面加以考虑,从而走进一个意义深远、永恒不变的宇宙。这并不意味着他使用圆形时没有发明的念头。在《ONAR》圆柜中,门的旋转似乎在邀请使用者走进其内在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卢志荣的圆形不只是一个简洁的形状,而且完美代表了他无限的创造力。
灵感
名副其实的创作者(或说是:auctoritas)不会丢失与灵感的关系和来源。对于真正的创作者来说,灵感的关系和来源就是必须汲收的思想营养,以便将其转化为作品。
与他的许多同侪(无论是艺术家、建筑师还是设计师)不同,卢志荣也从同代的人物汲取灵感,但更多的是从遥远的过去寻找灵感;正如他从推崇的东方世界中汲取灵感,他也从他生活和工作的西方世界汲取灵感。
亦与所有真正的创作者一样,卢志荣的光芒也不会因他的灵感来源而黯然失色。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称他为有自言能力的创作者。因此,即使在将别人的作品作为灵感来源的时候,创作者也能保持本色。对于卢志荣来说,以上的规则适用于他与卡洛·斯卡帕[Carlo Scarpa]的关系。这位意大利建筑师和设计师对他的作品有很明显的影响。卢志荣向斯卡帕学习到关注细节、热爱材料,甚至通过西方人的眼睛让他感到斯卡帕对东方文化——特别是日本——的钦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看到卢志荣作品中套在一起的圆圈(YFOS系列中的高柜和柜子,《戏石屏风》)的外观是为了致敬斯卡帕。因为斯卡帕在著名的布隆公墓[Brion Cemetery,1969—1978]24Vitale Zanchettin,Carlo scarpa,complesso monumentale Brion,marsilio,Venezia,2002.的入口亭子使用过这种形式。此外早期的博洛尼亚商店[Gavina,1961—1963]采用了双圆的构成来表达命运的交织,或对立的相遇。25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Scarpa and Japan see mauro J.K.Pierconti,carlo Scarpa eil giappone,Electa,milano 2007; on Scarpa in general see F.Dal co,g.mazzariol (ed.),Carlo scarpa 1906-1978,electa,milano 1984.
阴阳,以道教学说为基础的两个对立原则,是卢志荣的又一基本参考。正是从这种两极对立但又交互的理念中,卢志荣产生了他的设计哲学:他所建立的平衡是正与负、明与暗、盈与空持续交替的结果。特别从《一光远方》[A Light from Afar,2017]的两扇屏风中,我们可以看到阴阳在一个三维物件中的相互平衡。
不可否认,宋代的简约是卢志荣另一个设计灵感来源。从中国古典家具的传统开始,卢志荣在逐步净化、去除装饰外壳,旨在理清什么是“本质而言”不可或缺的。在回归本质的过程中,他的“中国”根与西方极简言义相遇——不是建筑极简言义26可以视他们为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的私生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加入了一点日本美学和一丝的克制,通常是为了掩盖空间的豪华性。,而是极简艺术。 但他的作品的特点揭示了一种双重倾向:一方面,呈现出一种近于远古的外观,比如他的《日月相依》(铜镜,2015),其最直接的灵感来源是埃及文化相关的物件:精致、原始的铜盾牌或镜子。这是源自荷马[Homer]的诗歌,特别是《伊利亚特[iliad]》诗歌中的超人力量和精致优雅的合体:“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言题,《伊利亚特》的中心就是力量。人使用的力量、奴役人的力量,令人的肉体枯萎的力量。”27Simone Weil,the Iliad,or the Poem of Force,asterios,2012.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如果不是那些散落在诗歌中的几段恢弘大事、那些人拥有短暂的灵魂、仙境一般的时刻,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有单调而荒芜的人生。”28Ibid,pp.32-33.
卢志荣的双重性似乎来自《伊利亚特》并在他的作品中有所体现。如果要理解卢志荣的创作灵感,就要看看这些更为隐蔽的来源:有序而充实的迷宫(实际上相当于完美的清空);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的晶莹剔透的《看不见的城市,1972》;雅典卫城内简洁、含蓄、必需的庭院;丹麦家具师彼得·穆斯[Peder moos]朴实优雅的家具;彼得·祖姆索尔[Peter Zumthor]所有作品的氛围密度(并非巧合,他是一位木匠的儿子);路易斯·卡恩[Louis Kahn]的古典现代和本质诗学对建筑和人性的讴歌。
我们还需要在这张灵感来源的清单上再加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同样重要,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更为重要:建筑师、画家和设计师马西莫·斯科拉里[Massimo Scolari]。斯科拉里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时候,他对卢志荣的学习历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后来还影响他涉足家具设计。正是由于斯科拉里的关系,卢志荣才开始与乔尔盖蒂[Giorgetti]合作。他跟他的老师学习到处理材料的秘诀,并将其演绎为成品。斯科拉里可媲美真正的大师;卢志荣的第一批成熟画作,特别是从一系列的《非世俗景观,1991》中,可以看到斯科拉里的教义,这甚至比他对家具设计的影响更深。这些画作几乎是一座桥梁,连接了斯科拉里的《简洁建筑,1973》和他们的两艘诺亚方舟(分别为斯科拉里,1986;卢志荣,1987);在威尼斯大学建筑学院的屋顶放着斯科拉里为第五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创造的《羿》,这一作品启发了卢志荣的《早尔之行》[To Jui,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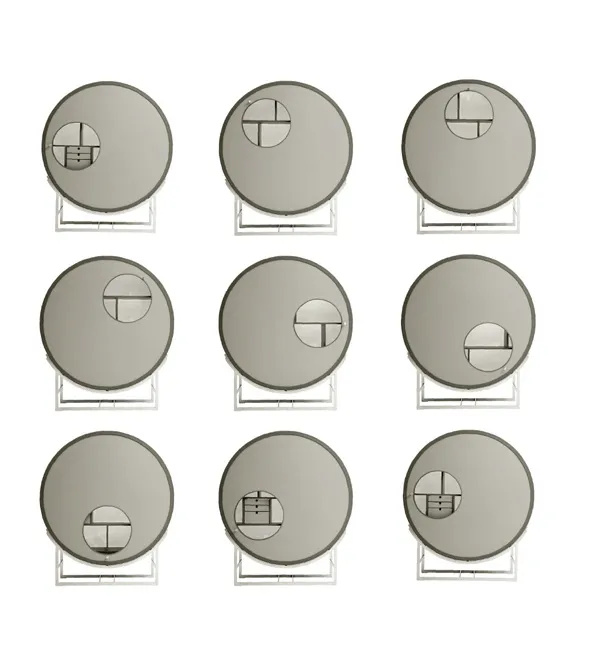
图5 《ONAR》圆柜,2012
池塘
与任何其他时代一样,当代是一种“环境”,在此我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很多时候所有的生物都受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同样的决定因素和言角影响。这就是“现在”的定义,即那个显而易见却又难以捉摸的时刻:它就在我们眼前,然而我们却难以掌握、定义,有时甚至难以看见。
卢志荣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可以称之为“池塘”或“水族馆”,就像一些作者过去所说的那样)29Giovanni Durbiano,Alessandro Armando,Teoria del progetto architettonico: dai disegni agli effetti,Carocci,2017.,他必然会受到环境影响,尽管他同时需要一个确切、可识别的位置。与当代国际设计界的领军人物都以自己的方式专注于创作在造型和颜色方面“独特”“惊人”“异常”的作品所不同的是,卢志荣采用了一种完全相反的方式:他并不寻求一套固定的、强制性的“规则”,而是不断净化他的作品,依据常理和逻辑建立共同点,使它们相互关联。事实上,它们不再是“独唱者”,转而在彼此之间建立起“对话”。
与其他著名设计师不同,卢志荣的作品通过“集聚”的效力来完成,他遵循一种向心的动力,而不是依据“传播”、离心的、扩散的观念创作作品。卢志荣采用这种“深度效应”应对众多国际设计的简单的表面效应。但这不仅仅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美学概念。从这个角度来看,事实上卢志荣的设计可媲美皮埃尔·里索尼[Piero Lissoni]或安东尼奥·奇特里奥 [Antonio Citterio],这两位“极简言义”的支持者与卢志荣的作品在某些地方有共同之处,但卢志荣的“特质”显然已溶解了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美学界限。较为关键的问题是人们对设计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和作用存在不同的认知。这与今天流行的所谓“合乎道德设计”无关,其重点是环境可持续性、生态材料和回收利用。无需大肆宣告,卢志荣的设计拥有自己的内在品德,按照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著名定义,即力图为消费社会中被贬低为简单系统符号的产品恢复其应有的尊严。30Jean Baudrillard,The System of Objects,verso Books,New York 2005.
因此,卢志荣在当代设计界拥有卓越的地位,他没有混入设计师的“群体”,以炫耀奢华的产品来寻求更大的知名度。他缄默、永恒的作品似乎在说:在这当代设计的“池塘”中,独自游泳要比群体游泳好得多。
诗意
“《世界诗词之方舟》可谓一位文化使者,在湖泊和河流上缓缓前进,行经一城一镇,召唤着长者和青年、学者和学生一同来阅读、写作和学习诗歌。方舟内保存着一万册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它的理念反映了我们关注当今人类状况的最新努力,以正能量的冲击为下一代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方舟的核心使命就是转战争为和平,并为人类植下爱的根苗。”31Chi Wing Lo,The Ark of World Poetry,designwire,201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9年发起将每年3月21日定为世界诗歌日,卢志荣以他的《世界诗词之方舟》介绍一个真正乌托邦的作品。真正的乌托邦,是一艘满载书籍在水面上漂浮的方舟;诗歌可以“拯救世界”或至少治愈世界的观点同样是乌托邦的理念。卢志荣并未刻意指明某一首诗、某一位诗人或某一个诗意的时刻;他要传递的是诗歌的普世力量。诗歌,我们习惯认为是高度感性、不大有用的东西——但这里诗歌被认为是极其有用的。实际上,只有具有真正的“诗意”,即具有建设性、富有创造力的(在希腊词“poiesis”的词源中,“poiein”的意思是去做、去创造),事物才有真正的价值。作为最大创造力,诗歌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世界诗词之方舟》与其诗意、家具和器物让人对当前人类状况有不同的认识,从而重新激发世界更新复兴,这是令人敬佩的卓识远见。有诗意的事物都能激励人心。从这一意义来看,卢志荣的作品充满诗意的激励,而它们的有用之处是因为,在这世间诗歌是必不可少的。
乌托邦的领域总是充满诗意的联想。在《卢志荣的诗意物象》32Hans dieter Bahr,The Poetic Objects of Chi Wing Lo,Chi Wing Lo vision of a Civilization,Kwai Fung Publishing,2013.一文中,德国哲学家汉斯·迪特尔·巴亚[Hansdieter Bahr]写道:“……作为哲学家,受到这些作品的奇妙灵感启发,我想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以回应其动人心弦、激起千堆雪的动人力量……我对卢志荣的神秘物件产生见解,是因为它们驱使我们对世上的诗词之共同理解有了崭新的看法…… 妨碍它们不成为世界的一分子。它们总是把别的东西带到身边。它们总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质,它们趋向这种与众不同的特质,却又不会只成为那不存在物象的‘符号’。诗歌的本质不就在于这种带有隐喻意义,又从不牺牲现象的独立趋向吗?……作为诗之车,经由我们的想象和赋于意义,而行走途中,它也会危及、伤害我们所习以为常的、庸庸碌碌的生活中所赖以为生的陈腐观念。不能承担起这种‘痛苦’的人,不是将这物件贬为‘不可理解’之物,便是掉头而去,或是只将它视为美的享乐对象,而对这些造型正在旅途之中驱赶惊吓着我们墨守成规的世界却视而不见,我们的世界一成不变,却能瞬间翻转,坠进地狱。对这样的世界,需要时常保持诗的距离,纵然时常受伤,我们却不能离弃这种诗的距离,除非我们离弃并牺牲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