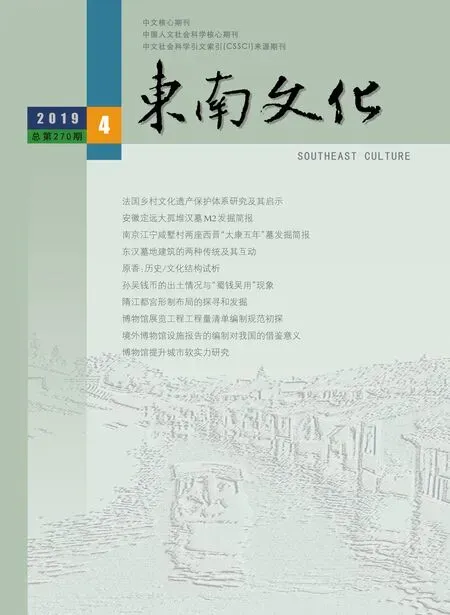原香:历史/文化结构试析
王 曦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在古代中国社会礼俗中,“焚香”不仅具有重要礼仪功能,更蕴含着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心理结构。从人类学的视角,结合文献和考古材料分析,可以梳理出祭祀用香材料和方式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探寻“香通神明”背后的隐喻结构。从“取萧祭脂”到“焚香酹酒”以礼化俗的过程,实是维系“家国一体”社会结构和“差序格局”的仪式象征。从“尚臭”到“香火”,旨在敬天法祖、延续血缘、为子孙后世祈福,以实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儒家伦理秩序理想。
为什么“焚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延续数千年不断的礼仪习俗?“香”的使用已成为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经验,其后究竟隐藏着一种什么样的深层社会心理结构?对这一行为的学术解读,除了对于“香”文化的介绍性通论之外,主要有三种路径:第一种是物质文化史的研究路径,通过结合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偏重于考证梳理历代的香具器型和用香方式等变化[1];第二种是经济社会史的研究路径,发掘香料贸易在文化互动中的轨迹,分析香料和香药在社会消费中的变化等[2];第三种是人类学的研究路径,以祭祀用香为中心,对“香火”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进行分析,试图给出一个更具深度的解释模式[3]。“香”作为沟通古代中国现实社会和精神世界的一种物质,不仅承载着重要礼仪功能,更蕴含着一种深层次的历史和文化结构,关涉的是对中华文明传统中“人”与“物”关系的理解。本文试图借助结构人类学的视角和考古出土材料分析,在对“香史”进行历时性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香火”背后文化心理结构的共时性因素。
一、从“尚声”到“尚臭”:祭礼的交换环节
《礼记·礼运》篇有“夫礼之初,始诸饮食”,道出了饮食作为礼的起源之一;而《说文解字》则将“香”字解为“芳也,从黍从甘”,其本义亦指黍米等食物的味道好闻。由此我们可以认为,“香”作为一种人类感觉,在古代中国最初是与“礼”勾连在一起的。人类学家李安宅在对《仪礼》和《礼记》的社会学研究中,强调了“礼”作为等级、交换和道义的平衡模式,注重的是相互关系[4],而莫斯(Marcel Mauss)在其经典之作《礼物》中对“礼物经济”的分析,既是“物的交换”也是“人的交换”,是一个天地人神“混融”的整体呈现的社会实在[5]。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评论莫斯的“礼物社会”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契约论的政治哲学”,一种“宗教人类学的世界观”。实际上其中包含了“双向契约关系”,“礼物”除了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横向契约关系”,更重要的是作为类似神(最高公意)人(社会共同体)之间的“纵向契约关系”,这种“全面契约论”,才是人类生活共同体分享伦理秩序和道德情感的社会基础[6]。我们再看杨联陞对中国传统中“报”观念的梳理,他指出甲骨文中“报”字的原意是“郊宗石室”(王国维),即源于祭祀,并且“报”的观念贯穿了“祭”的整个过程(梁启超)。因此,“报”成为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7]。
在中国传统祭祀的仪式结构中,由于在“绝地天通”的先民社会,鬼神是“不可见”乃至“不可言说”的,所以,无论是听觉还是嗅觉,在作为先民祭祀沟通地天、人神上下两界的“纵向契约”的“导引”感官媒介上,相对于视觉均具有优先性。因此,经历了从有虞氏“尚用气”到“殷人尚声”,再到“周人尚臭”的演变之后,“周人尚臭”成为了祭祀用香的源头。《礼记·郊特牲》载:“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郁合鬯,臭阴达于渊泉。灌以圭璋,用玉气也。既灌,然后迎牲,致阴气也。萧合黍、稷,臭阳达于墙屋,故既奠,然后焫萧合膻、芗。”郑玄注:“萧,芗蒿也,染以脂,含黍、稷烧之。《诗》云:‘取萧祭脂。’”
先秦祭祀用香主要体现在国家祭典之中。所谓的“尚臭”,是指宗庙祭祀对气味有特别的重视,灌献在前,作乐在后。在连通天地的“纵向契约”结构中,又区分了向上和向下两个方向。从甲骨文及后世辑佚的文献来看,天子祭祀各方神明,要以木柴、牲畜、玉器一起焚烧,用燃烧产生的烟气敬飨神明,这就是所谓的“燔柴祭天”,香料燃烧后烟雾缭绕,属于朝上的方向[8];宗庙祭祀,则需要用郁金和黑黍制成的香酒灌注于地,使香气通到黄泉,为地下的神明所享用,这就是“郁鬯”——“郁”是姜黄科的香草,“鬯”是黑黍酿成的酒,“郁鬯”是指郁金和黑黍做成的香酒——属于渗下的方向[9]。用马尾蒿涂上动物油脂,与黍稷一起燃烧,使香气飘在屋内,这就是“取萧祭脂”[10]。
在《诗经》中,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到香气在祭祀中的具体场景。《诗经·小雅·楚茨》曰“苾芬孝祀,神嗜饮食”,而《诗经·小雅·信南山》谓“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报以介福,万寿无疆”,《诗经·大雅·生民》则更清楚地说明了香气在祭祀中的功用:“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以兴嗣岁……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从上述“燔柴祭天”“郁鬯”“取萧祭脂”这三道祭祀程序来看,先秦时代的祭祀用香,就香料而言,既包括郁金、蒿、艾这样的香草,也包括粟、黍这样的粮食,还包括柞、棫等燎祭用柴。从使用方式而言,主要是制作香酒,或者直接焚烧。这一时期与祭祀用香制度相配套的用具,主要是灌酒和熏吸的酒具,如河北元氏县西张村西周邢国墓地曾出土的两件铜卣,自铭为“小郁彝”[11],以及直接用以焚烧木柴的祭坛等。
由此,我们或可推论出从“尚声”到“尚臭”的转变。首先,这是伴随着殷周之际祭祀对象的变化而发生的。正如张光直先生指出,“从西周开始,祖先的世界与神的世界逐渐分立,成为两个不同的范畴。这个现象是商周宗教史的大事”[12],即从“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转向“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从信奉最高神权的“帝”到尊崇天意和人事结合的“德”。陈来称之为“中国早期文化的理性化道路”,即是先由巫觋活动转变为祈祷奉献,而祭祀的规范化则进一步产生了周礼体系[13]。因此,“香”也跟君子为政之德联系在一起,故而伪《古文尚书·君陈》中有所谓“明德惟馨”。其次,在以“报”为核心的先秦祭祀结构中,燃烧产生的香气除了本身能导引通神之外,还形成了双重的交换结构。我们借助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宗教理论,以原始宗教提炼出的“积极膜拜”的要素为参照,即通过祭祀仪式中食物共享等方式,实现神圣与凡俗力量的互相交换[14]。“尚臭”由于其在祭祀仪式中同时连接天地和四方,勾连了火神与作为土地神的“社”,因而与殷商巫乐的“声”相比,在祭祀仪式中逐步占据了优先地位。从殷商“神人交换”纵向模式转变为周代宗法体系中“人神——人人交换”的综合模式[15],西周祭祀实质上已由宗教程序转变为世俗礼法程序,主持祭祀者掌握着政治经济的分配权,《礼记·祭统》提及重在“设俎施惠”,“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散发“香气”的祭肉分配,成为确立宗法秩序中的身份等级和政治分封的象征,实质上成为增强宗法社会联系的象征性纽带。
二、由“燔燎”到“烧香”:大小传统的混融
法国社会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在《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中,通过对《诗经》和祭祀的社会学阐释,试图揭示官方礼仪“大传统”的基础源自于对乡野“小传统”的改造,被改造的民间节庆演变成了官方宗教礼仪。而在特定时期、疆域和场所举行的祭祀等宗教活动,又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变得与时间和空间要素无关,最终形成“仪式技术”[16]。
自秦汉以下,虽然国家祭祀格局已然改变,但汉武帝时仍用“芬芳不备”来形容雍地祭祀,可见以香气沟通神明的祭祀“仪式技术”虽衰落,但依然延续,“燔柴祭天”“郁鬯”和“取萧祭脂”作为官方祭典中的不同程序仍然保留了下来[17]。《后汉书·礼仪上》曰:“宰祝举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六宗燔燎,火大然,有司告事毕。”《后汉书·礼乐志》又有“清明鬯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抚安四极”的歌颂,而《汉书·礼乐志第二》则留下了“炳膋萧,延四方”的记载。自东汉起,在非官方祭祀的场合,也出现了许多有关“烧香”的记载,最早见于成书东汉初年的《易林》(《道藏》第36册):“秦失嘉居,河伯为恠;还其御璧,神怒不佑;织组无文,烧香不芬”,裴松之注《三国志·孙策传》则记载,“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策曰:荆州刺史张津‘尝著蜂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吴书·士燮传》谓“胡人夹毅焚烧香者常有数十”。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此时的“烧香”者多为道士或胡人,无论是来自佛教或道教[18],总之尚被视为非儒家正统的风俗,这种“仪式技术”在民间宗教中的兴起,亦在为通神祈禳之用。
如果我们对汉代所谓“烧香”记载略加分析,就会发现其独特之处。首先,尽管关于“烧香”记载很有可能只是语词上代指先秦的“燔柴祭天”“取萧祭脂”,但其在史料中出现的场景基本属于非官方的行为习俗,因此,可以将之视作是一种与官方祭礼不完全相同的“仪式技术”。20世纪80年代山东枣庄地区出土的一块东汉时期的“双鱼”画像石,画面两边各有一盘,盘中各摆了一条鱼,画面正中为一炉,上插有三根条状物,中间者最长,两侧略短(图一)[19]。因同期汉代墓葬中祭桌祭品屡屡出现,推测壶中的条状物应同样为祭祀之用,至于是蜡烛,还是用牛尾蒿缠上油脂绕成束的“萧炷”,抑或甚至是线香,尚存疑问,仅备一考[20]。
其次,“烧香”所燃烧的“物”也发生了变化。随着西域和南海贸易的兴盛,外来香料如龙脑香、安息香[21],以及东汉年间逐渐传入的氍毹、五木香、迷迭、艾纳、都梁香等[22],这些树脂类或木类的舶来品,因其气味比本土香草要浓郁得多,逐渐成为皇族和官宦阶层的新宠。
再次,伴随烧香的兴起和香料的改变,香具相应也发生了变化。前述先秦祭祀所用的香具,并非后人习见的香炉,而是作为礼器的酒器或食器;在生活用香上,主要是宽矮的香炉,无论是曾侯乙墓出土、残存了褐色烟灰的铜炉[23],还是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的残存了茅香、高良姜、辛夷、藃本等香草炭状物的豆形熏炉[24],都具有燃烧面积大、空气流通性强、烟气重的特征,这也与直接焚烧香草的方式有关[25]。汉代博山炉的出现,主要是受战国至两汉的升仙观念影响,其炉盖雕刻为海外仙山状,明显有神仙信仰的祈祷含义[26]。这一升仙的观念可说是本土神仙信仰和方士巫术的表现,在国家祀典之外,呈现出时人渴求与神明相通的另一图景。此外,实用性的考虑不可忽视,博山炉内部有足够的空间,可满足以炭块助燃树脂香料的新需求,无须以炉盖来控制香味散发。时人可通过控制炭火慢慢加热香料,香味徐徐散发又少烟气,博山炉的实用功能可见一斑[27]。
三、以“三焚香”代“三献”:符号系统的转喻
汉末以来,官方祭祀的“大传统”向民间弥散,随着佛教东传和本土道教的逐渐兴起,“烧香”以“邪俗之道”的形式大量出现,实是儒家官方礼仪“大传统”和佛道“小传统”产生双向互动而成。道教吸收了先秦的祭祀科仪,以香味向神灵祈祷行道,烧香者凭诚心借香烟可上达天界[28]。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徒开始以焚香行礼的方式来祭拜祖先,或始于寇谦之对天师道的改革。其《老君音诵诫经》(《道藏》第18册)称:“君曰:道官、箓生、男女民,烧香求愿法,入靖,东向恳三上香讫……今日时烧香愿言上启,便以手捻香着炉中,口并言……复上香愿言某乙三宗五祖,七世父母……后上香言,愿门内大小口数端等……复上香愿仕官髙迁。复上香愿县官口舌,疾病除愈。一愿一上香,若为他人愿通,亦无苦。”
同时,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丧葬之礼中开始出现“烧香”的线索。《南齐书·萧嶷传》记其嘱,“三日施灵,唯香火、槃水、干饭、酒脯、槟榔而已。……朔望时节,席地香火、槃水、酒脯、干饭、槟榔便足……后堂楼可安佛,供养外国二僧,余皆如旧”,祭品中出现了“香火”。传统祭品中的香品是“爇萧”,也就是香草、动物油脂和粮食的燃烧之气。但在萧嶷理念中,佛家的“香”已经替代了传统的“爇萧”,佛教烧香与朔望祭祀进一步合流[29]。“烧香”之俗又逐渐进入上层皇族的日常,《晋书·杜太后传》记载“桓温之废海西公也,太后方在佛屋烧香,内侍启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晋书·佛图澄传》记载“勒召澄,试以道术。澄即取钵盛水,烧香咒之,须臾钵中生青莲花,光色曜目,勒由此信之”。梁武帝对郊祭礼仪的改革,亦受其影响。《隋书·礼仪志》记载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年)何佟之上奏:“《周礼》‘天曰神,地曰祇’。今天不称神,地不称祇,天欑题宜曰皇天座,地欑宜曰后地座。又南郊明堂用沉香,取本天之质,阳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于人亲,宜加杂馥。”帝并从之。
先秦两汉官方祭祀,焚烧燔柴,祭品是柴、牺牲、玉帛产生的烟气;但在佛教的影响下,官方祭品已转为沉香和上和香(杂香)。如果说梁武帝的改革还限于郊祭,到了唐代,焚香则逐渐成为宗庙祭礼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第一,以三焚香代替三献,并从便于施行出发,将祭品改为素食。《旧唐书·礼仪六》唐天宝八年(749年)敕文记载:“禘祫之礼,以存序位,质文之变,盖取随时。……自今已后,每禘祫并于太清宫圣祖前设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礼,钦若玄象,下以尽虔祭之诚,无违至道。比来每缘禘祫,时享则停,事虽适于从宜,礼或亏于必备。已后每缘禘祫,其常享以素馔,三焚香以代三献。”
第二,明确在皇家的丧葬之礼中使用香案、香炉、香烛。《通典·凶礼七》卷八十五引《大唐元陵仪注》称“启前二刻,内所由设奠席及香烛于帷门之外”,《通典·凶礼八》卷八十六又称:“内谒者帅中官设香案于座前,伞扇侍奉如仪……内谒者、中官舁香案出……内谒者帅香案进于辂前……山陵日,依时刻,吉凶二驾备列讫……内侍捧几,内谒者捧香炉,各置舆上……内谒者捧香炉置座前,舆等退就列。”
安葬唐宪宗时,唐穆宗下诏用香药代替鱼肉作供品“入景陵玄宫合供千味食,鱼肉肥鲜,恐致熏秽,宜令尚药局以香药代食”,认为香药清洁,而时鲜熏秽,这明显可见佛家对于荤食态度的影响,实是出于佛教轮回和报应的观念,坚决反对杀生和血食[30]。
第三,佛家对国家祭典的影响,还体现在国忌日行香的典礼上。所谓的“行香”,即通过燃香熏手或以香末散行,最早出现于南北朝佛教的祈雨仪式中,后来在唐代贞元年间成为定仪。狭义的国忌日行香定期举行,由在位帝后率大臣在京城佛寺或道观进行;广义则指普遍进行的行香活动。从行香的规程来看,除了焚燃香灶、跪拜礼敬、主持唱赞外,还有宰臣跪焚香等带有祖先崇拜意味的内容。一般来说,在行香之前,皇家或大臣也会先行布施[31],以上可从敦煌出土文书和法门寺地宫出土香料中窥见一斑[32]。
除文献外,唐李邕墓出土壁画中有一副“仙人捧盘图”,人物手托长方盘中立插十余支线香状的细竿。有学者研究称,白衣人为仙界人物,该细竿为香则恰如其分[33]。一般认为,唐宋用香还是以合香而成的香丸、香饼为主,线香在元明时期才确定出现,故而唐代有无线香还在未知之数。对此,考古发掘整理者也持谨慎的态度,认为线香兴起的开端是否在晚唐或更早抑或更晚的其他历史时期,目前并无有力证据证实[34]。而若此图表现的是仙人捧香,则我们对唐代佛道二家焚香科仪之影响,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总之,焚香一事渗入了郊祭、宗庙祭祀和丧葬之礼,成为祭祀用香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传统的燔柴郁鬯爇萧之礼是否还实行呢?唐前期曾有一次针对燔柴在前还是祭神在前的争论,最后以先燔后祭的结论告终[35]。另外,封禅也需要燔祭之礼,从武则天封禅而赐“金鸡树”之名来看,燔祭在祭天地诸神中的作用仍然十分强大[36]。至此我们看到,唐代在佛道二教的影响下,宗教用香的方式开始渗入官方祭典:佛家将香作为供养菩萨的圣品,以香供佛,代表除灭一切生死烦恼,得到清净自在[37];而道家也注重焚香,不但因为香可用来供养三界诸神和道、经、师三宝,还因为它是除祛污秽的重要净化器,道教的授经、授符、服食、存思、通神、炼丹合药、祈福攘灾、解罪除恶等都需要行香,并有赖于香料的使用。从香料上来看,佛教文化带来了大量的新的香料,从而加强和丰富了中国的焚香传统[38]。
如果我们借助“隐喻——转喻”的方法来分析,一方面,可以发现“转喻”发生在纵向结构上,佛道两家的香说经过了多重转喻,逐渐实现对“周人尚臭”结构中的沟通“介质”的替代,才使得与鬼神沟通之香几乎成为近世以来宗教仪式的专属。而另一方面,在横向结构上,正如李亦园、王斯福等学者指出,与西方具有超越性意义的“朝圣”相比,中国的“香火”是“人间行政等级体系的翻版”[39]。自“烧香”泛化到地方民俗宗教的仪式之后,从乡民祭神的集会中进一步分化出了流动的“香会”,成为帝国逻辑在地方的隐喻和投射[40],并赋予了其联结和维系民间社会秩序的力量。
四、“焚香酹酒”之兴盛:物的文化动力学
唐宋之际在社会阶层、经济结构、风俗人文等领域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影响广泛的“唐宋变革论”在诸多层面揭示了“近世化”的倾向[41],唐五代以后,士庶之间已不像原来那样泾渭分明,礼仪上呈现为“士庶通礼”的趋势,世俗化也激发了士庶阶层对于一套便于施行的冠婚丧祭礼仪的强大需求。为此,官方和士大夫阶层都希望能够“化民导俗”。
在官方祭祀层面,宋徽宗时期修编《政和五礼新仪》。官方祭祀的神明虽种类繁多,包括昊天上帝、五方帝、日月星辰、后土、社稷、宗庙陵寝等,但综合祭祀礼节中涉及以气味通神的部分,仍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燎祭和焚香。据《政和五礼新仪》卷六十五,郊祀需“俟火燎半柴,礼仪使跪奏礼毕”,所用焚烧的木柴包括松木、柏木等。就焚香而言,常祀所用之香是内廷专门制作,即《宋史》卷九十八“吉礼一”所载“凡常祀,天地宗庙,皆内降御封香”,其中“大祠悉降御封香,中、小祠供太府香”[42]。在国忌日行香的仪式中,宋承唐制规定了行香的科仪,即《政和五礼新仪》卷一百十四所载“内侍奉香,太常卿奏请,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当然,一般认为,由于《政和五礼新仪》过于繁琐,脱离社会生活实际,在当时并未能真正实行。随着近代意义上的“世俗社会”兴起,世人需要一种更简单便捷的沟通祖先和神明的方式,于是“焚香酹酒”成为了首选。但这种做法对严守古礼的儒家士大夫而言并不能完全接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十七元丰四年(1081年)“十月己未”条记载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讨论礼文时就称:“近代有上香之制,颇为不经。梁天监初,何佟之议郁鬯萧光,所以达神,与其用香,其义一也。上古礼朴,未有此制,今请南郊明堂用沈香,气自然至天,示恭合质阳之气;北郊请用上和香,地道亲近,杂芳可也。臣等考之,殊无依据。今且崇事郊庙明堂,器服牲币一用古典,至于上香乃袭佟之议。如曰上香亦祼鬯爇萧之比,则今既上香,而又祼爇,求之古义已重复,况开元、开宝礼亦不用乎。”
到了北宋元符年间(1098—1100年),将“郁鬯”和“取萧祭脂”改为“焚香酹酒”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宋史》卷九十八“吉礼一”记载:“周人以气臭事神,近世易之以香。按何佟之议,以为南郊、明堂用沉香,本天之质,阳所宜也;北效用上和香,以地于人亲,宜加杂馥。今令文北极天皇而下皆用湿香,至于众星之位,香不复设,恐于义未尽。”可见,以焚香取代郁鬯和爇萧这一做法似乎已逐渐为士人所接受,并一律用合香祭祀天地,“焚香”对于“郁鬯爇萧”的替代关系也进一步明晰。宋代儒家士大夫之所以逐渐主张废弃“郁鬯”,首先因为这是天子诸侯之礼,不可谮用;但最主要还是因为无力找到郁金和黑黍做成的香酒[43]。因此,灌郁鬯的习俗连官方祭典都不再使用,唐宋之后就基本废弛了。
在士庶之礼方面,宋代儒家士大夫兴起了私家修礼的热潮,最著名的当属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和朱熹《家礼》[44]。以二者为代表的士大夫所制的“家礼”中,都有焚香酹酒的程序,“焚香”是降神所需,“酹酒”则为神灵享用。司马光对这一古今变化有着更为切实的考虑,《书仪》卷十中记载了他的观点,“古之祭者,不知神之所在,故灌用郁鬯,臭阴达于渊泉;萧合黍稷,臭阳达于墙屋,所以广求其神也。今此礼既难行于士民之家,故但焚香酹酒以代之”,“主人升自阼阶,立于香卓之南,搢笏焚香”。在朱子《家礼》卷四至卷五中,“焚香”的程序处处都在,凡降神就要焚香。家庙必备香桌,香桌上备香炉,宾客来时要焚香、酹茶酒。宋墓壁画中屡屡出现的“夫妻对坐图”,尽管对其性质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含有祭祀意味这一点还是大致可以确认的,而墓中常常出现酹酒题材,桌前也有香匙等物。有学者考证赤峰沙子山元墓西壁所绘的燎炉、长流注壶和长柄勺,东壁长桌上的带盖梅瓶和劝盘酒盏,即分别为朱子《家礼》所言执事备器具过程中的“茶酒之具”,即所谓“火炉汤瓶、香匙”和“酒瓶、盘盏”[45],这足以说明“焚香酹酒”成为宋人用以祭祖通神的方式。不过在此问题上,朱熹也有反复,《朱子语类》卷七十四“或以为焚香可当爇萧,然焚香乃道家,以此物气味香而供养神明,非爇萧之比也”,朱子反对完全以焚香替代燃烧脂蒿,但又不得不承认了焚香的功能。同时,他在《家礼》卷五中提出对始祖的祭祀将“脂杂以蒿为一盘”,略显“取萧祭脂”的古意。或许这也正是儒家士大夫“礼从俗”的考虑。可见,废弃“取萧祭脂”跟社会的世俗化和饮食习惯的变化有关。通神在上古本是士大夫以上的专属,由于宋代以来“礼下庶人”的需求,加之郁金、萧这样的香草又不再大行于世,理学家也不得不从俗考虑了。
更有意思的是,在宋代士大夫“焚香酹酒”的习俗再造过程中,借以承载这一习俗的物质中介,即香炉,也主要是由三代青铜礼器的形制变化而来。两宋的香炉形制变化多样,究其文化源头,无外乎佛教西来[46]、宋代礼制改革[47]、其他域外或本土信仰的影响等几种。仿古式香炉,尤其是鼎、鬲、簋、樽香炉,成为宋以后的主流香炉器具[48]。这其中虽然有使用便利性的考虑,但相较于脱胎佛教的手持香炉、高足香炉等形制,从青铜礼器变化而来的“本土”香炉,显然与宋代士大夫的理念和趣味更为契合。三代礼乐之治的食具、酒具等形制,一变而为宋代的香具,“场合”发生了神奇的错位,然而追慕祖先之意却更为浓厚,这大概也是“香通神明”这一持续两千年心理结构的强韧生命力的极佳说明之一。再举一考古材料为例,四川广元1980年出土的南宋杜光世夫妻分室合葬墓,其西室西壁第三层岩石上刻有焚香图:中部以上刻有一神牌,侧刻一树,树下一人拂袖跷足依树而坐;另一侧刻有一人,手捧三足两耳的鼎式结构的香炉,作躬身拜祭状(图二)[49]。从宋辽金元墓空间结构来看,根据宿白先生提出的“借壁画器物或砖雕器物来代替实物”的见解[50],引申出其空间家宅和祭祀意味的加强[51],因此或可以推测,焚香图代表的并非生活中焚香的情境,而是祭祀用香的情境。事实上,与这个香炉形制类似的鼎式香炉,是宋代追慕三代复古之风下制造的仿古器物,具有礼器的性质,这样的器物也常常在供桌或水陆道场中被发现[52]。广元石刻墓焚香图所显示的祭拜场景,可与《书仪》称百姓将“木主”与祖先画像并列的习俗相呼应[53],显示了焚香之俗在宋代士庶群体祭礼中的广泛影响,并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在此略加申论的是,有宋一代香事大盛,举凡祭祀、饮食、医药、妆容等等,处处都有香的影子,随着宋代以来近世意义上的“消费社会”兴起,作为“物”的香也发生变化。首先,在香料上,宋人所焚的“香”,已非汉唐以前的佩兰、茅香、桂皮、花椒、高良姜,随着两宋海上贸易的盛行,沉香、龙涎香、檀香、乳香、降香、没药等外来的木质和树脂香料,逐步替代了本土香草,也让香逐渐从奢侈品变为必需品。其次,宋人的焚香的方式,也已不再是直接燃烧香料,而是将各种香料切割磨碎再用粘合剂混合成复方香调。因此,“合香”和“窨藏”成为重要环节,然后再将合成之香放在炭块上焚烧[54]。在用香上,皇族以豪奢为风气,士大夫以清雅为特征,庶人群体以实用为目的,官府则垄断了香药的专卖权。如果我们借助西敏司对“糖”的经典研究中关于“仪式化”和“顺延化”的区分[55],就会发现香也是通过类似的方式,加速流入生产、消费和交换的各个环节,成为让“焚香酹酒”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日用礼俗的重要文化动因,并在意义结构上完成了新物质的编入与象征再授予(symbolic reinvestment)。
五、小结
宋人丁渭《天香传》称香“所以奉神明,所以达蠲洁”,《陈氏香谱》则引伪《古文尚书·君陈》“至治馨香,感于神明”,可见“香通神明”作为一种文化政治的隐喻和社会心理结构已深入华夏文明。正如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提出,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宗旨,是“探求不变的事物,或是从表面上歧异分殊的众多事物中,追索出不变的成分”[56]。从周代起,香气在祭礼中发挥重要的沟通上下左右的作用,自两汉至唐,随着佛道二家大兴中土,随着西域和南海而来的异域香料的大量引入,“香通神明”的历史文化意义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转喻”已悄然发生:其一,“香”不再是上古时期的兰蕙椒桂郁鬯;其二,“通”的方式也变为今人所熟悉的“焚香”;其三,“神明”的范畴也扩大了,在祭祀天地四方与祖先之外,呈现了官方祭祀之神与佛道及各种民间信仰神明的混融。宋人作《香谱》,还将“香通神明”追溯至三代祭祀之礼;到了清代,《钦定四库全书·子部九·香谱谱录·类一·器物之属提要》中显示四库馆臣对南宋《陈氏香谱》的评价,就认为将“龙涎迷迭”的源头追溯为“左传馨香”是“殊为无谓”了,可见博学如四库馆臣,已不觉得香事与“黍稷馨香”有什么关系。而如果我们以现代人类学的眼光来看,历史的辩证法始终都是“结构的”,历史中特定的结构“都在旧范畴中积淀了新的功能性价值”,而正是这种在历史延续与变异中的文化接纳(cultural encompassment)又促进了结构的再生产,所以萨林斯一再强调,“历史乃是以文化的方式进行安排”,并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向历史“开放”[57]。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试图梳理“香”作为文化结构中所指向的“物”以及满足社会心理需求的方式“通”在不同时代的流变,正是为了揭示“香通神明”正是中华文明史中延续不变的且具有能动性的文化结构。这一结构在凝聚横向社会秩序的“共时性”方面,从“取萧祭脂”到“焚香酹酒”以礼化俗的演变过程,正是基于“香火”在仪式程序中简易化的实现,促使了不同社会阶层在日用礼俗的共通,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满足了维系“家国一体”社会结构和“差序格局”的需求。而在延续人类世代的纵向历时性上,从“尚臭”到“香火”的仪式技术隐喻,则一直致力于实现沟通祖先、延续血缘关系,以实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儒家伦理秩序,最终进一步衍生出了后世民俗“续香火”之说,焚香尽其诚以敬天法祖,是一种为子孙后代祈福盼“报”的历时性文化心理结构。而明清以来遍布华夏乡野的“天地君亲师”牌位,在家堂以香火供奉[58],则可视为上述纵横双向文化结构最具象征意义的交汇点,高度浓缩了中华文明观中宇宙天地、政治社会、家国天下、物我群己的精神内核和价值精华。
[1]a.扬之水:《香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b.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07—114页;c.崔叶舟:《魏晋南北朝香炉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18年;d.霍小骞:《宋代香炉形制研究》,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2]a.〔澳〕杰克·特纳:《香料传奇:一部由诱惑衍生的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b.温翠芳:《唐代的外来香药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c.夏时华:《宋代香药业经济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3]a.黄美英:《访李亦园教授:从比较宗教学观点谈朝圣进香》,《民俗曲艺》1983年第25期;b.王铭铭:《从“朝圣”看作为“历史中的文化翻译”的人类学》,收入《人类学讲义稿》,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
[4]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16页。
[5]〔法〕马塞尔·莫斯著、汲喆译:《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9—210页。
[6]〔美〕马歇尔·萨林斯著、张经纬等译:《石器时代经济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99—208页。
[7]杨联陞:《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中华书局2016年,第14—15页。
[8]a.焦智勤:《卜辞燎祭的演变》,《殷都学刊》2001年第1期;b.王贵生:《周初燎祭仪式考辨》,《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1期;c.许科:《古代燎祭用物及其意义》,《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d.李锦山:《燎祭起源于东部沿海地区》,《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春之卷;e.詹鄞鑫:《神灵与祭祀:中国古代宗教散论》,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98—299页。
[9]何驽:《郁鬯琐考》,《考古学研究》(十),科学出版社2013年。
[10]孙庆伟:《周代祭祀及其用玉三题》,《古代文明》(第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11]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元氏县西张村的西周遗址和墓葬》,《考古》1979年第1期。
[12]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429页。
[13]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10页。
[14]〔法〕涂尔干著,渠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05—411页。
[15]王铭铭:《从礼仪看中国式社会理论》,收入《人类学讲义稿》,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第441页。
[16]〔法〕葛兰言著,赵丙祥、张宏明译:《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7—208页。
[17]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36页。
[18]吴焯:《汉代人焚香为佛家礼仪说——兼论佛教在中国南方的早期传播》,《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3期。
[19]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2卷),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141页。
[20]a.杨爱国:《东汉时期佛教参与丧葬礼俗的图像证据》,《齐鲁文物》(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6—20页;b.宋丙玲:《汉画中的用香习俗探析——从一块东汉画像石说起》,《民俗研究》2014年第11期;c.詹鄞鑫:《神灵与祭祀:中国古代宗教散论》,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99页。
[21]关于龙脑香,参见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60页;关于安息香,参见温翠芳:《返魂香再考——兼与罗欣博士商榷》,《经济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2期。
[22]汉乐府诗有“行胡从何方,列国持何来?氍毹毾登五木香,迷迭艾蒳及都梁”。引自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第287页。
[23]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47—248页。
[24]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报告》(上集),文物出版社1973年,第125页。
[25]如长沙楚墓M569发现一件豆式陶香炉,炉中尚存未燃尽的香料和炭末,但扬之水认为,与炭同燃的香料,自非草香。扬之水:《两宋香炉源流》,《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1期。
[26]博山炉形器本身具有通神祈福、求长生求升仙等含义,一般认为其主要与本土神仙信仰有关,也有学者认为域外文化对其挂饰形制等影响较深。可参见a.艾素珊、李莎:《西汉时期的博山炉——一种类型学和图像学的分析方法》,《民族艺术》2009年第4期;b.罗森:《中国博山炉——由来、影响及其含义》,收入《祖先与永恒:杰西卡·罗森中国考古艺术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c.巫鸿:《玉骨冰心:中国艺术中的仙山概念和形象》,收入《时空中的美术:巫鸿中国美术史文编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d.惠夕平:《两汉博山炉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e.同[20]b。
[27]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60—361页。
[28]张泽洪:《论道教斋醮焚香的象征意义》,《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1期。
[29]龙圣:《朔望烧香祭祖礼仪考源》,《民俗研究》2017年第2期。
[30]〔美〕祁泰履:《由祭祀看中国宗教的分类》,李丰楙、朱荣贵主编《仪式、庙会与社区:道教、民间信仰与民间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年,第551页。
[31]a.梁子:《唐人国忌行香述略》,《佛学研究》(总第14期),2005年;b.张文昌:《论唐宋礼典中的佛教与民俗因素及其影响》,《唐史论丛》(第十辑),2008年。
[32]敦煌文书P.3047《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乾元寺科香帖》记载,乾元寺向僧尼科征乳头香、旃檀、郁金香三色共六两,分为六组征收。平常寺院僧尼个人所用香料有相当一部分是民众针对性的施舍。见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寺院香料的科征与消费》,《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2期。《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账碑》记:“乳头香山二枚,重三斤;檀香山二枚,重五斤二两;丁香山二枚,重一斤二两;沈香山二枚,重四斤二两。”描金木山11块,原放置于地宫后室,懿宗供奉。《衣物帐》记为乳头香山、檀香山、丁香山和沈香山,雕刻描金而成。块高14.2~28.3、宽4~12厘米,共重1701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上册)》,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27页。
[33]魏军、卫峰:《李邕墓壁画中特殊画面之探析》,《文博》2012年第1期。
[34]陕西考古研究院编著:《唐嗣虢王李邕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21页。
[35]见《旧唐书》卷二十三“礼仪三”:“显庆中,礼部尚书许敬宗等因修改旧礼,乃奏曰:谨按祭祀之礼,周人尚臭……委柴在祭神之初,理无所惑……是知自在祭初,别燔牲体,非于祭末,烧神余馔。”
[36]如《新唐书》卷七十六“后妃上”:“太后加号天册金轮圣神皇帝。遂封嵩山,禅少室……封坛南有大槲,赦日置鸡其梢,赐号‘金鸡树’。”亦见《旧唐书》卷二十三“礼仪三”:“至天册万岁二年腊月甲申,亲行登封之礼。……登封坛南有槲树,大赦日于其杪置金鸡树。”
[37]全佛编辑部编:《佛教的香与香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38]〔美〕薛爱华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第十章“香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55—370页。
[39]黄美英:《访李亦园教授:从比较宗教学观点谈朝圣进香》,《民俗曲艺》1983年第25期。
[40]a.顾颉刚编著:《妙峰山》(影印版),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中山大学民俗学会1928年,第1020—1027页;b.〔英〕王斯福著、赵旭东译:《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8—152页。
[41]a.〔美〕包弼德著、刘宁译:《唐宋转型的历史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1卷第3期,商务印书馆2000年;b.李华瑞:《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从多视角看“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古代文明》2018年第1期;c.〔日〕伊藤正彦:《“传统社会”形成论=“近世化”论与“唐宋变革”》,《宋史研究论丛》(第二十二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
[42]综合后世辑佚的资料来看,御封香、太府香应是多种香料磨碎混合加粘合剂制成,是合香而非单一香料,气味则以木质的沉檀为主。《陈氏香谱》则记有宣和御制香、御炉香的香方。参见宋·陈敬撰:《陈氏香谱》卷二,四库全书本。
[43]其实,唐代判文中就有“太常申博士请供郁鬯酒,光禄以久无匠人,且金草不知所出,不造”的记载(见《全唐文·卷九八一》)。虽然是考试中假设的情况,但判文多有所本,也从侧面反映了现实。
[44]姚永辉:《从“偏向经注”到“实用仪注”:〈司马氏书仪〉与〈家礼〉之比较——兼论两宋私修士庶仪典的演变》,《孔子研究》2014年第2期。
[45]袁泉:《从墓葬中的“茶酒题材”看元代丧祭文化》,《边疆考古研究》(第6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另外,从登封箭沟宋墓、新安石寺乡李村宋四郎墓、温县前东南王村宋墓、安阳小南海宋代壁画墓、河南焦作金代邹瓊墓等墓葬出土壁画中,也常常可以看到成组侍者备献酒食的场景,与有关“焚香酹酒”的文献呼应。参见邓菲:《宋金时期砖雕壁画墓的图像题材探析》,《美术研究》2011年第3期。
[46]扬之水:《莲花香炉和宝子》,收入《古诗文名物新证》,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第12—23页。
[47]宋代追慕三代的礼制改革对于物质文化和器型的影响,前人论述颇多,可参见a.李零:《铄古铸今:考古发现和复古艺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43—65页;b.陈芳妹:《追三代于鼎彝之间:宋代从“考古”到“玩古”的转变》,《故宫学术季刊》,第23卷第1期,2005年;c.扬之水:《两宋香炉源流》,《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1期。
[48]a.王楷:《宋金出土瓷香炉初步研究》,山西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b.同[1]d。
[49]杨文成、匡远滢:《四川广元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2年第6期。
[50]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54、94页。[51]李清泉:《“一堂家庆”的新意象——宋金时期的墓主夫妇像与唐宋墓葬风气之变》,《美术研报》2013年第2期。
[52]同[48]b。
[53]从宋代有关木主的记载来看,木主上下左右都要钻孔,使祖先魂灵得以进入长存,但图中的神牌没有小孔,是否是木主的类似物,尚不能得出确定的结论。吾妻重二、吴震:《木主考——到朱子学为止》,《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54]宋人编纂的各种香谱开始出现。宋初沈立有《香谱》,丁渭作《天香传》,任职泉州市舶司的叶廷珪作《南番香录》,洪刍作《香谱》,颜博文著《香史》,最后由宋末陈敬集大成为《陈氏香谱》。
[55]〔美〕西敏司著,王超、朱建刚译:《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51—153页。
[56]〔法〕列维—施特劳斯著、杨德睿译:《神话与意义》,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18页。
[57]〔美〕马歇尔·萨林斯著、蓝答居译:《历史之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326页。
[58]余英时:《“天地君亲师”的起源》,收入《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