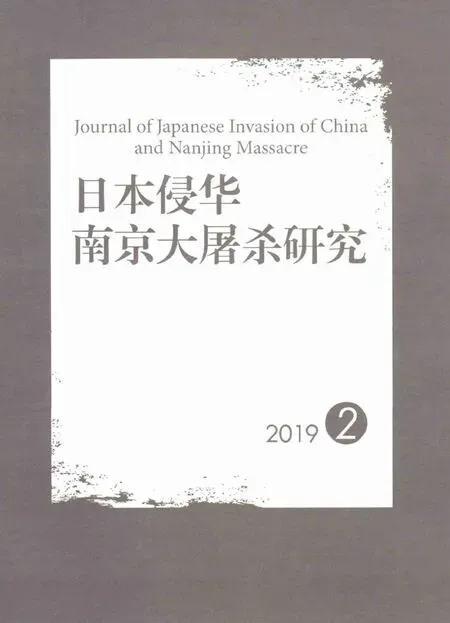豫东沦陷区伪军的生存策略
——以伪军与伪政权的粮食竞逐为中心
姜子浩
本文旨在将豫东的伪军与粮食问题联系起来,通过考察日军当局、伪政权与伪军各自的生存策略,审视豫东沦陷区“文”“武”关系潜在的张力。学界已有研究豫东伪军或粮食的成果,但多囿于单独考察个别伪军头目,[注]有关豫东地区伪军的描述散见于各县文史资料及后人的回忆录中,其中较详细者有中共商丘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张岚峰其人》,中共商丘县委党史办公室,1985年。或阐释日军当局和伪政权的粮食掠夺及粮政机构,[注]关于豫东粮食,目前最为完整的研究参见オドリック?ウー(OdoricWou)著、吉田豊子訳「河南省における食糧欠乏と日本の穀物徴発活動」、姫田光義、山田辰雄編『中国の地域政権と日本の統治』、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207-228頁。未将该问题置于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历史脉络、日军及伪军的生存策略中加以考察,也未梳理日军当局与伪军合作中带有竞争的动态关系。本文试图以此为切入点,重新构建豫东沦陷区农村复杂的政治图象。
一、豫东沦陷区与华北粮仓
华北沦陷区中以豫东地区局势最为复杂,是日伪、国、共三角斗争的角力场。日军具备压倒性的军力优势,控制了沦陷区的战略要地,即城市及铁路周边地区,但军力的强势不能完全掩盖日军兵力不足、战线过长的现实。以河南沦陷区为例,日军在新乡、开封、归德设有特务机关,分别控制了豫北及豫东地区。控制开封、新乡地区的是日军第三十五师团,控制归德地区的是骑兵第四旅团。但日军的大部兵力需从事作战及车站等要地的警备,对点的控制尚且勉强,对农村面的渗透、对民众的控制更难称深入。
沦陷区之大与日军兵力之少,制约了日军的部署。为保持机动作战及军队战力,日军无法分散部署于沦陷区所有据点,若一味龟缩于城市,也难以维持基层的社会与生产秩序,这无异于放任国共在农村的发展。河南的日军特务机关也认为,统治的最大困难在于难以获得地方精英的支持。为了弥补伪政权的弱势,日军特务机关着力吸纳河南沦陷前后出现的民间武装,将其转化为县警备队、保甲自卫团等。[注]《1942年9月份省及各地特务机关的部署情况(河南部分)》、《华北方面军的治安肃正制定〈肃正与建设三年计划〉》,陈传海、徐有礼、刘海涛等编:《日军祸豫史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3—274、359—362页。通过伪化原来的会门、土匪、保安队、自卫团、地主武装,再将其部署于次要和外围防区,以此间接控制地方基层。
日军当局在中国沦陷区的如意算盘为,提供少量装备、给养和部队番号以诱使伪军分担防务,尽量使更多日军腾出手来对国共发动攻势,形成了沦陷区少数日军驻守核心地带,多数伪军驻守外围地区的分治现象。[注]苏振华:《开辟敌占区工作初步总结》(1941年4月7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 文献部分(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60—562页;《根据地的创造与巩固基本政策起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 文献部分(中),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相反,伪军也利用日军“以华制华”的策略大肆扩张地盘,以为后图。日军与伪军各取所需,彼此利用。在豫东地区,日军于占领后不久组建“豫皖剿共军”,1939年4 月在开封组织“绥靖委员会”,胡毓坤任主任,张岚峰等9名伪军头目为委员,翌年又允许汪伪政府设苏豫边区总司令部,以加强对豫皖苏边的掌控。[注]中共商丘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张岚峰其人》,第7、15—16页。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批日军被调往太平洋战场,张岚峰等伪军头目开始掌控更多兵力及实权。[注]参见王翔九《我所知道的张岚峰》,毛德富主编:《百年记忆河南文史资料大系》军事卷卷1,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96—406页;《汪伪军事组织和伪军的变迁》,邢汉三《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河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205, 283—288页; 王飞霄《六年地下工作的回忆》,商丘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商丘文史资料》第2辑,2001年,第22—23页。
日军一方面裹挟伪军稳定战线,另一方面为建立“日满华”经济同盟,需要在人力、物力乃至思想上实现更广泛的战时总动员。特别是1940年美、英等国冻结日本的海外资产后,日本原有的贸易网络深受打击。为弥补失去的原料来源及外销市场,日军一方面加大力度搜刮殖民地和沦陷区的资源,另一方面也要求后者“自给自足”。由此,华北沦陷区的经济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化,其中最关键的是粮食供应的改变。近代以来,华北每年大量从其他地区输入粮食,以满足城市人口的需求。1940年以后,澳、美、加等主要粮食输出国不再向华北供粮,即使日本本土和伪满洲国,其粮食输出亦因故锐减,而在需求方面,华北沦陷区军需民食所需粮食却不降反增。华北沦陷区黄淮平原的广大农村,从豫东、皖北、鲁西到苏北的粮食产区一时成为日军的“战时粮仓”。
华北粮食供应的“本地化”与伪军规模的迅速扩张是并存的。从维持治安的角度看,伪军的存在或是不可或缺的,但从获取资源的角度而言,伪军却是日军调度农村粮食、调剂城乡民食难以逾越的障碍。
二、豫东地缘格局及伪军的坐大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政委苏振华曾指出:当地“敌人相当注意,靠近敌人交通要道,但处于敌人两大建制的接合部。华北敌自北而南,华中敌自长江而北,因而这里敌人最弱,统治最不普遍,不深入。”[注]《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水东工作讨论记录》(1942年12月27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 文献部分(中),第351页。这基本概括了豫东地区作为日、伪、国、共多方力量缓冲区的特点。黄河改道后,日军以开封、商丘为中心,沿陇海铁路和公路控制重要市县及集镇。[注]《水东独立团一九四三年工作报告》,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 文献部分(中),第885页。
豫东地处日、伪、国、共之间及地方势力内部各系统的边缘地带。日伪将豫东地区以“豫东道”之名划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及伪河南省公署辖区,重要事务实际由开封及归德的日军特务机关(后更名为陆军联络部)决定。当地伪军建制混乱,部分属汪伪的伪苏皖边区司令部,部分听命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及当地绥靖公署,另有一些只注重地方事务的杂牌军、保安队,无统一的整体规划。[注]开封日军特务部指挥开封、陈留、通许的伪军,归德日军特务部控制睢县、民权、柘城、太康等地的伪军,双方配合和各县间的协调不良。参见《水东独立团一九四三年工作报告》,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 文献部分(中),第894页。到抗战后期,伪淮海省属的张岚峰部与华北系之孙良诚、庞炳勋部成为在豫东活动的主要力量。[注]《一九四四年水东军事工作总结》,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编:《睢杞太地区史料选》(中),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5—254页。国民党方面,第一战区及鲁苏豫皖边与豫东隔河相望,视豫东沦陷区为黄河河防的前沿阵地,持续派小股游击部队于当地活动。中共方面,河南沦陷不久,新四军游击支队联合数支地方武装,在豫皖苏边建立抗日根据地。1941年,豫皖苏边区主力转赴津浦路东,只留下少数部队继续在睢杞太地区活动。同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将该地区暂划冀鲁豫边区党委代管。1944年,新四军第四师重返津浦路西,联合冀鲁豫军区在河南发展。[注]李中一:《坚持和发展睢杞太(水东)抗日根据地的片断回忆》,中共商丘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回忆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35—736页。整个抗战时期,八路军、中央平原局、新四军第四师、中共豫东工委等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介入了当地事务,然彼此间之联络并不紧密。[注]《商丘地区征集党史资料第二次老干部座谈会》,中共商丘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党史资料》第3期,1983年,第1—3页。
豫东既为三方接合部,也是战略要地,日军要维持陇海铁路,国民党军则坚守黄河防线,中共希望打通华北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中共水东干部以“五鬼闹水东”形容“敌、伪、顽、匪、会”在当地的活动,客观反映了当地的复杂形势。日伪、国、共三方斗争在此缓冲区形成了微妙的势力平衡。三方之外的会门、土匪、杂牌军等灰色势力乘机活动,三方对其也拉拢或打击,希望能打破当地的胶着局面。[注]参见《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水东工作讨论记录》(1942年12月27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 文献部分(中),第354—355页。
在日伪、国、共三方中,日军战力最强,又控制了作为物资集散地的城市和铁路,在扶植地方武装上占有优势。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当局面对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的问题,亟待扩充伪军以分担防务,以压缩国共的生存空间,为此,有意识地“伪化”杂牌武装,豫东社会军事化的状况因此更为严重。[注]参见《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水东工作讨论记录》(1942年12月27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 文献部分(中),第345页。
日军主导、伪军协助是沦陷区军事活动的常态。1943年,中共冀鲁豫边区估计当地日伪军之比为1:15,日军约6000人,而伪军有10万人之多。[注]黄敬:《对敌斗争报告》(1943年11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三辑文献部分(下),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13页。在沦陷区外围地带,日军与伪军合作,大量构筑“碉堡、据点、公路、小碉堡、封锁沟”,把国共武装的势力范围分割为不能彼此相连的“孤岛”,而后集结兵力逐个击破,再向内压缩“蚕食”。在治安相对稳定的城市周边,日军则把日常警备任务委交伪军,以抽出更多兵力。1943年,日军华北方面军依照所谓“对华新政策”建立“决战体制”,伪军更被视为该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注]《冀鲁豫军区一九四三年军事工作总结报告》,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 文献部分(中),第914页。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当局见所谓“支那事变”短期内无法解决,开始有系统地大规模扶植伪军,以实现“以华制华”。1939年4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发布《治安肃正要纲》,把收编地方武装列为治安维持的重点工作之一,作战与“宣抚”并举,因势利导,诱使沦陷区内外的地方武装投日,再根据《归顺工作实施要领要领》及《归顺部队处理要领》,将其整编为警察、自卫团,专司维持地方治安。[注]「昭和14年陸支受大日記第22号1/3」(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120833000、按理,伪军的后勤给养概由伪政权负责,惟在特定情况下也允许伪军“自活”,即就地征发粮饷。豫东民风尚武、枪枝泛滥,种种有利条件为“强人”“拉枪杆子”割据一方提供了便利。日军对沦陷区之控制愈加严密,这些“强人”中的许多人即率部降日,成为了豫东伪军的一大来源。
资料来源:《敌在华各战区训练之伪军一览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篇—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四),(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435—1441页。
豫东伪军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为较成体系的剿匪军、剿共军、绥靖军,因获日军扶持,军力相对较强,其整训由当地日军特务机关负责,部分给养由日军当局解决。另一种为一些地域性较强,组织较为散漫的土匪、会门武装,其部分是日军和伪政权以威吓、利诱、抽丁等方式编成的。这些武装多被伪化为保安队、自卫队、民团、防共自卫团等,以县为单位活动,军力较弱,给养也完全自筹。[注]《伪军概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篇——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四),第1425—1432页。不论何种伪军,均不同程度地寄生于地方。即使伪政权能基本满足其给养需求,伪军上至头目,下至士兵,仍有欲望搜刮更多的粮饷和物资。在战乱的农村地区,攫取粮食顺理成章地成为维持伪军生存的要务。这些武装自保自利的攫夺行为,与伪政权试图将都市民众的粮食需求转嫁至豫东农村的做法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具体而言,日军为推动“以华制华”策略,放任降日部队的扩张而不提供全部给养的做法,使这些武装割据一方以求生存。在此情况下,伪政权将养活伪军的责任转嫁到驻地乡村,固然大大减轻了日军当局和伪政权的物力、财力负担,但也不可避免地制约了伪政权对农村基层的治理。
三、伪军与伪政权的竞食
伪政权治理农村面临诸多挑战,就豫东地区而言,伪政权面对的主要是“治安维持”与“粮食攫取”不能兼得的两难困境。这归咎于日军推行“以华制华”策略,即倚赖伪军维持沦陷区的基本秩序,并把大片外围地区委交伪军管治。实际情况是,少数日军倚赖伪军分担防务,伪政权却无力为伪军提供足够给养,为确保伪军继续发挥作用,日军当局自然默许伪军就地“自活”,这变相为伪军干涉地方政治经济事务大开方便之门。[注]「陸支受大日記(普)別冊昭和16年1—5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歷史资料センター)、Ref. C07092281900。日军利用伪军,伪军也通过附日控制乡村,并掌控基层权势及农产品,由此,地方政治军事化愈形恶化。日军放任的态度客观上导致伪政权与伪军“文”“武”相争,双方围绕有限的粮食资源展开“竞食”。
“这里民不聊生,求死不得,谁能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谁就能吃得开。”战乱时期的粮食,既是稀缺的消费品,也是战略物资。在天灾兵燹不断的豫东,不单民众要粮,地方武装和伪政权也要粮,各方都期望能持有更多的农产品。[注]《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水东工作讨论记录》(1942年12月27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 文献部分(中),第356页。特别是对伪政权和伪军头目而言,粮食既可供给部队,又投机倒卖,换取其他物资。欲谋求地方武装的长期发展,伪军头目必须在伪政权面前“吃得开”,遂有必要干预甚至控制地方行政,并联合地方士绅及伪政权控制当地的财粮资源。只有兵粮充足的伪军才具有与日军当局、伪政权甚至国共交涉周旋的筹码。换言之,随着规模扩大,伪军头目为了供养部队,势必将权威由军事层面延伸至地方伪政治和经济机构中。豫东治安恶劣,不掌握武装就无话语权,这使伪军头目往往成为地方仅次于日军头目的实权人物。日军当局“以华制华”策略下培育出来的伪军,反过来控制地方、压迫伪政权,造成军事、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溢散。
日军当局面对物资短缺、物价上涨等问题,于1942年在华北确立“决战体制”,贯彻以战养战、现地自活方针,加强对当地人力物力的控制。此时,豫东握有实权的伪军便成为伪政权征发农产品以供给城市时难以逾越的障碍。

1943年度豫东伪地方武装征发粮食数量表
①辖下部队包括伪暂编第一军及伪剿共第一路军。
②孙良诚部伪第二方面军主要驻冀鲁豫边、豫北地区,投放于归德地区的兵力相当有限仅五百余人。孙部向日军开封特务机关,而非归德特务机关负责,此或可解释为何归德特务机关之表格中列出伪第二方面军却未列出其获准征粮之数字。此数字为日军归德特务机关准许当地伪军征粮之总数字,扣除其他已知部队征粮数所得之数字。参「河南省と田赋实征实施の诸条件调查觉书———实验县宁陵县に于ける实验の性格とその一般化の可能性の问题」(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21页,Ref.HJ4406.Z9H6651944,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亚洲阅读室(LibraryofCongressAsianDivision)藏。
③番号为剿共第一路军,然实则仍由伪暂编第一军管辖。
④包括伪苏豫边区司令部、伪暂编第一军及伪剿共第一路军。
资料来源:『河南省と田賦實徵實施の諸條件調查覺書——實驗縣寧陵縣に於ける實驗の性格とその一般化の可能性の問題』(華北総綜合調査研究所)、22頁,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亚洲阅读室(Asian Reading Room, Asian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藏。
由上表可见,驻河南的地方武装规模庞大,粮秣征发量极多。部分土匪、流氓武装更以抢掠维持生存。[注]「昭和13年陸支密大日記第25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120407100。据商丘日军特务机关的推算,1943年度豫东伪军获准于防区内摊派的粮食逾3400万市斤,即1.7万吨。另据开封日军特务机关1943年初统计,河南省内获伪省署补给的正规伪军逾10万人。[注]「河南省と田賦實徵實施の諸條件調查覺書——實驗縣寧陵縣に於ける實驗の性格とその一般化の可能性の問題」(華北総綜合調査研究所)、21頁,Ref. HJ4406.Z9 H665 1944,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亚洲阅读室 (Library of Congress Asian Division) 藏。若每个士兵每月消费粮食30斤,河南省内伪军每年最少消耗粮食3.8万吨。[注]「河南省に於ける小麦·雑穀の蒐荷に就て」(華北総合調査研究所食糧調査委員会)、PRIMAFF(農林水産政策研究所)、Ref. 01500000144020、国立国会図書館支部農林水産省図書館農業総合研究所分館蔵。对照日军开封及归德特务机关推算的数字,可大概察知日军准许豫东伪军于防区征收之数量,应接近或稍低于日军心目中的最低需求。然事实上,仅豫东一带1943年已驻有张岚峰的伪暂编第一军、孙良诚的伪第二方面军及伪开封绥靖总署、庞炳勋的伪暂编第二十四集团军等。日军允准伪军征购摊派的粮食数量,严重低估上述伪军的需求和野心。在无从监管的情况下,伪军征购、摊派粮食的实际数量,已远超日军当局、伪政权之限制。1943年度,豫东一带之伪军已在当地征发粮食近万吨,更有说法称,伪军仅在归德地区即征购粮食近2万吨。[注]「河南省に於ける小麦·雑穀の蒐荷に就て」(華北総合調査研究所食糧調査委員会)、PRIMAFF(農林水産政策研究所)、Ref. 01500000144020、国立国会図書館支部農林水産省図書館農業総合研究所分館蔵。伪军规模扩张,伪府苛征滥索,沦陷区农民面对双重盘剥,负担日益沉重,生计更难维持,逃荒卖田者有之,当兵吃粮者有之。“文”“武”竞食,将沦陷区农村经济推向生死边缘,农村状况也就愈加不可收拾。
以商丘县为例。1942年河南大旱,粮食产量大减,黄泛区已至“春树叶草根吃食殆尽”,“不惟无吃食之麦,且大多数无下种之麦”的境地。惟在此歉岁之后,伪县公署除向农民每亩征收2斤小麦外,又为周边多支伪军征发粮食。[注]《河南商丘县民众侯和卿等陈诉生产二麦不堪摊缴请负量减代电》(1943年10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25页。另一方面,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服务的采运社、合作社系统,亦在当地派购小麦7500吨。由于伪政权及伪军的滥征,农民卖畜籴缴者有之,弃耕逃荒者亦有之。[注]《河南商丘县民众侯和卿等陈诉生产二麦不堪摊缴请负量减代电》(1943年10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第824—826页。
在太康县,日军、伪军、国民党军等纷纷到农村摊派粮食,摊派量达每亩30—40斤,占粮食亩产量的三到四成,造成大户抗税、贫农逃荒。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4年,豫东某县每亩征收田赋0.3元,而1942年则增加到1.5元。伪太康县公署任意开征临时杂税,规定农民需以极贱价格向日军、伪军提供大麦、高粱、黄豆等,还要求农家向警察、新民会先锋队、和平救国军等大小名目的武装缴纳各种税款和实物。[注]「緊急食糧対策調査報告書帰徳地区」(華北総合調査研究所緊急食糧対策調査委員会)、PRIMAFF(農林水産政策研究所)、Ref. 01500000542900、国立国会図書館支部農林水産省図書館農業総合研究所分館蔵。
豫东伪军在地方的权威凌驾于伪政权之上。1943年“新民会”召开全体联合协议会,在会上,河南省代表王伯雨指出,当地驻军粮秣非由伪府筹措,多直接向民间征发,加之协助伪军征发军需的经纪人从中敲诈渔利,大批民众不堪摊派,苦而离乡。王请求伪政府制定粮秣统筹供给办法,望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能从丰收地区采购粮食,供给河南的伪军。[注]《全体联合协议会会议录》,“中华民国新民会”,1944年,第148—149页。这一意见反映出王认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在伪军粮食问题上并未尽力,造成河南伪军习于防区“自行筹粮”的现象。且不论伪政权是否有动机和能力实现王的建议,伪军征粮只会多多益善,并不一定因外来供给增加而有所收敛。一些较强势的伪军头目禁止粮食输往县域之外。如张岚峰曾经在太康、柘城等地禁止获伪政权授权之商社、粮商收购粮食。[注]「華北各地区食糧収買事情地区委員会幹事長会議報告要旨」(華北総合調査研究所緊急食糧対策調査委員会)、PRIMAFF(農林水産政策研究所)、Ref. 01500000543049、国立国会図書館支部農林水産省図書館農業総合研究所分館蔵。由此可见,伪军亦是伪政权建立地方行政权力、贯彻地方粮政的一大障碍。
伪政权软弱的文官体系,曾试图利用法规制约地方武装的滥征摊派,但成效不彰。1943年6月14日,驻河南日军特务机关制定食粮补给办法;开封陆军联络部也规定,辖区内武装的军粮应由伪省府公用管理委员会统筹,拟从各县农地中每年每亩额外征收粮食3斤,以补助军队之需。该办法覆盖了约7.8万伪军,每年拨给粮食2880万斤。在公用管理委员会中,张岚峰与日军特务机关长、伪县长磋商议决由伪军、伪政府、合作社三方以“5∶3∶2”的比例摊分在当地征购所得的粮食,[注]「河南省に於ける小麦?雑穀の蒐荷に就て」(華北総合調査研究所食糧調査委員会)、PRIMAFF(農林水産政策研究所)、Ref. 01500000144020、国立国会図書館支部農林水産省図書館農業総合研究所分館蔵。但在实际操作中,未获补给之武装固然继续肆意征粮,即使获补给的伪军部队,如伪第二方面军和伪第二十四集团军等也多无视该办法,仍强迫驻地伪县公署及“公用管理委员会”供粮。无可避免地,由于当地的地主、士绅多与伪军头目沆瀣一气,伪政权的行政机关难以有力约束伪军于当地的活动。更有伪军以武力为后盾无视伪政权的基层组织,直接强迫防区内的农民供粮,征发数量远超办法规定及实际所需。[注]「河南省と田賦實徵實施の諸條件調查覺書——實驗縣寧陵縣に於ける實驗の性格とその一般化の可能性の問題」(華北総合調査研究所)、23頁,Ref. HJ4406.Z9 H665 1944,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亚洲阅读室 (Library of Congress Asian Division) 藏。
伪军不能从伪政权处获得足够的给养,于是多将粮财负担转嫁于当地农民。可以说,伪军及其他地方武装间接挤压了伪政府的税源,伪政府税入低落,在地方可发挥的影响力亦受限。伪政权的弱势,无形中又助长了伪军势力向政治、经济等各层面扩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北沦陷区的粮食愈加依赖陇海铁路沿线地区。有鉴于此,日军当局动员伪政权、商社、粮商、合作社,决意要从当地征购更多粮食,以求华北的自给自足。但在豫东地区,伪军在地方的主导性地位,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发布的一切粮政指令,在当地都难以完全贯彻。一方面是掌握武装、积威难犯的伪军头目,另一方面是无武力支持,且不一定熟识本地状况的商社、合作社、伪官员等,两者“竞食”,前者即使不占有压倒性优势,至少也占主导地位。
豫东的粮食问题,反映出日军当局实施的“以华制华”策略实际上可能有损伪政权的利益,客观上反而有助于伪军割据地盘,掌控地方实权及产出。
在豫东地区,张岚峰等就是这一策略的最大受益者。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张岚峰只是一个不得志的西北军旧人,但在河南沦陷后,张率部投伪并获日军当局扶持,在陇海铁路沿线确立了自己的地盘,部队规模日益扩大。到1944年初,其伪第四方面军下辖第一军、第八军及涡南挺进军,建制达9个师,实际兵力约6万。在此情形下,张岚峰盘踞豫东、皖北12个县,在华北、华中多支伪军中,其部队战力与地盘均属首屈一指,[注]参见杞县地方史志办公室编《杞县人物大典》,2014年,第706页; 中共商丘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张岚峰其人》,第8、 17页; 王翔九《我所知道的张岚峰》,毛德富主编《百年记忆河南文史资料大系》军事卷卷1,第396—406页; 《汪伪军事组织和伪军的变迁》,邢汉三《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河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205、283—288页。迅速跃身为掌控豫东、皖北的实权人物,并握有各县伪官员人事权,与地方士绅、大户结成恩庇关系,凌驾于地方伪政权之上。[注]中共商丘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张岚峰其人》,第57页。
张岚峰为了保证部队给养及社会秩序,涉足地方政治。地方士绅、商人、大户托庇于张,张也利用这些地方势力来达到巩固、经营、掠夺地盘的目的。豫皖苏和鲁西南地区的地主、名流纷纷附于张名下。事实上张的实力与地位使其与豫东各县的士绅、地主形成利益共同体。由此,张利用武装和地方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豫东、皖北沦陷区乡村秩序及农产品。举例言之,张岚峰的家乡柘城县,沦陷时期有近八成的土地落入伪军头目的手上,前述掌握地方供粮事务的“公用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也多由参加伪军或与伪军勾结的地方士绅担任,军事地位与经济利益的结合,使伪政权的政令难以落实,日军的调查员以“行政力渗透之癌”来形容这种形象。[注]「河南省と田賦實徵實施の諸條件調查覺書——實驗縣寧陵縣に於ける實驗の性格とその一般化の可能性の問題」(華北総合調査研究所)、23頁,Ref. HJ4406.Z9 H665 1944,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亚洲阅读室 (Library of Congress Asian Division) 藏。
张联同地方士绅控制地方行政机关,不仅有助于集中农产品供给部队,也为他参与黄泛区的走私活动提供了必需的资本和商品。张利用自身的特殊地位及所部在豫皖边的势力,在走私活动中的多个环节牟取暴利,这些利润又成为整军扩军、上下打点的主要财源。在张实力壮大的过程中,地方士绅、商人或主动或被动成了张的协力者。[注]《伪军张岚峰部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阶级基础》,中共商丘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党史资料》第3期,第40—41页;中共商丘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张岚峰其人》,第56—61页。在动荡不安的战乱时期,军事、政治、经济的关系密不可分,伪军头目为了养活部队,很自然地以筹饷、摊派等名义与地方士绅勾结起来,染指地方财权及至伪政权。张与地方精英,包括商人、地主、士绅等结成的恩庇关系,使伪政权落实粮食的“行政收购”、动员粮商及合作社以搜刮地方粮食变得困难起来。由于伪政权在地方的粮政机关及人员,实际仍需依托地方精英,但在伪军已然坐大的情况下,伪政权的粮政机关不但难以消除伪军的影响,反而更容易被伪军控制或被边缘化。
伪军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为日军、伪政权和地方精英提供“治安维持”的武装集团。伪军在资源及利益分配上虽与伪政权、地方精英存在龃龉,但在最根本的安全问题上仍能勉强共存。毕竟日军当局与伪政权需要伪军担当警备任务并维持乡村秩序。地方士绅、商人、地主等也需要强人保障身家性命及社会秩序。在此前提下,只要不涉及抗日,伪军头目在地方政治生态中实际享有近乎压倒性的话语权。在朝不保夕的年代,伪军头目若能维持地方治安,其巩固地盘、攫取地方资源的“越界”行为,或引起当地伪官员、地方精英和一般民众的不满,但在枪杆子的压力下,更多的文官和商人倾向容忍与合作,而非抗衡。特别是抗战后期,日军兵力进一步减少,对伪军的倚赖日深,在此情形下,伪军在地盘内征发粮食,或超越民众负担及成文法规,但在日军主事者眼中,至少也是难以苛责的行为。
日军的放任态度,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伪军将影响力从军事政治扩张至社会经济层面的趋势。应当说,伪军头目若能有效控制地盘、榨取更多资源以维持部队的需求和实力持续扩张,反而更有助于巩固该部在日军眼中地位及在当地的影响力。伪军大肆征粮,既是内部大小群体求存求利的结果,也是当时畸型政治生态下产生的独特的生存策略。另一方面,部分伪军头目也与抗日力量保持联系,为后者提供有限的物资、情报和交通便利等。[注]如张岚峰于1942年前后与第一战区汤恩伯、何柱国、蒋鼎文等合作贩运走私业务,又与界首方面官员、戴笠等保持联系,1944年9月,张更接受蒋介石任命其为地下军第三路军总司令的委任状,参见中共商丘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张岚峰其人》,第9页。在军事层面,伪军头目固然是日军当局及伪政权驱使的爪牙,但在地方行政方面,伪军截留地方资源,不啻为伪政权的竞争对手。
结 语
伪政权单凭政令和软弱的文职机构,难以与当地武装竞争地方粮财资源。伪政权所能掌握的税源愈少,反过来愈削弱行政系统的作用。在此恶性循环之下,伪军反客为主,成为控制地方行政的实力派,而伪政权的文治机关则成为仰其鼻息的辅助工具。伪军的勃兴,相当程度上是日军控制点线的结果。然而当日军愈加倚赖伪军控制乡村,伪军即在日军当局的放任下坐大,伪政权反被边缘化,其他征粮机构也难以顺遂活动。伪军的粮食掠夺反映出其在地方的强势地位已逐渐压迫到伪政权在当地的活动空间。在沦陷区畸形的军政格局中,日军及伪政权既然无法为伪军提供足够的后勤给养,遂难以在资源层面制约伪军割据地盘,自筹粮饷似乎也变得无可厚非。从伪军的角度而论,搜刮愈烈、自身资源愈充足,愈能在豫东三角斗争地带保持并增强其政治、军事地位,对地方政治和经济资源的控制也愈形深入。
匪过如梳,兵过如篦,豫东伪军寄生于当地落后的乡村经济之上,农民既要供给伪政权需要,又要满足伪军的征发,加上天灾频乃,已超出农民的承受能力。农民倾家荡产、弃田离村,破坏了农村经济的基础。[注]《河南地区》,《华北食粮需给状况调查报告书》,“华北合作事业总会”,1943年,第2页。日军当局“以华制华”的军事分权与“以战养战”的经济集权两种治理华北的策略存有潜在的矛盾。伪军在地方割据地盘,轻易将军权转化为地方行政权,使豫东伪政权及其代理人受到压制。豫东沦陷区的政治乱象,从另一角度证明日军或能凭忖军事优势一时“马上得天下”,却在地方治理方面难以摆脱“不可马上治之”的困境。
- 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其它文章
- 东京审判对南京暴行的审理模式与历史记忆*
- 叙事话语与大屠杀记忆:以美国、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