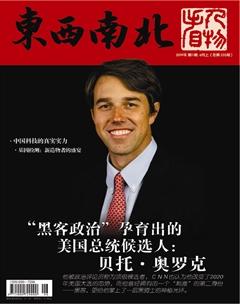“鬼后”罗兰:在戏里面,我只是芫荽葱
张明萌

2005年,为了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香港电影界举行了一次全民选举,罗兰赢得了“最佳绿叶奖”,这个奖项更像她一生的写照。
罗兰,香港女演员。1950年涉足影视圈以来,她参演了400余部影视剧,长期担任“绿叶”,是香港极具代表性的甘草演员。
在作品中,罗兰的演绎呈现出明显的两极——穷凶极恶的女反派,善良慈祥的老婆婆。前者几乎贯穿了她整个演艺生涯,后者则在演艺生涯后期颠覆了她的惯常形象。
1960年,她遇到生命中的贵人——岭光影业公司创建人黄卓汉,与她签订演员合约。其时公司有花旦丁莹,主演正面角色。黄卓汉称罗兰“眼大大、鼻高高”,有成为大反派的潜质。还送她一个艺名“罗兰”,罗兰由此开启了她的演艺生涯主轴。
在这条主轴上,以裘千尺为代表的武侠电视剧角色、以龙婆为代表的香港恐怖片角色成为她的经典形象。上世纪90年代,香港恐怖片风行一时,钱升玮导演几乎以每年一部的速度摄制了《七月十四》《正月十五之一生一世》《七月十三之龙婆》等惊悚鬼片,以鬼怪事件为框架,延伸出爱情、友情和家庭情感。罗兰在这个系列中扮演“龙婆”(能预知和联络鬼魂的妇人),依靠摄影技巧和打光与特效,每每镜头打到她脸上,总会有极佳的视觉效果。凭借“龙婆”,她获得了两次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提名。90年代中期,导演邱礼涛拍摄《阴阳路》系列,罗兰前后出演16次,扮演性格不同、故事各异的女鬼。经过这波潮流,罗兰与捉鬼道长林正英一同成为香港鬼片的代表人物。在最近参演的影片中,她被冠上“鬼后”的称号。
1999年,叶伟信导演的警匪片《爆裂刑警》上映,罗兰饰演轻微老年痴呆的四婆,错认两位闯入自己家的刑警(古天乐和吴镇宇饰演)为多年不见的孙子,发生一系列故事。四婆成为警匪之间的纽带,情况危急时,她的出现能够淡化紧张氛围,让这部戏多了温情。此前罗兰也有过类似角色的演绎,但这部电影让她凭借配角的戏份连获香港电影评论学会最佳女主角、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成为她职业生涯中的高光时刻。
至此,罗兰的演技获得了奖项上的认可。那年她已66岁,至今仍是香港电影金像奖历史上最年长的获奖者。奖项来得似乎有点晚,且阴差阳错,演了一辈子配角的罗兰在香港电影金像奖上唯一的斩获竟然是最佳女主角。但领奖时,全场雷动的掌声昭示着她在奖项以外的声誉与名望。

70岁那年,罗兰宣布不再和TVB续约,无线赠给了她“敬业不懈”的荣休金牌,称她“嫁给了TVB”。沒过多久,罗兰又开始出现在大小荧幕上,因为“医生说,不演戏大脑机能就会退化。而且我喜欢这个工作。”
2005年,为了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香港电影界举行了一次全民选举,罗兰赢得了“最佳绿叶奖”,这个奖项更像她一生的写照。
在被数次问到“想不想演主角”的问题时,罗兰的回答从来是:“我不是一个明星,我是一个演员,演员就是要演好自己的角色。做主角?我想都没想过。做什么主角呢?主角不也是这样演。在戏里面,我只是芫荽葱,可有可无。蒸条鱼,加芫荽也可以,加葱也可以,不加也可以。加了会好吃点咯。”
(以下为罗兰口述)
本来可以读大学的
我本名卢燕英,1934年生于香港,是有印尼血统的华人。爸爸本来是律师,后来开始做生意,生产镜牌砂肥皂和地蜡,卖给香港四大酒店。日子富足,吃喝不愁。不多久,日军攻打香港,我家什么都没了,迅速和香港大多数人家一样陷入赤贫。
饿殍遍野是我童年最深的记忆。日本人来了,大家都把泥涂到脸上,弄脏自己。我不知怎么回事,问妈妈,妈妈只灌我水。但因为紧张害怕,连我鼻子嘴巴都分不清。城里没粮食,人们都吃木薯粉,吃了十多天得了疟疾,有的死在路上,两个人推着四四方方的木头车,见到死尸就扔上去。有的死在租屋里,房东怕弄脏,就扔到隔壁。晚上睡觉,妈妈说听到有人叫救命,叫了几声就没了。第二天听人家讲,隔壁有人死了,大腿肉都被割掉了。他们已经死了,本来也瘦,腿没多少肉,还被割掉了。舅舅去饮茶,在包子里还吃到过人的指甲。
战争开始了,我们才发现,原来爸爸在外面还有一个女人,他在那里染上了烟瘾。打仗了抽不了,戒烟戒出病。我每天按妈妈吩咐拿着金银首饰去当铺,换钱抓药,最后还是没有救成。战争第一年,我外婆去世了,第二年,爸爸去世了。
失去家中的经济支柱后,我要打工接济家用。一次,我跟几个同学去看人拍戏,一个剧务对我说,“我们缺一个婢女,看你挺适合,梳两条辫子来拍吧。”“我不会拍戏啊。”“导演会教你的。”“我害怕哦。”“唔怕。”导演说,“那个人对你说,‘叫小姐出来,你说‘哦,就可以走了。”我照做,给了我10块钱。一句“哦”而已啊,10块钱。
过了三四天,剧务找上门来,让我接着拍下一场戏,继续演婢女。我妈妈知道我在拍戏,很生气,说你做什么不好去做戏?那时候娱乐界给人印象非常差,一句俗话是“成人不成戏,成戏不成人”,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人才去做戏。剧务求我妈,说不让我去他会丢掉工作。我妈最后勉强答应,说她要跟着一起去。从那时候开始,我拍戏妈妈都会跟着一起。
有人说,世道艰难,女孩就卖了吧,卖给别人或许是放她一条生路。妈妈说,我不卖,要死一起死。妈妈98岁过世,我难过,神父跟我说,你想怎样?她一个人活了两辈子了。平时我们一起上圣堂,后来我自己去,都是哭着回家的。她走了二十多年了,不过这么多年还是舍不得。她过世我才拿影后,小小遗憾。我信她还在,殡仪馆的照片我一直放在家里,早晚会对着她念经或者讲话,出门也会说,妈我出门了。我这辈子只有这一个妈妈,她照顾我很辛苦。我小时候多病,占了她很多时间,怎么都弥补不了。在她的墓碑我也写了:我永远爱你。
其实做这行,学好学坏都在自己。我记得在化妆间看到谢泽源的徒弟,他说小姑娘不要怕,收工了不要去喝早茶,不要跟人兜风。喝茶,人家放东西在你杯子里,你喝了就跟他走了。兜风,带你去新界,去很远的地方,“咸湿”你啊——我们那时候都不说强奸,说咸湿——你想反抗,怎么办?天不应地不灵。我说,是,真的不可以,这两件事千万不要做。
有段时间,我去拍《黄飞鸿》,按理说有几百块,但没有支薪。有一天导演叫我去他家收钱,门张了个缝,递出60元,马上就把门关上了。我当时收下60元,很难过。我不是贼啊,这是我应得的,你怎么这样呢?我心里很难受,哭了。哭的时候我就恨日本人,因为你打中国,害得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日本人打了三年零八个月,三年零八个月啊。如果不是他们,我爸爸说,我可以读大学的。
我是一个演员
最开始我一直在做特约演员,1960年和丁莹拍完《电梯情杀案》,黄卓汉请我去写字楼。说你眼大大、鼻高高,当家花旦有个丁莹,我们要培养你做反派。我签了约,当时就有第六感:我签了这个约,电影就是我的终身职业。
十多天以后,黄老板说,“卢燕英不是演员的名字,给你想了个名字叫罗兰。上海有很多名媛都喜欢叫什么兰,有一个就叫罗兰。岳峰导演的老婆也叫罗兰,这位前辈戏很好,你像她一成都不得了了。”
因为一开始就讲好做反派,很长时间我的角色都是类似的:丁莹一定是最凄凉的那个。她会有个公子哥喜欢并结婚,我就演她丈夫的表妹,在我姨妈面前,讲她有多不好,她孩子有多不好。徐小明那时候常演丁莹的儿子,我很多戏都要打他。他被我从小打到大。
有一次我走到维多利影院门口,一个女士见到我,说一句很难听的话,她说“死鬼婆”。我低下头默默走,心想别再望她,别再望她。我亲戚跟我讲,他朋友说罗兰好凶啊。不凶怎么做反派?我觉得他们很固执,奸的就是奸的,忠的就是忠的。
我不明白,我真的从不介意,我觉得我不是明星,我是一个演员,演员是演活戏里的角色,演活剧本里的角色。有一年,我演裘千尺,那个角色很恐怖。剧本有一句对白,是凄厉的笑声。我想凄是凄怨,厉是厉鬼,怎么做啊?我对着镜子一直笑,笑到我觉得可以了。化妆的时候,有个女孩子跟我说,罗兰姐,我不敢看你啊,好怕。我说行行行,除了去洗手间,我都不动。你不用怕啊。

播出的时候,演到裘千尺脑袋磕出了血,流到脸上,她又没有几根头发,牙齿也是黑的,18年没见阳光,面色铁青,手脚筋都被挑断,样子特别可怕。我妈妈骂我,TVB没人啦?这样的角色你也演,这么丑。我说没有啊,我想试试我做不做得到,能不能做出那种味道。我很开心,今时今日,都有人记得。可能因为太难看了。
裘千尺的绝活是棗核钉,我当时去买了好多西梅,吃完试着吐。我力气小,吐不了多远就会掉下来。拍的时候武术指导就在旁边,我一吐,他用力弹出去。最后也像模像样。
后来重拍《神雕侠侣》,古天乐和李若彤主演,也是我去演裘千尺。每隔一段时间,有人撞见我,都说,哇,你那个角色好厉害啊,我们害怕到现在。他们一讲话,就说“哎,那个吐枣核那个啊”,不记得戏名,也不记得角色名。
再往后就是龙婆了。上世纪90年代,我离开TVB,拍了《七月十四》。那套戏观众喜欢得不得了。他们都去看午夜场,吓到整个人从座位上跳起来。他们喜欢惊悚,不去看不行,又喜欢,又害怕,又要去看。几天前,我看到一个观众,看着我,要和我拍照。拍完照之后跟我说,你真是好吓人啊。
其实龙婆就是一个鬼怪上了阿婆的身,她就变成了那个鬼怪。为什么有人说我演得像呢?我十几岁和妈妈一起去找过问米婆。刚刚和平后,妈妈想念外婆,就去找问米婆通灵。问米婆拍着桌子眯着眼,上来就叫“家嫂”(粤语,儿媳妇)。妈妈说,不是啊,我找我妈妈啊,怎么叫我家嫂。我亲眼看到问米婆睁大眼睛说,啊,带错了,重新来。我妈当时泣不成声,但出门了说,刚才都是假的。我想那你还去问,还哭得那么伤心。那里真的有神位,木房子,阴阴沉沉。我也想到陈立品前辈,借鉴她的表演方式。但其实这类角色的成功还是工作人员集体的功劳。角色的惊吓不是我演员演出来的,是我站在那里,灯光师找个光管摆在我脚下,垫块玻璃纸,拿黄色的光打上来,我的脸就白了。换青色的,打上来我的脸就青了。这些完全是幕后的工作,不是我自己的成功。我表演的那些,不是很深入的,都很皮毛。
后来我拍电影,无意中拍《爆裂刑警》,无意中拿了影后。我去老人院见过一些老人家的动作,和他们的言行举止,有些老人喜欢坐着就搓搓膝盖,我就加到表演里。掌掴古天乐,我很忐忑,我怕打到眼睛,但是你不用力又不像,轻轻地NG几次不是更辛苦。所以我就找到位,到时候就一巴掌下去。当时也很不好意思。我拍完《爆裂刑警》,就叫我去参加金像奖。谁知道呢,这个阿婆拿到金像奖,做了影后。
对我来说,拿不拿奖真的无所谓。
嫁给TVB
1971年我进入TVB,做EYT(enjoy yourself tonight,欢乐今宵,TVB上世纪70年代一档综艺节目),我在里面扮演接线员。有次去航工展会,广播说“咩咩小姐,有个仔等你”。她有点伤风,声音有些沉。我觉得这样说话也不错,在节目里就拿起电话说,“有咩事你快点讲。”初期有接线员打电话投诉,说破坏职业形象。导演跟我说,罗兰姐,如果因为投诉就停掉,我们好多节目都不用做了。后来这个角色很受欢迎。
之后拍《武林圣火令》,给你四句话让你自己创作。类似“百物腾贵无尽头,贫苦大众日日愁,伤残拿药都等人救,请你伸出同情手”。挥旗子,讲“阿善开报馆,善有善报”。每一期都很需要创意。有次要吊威亚,扯我上去,我掉下来,有人扶起我,我还能走动。我说了一句“不要告诉我妈”就不省人事了。医生问我怎么跌倒的?我说不知道。他们说大脑受震荡就会这样。我住了十多天院,还好神经中枢没事。以后看到威亚就害怕,公司也再不让我上威亚了。
那时候拍戏,我们没人教的,不像后来有艺员训练班。导演让我们拍戏的时候都在旁边看,看前辈怎么演戏,再想自己怎么演。拍重要的戏我都要看三遍,每看一次找一次我做得不足的地方,静下来,慢慢看。其他时间,不开工就是看剧本。
现场也有很多可以学。拍岭光的戏,导演让我试一个开房门的戏给他看,我试了几次,他说你屁股很美吗?对着摄影机干嘛。我就学到了,原来开门要侧身,出门要正着出去顺便拉到门,这样摄影机才能看到你。演戏这门功夫啊,我到现在也还在学。
当时看楚原导演,他拍戏很快,记忆力很好,一会儿一百零几场,一会二百零几场,都记在脑子里,随拍随来。去年一个贺岁片,王祖蓝导演的,他也很厉害,记忆力很好。萧芳芳比我小,她有一米七多高,很靓很洋气。我们拍了黑白粤语片,后來又拍彩色片。后来我演《神雕侠侣》,跟刘德华和陈玉莲拍,他们很辛苦。拍《鹿鼎记》时,梁朝伟也很辛苦。都是真的摔下去的。
他们都是热爱这个行业。我觉得戏里面有主角,有配角,还有再闲一点的闲角,是群体生活、群体工作。一个餐厅的戏,不是只有男女主角就能演完啊,都要有点临时演员,也要有点配角,整餐(做饭)啊,捧餐(端饭)来啊,说一些话啊。每一个角色都重要。幕后,没有化妆、没有梳头,不行;没有灯光,不行;没有摄影师,不行;导演,没有助导,不行;没有场记,惨了,就全乱套了。没有任何一个都不行,全部是群体合作的。
我至今没有结婚。对男女关系有很大的恐惧,为什么男士总爱讲大话?我们以前拍戏,不是现在有尼龙椅那么舒服的,是一个马扎。我坐那儿,很累但没睡着,听到有几个男士在旁边聊天,说什么呢,昨晚我去东方夜总会,那个女的啊,好正。另一个又说怎么怎么。我想这些都是有家室的人,竟然这样,好恐怖啊。又一次我晚上12点多收工,男主角在旁边打电话,跟老婆说,今晚不用等我了,我会拍到天亮,你先睡觉。我想明明收工了,为什么要说拍到天亮。你说是不是可怕,会没有信心?我拍拖的时候,我check他,差不多二十多年前,11点半打过去,他妈妈说他(在家)不回(电话)了。第二天我问他,你去哪儿了,人家讲什么我都不信。没多久就分手了。之后恋爱都不成功。疑心大,醋意浓。
退休的时候,公司说我嫁给了TVB。有工开,我们才会开心。一回去,就是一大班人,是熟悉的群体生活。如果你热爱那样东西呢,你就不会觉得辛苦。如果你不热爱那样东西呢,你就会觉得辛苦。但是我也没办法啦,我恋上了它,爱上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