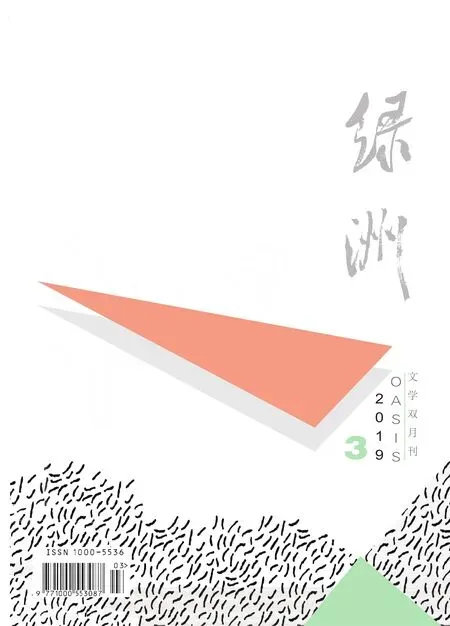看见生活(组诗)
春无眠
少年的我 青年的我
以及渐渐成形的
中年的我
爱着生活的困顿
它用盲人的深瞳虚构我 就像虚构一场
来自身体内部的喧嚣
虚构的乌鸦在高飞
寂静在下坠
黑夜在建立自身发光的宫殿
而这座被虚构的宫殿
多像肉体又一次塌陷和消解
它何尝不是人世间又一个隐喻呢
夜晚多么空旷
夜晚多么空旷
像一封打开很久的信
当风收紧了榆树的外衣
也收走了雨水中刚刚绽开的绿意
在这平常的一天 这个夜晚
一切都像是刚刚好
但是 平常的夜晚过于昂贵
笑声中的悲哀和茫然不会漏出这个夜晚
不会漏出女主人的叹息,厨房的油烟
邻居们的争吵
以及受苦人松开的愤怒
不会漏出稿纸静静的水底
那鱼群般推动着永不止息的波浪
——因为 在所有这些平常的夜晚
我早已将一座石头山
安置在了沉沉笔尖
那未知的——
一定有什么
我还没有忘记——
所有蓬勃和衰败的生活都被我经历过了
这是否意味着
厄运可以再次轻松跨越?
我深知那弧度中的力量
直白 尖锐
一个失去荣耀的人
肉体紧绷到黎明
像在寒风中哈气
我忍住逆行中奔跑的速度
就像忍住胸腔中一阵小小的微澜
——现在 它携带着一整座城池的冰
要将我弹向一片未知的水域
又一天
又一天了
世界搬动自己的黑暗
慢慢推开晨曦 就像推开一个稀疏的节日
一枚集体主义者的太阳高悬
使前一个崭新的我已过去
而后一个我还没到来
就已老旧
我羁绊于光芒的涌动
不配再拥有孤独者的力量
——可是 融入在我这里
始终是一个棘手的哲学问题
有如秩序的两面
有着暗夜的空洞与节拍
它谦恭、缄默 但没有一丝退缩
当冬天最后一场雪被制止
有人在世外听风
有人在梦中开悟
献出——
我从不向八月献出夜晚
就像苔藓献出涡纹
蜜蜂献出它的毒针
连同整个夏天的白日梦
我不向坟墓献出阴影
这些坟墓 曾是许多影子的言辞
声音布满法术
现在 它们全都化为它的儿女
我不向衰老的灵魂献出暮色
当时光吹到膝下
增加词语的黑暗
要允许它离开幽暗的长廊
我也不向天空献出鸟
不献出蜜蜂与花朵的葬礼
不献出黑色泥泞 让它从脚趾缝朝着悲哀打开
甚至 不以我更黑的肋骨
向拾荒人献出分币
可是 若我全都献出
我又改变什么
最后 我没能献出的是身上的荣誉衣衫
它有四个角落
正在褴褛的胸口上与我形影相依
洪荒之花——献给丝绸之路南道上的瑞典女士布丽吉塔
为什么她这样安静
她睡着了 睡得像死去一样
当月亮变小 小得像她的阴影
我摸她的皮肤只感到冰凉
是什么东西在她体内沉睡
当她在黑暗中坐起
像孩子一样大叫
当植物的躯体进入她的体内变成了黑色的血
像潮水一样冲涮她的全身
——如果我们承认黑暗
那么就允许她永远处于黑暗之中
这是我遇到的一个女人
布丽吉塔
她的身体是一个要塞 是一个老战士
她让我知道了还有许许多多同样的女人
我们一起跳舞、嬉戏、蛊惑男人
不再四处躲藏
向他们展示身上被称为魔鬼的部分
但他们仅仅改变的
只是我们躯体上面的一块土地
布丽吉塔 你说我们身上还有奥妙的生命
——这是我们的天性
看得见又看不见
直到那些男人们忍受着第二次死亡
讲述
请听我讲讲
这个在纸上长大的人
从未诞生
却怎样成了一个锋利的孩子
请听我讲讲这个低廉、傲慢的生活
我靠近它 像靠近一张纸
靠近一种新的含义
我不想说得太多
比如 要学会用一种气味洞悉生活
要学会剪裁火苗
不喂养阴影和孤独的腥气
允许它离开幽暗的长廊
要参与行乞者的哭泣
缺失使我更加完整 肉体紧绷到黎明
——可是 我讲述的这些
全部在人世间的低处
与一只逃亡的鸟的睡眠中
我不能提问 也无力回答
再给我一个下午的风
醒来时一定会像枝叶 高过自身
诗歌课
没有陋习的事物是不可信的
我写诗
是出于对无名的需要
当有一天 我终于洞悉了生活
给语言以阴影
像从善中提取恶
这暗处的力量再一次绷紧了它的弓弦
当奉献已尽
这无用的手艺
已不能与人世间的草芥和浮尘相融
而尘土
落向了最后一个头戴金冠的人
带着下沉的心——
我凋谢了 而你全都原谅
生日信札
她最脆弱的部分
肯定不是死
这个动词正蜕变为虚词
一些尖须卷曲着
躲避生活的利齿
倘若我告诉你
她的胸腔里怀着夏日母性的心肠
爱着我粗鄙命运的黑衫
和一个黑夜沾了水的灵魂
她是谁呢
像一些相爱者不在梦中
一个没有温度的形象被虚构
当她出现
是众多失语方式的一种
勿忘我
植物中唯一的
不完整
当一个迷途者遭遇了自己的声音
她说 不要忘记我
——不要忘记我
这怎么可能?
它只是一个字 一个事件的开头
一个构成貌似诗意音节的一部分
单独的花瓣只有一种颜色
有一次 我差点喊出了声
所幸的是 我正好
被迟迟到来的,谨慎的黎明
所吸收
卑微者之歌
有谁陷入生活的尘土 又从中抽身而出
每一次细微的移动
都记录了一次灰暗的退出
谁是那个躲在黑夜的屏障外聆听的人
请不要惊动我 不要离去
让我无休无止地
说出一个卑微者的梦想和困扰
让你像一个算命老者
用咒语检验我这第一个开口说话的人
请不要温暖我 不要离去
让我说出哑巴的拐杖、盲者的爱情
说出健康与病魔的输赢之分
说出弃儿的守护者
说出泥土、阳光和水
被一张初进城市的农妇的脸所吸收
她的瞳孔里写着害怕、孤独和绝望
还有 请不要离去
——送我致命的亲吻吧
需要在黑夜里撞击你的身体
再送我刺目的才华吧
需要在诗中撞击你的灵魂
只是——过于迅疾的愿望
在自身的虚幻中失掉了翅膀
就像过于耀眼的露珠
正被巨大的光芒所遮蔽
壁虎
你好 壁虎
当我厌倦了黑夜
常常从梦中坐起 我看见你
睁着年轻动物的眼睛
多梦的身子深陷于月亮
像黑宝石一样生就一双
寒冷的眼
你盯着我 用白天的呼吸和夜晚的寂寞
当午夜的梦游者
闪出阴郁的双肩
谁能料到
面容依稀的人会时时
把我伤害
黑暗中 我们彼此相互寻找
你不经意的一瞥使我
悄然改变
即使在睡眠中也保持着
无边的沉默
当偶然的躯体醒来
我和你一样
在黑暗中如何
白昼也同样干枯
蚂蚱
六月多么恶毒
暴露夏天的隐情和伤口
还有蚂蚱
这个被大地原野随意丢下的弃儿
它是深褐色的
脚下有一大片繁生的蕨类
在每一个星星
渐次醒来的夜晚
它悄然来到世人的屋檐下
从不间断
它不需要观看 不倾听
世人的窃窃私语
即便是面对一扇错误的窗子
也从不张望
一个偶然的躯体醒来
它跳跃,转身
丧失了时间和记忆 在行进中
还原了生活的本来面目
难道就这样结束对孤独的恐惧
蚂蚱 这个田野上无辜的弃儿
它的行踪破坏了整个北方的霜冻
使蕨叶在背面伸出舌头
无计可施
它曾在我的童年尾随过我
现在 又看着我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衰老
遇见
我有我自己的旅店
当我走在路上 遇见第二个人
那个迟来的围观者 是痛苦的
我曾经有过一个家庭 结实、辽远
每一天 顶端最轻微的沙粒轻轻滚下
露出棺木的光泽
我有我自己的形状和简洁的名称
曾在每一个黑夜里
顺从黑夜和黑夜里的人
我还需要什么 那多出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当流水改变着意义
当我像风帆一样飘走
当我把岸还给你的时候
未删节的
操劳 让写作变得昂贵
带来了词语的荒凉
最后 是宽恕
现在 一个全身晦暗的人屏住呼吸
就像一个失去荣誉的人
突然触到缺席者的抚摸
我知道 我只能聆听
不能提问 也不能回答问题
每一个字都是一条敞开的路
“如果诗歌不能赦免我们”——
他对自己低语道
“那我们就不要希求从任何别的地方获得怜悯”(引)
——引文见扬尼斯·里索斯《诗人的空间》
一瞥
一个垂暮的老人坐在光阴里
心怀各种杂念
它们太多了
以至于那些慢下来的词语
因道德的消失而干枯
而一个个完整的暮色
刚好将它们掩埋
一只猫跳上石阶
它的眼里有着对他,以及整个世界的睥睨
麻雀的志向
天空中没有道路——
走入鸟中,才知道飞翔的艰难
才知道表达的怯懦
还有灵魂的慌不择路
比如 当麻雀突然飞起

而天空在上升
云层铺开咒符
河流在翻身 鱼类在清洗伤口中的盐
道路由南向北,或由北向南
都是通途——
而麻雀在飞翔时
始终注视着云端上那个耸立的巨人
他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他是最大的虚空
当它仰望,他就消逝
当它接近,他就游移
当它描摹,他就抽空
天空永远在高处,在赞美的言辞里
但它信赖这个虚无的巨人
就像信赖它其实就在自己的身体里
就像信赖你
会带来另一世界的奇迹
一日
当这一天在锋利的落日中止息
没有一丝阴影
我看不清
它背后的种种可能
譬如人性的踌躇
和日复一日的古老,凶险
我甚至看不清
天地间悠远的古意中
一粒金色的沙
但是 新的一天也是所有万物的黎明
露水、草霜、山谷的皱褶
偶尔也会泄露马腹中的一声惊雷
新的一天
我在时间的密纹里悄悄哈气
感知肉体的谦恭
以及万物移动的温暖
写诗的我
我的笔 有着直立的影子
笔尖上的裂纹
来自生活中的一次敲击
在每一个深夜
我秘密地写诗
试图用词语去修补白天的荒诞
以及微凉中
对生和死的独享
坡行者
爱与死 是一个问题
但不是唯一的问题——
每天 我靠写作进食
用它来克服夜晚的肉欲
在那些可指责的章节中
不死 就是另一种沉默
去对抗集体,人群的恐惧
我仍活在步伐中
只有坡行者给了我更高的台阶
黄昏
在缩水的黄昏时刻
道路变脆
行人顺着垂暮的方向
碎纸一样疾驰
吸进城市的胸腔中
真的没发出一点儿声音
而家中电视机里的嘈杂如同广场
和尘土的技艺共同构成了喧嚷而卑微的距离
无人看见 一群黑亮的乌鸦滑过屋顶
它的轻盈 乃是万物变迁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