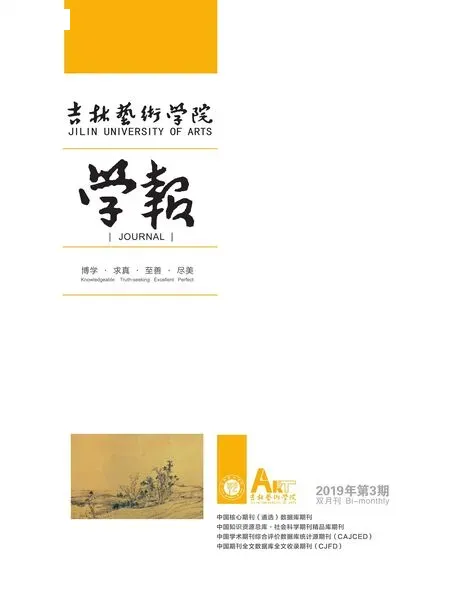用影像呈现中华文明进程中“他者”的身影
——评六集纪录片《中山国》
王庆福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200083)
一、悬念化叙事唤起对“他者”的好奇心
“他者”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概念,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凡外在于自我的存在,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可见还是不可见,可感知还是不可感知,都可以称为“他者”。[1]在中国的历史书写中,“中山国”就是以他者形象出现的。由于中山国是一个由鲜虞戎狄人建立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书籍中并没有大篇幅记载,即使是司马迁的《史记》在为各诸侯国做传时,也没有给予其一席之地。然而,在春秋战国的历史舞台上,“中山国”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无不像影子一样若隐若现地存在,这就为今天研究那段历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团。纪录片《中山国》在开篇所呈现的问题是:一次考古大发现震惊了世界,青铜器上刚劲秀丽的铭文,揭开一个被遗忘国度神秘的面纱,各种器物的造型风格显示它们与中原文化迥异,它们的主人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这一系列问题属于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在中山王厝墓考古现场所面对的问题,今天通过屏幕重新出现在观众面前。但影像表述不同于文字表述,影像的叙事必须服从于影像本身特有的逻辑。为此,纪录片采取了通过设计悬念,激发观众好奇心的叙事策略,这种悬念化叙事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1. 以传记式为切入视角
中山国历史二百年是春秋战国时期风云激荡的二百年,如何在这二百年中将中山国的荣辱与兴衰讲清,需要高度的智慧。《中山国》以中山国七位君主的人生历程作为叙事脉络,在这一脉络下,国家的关系成为不同国家君主之间的利益博弈,从而将枯燥的历史知识还原为具有丰富人性内容的生活故事,于情节的起伏跌宕中引发观众的好奇心。如在影片中,讲述中山伐燕的故事,其中伐燕的过程着墨不多,重点在司马赒伐燕归来、王厝命其监造青铜器铸造一事,以此呈现二人之间微妙的君臣关系;而讲述赵武灵王灭中山,叙事的关键则在赵武灵王与中山国君主恣㤵二人之间治国方式的对比,以此呈现中山国走向灭亡的必然结局。
2. 搬演式纪实与动画再现结合的叙事手段
历史题材纪录片所讲述的内容往往因为年代久远不容易在当代观众心中产生共鸣,如何拉近这类题材和观众的距离,纪实拍摄就成为纪录片创作者的不二选择。如纪录片《望长城》就属于此类拍法,但历史文化题材纪录片所面对的一个最大问题是直接拍摄到的纪实影像缺失,即在考古现场要受到挖掘时间的限制,而通过搬演的方式创造一个仿真的现场无疑是当今历史题材纪录片所采取的策略。纪录片《中山国》根据当事人的记忆,以搬演的方式创造了这样一个现场,并让这一现场成为影片讲故事的线索,从而设置悬念,引领观众进入历史的情景之中。在这部纪录片中,考古现场始终是一个若隐若现的线索,搭建作品整体的叙事结构,在呈现具体的历史情景中,如战争、百姓生活、宫廷乐舞以及灵寿古城建筑则采取戏剧式再现和动画再现相结合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为观众创造身临其境的现场感。
3. 专家团队解惑释疑
纪录片与故事片因为材质不同,造成功能不同,如果说故事片是一个梦工厂,那么,纪录片则是一面镜子,人们希望通过这面镜子,认识他人,获得未知。就《中山国》而言,这种解惑释疑的功能主要是通过专家团队完成的。中山国的专家团队近40人,从直接参与中山国出土文物挖掘的考古队工作人员,到河北本地研究中山国问题的学者,全国各地涉及中山国历史的相关学者,直至海外研究中国历史的著名学者无不涵盖。不同领域的学者分别从不同的层面讲述中山国的故事,参与当年文物考古的工作人员直接回忆文物出土的现场,将文物出土的情景直接呈现于观众的眼前,研究中山国历史的专家通过自己的理性分析,引领观众在宏大的历史中认识中山国的真实面目,海外学者则通过个人的经历,以他者的视角呈现中山文化的魅力,通过这种多重视角的专家解读,既满足了观众对“他者”的好奇心,又实现了纪录片的认知功能。

图1 《中山国》海报 2018

图2 《中山国》仿真现场拍摄

图3 中山国出土文物
二、宏观与微观互动讲述他者参与的“大历史”
大历史是由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应该采取以长时间、远距离、而尤以超越人生经验的着眼研究历史”[2]。在《小历史与大历史》一书中,学者赵世喻将“大历史”与“小历史”做一比较,他认为小历史指那些局部的历史,也是那些常态的历史:日常的、生活经历的历史,喜怒哀乐的历史,社会惯例的历史。……大历史,就是那些全局性的,比如改朝换代的历史、治乱兴衰的历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典章制度的历史等。[3]纪录片《中山国》所呈现的中华文明历史,正是这样一个由“他者”参与的大历史,但在正史中,关于中山国的记载一直是片段的、零碎的,如何将“他者”的形象清晰起来?从“大历史”的角度观照这部纪录片,发现其主要采用了宏观和微观两种视角,并通过两者的互动,实现了对这一时期中山国整体历史的故事化讲述。具体表现为如下方面:
1. 宏观视野观照下的“大历史”
大历史要求有宏观视野,在超长的时间段中去发现事件之间的联系。纪录片《中山国》第一集《发现》将中山国的起源、崛起、消亡置于其与中原各大国的矛盾背景下,由此将二百年的中山国历史变成一部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争霸史,中山国的历史由此成为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如在影片开端,讲述中山国的来源,就将其变迁包括前身猃狁、鲜虞的迁徙史一一呈现,从而回答了在当时中原王朝的腹地为什么存在一个由草原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国家的问题。再如第二集《崛起》中魏国攻打中山国一事,同样没有仅仅停留于攻打过程的简单描述,而是首先将魏文侯攻打中山的想法提出,并通过魏文侯的思考呈现中山这枚棋子在魏国称霸棋盘上的位置,其次解决借道问题,先是牵扯入魏国和赵国的关系,并通过魏将游说解决,最后才是大将乐羊进攻中山过程的详细叙述。通过这种前因后果关联,魏国攻中山这一历史事件就变成战国时代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历史由此摆脱了狭义的地方史的局限,具有了区域国别史的视野。
2. 微观细节呈现的“大历史”
大历史要求有微观视角,田野考古目的在于通过对考古现场文物的挖掘、整理去发现史料中所缺乏的细节,进而获得对于历史新的解释。纪录片《中山国》所呈现的中山国,在正史中是一个被否定的对象,普通人对这个国家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中山狼”这样的刻板印象中。如何通过影像的叙事去消除偏见,进而还原一个完整、公正的中山国形象就成为纪录片所要解决的任务。20世纪70年代的一次大发现,让中山国的面目得以浮现,这次考古大发现所呈现的历史细节,正支撑起纪录片《中山国》对历史的解读,如影片中的中山三器上的铭文支撑起中山国伐燕这一事件,并上溯到几代君王治理国家的历史。将十五连盏灯、银手人俑灯作为画面元素与真人表演的情景再现相结合,去呈现王厝时代中山国的宫廷生活,而中山国王厝墓中出土的保存了两千年的一壶美酒,则直接支撑了中国文人作品中“中山美酒千日醉”的传说,并通过专家梁勇的解读更加生动。
然而,仅仅满足于“大历史”与“小历史”的客观呈现,还不能揭示历史本身的复杂性,黄仁宇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应该在宏观大历史中去发现微观的细节,并通过宏观与微观的互动,去揭示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此去发现历史本身的规律。纪录片《中山国》的创作体现出这种写作思路,如在第二集《崛起》中关于魏灭中山这一事件的叙述,就加入了“乐羊啜羹”的典故,并通过真实再现与专家采访,将这一停留于文字之中的历史细节加以视觉化呈现,令观众亲眼目睹父子之情被战争的车轮所碾碎的过程,产生内心的共鸣,这种细节在《中山国》其他地方同样可以找到,如“引水为鄗”“胡服骑射”等。正是通过这种宏观与微观的互动,让中山国的形象从被遮蔽的史书中走出,告别阴影走向前台。
三、在“自我”与“他者”关系中呈现“他者”
“自我”与“他者”是一对共生的概念,将他者作为被排斥、被征服的对象,历史的写作就必然是将他者的身影抹去,而将他者视为可对话的对象,他者就会成为自我建构中的一部分。“中山国”作为一个异于帝制中国的国家,从司马迁的《史记》被排斥到纪录片《中山国》纳入书写的过程,就昭示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如何看待“他者”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如何看待“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事实上,中国文明的进程本身从来都是一个他者参与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一个从对抗到融合的过程。在对抗中,他者是中原帝制国家的对立面;在融合中,他者又成为中华文化必不可少的因素。纪录片《中山国》就通过对鲜虞中山文化鲜明特征与融入中华民族过程的呈现强调了其对重建当下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价值,主要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1. 用各类具有西域特征的出土文物确证中山国的“他者”身份
文物是确证一个民族文化身份的直接证据。20世纪70年代王厝墓地考古现场挖掘出大量的文物,纪录片《中山国》就通过影像呈现了这些文物鲜明的草原文化特征,如玉器中牛角装饰的女性发髻、青铜盖豆上的狩猎场面,以及国宝级的文物四龙四凤铜方案、虎噬鹿,纪录片以微相镜头对这些加以或局部、或全景的审视,并通过专家的讲解,阐发这些文物的价值,进而确证中山国这一不同于汉族的草原游牧民族身份。
2. 通过海外视角阐述中山器、中山篆的魅力
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纳入研究视野,所面对的不仅是自我如何看待他者,同时涉及到他者如何看待自我,因为仅仅以自我的目光审视自身,往往不能看清自己,就需要他者的观照。近年来,中国的文献纪录片中不断加入了外国专家的采访内容,就这一视角在纪录片创作中的具体运用。纪录片《中山国》同样引入了海外视角,将中山文化的魅力在更广阔的舞台加以展现,从而为这一题材赋予跨文化的魅力。例如对于国宝级青铜器虎噬鹿一位旅日作家的解读是:“彪悍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使中原大乱,这已成为常识,建立中山国的白狄族则相反,他们被中原诸国所包围,最终被赵国所灭,中山国不是作品中的老虎,而是虎口中的鹿。能否说被强国包围的中山国的人们持有的危机感,成了这件作品的主题”。这一结论的得出,正是结合了创作者的个人经历,并融合了作者对中山文物长期观察的结果,而其本身所包含的内容正是国内研究所缺乏的。通过他者的观照,一个处于深处危机中的中山国国民心理被形象地呈现出来。纪录片在叙事过程中同时还加入美国学者拉铁摩尔等人的研究经历,将中山国问题纳入国际学术视野,进而提升了这一题材的国际传播价值。
3. 将中山文化纳入中华传统文化整体,呈现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价值
纪录片《中山国》在前五集的基础上,还专门增加《流韵》一集,讲述中山国灭国后“易”姓的演变,并对历史上不同时期中山国的介绍及与战国中山的联系,呈现出中山文化在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中的价值。在这一集中,从西汉的满城汉墓、明朝徐达墓、琉球中山国,以及世博会的中山篆、有海外学者参与的中山书法研讨会,分别从纵横两个纬度显示了中山文化在中国历史和当代世界的影响力,彰显了在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中的价值,从而增加了当下观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四、结论
历史叙事本身就是从“表述”到再“表述”的过程,纪录片《中山国》将“他者”纳入“自我”的叙事策略,是对于司马迁以来传统历史写作方式的再表述。通过这一再表述,历史写作重新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姿态,这种开放首先表现为视角的转移,传统史书中《中山国》是被消灭的对象,而纪录片《中山国》转变为历史舞台上的正面角色加以叙述;其次表现为叙事方式的转变,不同于人文历史纪录片满足于讲述自我故事的单线叙事,《中山国》的故事是在“自我”与“他者”关系之中讲述的,这里既有中山国本身的“自我”故事,又有中山国与战国其他国家之间的博弈。纪录片《中山国》将中山国这一由鲜虞白狄人建立的国家作为战国舞台上的一个重要砝码来呈现,揭示出推动中国历史由春秋战国列国纷争到秦走向一统的内部机制,从而呈现出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纪录片《中山国》无疑是一部史学品格与艺术追求兼具的纪录片,其成功经验无论是对于历史研究还是纪录片创作都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