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猫们
姚育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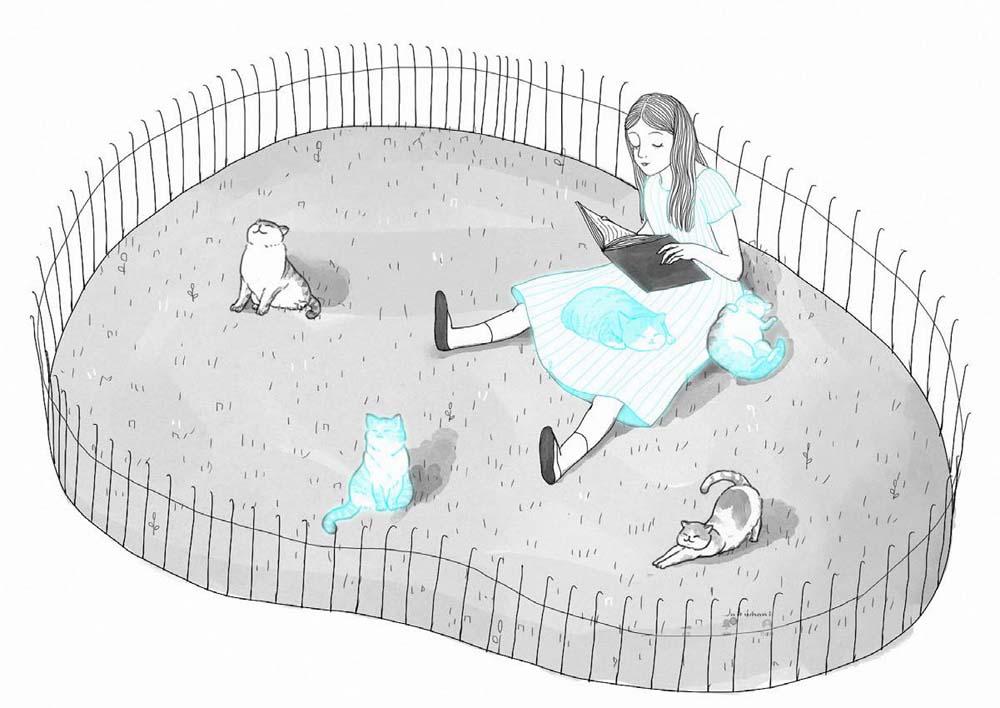
我家旧居院子一百平方米左右,几眼便看到底,但树木花卉不少,共计有一棵白玉兰,一棵紫玉兰,一棵石榴树,一架粉蔷薇,两株黑玫瑰,一棵淡紫香水玫瑰,一棵粉紫薇,一棵柿子树,三棵含笑,一棵无花果,一棵杏树,一棵大叶栀子花,五棵四季珠珠花,一棵红梅,一棵蜡梅,一棵大山茶,三棵桂花树,一棵鹅掌楸,一棵枣树,一溜紫红粉白相间的杜鹃花,一棵香椿,一棵黄杨,一棵蹿天大樟树,还有一片绿草地。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一一列出,是因为我一直看不够,还有无数的碧眼、绿眼、黄眼、黑眼,它们也是看不够,更是玩不够,其中一只还酷爱吞食玫瑰花蕾,它们就是被我们称为院猫的精灵。
我一直以为是自己收留了它们,却不知道猫们地盘意识强烈,至少六只原住民将院子视为它们的领地。后来,别处来的猫不甘心仅将此地当成开放式游园和免费餐馆,于是公猫们在院子里到处做记号甚至打架,母猫们互相对骂或者赖在猫屋里不走,瘦弱的有病的猫没力气参加竞争,便趴在阳台上等待我心软病发作。
流浪猫要抢占我家院子还情有可原,奇怪的是散养的家猫也来凑热闹,比如一只结实厚重的矮脚黄虎斑,一进院子就扑打所有的猫,连女猫小猫也不放过。如果我呵斥它,它就把尿喷到猫碗里示威,有一回竟当着我的面撕咬病弱的黑妹妹,我一时找不到棍子,脱下左脚的拖鞋扔了过去,拖鞋砸在它身上,吓逃的反是黑妹妹,黄虎斑纹丝不动,四只短脚像钉子一样牢固,它扭头镇定地看着我。天阴下来时,矮脚虎仍不回家,反而蹲守在猫屋顶上发威,院猫们只好胆怯地挤在阳台上。下雨了,它又窜过来,独自霸住阳台上的猫爬架,四脚朝天地睡得自在,原住民只好钻在冬青树下战战兢兢地躲雨。有时碰到院猫们都出去玩了,黄虎斑一人就乐得在院里打滚,看我的眼神也变得温驯,还不时喵喵叫着,好像说老子总算享到清静了。
还有一只黄白色的家养母猫,它名“咪子”,听它主人说,因为家里新进了一只白猫,就醋劲大发离家出走,这一走就走进了我家院子,主人来唤它装没听见,原住民和它对峙也不害怕,它的哈声比原住民更理直气壮。它不像黄虎斑会使蛮力,它使魅功,每当我说出咪子回家吧这句话,它都会原地跳起,倒下去时呈仰面状,前肢缩在胸前勾啊勾的,还飞闪着媚眼,活脱一温柔娘子。我伸脚扫它出院,它也不起身,像没有感觉的垃圾,侧躺着任你着力,我吓得收回了脚。
猫们拿定了我的软肋,只要遇到它们,我总没办法选择。过去,我一直遵循着“来的都是客”的原则,事实使我明白“来的都是麻烦”,于是修改小院规章,为了原住民的安定,也为了邻居耳根清净,我发誓,有主的猫一律不准入内,为此特准备赶猫棍一根;无主的狗也不准入内,想进餐外面等候。唯有流浪猫可以进来就餐,但不留宿。结果后者不高兴了。为什么准吃不准睡啊?
没法和它们讲道理,据说猫的智力相当于两三岁的孩子,一个幼儿懂得什么逻辑?我只好频频张望,一有情况就从屋里冲出去,从精神抖擞到精神恍惚,我的眼睛里只有猫!猫!猫!在它们眼里,我一定是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老猫,忽善忽恶,阴晴不定。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突然发现猫们安静了不少,除去我的努力和原住民的团结一致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猫王出现了。
猫王第一次出现在我家院子里时,所有的猫都低头不语,也有昂首的,却是闭着眼睛。有一只不大不小的猫刚想钻进院子,猛然看到猫王,吓得又缩了回去。这是只黑灰色的狸花,体型庞大,毛发蓬松,它无言地蹲在我家院子正中,目光懒散地扫过所有的猫,好像说,小玩闹们,我不来巡视一番你们就反了天了?
我大喜,捧出猫粮献殷勤,它对着猫粮目光呆滞地沉思一会儿,然后心不在焉地吃了几粒,又停住,我凑过去,讨好地说,你应该有个名,就叫你大松吧。它置若罔闻地看看猫碗,好像不明白刚才吃的是什么,我伸手想摸摸它,它反手就是一巴掌。咦?怎么恩将仇报?你算什么猫王,倒像老年痴呆症!
不知大松贵府何在?有没有人为它打理饮食?只知道它对餐饮不太敏感,有时闻闻刚倒上的猫粮,一粒也不吃,有时又把别猫吃剩的丁点猫粮舔得干干净净,弄得那碗像水洗过的一样。也看不出它有什么精神追求和兴趣爱好,它来了就像人一样用屁股坐着,两前肢腾空,没任何表情地坐着犯傻。奇怪的是这傻劲就能镇住群猫。它不久留,吃一会儿或坐一会儿就走,它走时全院的猫都行注目礼。
别看黄虎斑百无禁忌,却也惧这只大头大脑的猫王几分。如果大松进来了,黄虎斑还霸在院里不走,一场好戏马上开演,刹那大松显示猫王本色,每回打斗过后,地上都滚动着几大撮猫毛,有黄色的,也有黑灰色的。我可怜这只已显老态的猫王,只要有可能,就助它一臂之力,最后总能弄得黄虎斑落荒而逃。
最后一次看到大松是个下雨天,它竟然睡在我家阳台的猫爬架上,浑身湿漉漉的。我撑着雨伞去猫屋张望,院猫们都息在里面,不由感慨猫王到底是猫王,哪怕一副傻样。
有好长一段日子,大松和黄虎斑都不来了。偶然在班车上看到一位女子,主动来和我打招呼,她说咪咪中毒走了。我莫名其妙,哪个咪咪?她说就是经常来你家院子的黄猫咪咪呀。原来是它!如此健壮勇猛的猫竟然死了?它的主人又说,我后悔死了,没有带它去看医生,一开始以为它是便秘,只知道给它揉肚子,谁想到它吃了有毒的东西呀,胀了两天就走了。
知道这户人家后,再走过她家院子我就会朝里看,那里有个小土丘,我知道黄虎斑就埋在下面。想到咪咪这个昵称,我也不由嘘唏起来,它也是个受人宠爱的宝贝呀!
但是没人来告诉我大松为什么不来了,我不敢朝坏处想,在城市里,猫的真正天敌是人类。自从我听说猫贩频繁出入我们小区,还有小区里住着做烧烤的租户,我就常常为猫们担心。希望大松是寿终正寝了,不要经历那些酷刑。
终于又来了一个猫王,也许是大松的儿子,和它一样的毛色,一样的大头大脑,尾巴比大松还粗。我称它大松二世,后来嫌麻烦,就简称二世。
二世也常来我家院子巡视。它比大松年轻,皮毛也紧实,走路像狮子王一样优雅,既有弹性又四平八稳,它的眼梢微微上吊,眼神虽淡漠,神态却威严,有着天然猫王的气派。
我总算明白了,这个院子有着双层管理模式,猫王才是它们真正惧怕的管理者。我和猫王并驾齐驱,终于将院猫条件明确下来,住进来的猫必须符合三个条件:第一,我主动收进;第二,自己来投靠,全体院猫接纳;第三,猫王不驱。
咦?怎么猫王的权力放到了最后?想一想,现实就是这样,骨子里,我还是它们的主人。
有句歌词叫“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家院子被一些邻居称为“猫的天堂”“猫的乐园”,毫无疑问,我家小院具有魔法,十几只水碗映照着缤纷的色彩,碗里的猫粮也被花香熏染,院子里所有美丽的物事都没浪费,它们被无数倍地分享了。
后来它们死的死失踪的失踪,只剩数只顽强地活着。再后來,我们卖了旧屋,新来的人家改造了小院,挖掉了一大半的树木花卉,草地也变成了防腐木地板,并且一直延伸向河面,院子徒增面积,一下变得宽敞明亮,但是再也没有猫搅得风起云涌了。
此刻,我在新居的院子里抚摸着从旧居转移过来的猫咪白鸟,问它你还记得那个院子吗。它轻柔地叫着,好像还趴在旧日的树上,眼里映着无数的幻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