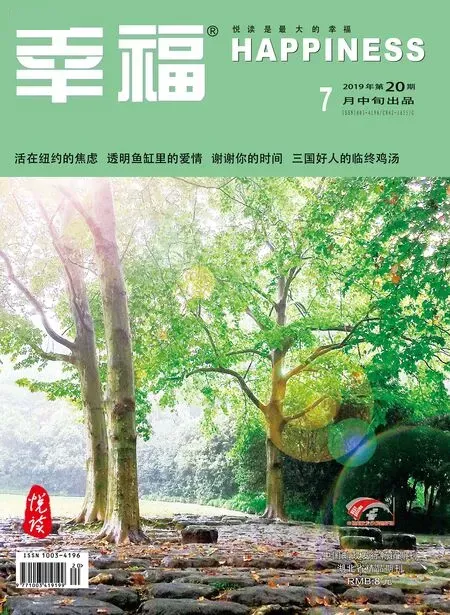一个90后眼里的秦怡
文/金昱杉

90后这个词,还是秦怡老师自己主动提起的,在她得知我是1992年出生的时候,她说,“你看你是90后,我也是90后,我94啦。你写的文章可以叫,当90后遇见90后。”
开始我觉得她就代表了“岁月从不败美人”,是电影圈的传奇,后来发现她更像一位亲切可人的邻家奶奶,人缘好,不大会拒绝别人。
2015年9月,第一次见到秦怡老师。在此之前三个月,她参加了石挥导演与赵丹先生的100岁诞辰纪念,但很少有人知道,那阵子她每周都会请人上门理疗,是忍着腿脚的疼痛去的。她说:“阿丹和我的表演是不一样的,他很有范儿,有那么一种仪式感,他更贴近中国早期的电影表演方式。我们都是那种为了电影做什么都可以的人。”《母亲》是秦怡老师最喜欢的一部电影,这部戏的导演就是石挥。她说:“石挥以前演话剧,他演的小人物活灵活现,满脑子都是故事,有时候想一出是一出。”说到这,她笑了,“都说《我这一辈子》是他导演的处女作,其实《母亲》才是他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当时他来找我,说一定要你来演,因为我很信任他,就答应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的,而且有人文情怀。”
有一天,我去看她。她给我拿了一瓶苹果汁说:“你们小孩子都喜欢喝这个,一路过来累了吧,你先缓缓。”然后呆呆地开始走神,片刻,开口说:“周小燕走了,葛存壮也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就剩下我了。和他们一块,就和昨天的事儿一样。”
七个月后,秦怡老师的另一位至交好友夏梦也去世了,“我比她大十岁,她是我的小妹妹。她是上海人,我之前去香港还见过她,不熟悉的人叫她,她都不出来的,她打麻将厉害。我去了,她还陪我逛逛。也就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能这样了。”后来又聊起她的老友王丹凤女士,“王丹凤很讲究的一个人,非常追求完美。她曾和我说,觉得自己最后几部电影拍得不好看,就再也不拍了。我劝过她,不要这么较真。像我们这个年纪,相熟的朋友走了好多了,也就我们两个还熟悉,我给她说说话,她还是听的。以前,我和她丈夫柳先生还会在理发店遇到,现在他们两口子更深居简出了,我们也不常见面了。你做电影研究,可以去看看她,如果见到她就和她说,我挺想她的。”
2017年4月我在华东医院采访了王丹凤女士,她说:“我好久没见秦怡了,她好不好啊,还挺想她。我年纪大了,好多事都记不清了。和我相熟的,除了她,也没几个啦。”如此对白,仿佛心有灵犀。
“出生在这个年代,你们这些孩子很幸福。”这是秦怡老师经常和我说的话,“最早在重庆时,我们住的都是大通铺,男女混住,中间就隔着帘子,很简陋。每天换衣服都必须特别迅速。到处都是战乱,但是你得活着,你得相信一定会好的。后来每演一个角色,我都会去体验生活,我能吃苦的。”秦怡老师拉起我的手,“你这一看就是不干活的手,你再看看我的。”她伸出自己的手,“都会有冻疮冻裂。当时拍《马兰开花》的时候,在秦岭沙场,他们都说,你是女演员,怎么好学开推土机。结果啊,我是当时女演员里,唯一一个会开推土机的!”回忆起这段往事,她神情骄傲得像个孩子。
这几年,秦怡老师一直在忙的就是电影《青海湖畔》,自编自导,也是其首次担任出品人。为了这个电影,她付出了很多,“我九十多岁了,要去演六十岁的梅欣怡。主题曲是毛阿敏唱的,她说秦怡老师不要片酬,我也不要。”秦怡老师感慨地说,“当时好多人都劝我不要去青海,3500多米的高原,我去试了试,还行,于是便拍了。他们说现在年轻人不喜欢看这种题材。我说不对,我坚信正能量的东西,能打动人的东西,必定会有人欣赏。”
每次告辞时,她都会起身把我送出门去,看到我习惯性地把耳机拿出来插到手机上会叮嘱:“走路不要玩手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