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原扁理:“做二休五”的都市隐居者
徐牧心

大原扁理
早饭通常是米饭和味噌汤,悠闲地吃下来,大概要花上30分钟的时间。
大原扁理十分享受这缓缓流逝的早餐时光——尤其是想到此时在东京的另一个地方,挤得爆满的电车和地铁中,赶着通勤的人们正艰难地站着,身后人呼出的热气喷在前面人的脖颈上,每个人都一身黏腻。
辞掉了工作的大原扁理,不需要辛苦挤进早班的地铁,但有时他也会在早高峰外出,看着站台上等候的人们,有的衣服光鲜亮丽,有的则皱巴巴的。“这光景仿佛是人类使用前与使用后的标本。”大原扁理说道。
26岁那年,大原扁理做了一个决定:他不要再被这个社会“使用”,过起了“做二休五”的生活——工作两天,“休息”五天,用最低限度的金钱保证自己生活无虞。
如今,已是他隐居的第9年,其间从东京辗转到了台湾,但唯一不变的是“做二休五”的生活方式。
在日本,想要过上“做二休五式人生”的年轻人不在少数,这让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很擔忧。他将日本这种社会现状与特点概要性地总结为“低欲望社会”,即人口减少、超高龄化,失去上进心和欲望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从而导致经济低迷。
21世纪都市型隐居
“所以你到底在做什么呢?”
不去上班,不去社交,因为停掉了手机,也不会随时与人保持沟通,于是偶尔会有人这样问大原扁理。起初,他也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直到某一次他脱口而出:“我正在隐居。”
采访大原扁理的时候,他的面前摊开着厚厚一沓纸,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对采访提纲的回答——独自一人隐居9年,他有时甚至怀疑自己得了失语症,所以在要与人交谈时,得提前准备好词句。
他很瘦,甚至有些单薄,皮肤有些黝黑,或许是因为常户外散步,但脸上那一副眼镜却又为他平添了一丝书生 气。
这丝书生气可能来源于他读书的习惯。自从辞掉工作后,大原扁理的收入锐减,但他很快发现,有很多爱好其实都不需要金钱,譬如散步,或者去图书馆待上一下午。“一个人就可以做到,不需要钱,也不需要特定的场所,甚至似乎可以让自己变聪明,堪称最强的兴趣。”
因为这一点爱好,以及大量的空闲时间,大原扁理开始将自己的隐居生活记录下来,集结成书,《做二休五:钱少事少的都市生活指南》。这是本薄薄的小书,花上一下午就可以读完,轻松得就像是大原扁理隐居生活中的每一 天。
大前研一忧心忡忡,“如果人人都这样向下沉沦无作为,必然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和国家的弱体化”。
隐居生活的一天从早上六七点钟就开始了。尽管是隐居,但大原扁理却要求自己始终过着“忙碌”的生活。“我不希望自己失去紧张感”,人一旦过着清闲的生活,就会不自觉地变懒惰起来,而如果不自己定下规矩并遵守,则没有事情可以督促他完成。
因此,当公司的职员们匆匆吃完早餐,喝一口续命的咖啡时,他早已吃完了清淡的早饭,开始新一天的隐居生 活。
早饭后是“忙碌”的时间。因为习惯早早将该做的事情做完,所以上午的时间,大原扁理会用电脑收发邮件,记录下隐居生活的琐碎。如果需要做家务,那么他就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洗衣服。
当不再需要挤出有限的时间来打理蜗居时,洗衣服的时间便可以尽可能地加长。那感觉就不像是在完成任务,而是一种享受。
午饭通常是煮一碗清淡的乌冬面,偶尔会加一些葱和芝麻,最多加一两种蔬菜,“加太多料会搞不清楚自己在吃什么”。
天气不好的话,他索性就窝在家里,睡一个午觉,或者把从图书馆借来的书阅览完。如果阳光正盛,午饭后就可以出门散步,重点是要避开信息泛滥的车站等地方,因此公园、河川便是个好去处。
在一次散步中,他发现路边就有很多可食用的蔬菜:加在味噌汤里的艾草,可当下酒菜的薤白,味道像笋干的虎杖,以及生食就有清香味道的紫苏。
于是在东京这样繁华的大都市里,大原扁理却过上了采集时代的生活。这片无人问津的田地与他人眼中的“杂草”,成为了专属他一人的,免费且24小时开放的“蓝天超 市”。
他心有疑惑:同样类型的蔬菜,明明长在路边无人问津,为什么大家都要去超市里花钱购买呢?
“没有钱就没有自由,这实在是太不自由了!”大原扁理写道。渐渐地,他发现,没有什么金钱,也完全可以过上吃喝不愁的日子:
蔬菜可以从路边采集;比起超市中眼花缭乱的洗衣液,廉价的小苏打就可以把衣服清洗得很干净;因为不需要社交与工作,手机也索性停掉了;图书可以从图书馆借阅,电影则可以在线上看免费的老电影;不需要医药保健的费用,因为这种生活方式他很少生病;近十年没有踏足过理发店,自己理发已轻车熟路;更重要的是,因为不需要租工作地点附近的房子,他只花了一半的价钱,就在东京的郊区租下了自己的房间。
一周7天,他过着与他人颠倒过来的生活——做二休五,一个月下来,只需要7万日元(约4448元人民币)的支出就可以生活。
在东京,这样的支出标准可能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大原扁理并不认为自己在“节约”——外出吃饭或者一日往返的温泉旅行,一个月就可以有一次;食材会挑选无农药的作物;一年会有几次精心打扮,与朋友相约前去市中心的餐厅吃饭。
如果削减掉所有这些支出,一个月的生活费大概6万日元就可以搞定,但大原扁理从没有想过太禁欲的生活。他不做勉强自己的事,无论奢侈的还是节俭的,只是跟随自己的内心。
告别“社畜”人生
在北京大原扁理的签售会上,报名人数一度爆满,这让大原扁理的编辑未免有些意外。此前他们也曾在成都举办过一场发布会,而北京的报名人数则比其整整多出一倍。
编辑猜测,或许成都生活着的人,早就习惯了这样悠闲的生活方式,而生活在北京的人们,却因为距离这种生活更为遥远,而更加感兴趣和渴望。
对于居住在北京的人们而言,“996”是他们生活的日常,来源于日语的词汇“社畜”是他们的自嘲。所谓“社畜”,意为“公司的畜牲”,指那些拼命为企业效劳的职工,睡眠和饮食都草草了事,甚至为了企业放弃身为人类的尊 严。

在进入隐居生活之前,大原扁理也曾是这样一名“社 畜”。
高中毕业后,大原扁理进入零件工厂成为了一名派遣员工,一周要工作五到六天的时间。忙起来的时候,连休息时间都要来回奔走。因为每天要工作超过12个小时,好不容易闲下来的时间里,就再也没有去生活的闲心——用便利店的饭团代替煮饭;用补觉代替出去玩;没时间关心政治,也没时间关心身边的人,因为大部分生命都献给了工作,剩下的只有粗暴的生理需求。
有时候大原扁理也会对這样的生活产生质疑,然而在跟当时的朋友谈论起来时,对方只是冷冷地回复一句:“工作12小时?这很正常啊。”甚至还有同事会把这种人生当作炫耀的资本:“我每天都睡眠不足,还曾经在月台上睡着,掉到轨道里喔!”
日本是个崇尚工作的国家,战后,日本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到80年代达到巅峰。那时,几乎每个日本上班族都将职场当做战场,甚至提神饮料的广告上都写着:“你能战斗24个小时吗?”
然而大原扁理那一代的日本年轻人,一出生就面临着经济泡沫的破碎。“在不景气中度过青春期的(我们),只好降低自己的物欲。”很快,进入社会的年轻人们发现,即使自己拼尽全力工作,最后也可能只落下“过劳死”的命运,与社会对其苍白无力的嘉奖。
“就算工作成那样,还是过得一点都不宽裕,这到底是谁的问题?”他无力地发问,“职场和这个漠然的社会,别说保护了,根本就是在夺走我们的时间、金钱。有必要这样为它拼命工作吗?”
于是,大原扁理扔下工牌,炒掉了工作。在曾经一天工作12个小时的生活中,他发觉自己变得十分自私,因为没有时间,做什么事都只能考虑自己,对别人则一分钱都不想花。闲下来后,他则可以帮助邻居搬家,可以在超市买好平价的免费烤制甜品,送给身边的朋友。
他将朋友圈缩减到了10个,留下来的大多是君子之交——因为不需要再应酬,每一次和朋友的交谈和外出,都让人打心底感到愉悦。
本刊记者有些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跟大原扁理成为朋友。他便掰着指头算了一下,随即噗地笑出了声,仿佛刚刚发觉了什么似的,“果然是正常上班的那种职员比较少”,都是“音乐家或者自己开店的人、模特,没有一个是正常公司上班的人”。
辞职后,大原扁理的年收入一下子降到了90万日元——100万日元之间,而在日本,年收入不足100万日元(约合6.4万人民币)的人群被划定为贫困人口。但精打细算下来,他仍有不少存款,甚至在他隐居生活的第三年进行了一次环球旅行——从伦敦到澳洲,他在一个人的旅行中,发现这世界上的“同类”竟然这么多。
世界旅行就像是大原扁理的最后一个愿望,回到东京后,大原扁理感觉心里安定了下来。也许有钱的时候也会继续旅行,不去的话也无所谓。“无论现在的我身在何处,似乎心里只要想着旅行就可以是一趟旅行。”他写道。
低欲望社会
在冬天的时候,因为嘴唇经常干裂,大原扁理十分喜欢涂一层厚厚的润唇膏。或许他喜欢的是润唇膏本身——虽然看起来是保养品,但在医药的分类上来看,却是准药品。“虽然被排除在医药界之外,但我仍然算是药喔。”他仿佛听见润唇膏这样说。对于被社会划分出去,但仍然算是人类的大原扁理而言,找到这根唇膏,就像是找到了同类般亲切。

在日本,选择比大原扁理更极端生活的青年大有人在,他们被称为蛰居族。所谓蛰居族,就是避免一切社会活动,靠着父母或其他方式作为经济上的支持,足不出户,这种状态持续数年以上的时间。据统计在日本国内,这样的蛰居族约有70万,另有150多万人濒临蛰居。
因此,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认为日本正在成为一个“低欲望社会”:“日本人低欲望这个倾向,与其说是单纯的经济现象,还不如说是日本在各方面表现出的社会现象。这些现象的背后,有着二十多岁、三十多岁日本人的想法:‘不想有责任,‘不想承担责任,‘不想扩大自己的责任。为此,即使进了公司,也不想出人头地,将结婚视为重荷,将买房贷款视为一生被套牢——这些想法成了日本年轻人的主流想法。”因此,他忧心忡忡,“如果人人都这样向下沉沦无作为,必然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和国家的弱体化”。
当大原扁理将自己的生活整理下来,写在博客发到网络上时,他也常常会听到人们的抨击声:“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人,日本的经济才会不景气。”
“但是我过这种隐居生活过了五六年之后,出了书,在日本出了三本,中国一本。我算了一下,大概会产生三千万日元的经济效益。”大原扁理反驳道。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人畜无害”,他没有接受旁人或者国家的经济支持,甚至他会一直保证手上有一定的存款,并且在年岁越来越高时,增添手中的金钱,为以后可能发生的病痛做准备。“如果身无分文还继续活着是很可怕的,所以为了以防万一,为了不成为他人的负担,我不会将存款花光。”
《做二休五》在豆瓣评分也比较两极,不少人流露出对隐居生活的羡慕,但是“谁又能真正放下呢”也是不少人担心的问题。面对与这个世界建立起的关系,稳定而安全的生活,谁又能有勇气坚定地斩断一切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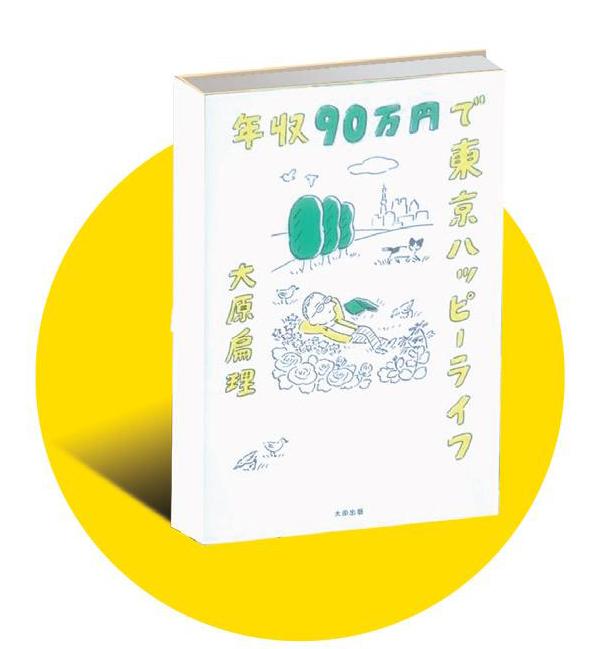
在东亚国家,大家遵循的是相似的“社会时钟”:毕业——一份体面的工作——娶妻生子——继续为工作奉献一生,这样的轨迹几乎是不可置疑的。遵循这样的时钟,好处就是一种安全感。
但大原扁理则有不同的想法:“可能其他人觉得遵守这种社会时钟比较安心,但是我却喜欢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由自己来决定,不是外人或者社会决定的。而且如果自己做决定的话,我会有一种紧张感,我其实非常享受这种紧张感。”
尽管将自己的生活称作茧居,但比起足不出户的茧居族们,大原扁理却更像是一个“大隐隐于市”的僧人。他始终想与这个世界保持最低限度的联结,“正因为没有出家,从旁人的眼光看来,我跟反社会分子的地位是一样的。明明我只是想要独自享受无欲无求的生活而已……”
大原扁理也曾去街头采访过流浪汉,才发觉比起足不出户的茧居族,或是幕天席地的流浪漢,他的人生或许更像是取了一个中间值:“对于隐居的人来说,都市的各种诱惑都在唾手可得之处,只是隐居者要主动与之保持距 离。”
大原扁理

21 世纪都市型隐居生活
租一间在郊区的便宜小公寓
一星期只工作两天
不带给别人麻烦
朋友都是精挑细选过的所以很少
没有手机
也没有电视
剔除无意义社交
偶尔会有进城的小奢侈
基本上没有欲望
不坚持己见
但坚持跟现代社会保持一点距离
最后是要热爱和享受自己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