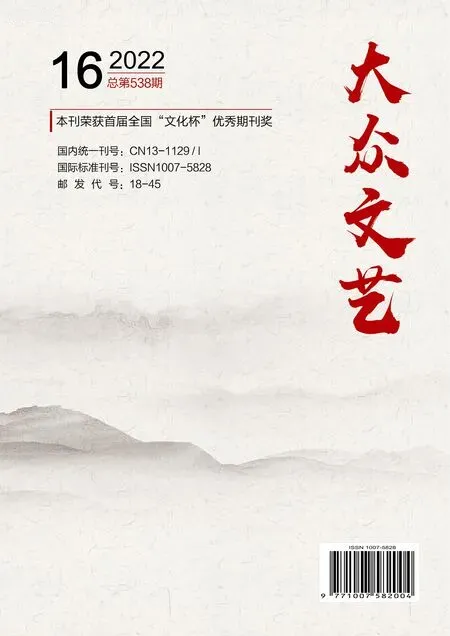从破碎到完整
——男女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创作下的女性形象比较
黄丹璐 (中国艺术研究院 100029)
超现实主义运动兴起的时期,也是弗洛伊德心理学蓬勃发展的年代。性本能是弗式精神分析的核心概念,受其影响巨大的超现实主义也因此将性与性别视为创作重点。这一倾向在男性艺术家主导的运动初期就已明显,并促生诸多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作品。1935年后,众多新加入的女性艺术家又将该主题进一步发展为对自我性别的再审视,并创造出风格与前者大为相异的作品。不同阶段、不同性别的超现实主义者创作的女性形象有何异同值得深入探讨。
一、男性超现实主义者创作下的女性形象
与许多现代艺术流派相同,超现实主义运动最初由男性艺术家发起。1919年,创始人布勒东借用催眠与自由联想等心理问诊手段发明“自动主义”技巧,创作一系列充满梦幻与想象力的诗歌与小说1。1923至1927年间,画家安德烈·马松跟随布勒东的脚步,利用同一技巧创作36幅自动绘画。他在画面上暗示性地勾勒出胸脯,腰身等女体造型,让这些躯干在象征潜意识活动轨迹的线条间漂浮纠缠。从布勒东和马松开始,潜意识与女性的关联始终是男性超现实者的重要创作母题。
超现实主义运动自1925年起走向盛期。诸多艺术家在美术,摄影乃至电影方面的实践,将这场重心本在文学上的革命发展为视觉领域的先锋运动。继马松之后,马克斯·恩斯特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画家。他将拼贴这一典型的达达主义技巧改造为布勒东式的“自动主义”方法,将画纸从解构一切的涂鸦墙变为引发自由想象的潜意识空间。
不同于马松简略的速写女体,恩斯特以拼贴方式创作的女性形象更具直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在早期的《解剖模型新娘》(The Anatomy as Bride)和《神圣对话》(Santa Conversazione)等作品中,恩斯特将裁剪而来的模型及机械部件照片与人体躯干拼合,组装成机器人偶般僵硬的女性形象。这些勉强组合的残破女体似乎象征着机械复制时代人性的压抑和泯灭。
除拼贴作品外,恩斯特架上油画中的女性形象同样承载着人性与机械关系的复杂命题。在《旋转的女人》(The Wavering Woman)中,恩斯特描绘了女子悬挂在钢轴上旋转的情景,一根铁管穿过她的眼睛与钢轴相连。在《女人,老人与花》(Woman,Old-man and Flower)中,恩斯特用生锈的金属扇面等部件构成上半身,以钢铁质感描绘赤裸的臀部及大腿,又用黑色线条简单勾出柔软手臂,拼合出诡异冰冷又真实的女子背影。
除这类“机械女人”外,恩斯特笔下的另一类经典形象是“无头女人”,表现为没有头颅的女性身躯或鸟首人身的半兽。这类形象在他早期拼贴作品中就已频繁出现,其源头可能是他早年去世的妹妹,2并在30年代后的油画中发展为代表性的个人符号。有趣的是马松也创作过类似的“无头女人”形象。在他1937年的雕塑作品《人体模特》中,服装展示人偶赤裸着身体,只有头部被关在鸟笼之中,嘴部也被口罩和花朵封死。
马松与恩斯特对女体的分解与改造尚算温和。而在另一位超现实主义者汉斯·贝尔默的“娃娃”(Doll)系列女体雕塑中,“机械女人”与“无头女人”这两类特质被进一步推到极端,性征表现也越发夸张。最早被完成的女体雕塑是1934年的“机械娃娃”。贝尔默以齿轮和钢杆撑起女性人偶的身体,利用球形关节将她们摆出各种诡异造型。在他此后的作品中,人偶头部乃至大部分肢干都被去掉,仅留下最具性征表现力的部分肉块般彼此纠缠。这种 “减法”让人联想到马松在“自动绘画”系列中的表现,但贝尔默对肉体质感的强调及雕塑本具有的实感都使作品的震撼力非前者可比。“娃娃”不仅呼唤着人的潜意识本能,更是一种对女体的直接暴力,让观者不由感到恐慌与不适。
若说贝尔默等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一类典型,另一类超现实女性典型的源头则可追溯至布勒东。布勒东最推崇“孩童般女子”(Femme-enfant),认为她们纯洁、天真且美丽,是超现实主义者的缪斯。他说只有在她们身上才能找到另外一种可见的光谱3,她们是艺术追求的使命。“孩童般女子”的变体“危险情人”则更具神秘危险的魅力,布勒东小说中的女性原型“娜嘉”正是此类代表。
曼·雷的摄影作品是在视觉层面诠释布勒东理想的极佳注脚。他选择的模特皆是面容美丽,气质古典的年轻女子,她们在镜头下呈现出或是娴静忧愁或是神秘诡异的梦幻气质。《长发女子》(Woman with Long Hair)和《安格尔的小提琴》(Vionlin of Ingres)等作品与欧洲古典时代的审美遥相呼应,也与贝尔默等人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然而,看似推崇与尊重的态度背后仍是一种男性中心的审视。正如波伏娃指出的,这些男性超现实主义者创作的女性是 “是入口、钥匙、门和桥……是鞋、餐桌、狼、大理石和糖……是一切事物……一切处于“他者”的形式之下。唯独排除了她自己。”4
二、女性超现实主义者的产生及其身份
正如上文所提,布勒东等人在运动之初便将女性放在十分推崇的位置上,视她们为艺术灵感之源。超现实主义运动也由此成为第一个欢迎女性加入的现代艺术运动5,为饱受社会传统禁锢的新女性们打开了一个自由叛逆又充满想象力的新世界。这是早期超现实主义在面对女性主义质问时十分积极的一面。
但需要注意的是,最早参与到运动中或与运动关系颇深的几位女性,身份大多是男性艺术家的伴侣或艺术家的创作对象。而非独立的创作者。例如,给超现实主义者带来诸多灵感的灵媒海伦娜·史密斯被布勒东赞为“创造性自动机器”6,却不曾被视为真正的艺术家。努什·艾吕雅,加拉·达利等人是艺术家亲密的妻子及模特,却不曾以艺术家的身份留名艺术史。这些女性不是超现实主义团体的正式成员,也没有参与两次《超现实主义宣言》的撰写与签署。7情况在1933年时有所改观,这一年布勒东在《自动信息》这篇纲领文章中极大拓宽了超现实主义的定义。新方向的号召使诸多女性艺术家加入运动,她们的影响力在1935时逐渐提高并开始频繁参与展览与刊物出版。8
女性创作者从创作对象到创作者身份的变更是超现实主义运动在长达半世纪的发展过程始终致力于自我改造的证明,也是运动早期作品与后期作品区别较大的原因之一。
三、女性超现实主义者创作下的女性形象
1935年后涌现了包括利奥诺拉·卡琳顿、弗里达·卡罗、雷米迪欧斯·巴罗和莱昂诺尔·菲尼等人在内的一大批女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她们从女性视角出发,并在作品中大量使用神秘主义,拉丁以及东方文化等非欧洲中心要素,创作了与男超现实主义者相比具有巨大区别的女性形象。
最直观的区别首先体现在年龄上。在“孩童般女性”这一理想下,男超现实主义者作品中的女性往往十分年轻甚至是年少。在卡琳顿的作品中,中年和老年女性则是重要的绘画对象。她们头发花白,表情冷酷,在《亲爱的日记》(Dear Diary)《狩猎》(la Chasse)和《移情》(Transference)等作品中结群出现。巴罗笔下的女性同样体现着年龄的沧桑,在《离开精神分析的女人》((Woman leaving psychoanalyst)等作品中,占据主要画面的女子有着花白凌乱的长发以及皱褶明显的面庞。
另外,男性艺术家经常创作赤裸且充满女性魅力的女子形象,她们有着曲线优美的身躯和阴柔美丽的外貌。女超现实主义者笔下的女性形象则有着强烈的中性化倾向。巴罗描绘的女子身材干瘦,仪态狂野,表情桀骜。卡琳顿则经常给笔下女子穿上宽厚臃肿的外衣以遮掩其性征。例如《祖先》(Ancestor)这幅作品,女子从头到脚都被长袍严密覆盖,只有若干细节暗示着其性别。弗里达更是在自己的自画像中用厚重的一字眉,浓密的唇毛或胡子及粗犷的五官营造雌雄莫辨的错觉,以此展现自己对性别的看法与态度。
这种中性化的趋势不仅体现在外貌上,也体现在女性与男性的关系中。菲尼在《黑色女妖》(Stryges Amaouri)以野兽与少女双重形象表现女性内心的一体两面。她们充满野性与又极具活力,保护着沉眠中的赤裸男子。菲尼自我评论道:“她们可以守护,她们也能威胁。”在她的作品中,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沉默缪斯,而是男女关系中的守护者
在女超现实主义者的作品中,破碎的“机械女人”和残缺的“无头娃娃”已经消失,取而代之是完整自然的女性外表。在巴罗的《音乐阳光》(Musica Solar)中,女子身披长袍,面带笑容,在大自然中以阳光为弦奏响与自然共鸣的音乐。女性不再是“安格尔的小提琴”,脸上也不再有痛苦的玻璃眼泪,她自由、自立且自得其乐。在卡琳顿的《女巨人》(The Giantess)中,画面被身材庞大,表情温柔的女巨人充斥。她面带微笑俯视渺小众生,拥有创造世界的丰沛力量。“大母神”形象的出现是女性内心意识的觉醒,她们希望成为历史与世界的创造者,追求属于自己的未来。
从年少到成熟,从被动到主动,从破碎到完整,在超现实主义这一独特而宽广的命题下,男超现实主义者与女超现实主义者就女性形象的塑造给出了风格各异的答案。但不管是哪一类艺术家,他们的共同追求都是探索潜意识心理的不同层次,解放想象力的诸多可能。超现实主义也因此始终焕发着蓬勃的生命力。
注释:
1.André Breton.The Lost Steps[M].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6:90.
2.Max Ernst.beyond painting[M].Solar Books,2006.
3.[法]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274.
4.同上,268-274.
5.Victoria Ferentinou.Surrealism Occulture and Gender:Women Artists,Power and occultism[J].Aries,2013(01):109.
6.Tessel M.Bauduin.Surrealism and the Occult[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14:90.
7.同④,109.
8.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