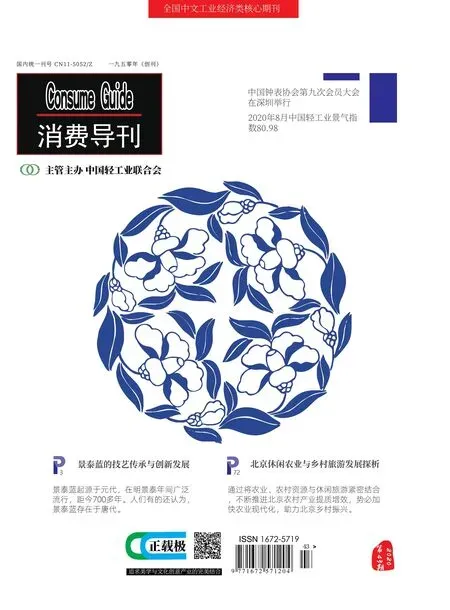生态文明建设中关于法律约束的思考
李红梅 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可以笼统地概括为三个阶段:从具有一定的自发性,到逐步具有规范性,再力求进步到自觉性这样的发展过程。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从不健全逐步推向健全,从无序化逐步发展向有序化,从不规范向规范化进步。当前,人类对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基本上处于在逐步规范化的基础上萌发出了一定自觉性的阶段,需要在不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规范化的基础上培育人们对保护环境的自觉性。然而,在当前实践中仅依靠人们对保护环境的自我觉悟是远远不够的,并且随着日渐明显的环境问题的到来,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即使有了很大的进步,在面对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当代利益和后代利益等选择时,依然需要法律约束等“硬约束”手段来规范。因此,如何处理好环境问题的不确定性、多样性和特殊性与法律约束的确定性、局限性和普遍性之间的矛盾尤为关键。
环境问题的不确定性与法律约束的确定性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在逐步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当今社会,由于环境问题的广泛性、起因和未来影响的不确定性等问题,仍然是困扰环境法律和政策制定的主要因素之一,比如,迄今为止,关于全球变暖的成因仍未得到完整的科学解释。引发环境问题的众多因素孰轻孰重、相互之间的作用和互动关系同样具有不确定性。也许在环境问题如此居多的不确定性面前会有这样的质疑,是否应该彻底搞清楚成因再去以减缓经济发展速度来保护环境,是否应更着力于科学研究,明确问题之后再制定出有效法律法规。对于这样的论调,最好的反击是:因为科学确定性的等待,即使最终可以等到,也是有代价的[1]。因此,我们不能停驻生态文明建设的脚步,更不能抱着侥幸心理来避免当前和未来的危害,即如何做好环境问题的不确定性和立即行动避免环境危害二者之间的选择,这是生态文明建设中法律约束面对的首要问题。落实到立法工作中,一方面,需要获取更多、更完善的信息来降低环境问题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遵循“预防性原则”,该原则在国际法领域特别有影响力,即倡导在面对重大但不确定的环境威胁时,要谨慎行事。
环境问题的多样性与法律约束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在立法工作方面,我国针对环境保护方面在建国初期曾制定过一些关于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改善环境资源的法规或规范性文件,但总体上,实践的可操作性不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来,我国着力全面清理现行法律法规中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相适应的内容,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间的衔接。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法律约束从纵向来看,法律体系越来越完整,并逐步加强法律法规间的衔接。目前我国环境法律体系以《宪法》中第二十六条“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规定为基础,成为环境立法的主要依据和指导原则。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法律约束从横向来看,在应对环境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上,法律规范逐步增加对新问题、新现象的规制。按时间顺序,法律约束从对自然保护区、噪声污染、大气污染、水污染等的规范,逐步增加对核电厂事故的应急管理、海洋环境的保护、电磁辐射的管理、排污费征收标准的划定以及新化学物质的管理等,在横向拓展其广度。
环境问题的特殊性与法律约束的普遍性之间的矛盾。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为了实现“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2],要求法律约束进一步细化、明确化、具体化。明确的法律约束主要运用于环境的监测和评估、环境行政执法、司法机关审判的客观指标、生态补偿标准、明确各个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等。在环境监测和评估方面,监测对象不仅包括生态环境,还包括对人的健康监测,更科学合理地实现对环境的监测;在环境行政执法方面,主要通过衡量或判断某个地区或流域的环境质量状况,用于考评地方政府,并监督排污单位的污染物排放是否符合标准的要求;在司法机关审理环境纠纷案件时,针对环境纠纷案件的特殊性,需要更为详细、明确的法律法规来规制;在生态补偿标准、税费征收等问题上,作为调整生态补偿关系、实现环境与资源保护的特定目的的手段,如何运用好这些调整手段需要法律的规范,多元融资渠道的建立、市场补偿机制的构建都需要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对于明确各个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综合来看,各有关环境的法律法规以规范各个主体的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总的来说,法律约束内容逐步明确化的过程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过程,为了尽可能避免等到出现了环境问题再去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被动性,就需要发挥法律约束的预防功能、调整功能,法律规范越明确具体,越能发挥更有效的功能,从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总之,为了运用好法律约束工具,处理好环境问题,一方面需要不断加强对环境问题的科学研究,以减少环境问题的不确定性、多样性、特殊性以及复杂性对法律约束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进一步细化、明确化、具体化法律约束,来切实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是党的十九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五位一体和突出地位的高度,确立“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和任务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