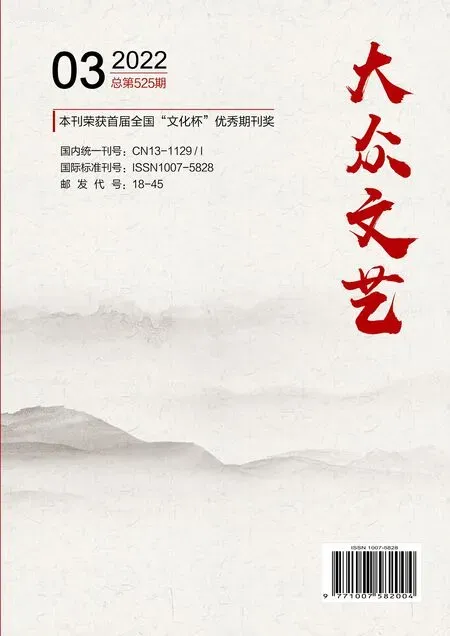类型叙事、家国主题与本土表达
——浅析香港武侠电影
(复旦大学 200433)
如果说在西方最为流行的文学作品是福尔摩斯以降的侦探小说,那么在中国曾经拥有最广大读者市场的文学类型当首推以金庸、古龙为代表的武侠文学。武侠文学中的快意恩仇、仗剑行侠、浪迹天涯与儿女情长等常见情节元素无一不承担着中国读者对于正义、自由和爱情的美好想象。而武侠电影作为武侠文学的派生物,和武侠文学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传承和影响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说,武侠小说是“源”,武侠电影是“流”,二者一同生长在中国武侠文化的这片沃土上,同时又不断地为武侠文化生产并输送着新的“养料”。
一、作为类型电影的香港武侠电影
本文对于香港武侠电影的关注,在时间范畴上主要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张彻、胡金铨、楚原等一批导演的事业黄金期(包括李小龙的功夫电影),一直到徐克的“新武侠电影”、成龙的“功夫喜剧”,再到后“九七”时代的香港内地合拍片。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的武侠小说与武侠电影双双步入极为繁荣的黄金时代,正如影评人魏君子在《香港电影演义》一书中所说:“武侠文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小说当以金庸、古龙最盛,电影则是张彻、胡金铨称雄。张彻虽多拍金庸小说,但塑造人物方面颇像古龙,动作讲求简捷有力,张扬男性阳刚之美,渲染死亡暴力美学,风格凌厉肃杀。而胡金铨则极似金庸,影片借由历史背景,服装道具,细枝末节务求俱细,风格则追求古朴凝重,透出禅学意味。”更为重要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武侠电影对后来香港武侠电影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香港武侠电影一路至今的发展格局。这里最为显见的例子当属当时香港的武侠电影导演对于后世武侠电影导演、武术指导及演员的重要影响,譬如张彻之于吴宇森、刘家良,胡金铨之于许鞍华,李小龙之于成龙、周星驰等等。正如张彻在《张彻:回忆录·影评集》一书中所写到的那样,“每个片种虽由我开始,但发挥尽致的往往不是我!我总是扮演先驱者的角色”,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武侠电影人的确起到了为后来者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或许其影像语言和情节叙事不如后起的导演所表现出的那么圆熟,但是在这一批早期武侠电影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后来香港武侠电影种种发展与变化的全部可能。而我之所以看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武侠电影,正是因为其一方面与香港武侠文学有着共生共荣的密切关系,是沟通武侠文学与武侠电影之间的关键桥梁,另一方面又可以被视为后来香港武侠片的某种源头性所在。
我们在面对“武侠电影”这一概念时,常常会遇到众多纷繁复杂且彼此相近的名称,比如“武侠片”、“功夫片”、“动作片”等等。而在我看来,如果想要真正梳理清楚香港武侠电影的发展脉络和演变趋势,从整体上把握香港武侠电影的类型特点,就不能将眼光拘泥于传统意义上的武侠片,更不必纠缠于武侠片、功夫片和动作片的琐碎概念辨析,而应该立足于一个更为广义、能够包罗万象的“大武侠电影”概念。所谓“大武侠电影”,当然包括张彻、胡金铨、徐克、李仁港等人的代表作品,同时也包括李小龙所开创的“功夫片”,成龙的“功夫喜剧”,洪金宝、林正英的“功夫僵尸片”,吴宇森、杜琪峰、林岭东、麦当雄、刘伟强、陈木胜的“黑帮片”与“警匪片”以及周星驰、王晶喜剧电影中所包含的一些“武侠元素”或“功夫元素”等内容。之所以将这些影片“熔于一炉”,是考虑到它们在情节模式和主题表达上有着一定的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即是我们所说的“类型”。借用陈平原教授在《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一书中的阐述:“类型划分绝不是给作品贴上可有可无的标签,命名仪式背后隐藏着的是对各种类型小说‘规则的体认’。”对于香港武侠电影而言,这种“规则的体认”也同样存在,它一方面决定了武侠电影之为武侠电影的根本特色,另一方面也使得武侠电影得以和其他类型电影相互区分。以成龙电影为例,成龙曾明确说过:“因为我知道喜欢我的观众,就是喜欢我拍的动作,所以任何事情我都是从动作开始”。“从动作开始”表面上看似乎意味着是从观众的市场需求开始,从成龙独特的个性特征和演员素养开始。这固然是一种迎合观众趣味与市场票房的做法,但在另一层意义上,“动作”即是成龙电影之为成龙电影的最根本特点,我们不能想象一部号称“成龙电影”的影片毫无拳脚功夫与闪展腾挪,而是成龙全篇都在和女主角谈恋爱。
类型小说和类型电影都具有其自身独特的内容、形式和创作规律,而当一种类型小说/电影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往往会在该类型内部形成更为细致的类型划分,我们可以称这些为类型小说/电影下面的“子类型”,而称其上一级的类型小说/电影为“母类型”。通常情况下,“子类型”既需要具有其“母类型”作为艺术“类型”的一般规律和要求,同时也需要形成自身独特的一套得以区分于同一个“母类型”之下其他“子类型”的内容、形式和创作规律。在这个意义上,香港武侠电影,则是一种包含了众多“子类型”的类型电影,我们前面所说的“功夫片”、“功夫喜剧”、“功夫僵尸片”、“黑帮片”、“警匪片”等等,都可以视为是香港武侠电影这个大概念之下的“子类型”,它们各有一套自己独特的类型特点(如“功夫僵尸片”必须有清代僵尸、贴符念咒、灵镜木剑等,其他武侠电影则不需要这些元素),又共同遵守着一套更大影片类型规则(如所有武侠电影都不同程度地包含了男性叙事、动作场面、暴力元素、正义担当等)。
而香港武侠电影之下的很多“子类型”,都是和其他类型影片相互融合、嫁接之后所产生的结果。比如袁和平、成龙所创立的以喜剧性动作为主的“功夫喜剧”(又有学者称其为“谐趣武打片”)就是武侠元素与喜剧元素相互结合的成功范例。正如贾磊磊在《中国武侠电影史》中所说,“这种喜剧化的处理方式,使许多武侠电影摆脱了传统的正剧面目,而换上了一种时而轻松愉悦,时而又紧张惊悚的兼容主义美学风格,即从一元化的美学体系笼罩下跳脱出来,呈现出多元化的美学风格”。又如洪金宝将武侠片、喜剧片、鬼片相结合所形成的“灵幻武侠片”和林正英进一步将武侠片与僵尸片有机组合而形成的“功夫僵尸片”也都是打破电影类型的典型代表,他们在武侠电影的基础上,考虑到大众审美需求的多元化,除了通过让人目不暇接的精彩动作来满足部分乐于此道的观众之外,还尽可能加入喜剧、鬼怪(包括僵尸)、恐怖等其他时尚流行元素以吸引和满足更广大的市场。影评人吴昊就曾指出“香港的僵尸电影只是功夫片的借尸还魂”,准确指出了这两类电影之间的内在关联。
甚至发展到最后,“类型”本身已经成为了某种“类型元素”,滋养着该类型以外的其他影片,这对于武侠电影而言,则是化身为“武侠元素”、“动作元素”或者“暴力美学”出现在其他影片类型之中(比如爱情电影、战争电影等等)。至此,香港武侠电影已经从一个独具特色的类型片,发展成为包含众多“子类型”的“母类型”电影,并最终成为了一种被其他众多非类型电影所吸收和借鉴的类型元素。
二、家国主题与本土表达
武侠电影中绝少不了动作或打斗场面,而这必然涉及到影片对于暴力的展示。那么如何在影片中合理地表现暴力则是每一部武侠电影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过分渲染暴力固然不可取,但对于武侠片而言,暴力又是不可回避的最重要元素之一。贾磊磊在《中国武侠电影史》一书中提出了五种常见的武侠电影解决影像暴力的方式,即“暴力的神圣化”(吴宇森枪战戏中的教堂与白鸽)、“暴力的伦理化”(将为民除害、为父报仇作为暴力的合理性依据)、“暴力的喜剧化”(成龙、洪金宝的功夫喜剧)、“暴力的舞蹈化”(徐克的新武侠电影、李安《卧虎藏龙》中的竹林大战、及中国自古以来“武”与“舞”之间的密切关联)、“以暴力的形式消解暴力”(牟敦芾、黄志强等人的作品)。
我们这里主要来分析香港武侠电影中“暴力的伦理化”这一条。在这种处理暴力的方式中,影片往往将对手塑造为“十恶不赦”之人或者与主人公有着“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通过对敌人的精神矮化和丑化,或者对仇恨进行强化来为复仇与暴力增加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很多武侠电影将这种“个人恩怨”进一步升级为帮派矛盾、阶级对立,乃至于民族和家国仇恨,即为施暴者的暴力行径赋予了“替天行道”、“铲除邪教”、“为民除害”、“反清复明”、“驱除鞑虏”等“神圣光环”。举一个非电影的例子,比如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一句词中充满了夸张、血腥和暴力,但因为其对象是“胡虏”和“匈奴”,似乎就变得正义凛然且合乎情理(这一逻辑不仅普遍存在于武侠小说与武侠电影之中,甚至也是后来很多革命战争小说中暴力叙事得以成立的合法性依据所在)。更为有趣的是,武侠电影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电影类型,从来都和中国形象与家国叙事密不可分。朱家昆在《香港类型电影漫谈》一书中就曾说到:“如同西部片之于美国电影,武士片之于日本电影一样,武侠片是最具中国民族特色的类型片种”。一方面在好莱坞与世界电影市场,最被广为人知的中国演员依旧是功夫明星Bruce Lee(李小龙)、Jackie Chan (成龙)和Jet Li (李连杰),而在好莱坞幕后发展最好的华语电影人也当属袁和平、元奎等一班武术指导,就连李安第一次问鼎奥斯卡也是凭借武侠题材的《卧虎藏龙》。武侠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电影乃至中华民族在全世界观众面前的形象,当然这一形象更多地还是借助视觉奇观的塑造来完成的(充满中国风意蕴的山水风光、清代武人的装束与辫子、充满了奇幻色彩的轻功等等)。而武侠电影中的深层叙事逻辑(“暴力的伦理化”)与其在世界市场上展示中国形象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某种二律背反。
当我们将这个二律背反放置在香港武侠电影中进行观察时,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香港武侠电影中一再被有意或无意涉及到的自我身份认同与反思问题。如同谭以诺所说“香港武侠电影最能直接纾解现实中政治上与经济上凶险与纷乱”。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张彻的“武打片”往往以“反清复明”言志;到李小龙的电影(《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江》)等脱离国家概念,进入华人范畴,以受压迫者的姿态给压迫者以反击;再到成龙的《警察故事》系列中塑造的香港警察以守护香港本土为最高职责……香港武侠/功夫/警匪电影对于香港自身身份的思考与定位从未停止。而在徐克的一些“新武侠”电影中,这种思考似乎更为深入,从表层的影片形式与故事,深入到了内在的文化隐喻和身份探讨之中。从徐克、李连杰的《黄飞鸿之狮王争霸》中,黄飞鸿京城舞狮、血战夺魁之后也只能黯然退回广州固守东南一隅;到《新龙门客栈》里,原本地处边陲做生意的龙门客栈被迫卷入来自中原的政治纷争,最后张曼玉所饰演的老板娘烧掉客栈,西出阳关,无不充满了“九七”前香港人对于自身身份的思考与对自己未来生活的选择。(富有意味的是,到了续作《龙门飞甲》中,陈坤扮演的风里刀和桂纶镁饰演的番邦公主没有选择策马西去,退出江湖,而是决定回到皇宫,毒杀万贵妃)
到了“九七”回归后,香港“武侠电影”依旧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现着时代的变化并表达着电影人对于时代变化的思考。甄子丹版的叶问并不像以往电影中陈真、霍元甲以抵御外辱,奋起革命为志向,影片中叶问的出手几乎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和捍卫自己的生活,甚至于曾经年轻有为、意气风发的青年黄飞鸿形象至此已经变成了“人到中年”的叶问(香港电影中的黄飞鸿多为青年形象,而叶问则多为中年形象);陈可辛的《十月围城》中,影片围绕商人李玉堂如何进入权力和历史的角逐而展开,武功在这部电影中只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在影片最后更是不得不被知识和财力所取代,走向黄昏落日般的终结。其实,不论是叶伟信、甄子丹的《叶问》三部曲,还是陈可辛的《武侠》,抑或是苏照彬的《剑雨》,传统香港武侠电影中侠义恩仇的江湖故事都纷纷让位于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表达,曾经终日仗剑行走江湖,到酒馆大声问店小二要二两好酒一斤熟牛肉的侠客们,现在也纷纷开始为房租、孩子的学费、甚至全家的口粮以及鸡毛蒜皮的家长里短而犯愁。
从颇具民族隐喻的霍元甲拳打西方大力士,到叶问为维护亲人出手或者为了生计被迫开拳馆,香港武侠电影消解暴力的方式和动机转变的背后是香港电影人对于时代与自我身份的体认和反思。而更大的时代挑战可能是,武侠电影本身正在不断受到冲击,武打场面与暴力影像在新一代武侠电影中慢慢被取代,转而发展成对权力与人性的拷问(如路阳的《绣春刀》),或者是对逝去的江湖规矩的想象(如徐浩峰的《师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