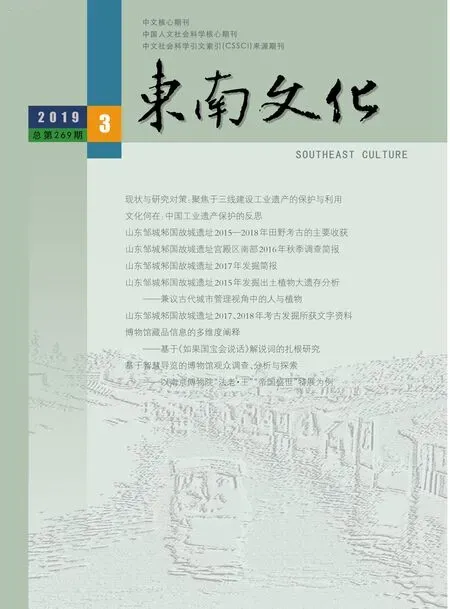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2015—2018年田野考古的主要收获
王 青 路国权 郎剑锋 陈章龙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内容提要: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省邹城市南10公里的峄山南麓,是东周时期邾国的都城所在和秦汉以后邹县县治。2015—2018年,山东大学邾国故城遗址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田野考古工作,主要包括城墙、宫殿区、仓储区和贵族墓葬的发掘解剖,及冶铸和制陶作坊区的调查等,出土了大批考古遗存,为研究邾国历史和山东南部地区东周秦汉文化面貌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邾国是山东地区周代的重要诸侯国,据《左传》《世本》《史记》等文献记载和历代考证,邾国为陆终氏的后裔曹安(晏)所建,晚商时期,周武王克商后封曹安的五世孙曹侠于陬(约在今山东曲阜东南)。据《左传》记载,鲁文公十三年(公元前614年)“邾文公卜迁于绎”,即春秋中期偏早邾国将都城迁到了“绎”,地在今山东邹城市峄山南麓的邾国故城遗址。战国晚期,邾国灭于楚,秦时以其地置邹(驺)县,汉代以后因之。邾国与鲁国南北紧邻,分别是孟子和孔子的诞生地,邹鲁成为山东古代文教兴盛之地,历代留下的文化遗存非常丰富,是鲁南地区的重要代表。自清代以来,该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和陶文就见于有关金石学著录,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曲阜鲁故城、滕县薛故城和庄里西贵族墓地开展了大规模勘探和发掘,鲁南地区的周代考古进入正式的田野阶段。21世纪以来陆续发现了枣庄东江小邾国墓地和徐楼东周墓葬,近年又有滕州大韩东周墓地的重要发现[1],预示着鲁南地区周代考古将进入新的阶段。2015—2018年,山东大学联合邹城市文物局在邾国故城遗址开展了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收获。其中有些发掘资料和成果已先期发表[2],其他资料和研究成果也将陆续发表。本文现对2015—2018年邾国故城的田野考古主要收获做一概述,希望这些成果能为鲁南地区新阶段的考古研究做些贡献。
一、邾国故城遗址及田野工作概述
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省邹城市南10公里的峄山镇峄山南麓纪王城村周围,还包括峄山街村和金张庄村等(图一)。遗址中心点坐标为东经117°1 1 ,北纬35°18 30 ,海拔102.5米。遗址地处丘陵地带,北枕峄山,南依廓山,东有高木山,西为平原,季节性小河金水河自东北向西南穿城而过,整体地势为向西开放的小盆地。遗址周围诸山以前震旦纪形成的花岗片麻岩为主,偶见石灰岩,表土为含较多砂粒的黄褐色砂土,峄山南麓坡下有较厚的黄土堆积。城址平面近似长方形,周长约9680米,面积约6平方公里(含北墙以北的东、西墙)。城址中部偏北有一处略呈方形的高台地,面积近17万平方米,俗称“皇台”,钻探发现有成片夯土建筑基址,可能是宫殿区所在。城址北部为贵族墓地,已探明包括甲字形大墓在内的墓葬20余座。城内金水河两岸发现有陶范和炼炉遗迹,推测为手工业作坊区,城外西南角发现多处陶窑,推测为制陶作坊区(图二)。城址自春秋中期作为邾国都城使用,秦汉以后是邹(驺)县县治,北齐文宣帝天保七年(556年)治所迁至今邹城市区岗山一带,该城址遂逐渐荒废。邾国故城的使用时间约1100年,其中作为邾国都城有330余年。明清以来陆续有村庄迁入,城址西部现为村庄占压,其余大部为农田,局部有果树林和柏树林,整体保存状况较好。
清代以来,该遗址就以出土大批陶文而著称,陈簠斋、王献唐等都有著作行世,王献唐还曾亲赴该遗址实地考察陶文的出土情况[3]。1964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邹县文管所对该遗址做了首次考古调查,并根据出土的陶文认定遗址为邾国都城所在[4]。1980年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东队和邹县文管所又进行了复查,对该遗址十余年来采集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等做了集中报道[5]。1977年,邾国故城遗址被列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现状保护较好,包含的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历年采集出土了大批各类文物,其中仅陶文就有3000余件(现藏邹城博物馆等),但该遗址一直未经正式发掘。
2010年,邾国故城遗址被列入国家“十二五”100处大遗址保护工程和山东省考古遗址公园重点建设工程。2012—2013年,鲁南测绘院对该遗址进行了全面测绘,山东省海岱文化遗产保护咨询服务中心对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勘探,并编制了《邾国故城遗址保护规划(2013—2032)》。通过以上工作,我们基本摸清了城址的保存现状和布局情况,为下一步的田野考古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2014年山东大学邾国故城遗址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地面勘察和初步分析,在此基础上制订了该遗址的《田野考古计划书》,并经国家文物局审定批准,由山东大学承担邾国故城遗址为期12年(2014—2025)的田野考古项目。
2015年春夏考古队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2016年对皇台及其以南地带进行了大面积勘探和系统调查;2017年春夏在勘探基础上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同年秋对皇台进行了再次重点勘探;2018年春夏对西城墙进行了解剖发掘,夏季对金水河两岸的冶铸区和城外西南角的制陶区做了大面积调查,同年秋冬对北城墙进行了解剖发掘,并在贵族墓地西南角发现两座甲字形大墓,抢救性清理发掘了一座(M1)。2015—2018年持续开展的田野考古工作累计发掘面积近4500平方米,勘探面积20余万平方米,调查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图二)。为了保证田野工作的科学、规范进行,考古队在鲁南测绘院制作的遗址平面图基础上,以遗址西南角为总基点,以400×400米为一个工作大区,共划分出63个大区将遗址全面覆盖,每个大区再分为16个1万平方米的正方形小区。运用RDK定位技术,将各工作区准确落在遗址地面实处,每次实地工作时首先明确所在工作区的位置,并按照坐标系法编号和布方,出土遗存也以RDK技术及时定位和记录。
二、田野工作主要发现与认识
1.城墙和壕沟的解剖
城址的城墙与壕沟大部保存较好,平面为不规则长方形,其中西墙长2940、北墙长1920、东墙长2700、南墙长2120米,西、北、东三面城墙外设有大致连贯的壕沟。城墙和壕沟的修建与走势均较好地利用了周围的地形地貌。西墙建于平原开阔地带,应是城址对外联系和防御的重点,建筑质量和保存现状最好,宽20~30米,现高多在3~4米,最高处约7米,以砂土夯筑而成,夯层明显,每层厚8~12厘米。东墙建于低矮的高木山山脊之上,也以砂土夯筑而成,夯层明显。东西两墙的北端均与峄山山坡相接,将峄山南麓纳入城内,显然是北以高大的峄山为天然屏障。北墙位于峄山脚下、皇台以北,只有东西两端残存高约1米,大部已因早年取土破坏而地面无存,勘探表明地下部分仍较直较宽。东西两墙的南端与南墙相接,南墙沿较矮的廓山山脊修筑,以砂土和文化堆积土混合夯筑(局部堆筑),较矮较窄,山脊低谷处可见石块砌筑,局部还可见向南突出的马面或瓮城迹象。诸城墙均发现几处缺口,是寻找城门的重要线索。
2018年对西城墙和城壕北部、北城墙和城壕中部进行了解剖发掘,分别开150×4米、110×5米探沟一条(TG1、TG2),发掘面积1150平方米。其中西城墙探沟TG1还清理灰坑3个、水井2口、墓葬6座、灰沟1条、灶3个(彩插一︰1、2;彩插二)。根据层位关系和出土陶片,西城墙及城外壕沟的兴废过程整体可分为三个时期:春秋中晚期为初始时期,出有陶瓮、盆、鬲等残片,城墙采用堆筑法,未见明显夯筑痕迹;战国至汉代为使用扩建时期,出有瓦、盆、罐和铜镞等,城墙为版筑而成,可见明显的单棍夯打迹象,夯窝直径4~5厘米(彩插一︰2);汉代以后为废弃阶段,堆积较薄,出土少量瓦、罐等陶片。第一期的年代与《左传》等文献记载的邾文公“卜迁于绎”的年代大致相当或略晚,第一、二期的墙体外侧发现大量铜镞(图三),铜镞质量较好,均为窄身长铤三棱镞,年代应在东周时期,从侧面印证了文献记载的鲁国等国曾多次攻入邾城的史实。另外,在一件汉代陶盆的口沿(2018J2①︰7)上发现一个戳印的陶文,初释为“闳”字,可能与巷门或城门有关(彩插二︰5)。
北城墙在现地面已大多无存,TG2发掘表明,城墙于地下残高1~2、底部宽约25米。发现有基槽、夯窝、柱洞等遗迹,墙体夯筑质量较好,夯窝分布密集,夯层比较均匀,每层厚度基本为10厘米(彩插一︰3)。底部挖有基槽,内铺有规律排列的大石块,用于加固城墙外侧(彩插一︰4)。基槽直接打破生土,为质地坚硬的红褐色粗砂土。还清理灰坑18个、墓葬8座、灰沟8条、水井1口、陶窑1座、灶1个。其中石椁墓、土坑墓各1座,瓮棺6座,随葬品较少,年代为汉代。灰沟在墙体内侧和外侧均有分布,与墙体基本平行,出土陶片较多。根据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可知城墙应建于汉代,部分灰沟与城墙同时,应属于内壕和外壕。这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结合东、西城墙到汉代仍在使用,而且东城墙的东南角呈内折直角形状,疑似有向西延伸构成南墙的迹象,很可能汉代时把东周邾城的南北城墙取直改建,将城的面积缩小以符合作为汉代县城的规制。类似情况在曲阜鲁故城和临淄齐故城遗址都有存在[6],具体还有待今后继续工作。
2.宫殿区皇台的发掘
宫殿区皇台位于城址中部偏北,为高出现周围地表3~5米的高台地,平面略呈方形,东北部略外突,面积近17万平方米。表面较平整开阔,从北向南逐渐倾斜,散布有大量陶片和砖瓦。2016、2017年对皇台进行了全面的重点勘探,发现数十个夯土基址,年代多为汉代,少数为东周时期。其中夯17位于西南角,开口距地表1.2米,平面呈长条形。夯土宽约15、长64、厚约0.4~1米,夯层厚10~15厘米,夯实较致密,初步推断可能与门塾有关。多数基址的外围发现有宽2~3米的窄墙,但分布不连续,应为各建筑院落的垣墙,暂未发现宫墙。台下西、南、北三面发现有壕沟(壕1—壕3),中部偏东有一道南北向壕沟(G3),大致将皇台分为东西两部分。南面壕沟的南侧发现有东西向道路(L1),延伸较长,长360、宽3.5米。西端连接一条南北向道路(L2),延伸近100米。通过勘探还发现,皇台的原始地貌为一个高出周围地表数米的土丘,后经人工将四周边缘地带修整堆平,成为一个平阔的大高台。
2017年春夏选择在皇台中部偏北发掘(F3工作区),共开5×5米探方19个,发掘面积近500平方米。此区域文化堆积平均厚1.5~2米,遗迹比较丰富,但破坏较为严重,清理各类遗迹300余个,包括灰坑、沟渠、房址、墓葬、水井、窑炉、灶以及部分柱洞等遗迹。出土大批遗物,如陶器有鬲、盂、豆、罐、盆、釜、缸、瓦、瓦当、砖等,年代多属春秋、战国和汉代,另有少量北朝至隋唐时期文化遗存。在发掘区东西两侧发现2座战国时期的窑炉(YL1、YL2),局部被晚期灰沟打破,每座长近10米,残留10余个直径数十厘米的圜底小灶一字排开,每个小灶下与一个拱形火门相连,周围堆积较多红烧土粒,并发现少量铜渣,推测窑炉与冶铸某些小型铜器有关。另在一眼西汉水井(J3)的废弃堆积底部出土了8件新莽铜度量衡器,包括权衡器一套5件(衡杆1、环权4)、诏版2件、货版1件,都有数量不等的铭文,其中诏版、石权和衡杆上为内容相同的81字完整诏书,应铸造于新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对研究王莽托古改制和我国度量衡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7]。推测周围应有度量衡器掌管机构的官署建筑,此官署的职能应与农业有关,其主管的范围应包括皇台下西南部的仓储区(下详)。综合分析,2017年的发掘区在战国时期应是官营冶铸作坊区,汉代则为官署区的组成部分。
3.贵族墓地的发掘
贵族墓地位于城址北部,南起皇台北壕、向北延至峄山脚下,地势由北向南逐渐降低,土质为较深厚的黄土,东西两侧的黄土略高形成南北向高岗,俗称“东岗”和“西岗”。地表现为果树覆盖,有数道深浅不一的南北向冲沟,局部有从峄山上滚落的大块岩石。勘探表明墓葬分布比较密集,墓地中部至少已探明22座,填土较深并多经夯打,有些探孔中发现了铜锈和朱砂痕迹。部分为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规模较大,还有部分墓葬比邻成组分布,可能是并穴合葬。墓葬年代初步推断多在东周时期,很可能是邾国贵族的“公墓地”,另在墓地的东西两侧岗地断崖上发现疑似宽约2~3米的夯土堆积,是否存在陵园垣墙有待进一步工作。
2018年秋冬在墓地西南角(G3工作区)的取土坑断崖上发现墓葬迹象,初步勘探表明是两座南北并列的甲字形大墓(外围似绕有一圈兆沟),编为西岗墓地M1和M2,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对其中规模较小的M1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墓为带一条东向墓道的甲字形竖穴土坑墓(下部穿凿岩层),墓向106°,全长25.13米,其中墓道长18、宽4.4米,墓室东西长7.13、南北宽6.5~6.6米,墓底东西长6.1、南北宽5.5~5.9米。填土经夯打较硬,墓壁修整平滑,墓室北壁和南壁基岩上分别凿有两组三个柱龛,南北对称,龛底和龛顶基本处在同一水平面,柱龛对应的墓室二层台面四角发现四个柱洞。葬具为重椁重棺,墓主经鉴定为成年女性,仰身直肢,头向东,腰部随葬两件龙形玉佩(图四),口内含有一件玉环。椁室外南侧设置一个器物箱,西端未被扰动,残存印纹硬陶、原始瓷、泥质灰陶、贴金漆器、兽骨等(彩插三︰1;封底)。墓室被盗严重,盗洞D1紧贴墓室西壁直下椁室;盗洞D2打破椁室东南角和器物箱,底部出土较多原始瓷、印纹硬陶和泥质灰陶片,大多数可以拼对复原。墓主人牙齿经测年为公元前493—前406年(校正后)。出土的原始瓷器、印纹硬陶和玉器与浙江无锡鸿山邱城墩M1战国早期越王墓出土同类器形制基本相同[8]。多件典型越国风格的原始瓷器和印纹硬陶的发现,反映出邾国上层贵族与越国有密切交往,也与此时越国国势强劲、北上称霸中原的史实相符。综合判断墓主人应为战国早期邾国国君夫人,不排除此墓墓主人来自越国的可能性。
4.仓储区的发掘
2015年春夏的第一次考古发掘,选择在文化堆积较厚的皇台西南约400米处(E3工作区),共开5×5米探方36个,发掘面积930平方米。此区域文化堆积厚2~3米,共清理各类遗迹700余个,以灰坑为主,另有少量水井、墓葬、房址、窑炉等;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主要包括鬲、豆、罐、瓮、盆、板瓦、筒瓦和量器等,部分陶器戳印或刻划有陶文,数量达200余个。遗存年代分属于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为建立该遗址的文化序列提供了丰富的基础资料,其文化面貌春秋时期与薛地接近,战国以来与鲁地趋同。灰坑可分为圆形和方形两种,个体较大,直径或边长普遍在2~3米之间,周壁和底部加工规整,有的底部残留有谷物朽灰。其废弃堆积包含大量板瓦和筒瓦,及少量小陶鸟,推测应与储粮设施的顶部建筑有关。结合有关文献记载推断,圆形和方形灰坑很可能分别是囷类和仓廪之类储粮设施的下部建筑[9]。采样分析表明,植物遗存中谷物以小麦为主,占有绝对优势,另有少量粟、黍、大豆等;动物遗存中老鼠的数量从东周时期至汉代逐渐增多,尤其在汉代时数量增加明显。综合判断2015年的发掘区应属于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官营仓储区[10]。
此次仓储区的发掘集中出土了十余件较完整的陶量。其中多数年代属于战国时期,泥质红陶或灰陶,形制为厚胎深腹筒形,应是粜籴谷物的量器,内底多戳印团龙标记,其中1件的口沿上还戳印“邾”字(H623④︰9)(图五︰1),另有几件配套使用的红陶罍肩部也印有“邾”字(H623②︰12、H623②︰13、H623③︰8)(图五︰2—4),这是“邾”字陶文在该遗址的首次发现,以出土的自证性文字材料印证了遗址至少在战国时期为邾国都城所在。而且,对出土陶量、陶罍测量尺寸、容积后所分析的量制与文献记载的齐国量制基本相同,说明这些量器应是由官府发行的,具有重要研究价值[11]。另外还发现1件秦代戳印“騶”字的陶量,形制为浅腹盆形,与该遗址早年出土的几件秦诏版陶量基本相同。
5.其他区域的调查
根据勘探结果和地表植被状况,2016年秋季对皇台以南、跨越金水河两岸面积10万平方米的窄长方形区域进行了系统调查,并对区内地表陶片全部采集,资料整理和统计分析表明,地表陶片的种类和密度均存在差异,与勘探结果的关联性尚待进一步分析确定。几次勘探表明,皇台以南的金水河两岸存在密集灰坑和炼炉遗迹,应是手工业作坊区。2018年夏,为配合金水河两岸的整治改造工程进行了调查,调查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在金水河北岸发现十余件铸造铜剑和铜戈的陶范(戈形属于战国时期),可见明显的高温烧烤和施抹脱范剂痕迹(彩插三︰2);另有陶水管和炼炉残迹,表明这一带应为冶铸区,应有官营铸造兵器作坊存在。另外,在城外西南部的勘探发现了至少4座陶窑,陶片散布面积数万平方米,应是制陶作坊区。2018年夏也对这里进行了调查,调查面积4万平方米,地表采集物以板瓦、筒瓦为主,另有陶鬲、罐、豆、盆、瓮等,年代多为战国至汉代。
三、总结与思考
四年的田野工作基本搞清了邾国故城遗址的年代和布局方面的整体情况,并对城墙和壕沟、宫殿区、仓储区及贵族墓地做了抽样式发掘,对手工业作坊区、冶铸区和制陶区进行了地面详细调查,掌握了局部区域的详细堆积信息和特点,为今后的田野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取得了一批阶段性发现和成果。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该遗址的面积巨大,内涵非常丰富,堆积也十分复杂,今后的田野工作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
结合已取得的成果和《田野考古计划书》的进度安排,今后一段时间将有三个工作重点:一是厘清不同时期各功能分区的准确年代和分布范围,包括寻找城门等设施、宫殿区是否有宫墙环绕、贵族墓地是否有陵园垣墙、仓储区和手工业作坊区是否存在围垣等,这些都是城市考古的基本要求;二是继续发掘各功能区的重要遗存,包括宫殿区的夯土基址、贵族墓地的成组大墓、手工业作坊区的作坊遗迹等,以厘清不同时期重点遗存之间的相互关系、聚落形态和布局演变等问题;三是配合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做好遗存的保护和展示工作,在公共考古方面继续做些探索和尝试。
[1]a.尹秀娇、王琦:《枣庄东江东周贵族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海岱考古》(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b.枣庄市博物馆等:《山东枣庄徐楼东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1期;c.刘延常等:《山东滕州大韩东周墓葬群》,《大众考古》2018年第8期。
[2]a.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等:《山东邹城市邾国故城遗址2015年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3期;b.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山东邹城市邾国故城遗址2017年J3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8期;c.王青等:《山东邹城市邾国故城遗址新莽铜度量衡器的初步研究》,《考古》2018年第8期;d.刘艳菲等:《山东邹城市邾国故城遗址首次发现“邾”字陶文》,《中国文物报》2018年7月27日第6版;e.刘艳菲等:《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新出陶量与量制初论》,《考古》2019年第2期。
[3]a.清·陈介祺:《簠斋藏陶》,稿本,又见氏著《簠斋论陶》(陈继楑整理),文物出版社2004年;b.王献唐:《邹滕古陶文字》,山东省图书馆拓本,1934年,山东博物馆藏。
[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邹县滕县古城址调查》,《考古》1965年第12期。
[5]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邹县古代遗址调查》,《考古学集刊》第3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6]a.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阜鲁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b.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齐故城》,文物出版社2013年。
[7]同[2]b、[2]c。
[8]a.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研究所等:《鸿山越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b.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研究所:《大越遗珍:鸿山越墓文物菁华》,文物出版社2008年。
[9]如《吕氏春秋·仲秋》高注:“圆曰囷,方曰仓。”《荀子·荣辱篇》杨注:“圆曰囷,方曰廪。”
[10]同[2]a。
[11]同[2]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