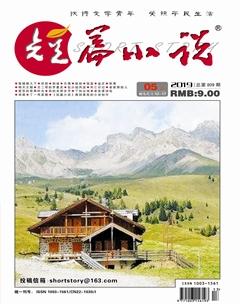无情
苏薇
苏杭在消失了三年之后,终于出现了。
他现在不叫苏杭了,他叫“无情”。四大名捕里的那个面色苍白,肌肤胜雪,外表温润如玉的老大。手持一把山河扇,冷酷内敛,以暗器和轻功闻名天下。眼神落魄而深邃,眉宇悲憤而忧郁,一生为情所困,未能真正无情,又不能洒脱忘情,最终,只能将自己的内心完全地封闭起来。
秦小西是在七月底知道苏杭的下落的,她回老家看父母,听母亲说,苏杭在一个景区当演员,演无情。有人认出是他,言辞凿凿,绝对是他。母亲当然不知道无情是谁,她接着说,其实,老早就有人见过他,少说也有一年多了吧,就是拿不准。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秦小西很生气。她突然感到委屈极了,压抑了太久的悲伤终于造了反,她扶着墙,慢慢蹲下身去,捂住脸,头抵在膝盖上,听着泪水从指缝间唏嘘着坠落,好半天,才喃喃地说,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
瞧你那点出息,我这不是不能确定吗?母亲停下手里的活,不满地说。她在整理旧衣服,她手里拿的正是苏杭穿过的银灰色衬衣,我也惦记他啊,你以为就你一个人关心他?我养了他几年,不比你心疼他?
母亲说得没错,苏杭是姑姑家的孩子,小时候,姑姑姑父都在铁路上上班,苏杭就寄养在秦小西家,从十岁到十五岁,直到该上高中了,才回到父母身边。苏杭懂事、善良,话不多,还聪明,深得父母的喜爱。长得也漂亮。苏家的男孩子都很漂亮,是那种经得起推敲的漂亮。
母亲又絮絮地说了很多,秦小西一句也没听进去,只听见了最后一句,你明天去一趟吧,看看到底是不是他。
这天真热,天气预报说,银城气温创历史新高,连续几天稳稳地停在40度。空调的风吹得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秦小西就坐在空调正下方,还是止不住地冒汗。她不停地在擦汗,心里充满了生无可恋的恐惧。她想起一些遥远的事情。
她想起了十年前的苏杭,五年前的苏杭,三年前的苏杭,又忍不住猜测起现在的苏杭。
十年前的苏杭,二十二岁,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大型的船舶制造厂。喜欢银灰色。他的衬衣永远是银灰色,有种苦尽甘来的厚重。他从技术员干起,一步步地做到高层。那几年,他几乎就生活在厂子里,下了班也不走,将车间里不用的机器拆了装,装了拆,反反复复,直到闭着眼睛都能把一枚螺丝准确无误地装上去。好样的苏杭,只用了短短五年的时间,就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苏总。那时的苏杭,如匹野马,一千里不够驰骋,他要万里纵横。变成苏总的苏杭去了一趟东北,具体去的哪里,他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就是那一次,改变了他的一生,他的腿被严重冻伤。
秦小西不止一次地问过他,苏总,到底怎么回事啊?
苏杭眯着眼睛站在五月芬芳的阳光下,只说了一句话,我只想做个问心无愧的人。
那时的苏杭还喜欢音乐,一把吉他弹得活色生香。他还会写词,秦小西很喜欢其中的几句:梦啊,破碎了,整理衣衫再出发。归鸦,家在哪?小桥流水无牵挂。不肯回头的河流啊,别哭了。就让我为你守住太阳,就让我为你挡住寒凉,就让我为你披荆斩棘一路去闯……
秦小西又问他,苏总,你看你步步高升财源广进,何以写出如此伤感的歌?
苏杭就笑笑,不说话。
当时的秦小西,无论如何想不到,五年后,这位才貌俱全的苏杭,会成为“无腿行千里,千手不能防”的无情。书上说,无情苍白如雪,面无表情,心思缜密,出手狠辣,但真正的内心却是外冷内热,面冷心慈。秦小西心里突然一阵害怕,她害怕生活再次跟她反目成仇。
你没事吧?母亲问。
没事,没事。秦小西闭上眼睛,她看见那个浅灰色的小瓷瓶在一点点放大,把她像个妖怪一样收了进去。
如果真是他,那他为什么不来看看我?他真把我给忘了?母亲还拿着苏杭的衬衣,她反复地想把它叠好,可怎么也叠不好。
大概是吧。秦小西心不在焉地说。
说完,她就掏出手机,报了那个旅游景点的团。一日游。临城,云水湾,武林风云汇。红包发过去了,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也都发过去了。明早五点,银城游泳馆门口集合。秦小西做完这些,心里像驻扎了一个不可预知的阴谋一样不安,她不知道,现在的苏杭,是否依然是个问心无愧的人。
苏杭的一生都像一个迷雾重重的赌。和自己赌,和命运赌,和时光赌。
第二天一早,秦小西就全副武装地上了车,她带了把伞,还带上了苏杭送给她的小瓷瓶,一只浅灰色的无脚鸟,据说是仿宋代的官窑。
路上,导游说,高速预计两个半小时就到,进入景区自由活动,无导游跟随。大家先看节目单,全天都有表演,每个演出场地都不远,计算好时间,可以穿插着来看。最后,特别强调,什么都可以不看,四大名捕系列绝对要看,否则你就白来了。又说,其中,《四大名捕之无情》是最好看的,全程武打动作全部是真刀实枪,主演无情也是最帅的。
车里一阵唏嘘,秦小西默默地听着。窗外,天阴了下来,一片接一片待开发的荒地,无着无落的空旷。她感到心底有股悲伤,不断撞击着肺腑,疲惫不堪又无处可遁。
到景区的时候,天阴得饱满,湿闷的空气风雨欲来,秦小西找到《四大名捕之无情》演出地点,距演出开始还有五分钟时间,她找了个座位坐下来,心里紧张极了,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演员进场的铁门。
音乐响起来了,最先出场的是两个穿着橙色长衫的侠客,接着是手持拂尘、一袭黑衣的叫什么的师太和四大名捕的师父诸葛神侯。接着,铁手、追命、冷血,都出场了,均是一袭蓝衣,个个英姿勃发,几个漂亮的武打动作,如行云似流水,精彩极了。
大概五六分钟后,无情终于出场了。
他坐着轮椅,手持一把紫色的折扇,白色的衣,墨色的发,冰冷的脸,在阴沉沉的天空下,黑色更显著,白衣更夺目,黑白分明,荡气回肠的俊逸。他潇洒地摇了摇手中的折扇,冷冷地说,你说得很是轻巧,我们之间隔着数条人命,这笔账,该怎么算?内敛的嗓音,听上去却霸气十足。
秦小西心头一热,这声音太熟了,没错,他就是苏杭。她站起身,努力想看清苏杭的脸,可离得有点远,只看见他的脸比以前黑了,瘦了,还有种说不清的巨大的陌生感。
秦小西什么也没看进去,她循着这个陌生感,又想起一些事情。五年前,苏杭从东北回来没多久,腿就间歇性地不听使唤了,时好时坏。听说那里冬天冷得让人绝望。苏杭对此事一直讳莫如深,只说是冻伤的,可医生说,是在受伤后又冻伤的,冻伤不是主要的。回来后的苏杭,一直断断续续地跑医院,用过的膏药能装满几大箱子,还做过针灸,身上扎满了针,像只大刺猬。这严重影响了他的工作,他主动辞了职,一心一意地治疗腿,希望有一天,桑田沧海奇迹出现。他用了两年的时间,终究是没有治好,走路变成了一高一低。曾经玉树临风的苏杭,无法接受命运给他穿的这个小鞋,他一天天地颓废下去,整日喝酒、打牌,灵魂被抽调到了另一个世界,内心的阴霾越积越多,他选择了自杀。
那天,刚下过一场特大的雪,据说是银城二十六年来最大的一场雪。
他没有死成,他掉到了一个雪人的怀里。那是一个超级大的雪人,据说是一群老同学聚会酒足饭饱后,突然心血来潮,在苏杭家楼下堆了个大得足有一层楼高的雪人,结果,这个雪人救了他的命。
苏杭,知道无脚鸟吗?这是秦小西在病房里见到苏杭后,问的第一句话。那是一个安静的中午,雪已经化得差不多了,空气寒冷而妖娆。
不知道。苏杭冷冷地说。他的脸白得诡异,眼里的冰冷参差不齐。
秦小西说,传说中有一种鸟,它天生就没有脚,只能够一直飞,一直飞,飞累了就在风里睡觉,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就是它死的时候。你送我的那个小瓷瓶,就是无脚鸟。
别扯那么远,我不想听。苏杭目光越过秦小西的头顶,看向电视。那里正在举行一场葬礼,逝者的黑白遗像年轻而英俊。
秦小西起身关掉电视,病房里突然有种深入人心的静。
一阵又一阵的掌声,秦小西不得不看向场地。
一群人打得很是热闹,只有无情从容地摇着扇子,气定神闲的样子。突然,他轻收折扇,衣袖微动,数枚暗器夹着呼啸的风声,从他的指间飞出,场上几个人应声倒地,挣扎了几下,就不动了。接着,音乐再次响起,所有的演员都聚在场地中央,向观众鞠躬答谢,整个演出就结束了。
无情被推走了,秦小西从拉着的隔离绳下面钻了过去。苏杭!她大叫一声。
没有人停步,也没有人回头。秦小西慌忙跑过去,拉住苏杭的袖子,苏杭,我是小西啊。
几个演员停了下来,都看着她,秦小西只好尴尬地对这群古装人解释,我是他妹妹,我来看看他。
你是谁?苏杭拉过自己的袖子,脸上木木的。
秦小西大吃一惊,她俯下身,盯着苏杭空洞的眼睛,再次申明,苏杭,我是小西啊。
我不认识你。苏杭面无表情地说。他没有看秦小西,扭头对推他的少女说,我们走吧。
秦小西一时不知所措,她拉着苏杭的袖子不放,跟他们一直走到演员入口处,被一个高大的门卫给拦住了。游客不能进入,都退到隔离线以外,别影响演员们休息。
我是他妹妹。秦小西对着门卫说。
我不认识她。苏杭也再次申明。他看着前方,声音像被压缩了一样,又冷又硬。
他不认识你,你没听到吗?门卫好脾气地说,快走吧,演员们还要休息,互相理解吧。
我有身份证。秦小西放开苏杭,慌忙在包里找身份证。
哎呀,你别找了。门卫很迁就地笑笑,身份证只能证明你自己的身份,能证明你是他妹妹吗?快别捣乱了。
秦小西茫茫然地站着,心底生出一种无言以对的悲凉,天空浓云翻滚,归去来兮。
明天吧,你明天再来吧。推轮椅的少女说。她穿着一身水绿色古装,在剧里好像是诸葛神侯的女儿。
那我怎么才能找到他呢?秦小西转向少女。
你記下我的电话吧,到时候再联系。少女同情地说。
苏杭被推走了,秦小西退回到隔离线以外。她盯着那个铁门,短短几米远,却像隔着半壁江山,一世红尘。她看了看节目单,努力想找一个感兴趣的节目,好打发这漫长的中午。可所有的演出都排到下午三点以后了。游客陆续散去,最后,只剩下秦小西和另一个带孩子的女人,还停留在场地。
秦小西在一棵大树下坐下来。
那个小孩跑过来,坐在秦小西身边,咬着手指头看着秦小西。一会儿,女人也坐了过来。
你们怎么还不走?秦小西问孩子。
女人笑笑,我们家就在景区外面,每天都来,这孩子,就喜欢看这个无情。
你们很熟悉他?秦小西试探着问。
是啊。女人说,我们看了他好几年了。
他是谁啊?我是说,演无情的这个人你们熟悉吗?秦小西紧张极了,她拉过孩子的小手,握在自己的两只掌心里。
知道的。女人说,他在这里很有名,是这个景区里演得最好的。但现在不行了,听说脑子出了毛病,经常忘事。不过还好,这个无情还是能演下去的。反正就那么几句台词,几个动作,我孩子都记住了
秦小西无力地靠在树上。四周越来越暗,空气闷热得让人窒息,一切都透着无法掩饰的荒凉。她松开孩子的小手,把头埋在自己的臂弯里。她觉得自己被捉弄了,现实跟她开了个不现实的玩笑。她脑子也出了毛病,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苏杭,医院里与死神擦肩而过的苏杭,给她无脚鸟只说了一句话的苏杭,还有,刚刚见到的这个,杀手一样冷酷无情的苏杭,她无法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这些真假难辨的苏杭,此刻,都围坐在她的周围,遥远而深刻地看着她。
那他是怎么变成这样的,你知道吗?好半天,秦小西才抬起头,虚弱地问。
听说是练习的时候,碰到了这里。女人指着自己的头,打打杀杀的,也挺不容易的。
那景区也不管吗?他们该负责的啊。秦小西的声音突然提高了,指着那个铁门,激动地说。
景区是赚钱的。女人被吓了一跳,也站起来,牵起孩子的手,准备走了。又看了眼秦小西,叹口气说,听说他家里从没有人来看过他,谁管呢。
女人走了,她最后的那句话,彻底地击中了秦小西。她觉得苏杭被抛弃了,她,她父母,所有的亲戚朋友,他们集体抛弃了他。他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是他们集体犯下的错,他们都该为这个错误买单。中午,女人带着孩子走了,这里就只剩下秦小西一个人了。她感到自己也被抛弃了,被命运抛弃了,被那个他抛弃了。
她低下头,用手捂住了眼睛。
半年前,那个他,从这个世界一下子跳到了另一个世界,没有跟她道再见。
十年来,他每天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给她发“早上好”。晚上,睡觉前,最后一件事,就是给她道“晚安”,除此,无它。十年从未忘记过。他们的相处也很简单,每到月底,她都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上面只有一句话:老时间,老地方,待会儿见!月底聚一次,地点固定在大学城旁边的“可可西里”咖啡屋。他不说话,只管安静地听。偶尔问上一句,也并没想得到她的回答。她讲一个月发生的大事小情,碎碎念一样。有时很激动,语速很快,风雨交加的。他就说,你慢点,听不明白。她就慢点,把刚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
她曾对他许下过一个诺言,十年后,如果你仍未娶我亦未嫁,那我就嫁给你。彼时,阳光正好,除了风,再无别的声音。她二十岁,他二十三岁。而今,距离那个承诺,只差短短的几个月。而他,竟以这种决绝的方式离开,谜一样无法解释。
他离开的这几个月,秦小西一直做着同样的梦,梦里,她孑然一身,手捧鲜花,走进墓地去看他,可墓碑上竟然是她的名字。她就抚摸着墓碑,又悲又喜地说,难道这是个梦吗?那我究竟是在梦里还是梦外呢?
没有人回答她,天空只有一个水墨般清纯的月亮。她看见时光和落花,像两团黑影,在她眼前飘过。
风过树叶传来密密麻麻的沙沙声,她抬起头,看见一枚树叶,在潮湿的风中,正无声地飘落。
第二天,秦小西一个人开车又去了临城。她在那个演出场地整整等了一天。节目单上依然有这个节目。秦小西坐在观众席上,等待苏杭的出场。终于等来了无情,一袭蓝衣,身形微胖,动作眼神台词都很生硬,第一个武打动作,扇子就差点打到身后推他的少女脸上。秦小西看见他尴尬地回头,一脸青涩的笑容。
演员换了?他不是苏杭!秦小西突然一阵后怕。
结束后,秦小西跑过去,问这个假无情,昨天那个无情呢?怎么换人了?
什么昨天今天的!假无情一脸不高兴,有种不被认可的恼怒。
假无情走了。又到中午了,游客们迅速四散,演出场地又变得空空荡荡的。秦小西依然在那棵大树下坐下,一时间,山河睡去,只有秦小西一个人醒着。
晚上八点,她终于见到了苏杭。
她是在景区后门见到苏杭的。对面是一条清幽的小路,远离市区,行人和车辆都很少,附近只有一个技工学校和几个宾馆,算是比较大的建筑。门里是一块演员练功的场地。苏杭依然坐着轮椅,还是昨天那个女孩子推着他。她穿着现代的衣服,秦小西差一点没认出她来。苏杭依然是无情的样子,雪白的衣,冰冷的眉,淡然的脸,在昏暗的光线里,竟有种浑然天成的美好。
秦小西俯下身,问苏杭,你是谁?
一个漂亮的皮囊。突然有人说话,声音里满是鄙夷。一个木偶,一个替身,一个没有灵魂的摆设。
秦小西抬头,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轮廓很霸气,上身长,下身短,让他看起来像个丑陋的大冬瓜。
秦小西愤怒地盯着来人,想起苏杭说过的另一句记忆深刻的话,让灵魂都要有尊严地活着。她转向苏杭,后者手握折扇,一脸萧瑟,镇定地坐在一处暗影里,灯光在他脸上流淌,让他看起来像个梦中人。
經理,她是苏杭的妹妹。女孩子对来人说。
大冬瓜站住,看向秦小西,一只手在胸前上下晃动,似乎在掂量秦小西的体重。他的眼睛真小,还挤到一块,看起来总像是想哭。
他不是木偶,不是替身,更不是没有灵魂的摆设。他是我表哥苏杭。你凭什么这样说他?秦小西也鄙夷地看了大冬瓜一眼,十分气愤地说。
大冬瓜笑了,不和你一般见识似的冲秦小西摆摆手,没理她。慢慢走到苏杭身边,低头看着苏杭。苏杭依然木木地看着远处,夜晚枯萎的光线下,他那张俊美的脸反而更加清冷孤傲,不近人情地遥远。他真的是无情。有那么一刻,连秦小西都有点相信他了。
大冬瓜看了会儿,很响亮地笑了声,拍了拍苏杭的肩膀,好好演,有饭吃。那语气就像在施舍一个乞丐。
秦小西厌恶地看着大冬瓜,就像看着一个快现行的妖怪,冷哼一声说,我要带他走。
一直不声不响的女孩子突然说话了,他不能走,他可是我们景区的摇钱树,好多游客都是奔着他来的,还不用开工资。
你说什么?秦小西愤怒地转身,盯着女孩子。女孩子看了大冬瓜一眼,脸一下子白了,赶紧低下头,装着拉平衣服上的褶皱。
晚上的景区,一片死寂,只有星星点点的几处灯光摇曳如火,苏杭变成了一个单薄的暗影。
秦小西转向大冬瓜,你这是犯法的,知道吗?
不知道。大冬瓜拉长着声音,抱臂站在秦小西面前,像棵被砍掉枝叶的树。我犯了什么法?他一个大活人,吃喝拉撒哪一样不花钱,还要请保姆,算起来,他还得倒找给我呢。
秦小西心里的悲伤愤怒风雨飘摇,又转向苏杭,跟我回家吧,好不好?
苏杭没有动,他的眼睛是沉静的,没有一点内容,手中的折扇潇洒地开合了两下,十分清楚地说,我是无情,我没有家。
大冬瓜走了。秦小西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具标本,被风干后挂在了墙上。
你不是无情,你是苏杭!秦小西阴冷地说。她紧紧盯着苏杭的眼睛,想从他的眼睛里窥探出一点秘密。
苏杭面色沉静,不悲不喜,根本不给她任何机会。一辆车从门外驶过,苏杭手中的折扇发出幽冷的紫光,冰冷而魅惑。
你不是无情,你真的是苏杭!秦小西拉着苏杭的袖子,声音变成了恳求。她感到浑身的力气都用光了,摸索着在旁边的石凳上坐下来。她坐得很慢很慢,像坐到另一个世界里一样艰难。
你到底是谁啊?真是他妹妹吗?他真的是苏杭吗?女孩子问。
你是谁?秦小西反问女孩子。
我是从最东边那个景点过来的,来了没多久,经理让我照顾他,说他记忆力越来越差,快成废物了。
你说什么?秦小西厉声问道。
女孩子慌忙闭嘴,走到不远处,站在一棵大树下,看着他们。
秦小西感到了痛,直抵心底的痛,百折不回的痛,说不过去的痛。她问苏杭,还记得小米吗?
小米是苏杭曾经的女朋友,高挑,白皙,有种不言而喻的美。当年,苏杭还是苏总的时候,他们交往了两三年。秦小西曾无数次开苏杭的玩笑说,小心点,看哪天白天鹅飞了,把你给甩了。苏杭总是笑笑,不可能。可等到苏杭从东北回来,腿伤了没多久,不可能终于变成了可能。
苏杭很意外地扭过头,目光斑驳地看着秦小西,迟疑着把手放在她的肩上,轻轻地拍了两下。秦小西像收到暗语一样,有种豁然开朗的恐慌。她认真地看着苏杭,又重复了遍,还记得小米吗?
我是无情。依然是清清楚楚的声音。说完,突然“哗”地收起折扇,手腕翻转,食指中指并拢,一道白光从他指间飞出,义无反顾地射到不远处的靶心上。
哇,太棒了!推他的女孩子大叫着跑过来。
苏杭低下头,又有车灯射过来,准确地打在他的脸上,灯光下,苏杭眼里的悲伤,是那样的真切。
秦小西震惊地站起,半天说不出话来。她脑子里迅速闪过一个念头,她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坏了,她四处看着,慌张得像在找什么。
女孩子以为她被吓住了,解释道,演员们每天都要练的,没什么稀奇的。我也能,不信我表演给你看。
不用了。秦小西有气无力地说。
下雨了,四周一片荒凉的冷。秦小西闭上眼睛,光与影在眼前纠缠着破碎,世界消失在一片神秘的昏暗里。她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那么清晰笃定。她还听见了其他的声音,流星坠落,风过山谷,马蹄远去,秋风渐起。
秦小西认真地看着苏杭,苏杭继续茫然地看着远处,眼里空无一物,梦一样寂寞。
推他的女孩子说,下雨了,我们该走了,你也走吧。
秦小西没动,呆呆地看着远处。
停了会儿,女孩子又说,你到底是谁啊?说完,似乎想起了秦小西的怒喝,讪讪道,我不管你是谁,反正我帮了你,你总要谢谢我的。
谢谢!秦小西木木地说。她握住苏杭的手,想起多年前那个暴雨的中午。
苏杭在消失之前,曾在一个酒店做管理工作,他很有能力,老板很欣赏他,许诺干够三年,把本钱收回来,就将酒店低价转让给他。那时候的苏杭,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老板的话,让他有了从头再来的勇气。那段日子,他依然眉目清朗目光深邃,笑容像从水里捞出来的,清清爽爽。他很卖力地工作,进进出出的客人,水滴石穿一样。他每天都要等到最后一个客人离开,才下班回家。虽然很累,可苏杭的脊背依然挺得直直的,他希望有一天,能靠自己的双手,再闯出一片新天地来。
可是,就在三年快期满时,那个酒店被划到了拆迁范围之内,一夜之间,赤橙变黄绿,苏杭的希望如滚滚长江东逝了。
酒店关门那天,苏杭站在酒店门口,一动不动,脸色灰灰地一直站到夜幕降临,星光满天。
不久后,他就从银城彻底消失了。
苏杭消失那天,还来过秦小西的家。那天下着暴雨,秦小西的妈妈还专门做了他爱吃的菜。苏杭很愉快地吃完饭,就走了。秦小西手里的小瓷瓶,就是那天苏杭送给她的。
那是一只无脚鸟。
好了,再见吧。
那天,苏杭用低沉的声音说完这句话后,就走了。
如果没记错的话,苏杭就是那天消失的。
雨越下越大,女孩子跑到旁边的车棚里避雨,招呼他们,无情,快过来,小心感冒。
秦小西站在苏杭身边,隔着雨帘,再一次问他,苏杭,我带你回家好不好?
苏杭没有动,而秦小西却分明听到一声无奈的叹息,像神秘的耳语。
好半天,苏杭终于说话了,他说,我是无情,永远都是。
秦小西眼里突然涌出了泪,她靠近他,那你还记得我吗?
苏杭痛快地摇了摇头,不记得。
秦小西又想起苏杭说过的话,要做个问心无愧的人。她寒冷地笑了,难道變成这个冷漠绝情的无情,与世无争,自生自灭,就算是真的问心无愧了吗?
秦小西看着远处,远处的远处。她又想起那个他,那个十年如一日给她发早上好和晚安的男人。他走了,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她握住苏杭的手,他的手冰冷,握久了,仍能感到一丝苍白的暖。
雨更大了,比苏杭离开的那天还要大。
秦小西回来了。
时间过得可真快,又到月底了。
一整天,秦小西心里都惴惴地,她不知道还能不能收到他的邮件。下班了,她站起身,看着窗外,看得久了,感觉自己的心,也如同这窗外老旧的建筑,已经一成不变了好多年。
有那么一刻,她的眼前突然出现一片墨染的黑,黑暗中,她看见一只鸟,在碧蓝的天空里飞,一直飞,一直飞——它没有脚。
责任编辑/董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