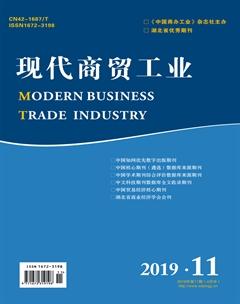故园渺何处:数字化生存下主体认同的危机与重构
李思思
摘 要:将当代社会的认同危机置于新传播革命语境下进行考察,试图勾勒主体在数字化生存下的认同面貌,以此检视影响主体认同建构的技术因素以及个体的心理机制,进一步挖掘当代多元身份认同建构背后的深层逻辑。同时,通过对隐藏于媒介技术背后的消费文化逻辑的考察,探讨当代认同可能的建構途径。
关键词:认同危机;主体焦虑;身份迷失;认同重构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11.006
1 “我是谁”:虚拟空间里的主体焦虑
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注定要终生追寻和探索“我是谁?”这一问题的答案。所谓自我认同,实际上就是自我与社会、主我与客我之间相对和谐的一种状态。主体对自我的感知首先体现为对身体的感知。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化,人们开始借助媒介来提升自己对于自身和外界的感知能力。麦克卢汉曾经用“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来描述人类与媒介的紧密联系。但即便如此,在网络技术出现之前,媒介对于主体和社会的影响力依然是有限的。互联网的兴起大大加速了社会的媒介化进程,媒介开始对社会的全方位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都无一例外地置于媒介的包裹之中,网络构筑的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逐渐重合,甚至开始取代乃至超越现实世界,李普曼提出的“拟态环境”已经成为现实。
虚拟空间重现并超越了现实的一切可能性,主体生命的有限性得以弥补和拓展。对于虚拟空间的深度依赖在很大程度上将主体重塑为“媒介人”。现代主体处于一种普遍的焦虑之中——愈加空虚、愈加孤独,也愈加失落。
首先,个体无法再继续凭借建构认同的传统因素,如民族、国家、信仰和家庭来界定自我,而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失去了传统的固定参照,个体无法理智地标定自身的位置,于是,人的主体性发生了转变,产生了一种自恋式的享乐主义倾向。这是由于虚拟空间中转瞬即逝的交往方式带来了一种不为地理接近性所局限的心理上的亲近性,人们可以很轻易地与陌生人达成情感上的亲密。伴随着网络对于日常生活的深入渗透,自我展演成为了当代人习以为常的媒介态度,一个展演式的景观社会出现了。在网络的虚拟交往中,一部分人渴望通过展演获取陌生人的注意力,从而获取声望与成功,另一部分人则积极地窥探着陌生人的私密世界,消费着他人的隐私与情感。展演文化的出现使个体在人机互动中被异化,自我认同机制发生了畸变,这种畸变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自恋表现出来。事实上,这种自恋背后投射出的实质是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与普遍的自我认同危机。这种不安全感植根于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主体的孤独感以及向社会展示自身的独特性的认同需求。个体出于对社会认可的需求试图通过虚拟交往获取支持和带来一种虚拟的亲密感,然而,陌生受众所投入的往往只能是窥探与漠视,很少能够提供情感抚慰与心理补偿,结果就是自恋心理的不断深化和个体孤寂感的持续增强。
其次,网络依赖症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虚拟空间的投入甚至超过了现实世界,“媒介人”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被网络媒介所重塑,伴随而来的是对失去“幻肢”的普遍担忧。人们不仅在网络空间中度过大量的闲暇时间,各种信息产品甚至开始渗透进我们所有的时间空隙,“互联网浸泡”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与现实交往情境的伴随状态。相较于在现实生活中进行人际交往与情感维系,人们更喜欢通过社交网络表达自我和展示生活。搜索引擎、门户网站、主题论坛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第一选择;网上购物、视频直播、在线游戏构成了人们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我们对于自我以及他者乃至世界的感知越来越多地来自于虚拟世界,我们观看和思考的方式也被网络化媒介所重新建构。这样一来,对于“幻肢”的愈加依赖导致了对于失去“幻肢”的焦虑与担忧,回归现实世界意味着与“幻肢”联系的断裂,于是,主体陷入深度的不安、失落与空虚之中,对于自我的感知也变得残缺不全和无所适从。
更重要的是,虚拟空间戏仿和重现了现实空间,但却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现实本身。赛博文化为“媒介人”提供了理想的“现实补偿”情境与防御机制,在这里,主体遭遇的现实困境都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得到解决:内向怯懦者可以在角色扮演游戏中尽情展现英雄气概,抒发豪杰情怀;身体残缺者可以通过浏览游记与图片以自由地游历世界,接触不同的文化与人群;感情受挫者可以在情感论坛与虚拟交往中获得暂时的情感慰藉与心理补偿;甚至边缘群体也可以在网络论坛中激烈抗争,建构民间舆论场域。但这些无不意味着人们越来越满足于影像和快感,主体独立思考与判断的能力被前所未有地削弱。一方面,虚拟空间弱化了主体对于现实的感知能力与现实联系;另一方面,主体的情感和欲望均被虚拟化了。最终,主体深陷于存在感和存在价值被消解的无尽焦虑之中。
2 “我们是谁”:网络社会中的身份迷失
媒介信息技术不仅塑造了一个全新的虚拟空间,更重要的是它建构起一个以数字技术为结构性力量的网络社会。表面上,数字技术拓展了人类的活动空间,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长河,但实际上,虚拟网络的强势崛起也威胁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拉伸了原有的社会距离。在网络社会中,人们仿佛将虚拟世界中的自我视为真正的自我。不同于现实中由地理空间与社会地位所局限的身份,虚拟空间中的自我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定制一个或多个身份,这样一来,人们要么部分丧失分辨真实与虚拟的能力,要么陷入某一种虚拟身份难以自拔,自我从而被割裂开来,成为一种流动破碎的东西。于是,“我是谁”和“我们是谁”这两个问题的社会基础被“我想成为谁”的虚拟身份游戏所摧毁了。主体对自身、他者、日常生活和现实世界的认知遭到破坏,由此催生了普遍的群属身份焦虑。
首先,互联网使个体丧失了对于空间与位置的感知,陷入无尽的迷失之中。虚拟空间本身对于现实世界的替代与重构将主体置于流动、漂浮、平面的虚拟世界,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迁移与流动,在陌生的空间中跳跃穿梭,主体丧失了对于方向与位置的感知。于是,空间和距离丧失了意义。当我们经由互联网相互联系时,电子社区的价值观悄悄取代了民族国家的价值观,物理空间变得无关紧要,而历史与文化也丧失了时间深度。
其次,网络社会中身份的易得性与多元性为主体提供了自由、快感与心理补偿,同时也带来了身份感知的困惑。虚拟身份与现实身份的脱节不仅导致主体对于现实身份的逃避,也使主体对于自我的感知变得模糊不清。长此以往,个体对自我和现实社会关系的感知出现错位,现实生活中的自我角色被边缘化,最终只能走向身份迷失與认同危机。
网络的虚拟性使人们得以卸下现实中层层的面具展现一个真实的自我,跨越生活中重重的限制扮演一个理想的自我。赛博文化下的自我不再是现实身份构成的主体,而是一个“虚拟化身”。“虚拟化身”是多元和不稳定的——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地转换与创造新的自我——它为主体搭建起自我建构与重构的理想路径,是主体自我赋权并提供心理补偿的一种模式。在这种虚拟互动与情感需求之下,数字媒介技术和赛博文化一同使人们聚合在一起,形成新型社区。这些虚拟社区的缔结跨越了时空界限,因主体的兴趣喜好而形成,帮助主体重新界定自己的群属身份。在这些社区中,主体通过自我书写与自我假定来自由地建构自己的群属身份,而不必受到现实规则的束缚。但是,太过自由的身份权力使主体频繁地穿梭于各种群体之间,可能无法形成真正的群体归属感。在这种情况下,群际交往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利己产物,难以作为结构性力量,帮助主体建构群属自我与增强群体归属感。
3 “我在成为谁”:媒介消费文化内的认同重构
现代消费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提供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在于其所能够提供的情感体验与心理感受。在此意义上,消费成为一种意义,商品成为一种符号。在马康纳看来,文化产品存在于组织数据向人们传输完美感觉与信念的文化体验之中,而这种体验正是建构人的态度、信念与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换言之,符号消费是当代“媒介人”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它既是用于建构认同的“原材料”,也是认同表达的符号和象征。而在消费方式“符号化”的过程中,媒介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推手。消费主义已侵入媒介社会的肌理,并通过二者的合谋,改变着社会文化的生成逻辑。
与传统社会相比,消费社会下的自我认同价值参照发生了偏移。坎贝尔对于这种认同建构的消费方式作出了说明,“现代消费的本质是为了实现自我梦想。消费核心不是对商品的实际选择、购买和使用,而是对想象性愉悦的追求,真正消费的主要是这种精神上的享乐主义的产物。”因此,人们通过这种意象性的符号消费来寻求自我的身份认同。“媒介人”在消费过程中所面对的不再是物质意义上的产品,而是以特定方式接近想象中的自我。个体与其所有物之间很难划分出一条明确的界限。个体借助所有物来建构自我并向他人展示自我,从而达成与他者的“区隔”以定义自我。这样一来,消费主义所强调的内容可能借助大众媒介对于现实的戏仿从而破坏个体的现实认同。因为,一旦消费的私人化成为了自我建构的重要手段,那么对于独特风格的追求就成为了不断变化的认同的主要内容。
在媒介消费文化语境中,主体的认同被变换不定的媒介图像的个人化和符号化所左右,传统体系中诸如阶级、种族、国家等社会和集体认同因素都被弱化或瓦解了。正是消费主义中的高度商业化和符号化使原本具有历史深度的自我指向物被抽象为同质平面的象征符号。消费社会中的大众媒介借助商品使消费逻辑内化为个体的生活理念和现实标准。因此,在消费主义中形成的自我认同呈现出表面性、不完整、不连贯的碎片化特征。人们越来越依赖媒介信息来认识和理解他人与外在世界,借助符号消费来定义自我与建构认同,媒介甚至成为自我的镜像与结构性力量。然而,消费主义并不能等同于消费文化,否则就可能陷入技术悲观主义的泥沼之中。相反,我们应辩证看待媒介消费文化在认同重构上的影响与作用。
现代性将人们带进一个充满差异、遍布风险的不确定的时代,市场经济与全球化进程在碾平生产方式差异性的同时,也建构了一个崭新的场域:不同民族、国家、地域的人们在这里相遇。伴随着数字技术的高歌猛进的是人们生活共同体和集体文化的衰落,个体感到身份意义模糊与意义缺失,这些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焦虑与压抑借助不同的文化产品,在具有相同价值观念的小众传播区间内得以释放。在这样以兴趣和偏好构建起来的群体中,人们更容易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由于差异性的逐渐增强,现代性并没有像马尔库塞所预言的那样将现代人转变为“单向度的人”,反而形成了多元文化并存的状态,主流文化、亚文化与反文化在不同的社会区间呈现出不同的格局。亚文化属性的符号消费本身成为一种身份认同的道具,通过这一道具,人们得以展示其内心独特的精神世界与人格形象。与此同时,媒介消费文化通过商品所附加的符号意义来界定社会群体。人们通过各类消费行为将自己归类于某种自己偏好的群体,这是在认同危机的时代对自我认同的反思性探索,人们在各类消费活动中持续开拓对自我新的体验和诠释空间。虽然对于传统社会权威的瓦解与对诸如民族、国家、阶级等社会因素的脱离使个体不免陷入一种迷失和焦虑之中,但是,媒介消费文化也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个体的存在价值,鼓励个体追求平等的文化权利和享受当前的生活,使个体不再受到传统的神圣化的体制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媒介消费文化因其流动性、碎片性和媒介性,导致了一种持续的认同建构与重构过程。当大众在网络社会中通过消费文化来界定自我时,个体并不是一次性获得一种整体性的统一概念。相反,个体可以在不同的时间,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形成一种群属认同与自我归类。这种不同层次、不同方位的认同建构充斥着日常生活领域。
4 结语
新传播革命将当代主体裹挟进一个全新的生存空间,如果说数字技术将虚拟世界演绎到极致,对于现实的模仿、迁移、延展和重构使网络空间超越了现实,比现实更现实,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主体焦虑与身份迷失。那么,对于伴随数字技术裹挟而来的认同危机的解决之道也必将回归传播媒介本身。当代新旧媒介融合的背后是消费文化逻辑,消费行为不再仅仅是由人们的社会身份所决定的附属物,而是作为主动的文化实践,成为人们建构认同的重要手段。虽然消费主义对于主体具有一定的异化与解构功能,但是基于个体的主动性,消费不失为一种支撑现代人自我认同的意义系统——人们借助消费行为产生群际认同,从而最终确定自我归属。只有正视当代数字技术与消费文化对认同的形塑,也许终有一天,我们能够顺时代洪流而下,重建理想的家园。
参考文献
[1] [美]Dean MacCannell.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M].张晓萍等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