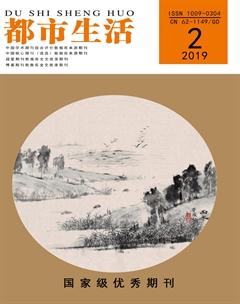漫步虚实之间的都铎宫廷画师——小汉斯?荷尔拜因



摘 要:身为都铎王朝亨利八世时期最重要的宫廷画师,小汉斯·荷尔拜因(Hans Holbein the Younger)为英国的艺术留下了大量的经典画作。画家将对人物姿容及其身份的写实与超现实的元素相结合,在丰富了人物的维度的同时,暗含了画师自身的思考,从写实描绘和精神映射上使得人物鲜活立体起来。漫步虚实之间,小汉斯·荷尔拜因从未为自己画过肖像,但他在每一幅作品里都表达着自己。
关键词:荷尔拜因 都铎王朝 宫廷画师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宫廷画师荷尔拜因为英国权贵和知识分子创作了大量的肖像,以其高超的写实技艺使其栩栩如生,又以虚拟的元素入画,增添了画面的深度与暗喻。了解宫廷画师荷尔拜因,也是在窥见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英国宫廷的一角;探索宫廷画师荷尔拜因的作品,不仅能瞥见时局变化的一些跃影,也是在走进一个宫廷画师的内心。
一、荷尔拜因其人
年轻时小汉斯·荷尔拜因曾在瑞士的巴塞尔发展,后两度前往英国,并在亨利八世的宫廷里担任画师。丰富的游历和多变的时局塑造了荷尔拜因的绘画观。
(一)受到人文主义者和知识精英青睐的画家
阿尔贝蒂曾劝诫画家们:“画家应当与诗人和演说家结交,因为他们广博的知识有助于激发画家的创造性构思。[1]62”艺术总是要切合时下思想甚至先于当下才能记录时情、反映时代,这就需要画家能够接触新思想、融汇新精神。
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运动的核心思想,时下的艺术家要想获得社会的认可,便需要对于时世思想有所融汇,对时代思想的弄潮儿们的趋向有所迎合。“一位要想引起人文主义者关注的画家,需要遵从一定这种特殊资源一致性的压力。[2]”荷尔拜因画笔下的人物——贵族、学者、商人、农民甚至是骷髅,形象生动逼真,其艺术以高度的现实主义表现为特点,又与进步的人文主义倾向相结合、统一[3]34-35。《墓中的基督》既刻画出一位与苦难人无异的圣人死后僵硬枯槁的情形,又通过这种“类人”的写实拉近了观者与神的距离。1516年的肖像画《雅各布·梅耶》是为了庆祝巴塞尔市第一位资产阶级出身的市长所作,画面中这位政治家手中拿着一枚金币说明了他金融出身的背景,发福的体型和随意耷拉的领口凸显了人物自在悠闲的气质。1519年的《阿麦巴赫像》,这位后来担任了巴塞尔法官和巴塞尔大学法学教授的年轻人仪态端庄、目光深远地望向远方。荷尔拜因的写实与刻画使得人文主义者和社会精英们趋之若鹜,在不断的创作和灵感激发中,也使得荷尔拜因画中的人文主义特质越加显著。
和伊拉斯谟的结识是荷尔拜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他为《愚人颂》(Moriae Encomium)配的插画得到了这位人文主义大家的赏识。此后他又为伊拉斯谟画下了几幅肖像,这些肖像画和伊拉斯谟的两封推荐信成为了荷尔拜因敲开都铎王朝大门的拜帖。
(二)阿佩利斯第二
亨利八世的大臣托马斯·索利马(Thomas Solimar)在其新书Paidagogeion中赞扬荷尔拜因:“宫廷画师,我们时代的阿佩利斯(Apelles)。[4]29”高度肯定了荷尔拜因高超的绘画技艺。这虽然是一种恭维,但并不夸张。
阿佩利斯是古希腊的著名画家,在老普林尼的《自然史》中记载了一件有关画家阿佩利斯的故事[5]356:阿佩利斯十分钦慕住在罗德斯的画家普罗托基尼斯(Protogenes),于是欣然乘船前往,但普罗托基尼斯不在家,于是阿佩利斯在画板上画了一条线,普罗托基尼斯回来后断言来访者是阿佩利斯,提笔用另一种颜料在之前的线条上画上了另一根线条。当阿佩利斯再次来访时,因自己的失败而感到羞赧,于是用第三条彩线分来两条线段,却没有给任何细线留下空间。普罗托基尼斯看后自愧弗如,立刻前往港口去寻找阿佩利斯。
这是一个在艺术史上广为流传的佳话。1521年巴塞尔的出版商瓦伦蒂努斯(valentinus curio)想要出版德国版的《基督教战士手册》(Enchiridion)(伊拉斯谟),委托荷尔拜因设计一个不那么常见的出版标记。荷尔拜因援引了阿佩利斯画与普罗托基尼斯画线的故事,“荷尔拜因不想仅以画板这种无聊的见证来表现艺术家的技巧,他还在加上了一只从云袖中伸出来的手,从而将阿佩利斯纯粹的技艺之手变成了神圣之手。”[4]37荷尔拜因对于画面的设计和构思充分展现出了超凡想象力与理解力。以技艺之手写实,以神圣之手构虚,荷尔拜因正是在这样的虚实之间完成了对都铎宫廷风物的描绘。
二、技艺之手的高超写实
荷尔拜因曾两度旅居英国,第一次旅居是其画作风格与英国文化初次碰撞的时期,在人文主义者、英国政治家托马斯·莫尔的欢迎与资助下,荷尔拜因创作了大量灵动而写实的肖像画,为英国的艺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一)托马斯·莫尔:《托马斯·莫尔》与《托马斯·莫尔全家像》
在第一次旅居英国期间,荷尔拜因为托马斯·莫尔创作了《托马斯·莫尔像》和《托马斯·莫尔全家像》,形象生动地展现了一位都铎王朝的廷臣、一个人文主义者的新知識家庭。
荷尔拜因的绘画遵循了早期荷兰绘画的精确传统,达到了现实主义艺术的最高标准。阿尔贝蒂在《论绘画》中提到“一个画家要是不能理解可视面的明暗关系,则永远只是个平庸的画家。[1]54”《托马斯·莫尔像》充分证实了荷尔拜因画技的不俗。莫尔既是一位人文主义者,同时也是都铎王朝所倚重的枢机大臣,画家将人物占据了大片画面的皮毛披肩描刻得根根分明,油滑柔软,显示出了这位主人不凡的地位和儒雅的气度。更妙的是压在皮毛之上的“S”纹链饰,它给了皮毛一个明暗有别的空间。同时它也展现了主人的身份——链条的中心垂下一枚精巧的金色玫瑰花,这是都铎王朝的标志,体现了莫尔对王室的忠诚。
画家是时代之笔,画作是时代之眼,“一幅十五世纪的绘画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积淀物”[6]。巴克森德尔所提出的“时尚之眼”的概念目的在于揭示艺术风格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在《托马斯·莫尔全家像》中,每个人物的名字、身份和年纪都被标注的十分清楚。荷尔拜因将人物之间的关系安排得十分得当:一家之主托马斯·莫尔位于家人的正中,坐在其右手和左手边的分别是仅次其地位的男性成员——他的父亲和儿子,女性成员们则位于画面的两端,最外层的则是弄臣和仆人,各个层级的人们十分清楚自己的身份并相应地装扮着自己[7]。
自然场景描绘和精准细节刻画使得荷尔拜因的肖像画十分写实。“整个画面不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展览,而是有情感交流的聚会,家庭的和睦和其乐融融尽现眼前。[8]”由于其高度的逼真和写实,以致于伊拉斯谟在给莫尔回信时也不禁赞叹道:“当画家荷尔拜因把你们全家的肖像图交给我时,我简直不能用笔墨形容自己的喜悦。它是画得那样成功,以致使我觉得,即使我和你们在一起,也不可能比这看得更真切了。[3]21”
(二)荷尔拜因笔下的国王:《亨利八世像》
第二次旅居英国时荷尔拜因的绘画风格发生了一些转变。“一方面,艺术家的现实主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却更多地反映了英国上层社会的贵族习气,未免使一些肖像显得比较矜持、呆板。[3]28”这并不是画家技艺的倒退,精准而审慎才是一位宫廷画师的必备素质。
在《亨利八世像》中,荷尔拜因从外貌形象上树立了一位高大魁梧的君主形象。在构图上,文艺复兴时期男性服饰上宽下窄的比例撑起了画面的主要架构——膨大的外套彰显着男性的孔武有力,紧致的肖斯袜勾勒出健壮的腿部,显出国王的年富力强。在细节上,此时正值德意志服饰风格流行时期,其特点是繁复、华丽,典型的装饰元素是斯拉修(slash),这都被画家以细致而高超的画技展现,细微复杂的纹饰、排布讲究的宝石以及考究的开口都被一一绘制明晰。
三、写实之中的绘虚:技艺之手与神圣之手的结合
技艺之手的高明之处主要体现在画作的写实上,它以最大化的逼真让人共情,神圣之手则是触动心灵的须,它会透过感知直抵心灵的田野。荷尔拜因在现实和虚幻之间表达着自己的理解与见证。
(一)对王国的警告:《染色玻璃设计的终点》
对于宫廷,荷尔拜因有着透彻、谨慎的思考。1525年,他曾画过一幅《染色玻璃设计的终点》(Stained Glass Design with Terminus)作为礼物献给亨利八世。画的主题有关死亡: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界,矗立着一个半身像,他的头部后方散发出光芒,可见这是一位神,这里是属于神的边界,画面中央写着格言“CONCEDO NVLLI”,意为“我不向任何人屈服”。据说灵感来源于1509年时伊拉斯谟得到的一尊珍贵的罗马雕像,雕刻的人物是狄奥尼索斯,代表了终点。“它表明了一种雄心壮志,但是基督教义解释的已然十分清楚:没有人可以躲避死亡。[4]98”而作为国王的礼物,荷尔拜因将雕塑画成和伊拉斯谟十分相似的模样,而那句格言似乎也表达了画家对亨利八世的一种高贵警告——“提醒这位嗜血的国王他在尘世的存在是短暂的,他应该留意那些萦绕在周围的声音[4]35”。
荷尔拜因是构建虚幻的大师,《染色玻璃设计的终点》是神话主题的虚幻,它更类似于过去的寓言故事或是带有神话色彩的历史故事对于现实的某种指引。而在写实中构建虚幻,讲述生死,展现高超的画技才是他的拿手好戏。
(二)骷髅意象:《大使图》
由于黑死病的肆虐,骷髅成为画作中的常见意象,意味着“生命的短暂,对明天的不确定,权利和荣誉的虚无”[9]。“画家和人文主义者创造了大量的面具,其意图在于铭记,作为一种对于虚荣和假象自我批判的途径。[4]222”在《大使图》(The Ambassadors)中,荷尔拜因在写实之中插入另一个维度里的骷髅意象,体现了其高超的画技。
画中的两位主角均为法国大使,左边的是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的使臣Jean de Dinteville,右边的则是拉沃尔的主教Georges de Selve。画家采取了一个与所见平面全然不同的空间描绘了一颗角度扭曲的头骨,光是从头骨的右上方照射下来,顺着这个角度,观者会不由得在脑中构建出它在另一个维度里的模样。这样的手法使得画面无论是从空间还是生死的维度上都一分为二。“图像是根据两个透视系统构建的,一个是组织活生生的人物和他们周围的现象世界,另一个是连接头骨,隐喻死亡。这两种系统共存于一幅画中,但同时又相互排斥:为了充分理解其中一种,观者必须忽略另一种。[4]262”有关这一头骨的寓意有许多猜想,至今未有一个明确可信的说法,但毋庸置疑的是,它所构建的虚幻和扭曲,是对画家展现其高超技能的有力证明。
结 语
荷尔拜因从技艺之手上唤醒了视觉,又从神圣之手中触及心灵。自由行走在虚实之间,荷尔拜因画下的写实摹刻细腻高超,而他从另一个维度里变幻出来的灵魂,是一种警示,也是一种救赎。
参考文献
[1] (意)阿尔贝蒂.论绘画[M].胡珺,辛尘,译注,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
[2] J?RGEN M?LLER.The Eye of the Artist: Hans Holbein's Theory of Art [J].Symposium Papers XXXVII: Hans Holbein: Paintings, Prints, and Reception,2001:141-153.
[3] 朱龙华.荷尔拜因,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
[4] Oskar B?tschmann, Pascal Griener. Hans Holbein(Revised and Expanded Second Edition)[M].London, 2014.
[5] (古罗马)老普林尼.自然史[M].李铁匠,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18:356.
[6] Michael Baxandall. Painting and Experience in Fifteenth Century Iitaly[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1.
[7] Ninya Mikhaila, Jane Malcolm-Davies. THE TUDOR TAILOR——Reconstructing 16th-century dress[M],2006:11.
[8] 靳技科.汗青中的艺术,艺术中的汗青——试论小荷尔拜因肖像画的汗青视野[D].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38.
[9] (法)米埃尔·马勒.图像学:12世纪到18世纪的宗教艺术[M].梅娜芳,譯,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124.
作者简介:熊畅(1995—),女,汉族,贵州安顺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7级世界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欧洲文化史,主要从事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服饰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