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罕见的罕见病
韩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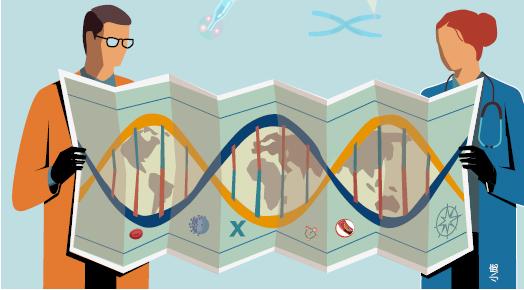
有一些人要与蛋、肉、奶甚至大米绝缘,因为体内无法分解和代谢苯丙氨酸(天然蛋白质中的成分),使得苯丙氨酸在血液中集聚,损伤大脑,他们是苯丙酮尿症患者。
有一些人时常四肢灼痛,必须泡入冷水才能缓解,心、脑、肾等各个器官逐步衰竭,平均寿命不到50岁,他们是法布雷症患者。
此外,还有“手舞足蹈”不受控制的亨廷顿舞蹈病、脾脏肿大的戈谢病、持久出血的血友病等。
这些病症,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罕见病。几年前,冰桶挑战让很多人认识了渐冻症。这些罕见病每个病种只有几万例、几千例,甚至全球只有几例的病症,从原本尘封的角落被揭开。
“公众对罕见病最大的误解,可能是觉得离自己很远。实际上,罕见病并不罕见,是严重的医疗与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离我们每个人可能只有一步之遥。”七色堇罕见病联盟创始人欧阳笠表示。
漫漫长路
李虹在知乎上的自我介绍写着:职业是生病,业余写作。今年47岁的他患有假肥大型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BMD),一种逐渐进展的肌肉无力与萎缩。
李虹出生在一个小县城,从8岁开始,他就跑不快、跳不起、投不远,体育成绩总是拖后腿。父母带李虹去看医生,得到的结论很简单:“不可能肌无力,小腿肚这么粗壮,一点没有萎缩的现象。”
18岁那年,李虹准备高考,始终不及格的体育成绩是个隐患。李虹父母托了城里的姑父找到市医院神经内科医生做检查,发现李虹没有膝跳反射,验血指标也出现异常。李虹立刻转诊至杭州浙医二附院,做了肌电图,显示为肌源性损害,确诊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
“当时医生开具了建议避免剧烈运动的证明书,建议不参加高考,学一些手艺,日后糊口。”李虹说。
不过那一年,他还是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只是身体各个机能逐渐退化,每天上课仿佛登山,大二时疾病累及心脏,开始出现慢性心衰,不得不休学一年。
后来李虹越发动不了,由于心脏严重衰竭,小感冒都会引发肺水肿,甚至导致脑梗。各种药物的副作用,也使他患上痛风和二型糖尿病。
直到2018年,李虹做了基因测试,才发现自己的DMD基因26号内含子第三位插入了一个T(胸腺嘧啶),多出来的这个T让他饱受折磨。
漫漫诊断路上,李虹是非常典型的罕见病患者,从发现迹象到最后确诊花费了10年时间,也未能及时监测疾病发展过程中的影响。
诊断难,治疗难,是典型的罕见病特征。
在罕见病领域,常听到一句话:“诊断罕见病的医生,更罕见。”20多年前,李虹在北医三院看专家号时,做过一次活体教具。专家看了他的病例,是万分之一的罕见病,立马喊了10多个实习生来围观,让李虹演示蹲下、站起的动作,并且讨论哪里变形、哪里萎缩。对医生们来说,这是“难得的病例”。
能诊断的医生不多,能治疗的药物也有限。目前,全球95%的罕见病没有任何药物治疗,而5%有药物可治的罕见病中,绝大多数药物的生产厂家只有一两家。例如,赛诺菲研发的注射用阿糖苷酶,是至今唯一一种针对庞贝病的治疗药物。
罕见病,是真正“缺医少药”的疾病。
近在咫尺
罕见病进入中国数十年,只是在近几年才引起关注。
2013年,北京医学会才成立了罕见病第一届专业委员会,41名成员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部队医疗系统、北京市医疗系统。2018年,国内第一份有关罕见病的综合性研究报告《中国罕见病研究报告(2018)》(下称《报告》)正式问世,五部委正式发布《第一批罕见病目录》,纳入121种罕见病。
《报告》中写道,罕见病包括了人体多系统疾病的几千种疾病;不仅是医学问题,而是跨越了临床医学、医学基础研究、药学研究、卫生经济学、法律法规等十多个领域。
换言之,对罕见病的关注与治疗体系的建立,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而中国的罕见病治疗体系的建立,发展相对滞后。
欧阳笠的另一个身份是遗传学博士,一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从事罕见病研究,“从数量上看,单个罕见病的确罕见,可世界上有多达7000种罕见病,总人数估计达3.5亿人,超过了艾滋病与癌症的数量”。
由于罕见病的定义并非以确诊疾病为前提,而是以某种疾病的发病率或患病人数为衡量标准,因此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种族差异、经济水平不同,对于罕见病的界定标准也不尽相同。
在欧盟地区,发病率低于5/10000的疾病为罕见病;在美国是患病人数低于200000人、发病率低于7.5/10000的疾病为罕见病;在日本则是患病人数低于50000人、发病率低于4/10000的疾病为罕见病。
而在中国,罕见病的定义始终没有确定。《报告》指出,目前国内没有建立罕见病注册登记系统,缺乏罕见病流行病学调查,因此不能得知罕见病某个病种的患病人数和患病率,无法得出中国罕见病的界定标准。
2010年5月,中华医学会医学遗传学分会在上海召开了“中国罕见病定义专家研讨会”,曾提出患病率小于1/500000或新生儿发病率小于1/10000的疾病可以定义为中国罕见病,由此估算出中国罕见病的患病总人数为1680万。
“美国3亿人口有3000万罕见病患者,也就是人口的10%。按照美国的比例推算,中国的罕见病患者可能达到1.4亿,加上罕见病会影响到整个家庭,实际受影响的人口可能数亿。”欧阳笠表示。
这是越来越多人重视罕见病的预防与治疗的重要原因,巨大人口数量为分母的前提下,得病概率很低,可对每一个个体患病來说,就是一个是与否的黑暗分割线。
罕见病到底有多可怕?一组基本研究数据显示,目前,80%的罕见病是由基因突变造成的遗传病,极大可能是终身患病。50%的罕见病患者是孩子,其中30%无法活过5岁,35%的新生儿死亡是由罕见病导致的。
欧阳笠分享了芝加哥大学一项研究,绝大多数人都有1-2个隐性致病基因突变,不计算显性基因突变和性染色体连锁基因突变的情况,当两个拥有相同隐性基因突变的人生育时,孩子就有25%的概率患上罕见遗传病或者夭折。国内甚至有研究发现,每个人平均有30个可能有害的突变,筛查600种较为常见的遗传病,97%的人带有至少一个致病基因突变。
从全球来看,至今罕见病的诊断都是难点,确诊平均花费4.8年时间,而在中国,所需时间可能更长。
“首先需要家长发现症状,并意识到严重性前往医院。普通医院的医生需要识别出症状的特殊性,并向上一级医疗机构转诊。”欧阳笠说,“这是一条很漫长的路”。
大部分罕见病与基因、遗传相关,产前筛查或者新生儿筛查会起到非常积极的正向防治作用。

《第一批罕见病目录》疾病相关治疗药物上市注册及医保纳入情况
在中美罕见病的治疗差异上,新生儿筛查是很关键的一步。在很多西方国家可以通过生物样品采集,为新生儿提供数百种罕见病筛查,一旦发现问题就采取相应措施。有药物的就开始用药,没有相关药物的就对症处理,例如一些罕见病会有癫痫现象,就提早准备癫痫药物。
以庞贝病(PD)为例,台湾地区的数据显示,PD发病率为1/17000,典型IOPD (婴儿型庞贝病)发病率为1/52000。在台湾地区,PD新生儿筛查已进行10余年,通过早期筛查治疗,IOPD患者生存期已由1 年延长为10年。
不过,基因检测只是确诊过程中的一部分诊断方式。欧阳笠表示:“如果一个新生儿检测到基因发生突变,是否确定有问题?能否确定该突变一定会造成影响,形成疾病?在很多情况下无法百分百判断。绝大多数突变都是中性突变,单纯基因检测很难判断。”
赛诺菲中国副总裁、特药事业部总经理吴清漪告诉《21CBR》记者,一些罕见病如果能够尽早诊断、介入治疗,同样可以过上有质量的生活。
“我们患者中,有一位在2岁时被确诊为戈谢病,发育受到严重影响,生命垂危。当时整个北京记录在册的患者不过数例。1994年,赛诺菲研发的戈谢病治疗药物注射用伊米苷酶(思而赞)在美国上市,两年后这位患者成了第一个接受无偿药品援助的患者。20多年后,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吴清漪坦承,从药企角度看,不断推动罕见病在社会上的关注度,才能让更多患者获得治疗,重返正常生活。
他山之石
疾病定义和数量统计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医学范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经济命题。
罕见病因为患病人群分散,绝对数量少,又被称为“孤儿病”。针对这些疾病研发生产的药物被称为“孤儿药”,即商业投资回报较低或者可能无法收回研发和生产成本的药物。
2013年,山东省罕见疾病防治协会在国际罕见病权威期刊《Orphanet JRare Diseases》上发表文章,提出可以根据药物研发成本来定义罕见病的思路,认为在中国如果某种疾病的患病人数低于50万人,制药企业就会缺乏研发新药的动力。
对于医药企业来说,研发病种多元而患者稀少的罕见病药物,的确是个很难平衡收支的生意。
“比起癌症药物研发,不少罕见病由于致病机理清晰,一些基因治疗药物的研发相对容易,但药物研发过程中的固定成本,例如团队开支、临床试验、申报审批、宣发等,每一种药物都差不多。”曾参与开发罕见病药品的欧阳笠打了个比方,如果开发一种常见病药物需要1亿美元,罕见病药物的研发成本可能就是5000万~ 6000万美元。
核心问题是,常见病患者有10万人,平摊医疗成本每人1000美元就可以回本。但罕见病人或许只有100个人,每个人需要承担的成本就高达50万到60万美元。欧阳笠表示:“商业化的难度在于受众少,药价高,如果医保不覆盖,药企就没有动力。”
吴清漪也坦言,研发罕见病药物,“投入巨大、过程艰难,回报有限”。但市场需求摆在眼前,开展罕见病业务对企业来说需要一点“理想主义”。
病有所医、医有所药,需要从顶层设计上给予创新环境与激励机制,解决商业层面的问题。
1983年,美国颁布了《孤儿药法案》,一旦药企获得孤儿药标签,就能获得高达临床试验成本50%的税务减免、药物营销申请费免除、长达7年的药物专享开发权、药物审批的快速通道以及科研基金申请的优先考虑权。
该法案的出台,标志着罕见病与孤儿病制度体系的建立。在该法案颁布之前,美国只有38种罕见病药物,而此后,孤儿药注册数量大幅提高。FDA已批准上市的孤儿药709项,获得孤儿药资格的有4688项。2018年前7个月内,FDA就批准了40项孤儿药。
效仿该法案,世界各地政府纷纷颁布相关法规与政策。比如,欧盟减免了孤儿药的部分上市许可申请费用,法国免除了孤儿药宣发或者促销活动支付的税款。
制度性完善使得过去30年来,孤儿药的注册申请大幅提高,跨国药企也愿意加大对孤儿药的研发与投资,比如赛诺菲收购了著名的孤儿药生产厂商健赞。
孤儿药的市场潜力被逐渐激发,预计到2020年,全球孤儿药的销售额将达到1760亿美元。2014-2020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10.5%,约为处方药市场销售额增长率的两倍(除仿制药外)。
在中国,孤儿药市场才刚起步。目前,在国家《第一批罕見病目录》纳入的121种罕见病中,74种罕见病在全球有适应证的治疗产品上市销售。而在中国,上述74种罕见病中,9种在中国无药,22种在国内有药但存在超适应证使用情况,13种有治疗药品但未纳入医保,部分药品即使被纳入医保也面临准入障碍。
“我与美国一家制药公司的代表聊过,他们知道中国有很多病人,但无法考虑中国市场。因为现有药物价格很高,以黏多糖症一型为例,在北美一年药物费用至少20万美元,在大多数国家都是医保覆盖,中国暂时没有。该公司曾经将另一种溶酶体病的特效药在中国上市,几年都没卖出去。”欧阳笠的观察,也是长久以来国内罕见病治疗的现状——医保制度不完善导致可及性不够。
身在药企中的吴清漪,感受更强烈,“欧美日韩对于罕见病有完善的体系与立法保障,拉美、俄罗斯基本实现了医保覆盖,而在中国大陆和印度,罕见病基本自费治疗”。
缺乏支付方,高昂的费用成了横在药企与患者面前共同的问题。1999年,赛诺菲率先在中国市场摸索罕见病药物可及性的路径,最初想要打开市场,只能是赠药模式。
赛诺菲最先通过与世界健康基金会(HOPE)合作,为戈谢病患者提供药品援助。2009年,与中华慈善总会合作开展“思而赞慈善援助项目”,为中国130余名戈谢病患者免费援助药物,至今累计援助金额超过13亿元。为了提升罕见病药物的可及性,赛诺菲还启动了多发性硬化和庞贝病患者的援助项目。
依靠持续赠药来打开市场的做法,对企业来说并不能长久。因此,不断扩大合作范围,也是吴清漪团队的主要工作之一,“如果能与更多的社会组织、基金会、慈善基金会合作,甚至募集一些针对罕见病的基金,整个领域的发展会更快”。
幸运的是,吴清漪和她的团队在摸索中看到了一些新模式的诞生。
从2005年开始,青岛市先后将多发性硬化、重症肌无力、运动神经元病、血友病、干燥综合征、肝豆状核变性等近20种罕见病纳入门诊大病病种范围,治疗费用可以纳入报销,同时在报销待遇上给予优惠。
2016年起,浙江省通过基本医保、大病医保、医疗救助、民政专项救助四重保障,将渐冻症、戈谢病、苯丙酮尿症纳入保障范围。上海也在2011年选定了12种罕见病,给予部分比例报销。陆续还有多个省市以不同形式针对不同罕见病种给予保障。
生态联盟
欧阳笠将国内罕见病患者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无药可医的患者,确诊是第一目标。“确诊可以帮助他们少走弯路,找到共同疾病的患者互帮互助。”
除了药企、公益组织、政府机构,互联网也在发挥作用。丁香医生医学总监魏玮说:“很多家长在当地基层医院作出初步诊断,或者只是单纯怀疑,通过丁香医生进一步咨询或者获取诊疗建议,或者联系医生赶赴更专业的医院就诊确认。”
第二类是国外有药而国内未批准上市的患者。例如黏多糖症的缓解药物Elosulfase Alfa(商品名:Vimizim)在国内一直未获批上市,依赖进口价格非常昂贵,国内不少患者甚至企图通过移民来解决问题。
第三类患者是国内有药可医,甚至已经纳入医保,但因为药占比、采购限价、地域限制等原因,用药无法保障,不少罕见病人都尝过“断药”之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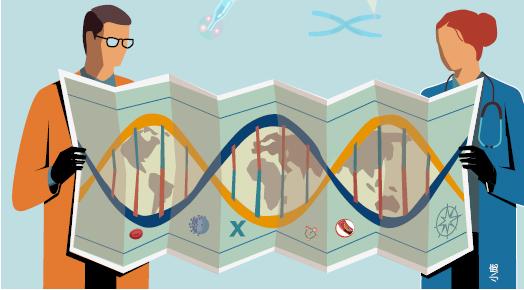
无论哪一类,都对中国的罕见病诊治系统提出了要求,包括疾病教育、提升罕见病的诊疗水平,以及探索多元化的救助模式。
今年2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强调,加强癌症、罕见病等重大疾病防治,要保障2000多万罕见病患者用药。从3月起,对首批21个罕见病药品和4个原料药,参照抗癌药对进口环节减按3%征收增值税,国内环节可选择按3%简易办法计征增值税。
产品上市的脚步在加快。赛诺菲研制的治疗多发性硬化的奥巴捷,在中国从获批到上市只用了58天,创下了国内罕见病创新药物从获批到上市的“最快速度”。
3月末,第二批30个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公布,其中有14个药品为罕见病药,占药品数量近一半,涉及的药品包括治疗法布雷病、乙型血友病、渐冻症等罕见病的重磅急需药。
这个群体的医疗可及性状况正在快速改善。“建立起罕见病药物目录,目录内药品优先审批,简化药物检验流程等,以此鼓励罕见病药物研发和上市。”吴清漪希望,能够从国家层面加大对罕见病诊断、治疗和预防的投入。
有人担心罕见病药物纳入医保后,会给医保资金带来压力。吴清漪觉得无须多虑,因为罕见病人数非常少,对整體医保构成的负担也有限。
在吴清漪看来,一个社会的医疗,从覆盖大多数人到关注罕见病,是一个特别大的跨越与进步,“人们开始意识到,哪怕只是很少人的患者群体,也有健康生活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