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光:科普作家的现实主义关切
徐 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
在回顾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历程时,郑文光显然是一个不应被忘却的名字。这位被誉为“中国SF之台柱”的杰出作家,曾被美国的《ASIA2000》杂志称为“能够驰骋于科学和文学两大领域的少数亚洲科学家之一”。而作为中国科幻银河奖“终身成就奖”的唯一得主,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科幻小说之父”。
在郑文光的一生中,有两次人生抉择值得铭记:一次是1947年,他从侨居地越南海防返回国内,去热切追求比继承家族的生意更高远、更宝贵、更有价值的东西,他开始涉足政论时评,以文字的方式投身民族解放事业,这里有时代的变局、“家园”的召唤与青年的热血;另一次则是1951年,他从遥远的广州来到北京,一次光荣的撤退,意味着有关梦想和挑战的全新起点,他选择以科普为业。三年之后,郑文光的第一篇小说《从地球到火星》顺利发表在《中国少年报》上,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第一篇正式标明的“科学幻想小说”。从此,一个全新的世界在郑文光的面前展开,他也注定要去亲历中国科幻文学的辉煌历史:见证它艰难的起点、非凡的转型,以及延续至今的发展、壮大。

《飞出地球去》
现在看来,作为中国“科学幻想小说”开山之作的《从地球到火星》,其故事显然是极为简单的:几个顽皮的孩子,趁爸妈熟睡之际,偷偷开跑了火箭船,他们一路飞到了火星,并围绕这个彤红的星球转了一圈。大概是因为当时的郑文光也不太清楚真正的火星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所以才没敢让这群放肆的孩子在这里“登陆”。然而即便如此,小说也激发了社会各界的足够兴趣,一时间北京城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火星热”。可是那个时候,北京天文馆还没有建立,为了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中国少年报》不得不在建国门的古观象台架起一座望远镜,这一下就真的热闹了,盼着看火星的学生们兴致勃勃地排成了长龙,直到深夜队伍都不愿散去。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孩子们对科学的热情,激发了郑文光沿着《从地球到火星》这条道路不断前进的强烈愿望。
这里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从地球到火星》名义上虽是小说,重要的却不是讲故事,而是借故事来传授知识。比如小说借人物之口非常细致地讲解了什么是失重状态,“一辈子都不会天亮”究竟是为什么,以及其他诸如流星威胁和火星尘雾等饶有意味的问题。这种刻意的科学普及工作,恰是郑文光当时科幻小说创作的重要目标。他接下来的一系列小说都是以此方式展开的,比如《第二个月亮》就借参观“人造月亮”的机会,通过科技的展示来讲解具体知识;而《征服月亮的人们》也借小说人物谢托夫教授之口,向少先队员们讲述地球和月亮的有关情况。甚至到了新时期以后的作品,那部最有代表性的《飞向人马座》,科学知识依然占据整部小说的三分之一,这便体现出典型的“硬科幻”风格,其小说也因此被誉为“通俗的天文知识读物”。这种通俗化的“科普”特征,正是那个年代科幻文学的普遍状况,其中的原因我们似乎也不难理解。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人们对于科学技术,尤其是宇宙航天技术的求知欲,无疑令人印象深刻。人们大概普遍认为这一类的知识才更加匹配“超英赶美”的世界雄心。当时随着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项目的全面开展,中国科技水平落后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地呈现出来。而落后的焦虑,直接催生了“向科学进军”的全民实践。一时间,全国上下掀起“学科学、爱科学”的热潮。当时不仅科学小品、科学童话、科学诗歌等科普读物大为火热,科幻小说也成为备受关注的对象。只不过,注重小说传播的功能性而非文学的审美性,是当时科幻小说的主要特征。那些热心倡导科学幻想小说的科普编辑,舍得在科学刊物或杂志副刊中拿出大量篇幅来发表作品,目的显然是为了更好地吸引读者投身科学,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和培养民族主义情操。郑文光等最早一批科普工作者无意间投身到这一热潮之中,有意识地将一些科学原理融汇到小故事中,慢慢发展出一种广受关注的科普文学。在郑文光看来,所谓科学普及,就是将与人民生活关系相对比较密切的科学技术、发现与发明,以一种比较浅显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理解和获得。然而,在一个人口众多、国家贫困、国民文化素质有待提高的国家进行科学普及显然是一件相当困难但也相当有意义的事情。在科普的诸多门类中,对少年儿童进行的科学知识普及,由于受到读者对象的知识能力和水平的限制,不得不用一些生动的、浅显的、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而科学文艺就是这种方法中相当有效的一种。

《战神的后裔》
当然,机遇从来不会青睐那些没有准备的人。对于科普小说创作来说,郑文光显然是非常合适的人选,确切地说,他作为一位科幻作家的“养成”,其实具有相当的“便利”。早在1949年以前,郑文光就曾辗转海内外多地,以教学和撰写政论时评及科普文章谋生。他1951年到北京,在中国科普协会工作,而“科协”的主要任务就是一手抓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一手抓科学知识的普及。在新的工作岗位上,郑文光也顺理成章地将创作兴趣由政论时评性文字转移到科学普及读物的写作上来。那些年他勤奋创作,取得不小的成就。仅1954年一年时间,郑文光就创作了超过百万字的科普作品,其中仅人造地球卫星方面的科普文章他就写了120余篇,尽管这对他本人的精力是巨大的耗费,但这行动本身却为他的科幻小说创作提供了充分的知识准备。而在具体的创作之前,郑文光又预先广泛接触了国外当时已经被译介到国内的不少科幻作品和文艺理论。1953年,他翻译了俄语小册子、亚力斯托夫的《为天文学中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而斗争》。苏联这一类科学哲学作品的翻译与研习,极大拓展了他的知识视野,让他的科普工作游刃有余。再加之对凡尔纳、阿西莫夫、齐奥尔科夫斯基、阿·托尔斯泰等人作品的阅读与学习,更使他的科幻创作得心应手。为了更好地投身创作,郑文光也在此后不断夯实自己的科学理论知识。他于1974年写了第一本天文学著作《康德星云说的哲学意义》,这本书涉及哲学、天文学和科学史等多个学科,知识含量令人惊叹。1975年,他与席泽宗共同完成了专著《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而另一部学术著作《中国天文学的源流》,则被认为是关于中国天文学史的作品中最为系统的一本。这种完备的知识准备,专业领域的苦功夫,甚至令今天的科幻作家都望尘莫及,而这些都为郑文光的科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进入新时期以后,中国当代科幻文学迎来了另一个创作高峰,而郑文光也顺应着这一潮流,投身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如前文所述,对于郑文光这一代中国科幻作家来说,尽管他们的作品洋溢着儿童的天真、原始的激情与昂扬的乐观主义,但由于科普的原因,始终屈尊于儿童文学之列。因此对他们来说,一个紧迫的任务就是,如何将科幻小说从“少儿科普化”的窠臼中解放出来,让它获得更深切的现实意义和更广阔的美学空间。作为新中国最早一批科幻小说创作者,郑文光也是最早自觉探索科幻小说理论的人。他从理论和实践等不同层面,就如何拓展科幻小说的现实关切有着严肃认真的思考。

《飞向人马座》
郑文光认为,在文学的世界里,科幻小说已经成为正统的创作形式,它甚至越来越与世界科幻文艺靠拢,因此单纯的科学知识普及功能不应该是它的唯一目的。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郑文光开始力图将科幻小说塑造为严肃文学的形式,处处力求以刻画人物、表现社会、表现人生为主。科普作家开始展现他清晰的现实主义关切,这当然意味着一种新的理论主张。围绕这一主张,郑文光在新时期的科幻文坛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剖析人生,反映社会”的文学诉求,这在稍后不久便被他郑重地称为“科幻现实主义”。无论是“剖析人生,反映社会”,抑或“科幻现实主义”的理论,其实是对一直以来中国科幻“科普论”创作一统化局面的猛烈冲击,而事实也证明,这足以让一代作家从“少儿科普化”的格局中突围而出。此后,中国科幻小说开始涉及更为广泛的社会现实生活,思考更为深刻的人生问题,表现更为复杂的“成人情绪”。这也标志着人们对科幻价值的认识,由科学普及的中心视点转移到人性和现实的中心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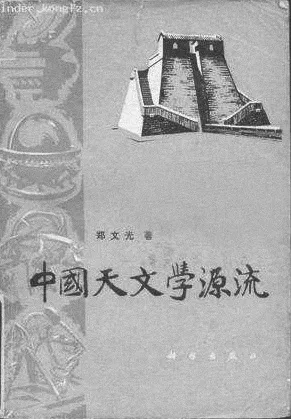
《中国天文学源流》
在今天看来,这种科幻小说的价值转移,其实并没有多么深奥。因为,对于郑文光等一批作家来说,科幻小说从“少儿科普化”向主流文学靠拢,其实只是意味着向彼时流行的“伤痕小说”靠拢。至少在当时,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回归现实的创作方式。在“文革”期间曾吃过苦头的郑文光,对当时众人控诉的所谓“伤痕”有所感触,并不难用这样的方式写出脍炙人口的作品。尽管在郑文光那里,所谓的“科幻现实主义”,其实仅仅只是科学的奇思妙想与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的简单融合,比如他创作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蚩尤洞》《地球的镜像》和《命运夜总会》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文革”的荒诞现实。但总体来说,这种转变还是顽强显示了科幻小说超越“科普”,切入现实生活的雄心,这是它脱离科普窠臼的艰难开始。

《太阳探险记》
除了向“伤痕”、“反思”等主流文学的靠拢,郑文光也以“科幻民族化”的追求,来超越“少儿科普化”的局限。就此话题,必须提及郑文光第一部小说集《太阳探险记》出版时的一个“小插曲”。1955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将小说稿件送专家评审时,有人曾严厉批评小说集具有“洋奴思想”,根据竟然是小说集中一篇小说的主人公明明是中国人,却起名为“谢托夫教授”。现在看来,这样的批评实在有些牵强,也令人费解。但在当时,于作者郑文光而言却是深深的震动。“洋奴”的指责如鲠在喉,这不断提示他,要为中国写一部科幻小说,写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命运。《地球的镜像》就是一篇讲述中国文化和中国命运的小说。它在“伤痕”叙事的荒唐景象之外,“嫁接”了人们极为熟知的郑和下西洋、火烧阿房宫的历史桥段,虽然只是一笔带过,还颇有些情景点缀的味道,但却是一种中国身份的有效标识,对于作者来说,也显然具有别样的意义。事实上,《地球的镜像》里的东方故事,颇受西方读者欢迎,这虽则有“东方主义”的元素在作祟,但也不能不说是浓郁民族特色的魅力所在。
为了超越科幻文学“少儿科普化”的局限,郑文光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在“科幻现实主义”、“科幻民族化”等方面所做的努力,无疑极大拓展了科幻文学的美学空间,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争议。这是因为,在由科普向现实的转换过程中,倘若科幻小说逐渐放弃科幻的科普功能,便不可避免地会使叙事焦点出现偏移,这样的话,科幻便成了一个噱头,一个可有可无的借口,“伤痕”成了故事的中心,而一味展示“伤痕”则成为常态。相应的,科普,或者说科技层面的东西反而特别模糊,特别暗淡,甚至很多被认为是“伪科学”的东西开始泛滥。比如1981年,郑公盾在《不要让鬼神进入科幻作品的领域》一文中便尖锐指出,写“借尸还魂”等人体神异的科幻小说“堕入了非科学的神秘主义的泥坑”,文章的矛头直指郑文光的《古庙奇人》等作品。在《古庙奇人》中,阴森古庙里死者复活的段落,无疑会让人想起《聊斋志异》的神鬼故事传统,也会让人忘记这是一篇科幻小说。这也难怪,当“伤痕”的历史动能不再强健,“伤痕”故事变得不再流行时,如何推进科幻小说的创新方式,这便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郑文光(左)与叶永烈
同样,还有人猛烈批评郑文光的《太平洋人》违反科学幻想,足可见出这一类的创作在当时引起的巨大争议。这里面最具有杀伤力的当属鲁兵的那篇名文《灵魂出窍的文学》。该文发表于1979年8月14日的《中国青年报》,文章将科学性视为科学文艺作品的灵魂,据此便严厉批评童恩正、郑文光等人的创作理论,视其为“走火入魔”。文章指出:“科学文艺失去了一定的科学内容,这就叫灵魂出窍,其结果是仅存躯壳,也就不能称其为科学文艺。”这篇文章也顺势牵出理论一篇科幻小说究竟姓“科”还是姓“文”的大讨论。争论双方的焦点在于:一方认为,科幻小说主要是艺术地表达一种“科学”的幻想,“科学”是科幻小说的灵魂,而小说只是手段;另一方则坚持认为科幻小说是文学,其核心任务在于塑造人物,“科学”不过是一种表达方式。从根本上说,这场争论还是源于对科幻小说概念的误解。虽然郑文光早已阐述过这些问题,但由于中国科幻小说科普化的观念深入人心,致使学界一直沿用科普标准来评判科幻,这样一来,包含着现实主义关切的不科普的作品,就变得荒诞和不严肃了。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无法清晰界定,究竟什么是真正的科幻小说,因为我们无法想象一种毫无现实瓜葛的科幻小说。围绕科幻小说,“硬科幻”的机械性与僵化感,“软科幻”的虚幻性和轻佻感,仍然是今天的科幻文学创作的棘手议题。那么如何调和二者的矛盾?这恐怕得涉及如何理解科幻文学的科学性与文学性,幻想的边界与小说的实效等诸多议题。而郑文光当年的思考,也注定会不断激起我们的理论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