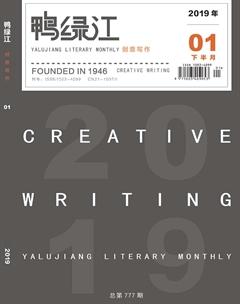《刀兵过》:从百年风云到河清海晏的历史画卷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我没有想到是这样一部作品,对作品的内容感觉意外,对写得这么好感觉意外。读《刀兵过》有当年阅读《白鹿原》的感觉。
这部作品的内容、故事、人物,总的看是写乡绅家族,写乡情人事,写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个传统文化很丰富,其丰富性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比如关于儒家文明、乡土文明、儒释道,以及医和茶。医和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与儒释道又有内在的勾连,所以这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是把一个世家身上所凝聚的各种文化因素,写出了一种民族和民间精神的传承,以及这种精神传承对一方水土的滋养和支撑。王家两代人就是九里的支撑,没有他们,九里这个地方怎么生存,怎么发展都要大打问号,而有了这种滋养和支撑,尽管百年间过了多少次刀兵,但是他们都坚持了下来,活了下来。
作品确实写出了中国文化很特别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以软对硬、以柔克刚。写乡贤写乡绅,能把作品写出这样丰厚的文化内涵,确实不多。作品通过这样一个角度解读了中国社会,尤其是底层社会、民间社会的很多奥秘,它有自己的小秩序——由乡贤和乡绅带来的秩序,这样的秩序有很强的转化能力,在不同的时代它都能转化成各种正面的和积极的能量。在写乡贤乡绅这样一些家族文化的作品中,这部小说是集大成者。
王家两代人是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和独特的性格魅力的。在作品的写法和叙述方面,滕贞甫表现了一种非常充分的中和之美。非常内敛,非常节制,非常干净。所有的恋爱都是情和精神的交融,甚至太中和了太干净了——这既是作品的长处,可能也是作品的短处。生活还是要有点杂质、杂音,要毛茸茸、湿漉漉的。
此外,滕贞甫对传统的、民间的文化吃得很透,拿捏得非常准,非常少见。写具体的事和人时,有一条线是能看到的生活层面、现实层面,还有一条线是精神层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较量,都是精神在起作用,很厚重。
梁鸿鹰(《文艺报》主编):
写乡村文化、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精神,《刀兵过》给人一种静水深流的感觉,特别扎实和蕴藉。中国乡村社会的秩序、传统、人的活法、人与外来力量的相互拒斥过程,看完觉得中国文化的混沌气,知白守黑,以少胜多,都在里面了。
作品的核心,是表现两代堂主在九里这个地区肩负着文化的传承和维系。按中国的秩序和社会进化来讲,如果不受到外力的入侵,会有一种天然的秩序。但是,一方面外敌入侵了,民族对立,搏杀,较量;同时,另一种文化也在对这块土地、人心和秩序进行改造,这两种力量都在发挥着作用。
《刀兵过》对中国人的了解还是理想化的——中国人非常有智慧,非常蕴藉,讲礼仪,识大体,以理服人,不拼体力而拼智慧,不是蛮干的、不讲究策略,不是在外力下易屈服的。
此外,它还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印记的作品。显然滕贞甫对中国文化有非常深的体悟和热爱,才能写出有这种气象的作品。在小说中,中医是两代人的职业,他们在疗救人的同时,也在疗救秩序、人心和国民性。
小说有完整的对乡村社会和自然的认识。比如写驴,除了刘亮程特别擅长,我看滕贞甫是第二个。小说中出现了很多东北的器物,还写到了婚丧嫁娶时的讲究,这些都能够抵抗时间的冲刷。过一二百年再考察东北民俗,考察非物质文化的痕迹时,可以到《刀兵过》里去寻找。
小说里还能看出中国文化中个体和整体的关系,有很多让人联想的东西。人们对世上的事物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社会秩序是由领袖、特定的人来缔造和维护着;而中国文化讲究整体,三圣祠、酪奴堂,是个人代表群体的,议事时韩马姚姜陶一起来,代表金木水火土,回到了中国文化的解释上,非常有意思。陈忠实写《白鹿原》时,我认为他没有考虑这么全。滕贞甫对东北传统文化的挖掘和认识非常深刻。
这部长篇小说的时间跨度非常大,因此很难避免气息缓慢和平均使力。但是到了王克笙,特别是在他结婚之后,读起来还是很享受的。关于长篇小说的吸引力和推动力,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爱情和性。《繁花》也好,《朝霞》也好,都是上海的作品,推动故事还是靠异性相吸的过程,或靠爱情故事,但《刀兵过》在这方面却有点意外,而且竟然能够进展到这种地步。
《刀兵过》写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跨度这么大,字数又不特别多,这种稳健特别令人肃然起敬,显然有很长时间的储备,它的不温不火和文化的气息需要深入的解读和了解,熟悉东北黑土地文化的人对它的了解会更深一些。另外,小说的写法上,一方面是想象力,另一方面还有地方性知识的考证和相互印证,这些都提供了有力的借鉴。滕贞甫一定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写,他还有多种可能,希望在今后的创作中多写好作品。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刀兵过》是一部有思想有厚度的小说,读了很震惊。写历史,特别是近代百年来的革命史,有的是通过家族来反映百年的发展,有的是用革命传奇的方法,都是想以此来反映百年风云变化。这些小说一般在情节和故事上有所变化,但对历史的认知没有太大变化。一个小说家,最重要的是能够对世界、对历史提出独到的看法,《刀兵过》就有这样的效果。白烨联想到《白鹿原》,二者确实有可比性,都对历史有独特的看法。《刀兵过》完全跳出了我们习惯的建立于暴力美学基础之上的历史观,去重新反思我们的历史,看到了暴力的革命性和破坏性在带来历史的进步,也带来了副作用——破坏旧世界的同时也破坏了珍贵的东西。暴力革命的摧枯拉朽带来了社会的进步,这是从宏观而言,但在破坏旧世界的同时,把我们传统的精神也伤害了。《刀兵过》写了传统文化在这样的过程中如何被伤害又活过来。它寄托了滕贞甫的期待,他期望在今天能够让它发扬光大。
《刀兵过》有很多寓意。主人公祖上姓朱,为避祸改姓王,因先人叮嘱“不到河清海晏之时,不可草率为之”,因此直到1981年才最终恢复了祖姓。这体现了滕贞甫对历史、对中国革命和对改革开放的认识——1978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想,不再以暴力革命为基本路线思路。而1981年也是我们政治路线进行重大转变的關键时刻。从这个角度讲,小说的题目很有深意:“过刀兵”是带来祸患——我们一直在过刀兵,一直处于暴力革命中,一直停留在过刀兵的思想状态中,还用那种暴力的思维方式来处理今天的事情。五六十年代为什么一直在折腾,就是在用过刀兵的思路来处理和平建设时期的事情,因此就有了一个又一个的运动,这些都是对历史的反思。《刀兵过》中最体现中庸之美的,是三圣祠,是民间信仰,它代表了民间对传统文化的认可、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理解,它强调了传统文化的作用,表达了对历史新的认识,作品的确提供了新的东西,这一点非常难得。我们的历史小说越来越多,但真正能够提供新的历史观的非常少。从“过刀兵”和“刀兵过”,评价历史抓住了关键点。
《刀兵过》的主人公是一个乡贤,但与《白鹿原》里的乡贤不一样,虽然从精神层面有一致性。在过去的社会,乡贤起到一种传递文化精神的作用。社会的基本精神,儒家文化精神,是靠乡贤维系的,《刀兵过》写的就是儒家文化在百年动荡中的飘移和漂泊——它有被摧毁和撕裂,也有锤炼和新生。王明鹤就是在坚守这种精神,并在動荡的时代让这种精神有效地发挥作用,而九里那样一个远离中心的偏僻地方也给他提供了一种方便。《刀兵过》的独特之处在此。
另外,《刀兵过》是文学性很强的小说,这是滕贞甫写小说的特点,他不是简单地讲故事,也不是像有些作家那样完全凭语言的天赋,但他有基本的审美追求:追求优美。这与他看中非暴力的东西有关系,为什么对暴力美学有反思,就因为他追求的是优美。这种优美体现在小说中,很强调它的象征性和寓意。《刀兵过》中很多东西是很讲究的,一个细节、一个物件都能看到作者很深的寓意。三圣祠,还有很多小物件都用得特别好,兔毫盏、蒲团、宋聘号茶饼,回味无穷。这都与他优美的美学追求有密切的关系。
陈福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刀兵过》40多万字,却写得特别绵密,这个绵密是出于作家的力量,没有力量是做不到的,很多小说都是粗针大线。
毕其功于一役,滕贞甫将对文学的理解、对文化的理解,以及多年的人生的经验全化入作品中了,能看出他的积累非常深厚。作品寄托着写作者的文化理想,也呈现着写作者个人的文学能力。这样的文本值得认真对待。
杜甫曾咏怀“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刀兵过》的人物,从安徽到天津到黑龙江,又受到了道姑神一样的启示,让他去西南。
小说中的酪奴堂是有深刻的文化象征的,有隐喻性。中国近代百多年来,文化上就是酪奴,是处在低的位置上,一直被打。鲁迅说“一首诗吓不跑孙传芳,一声炮响就把孙传芳轰跑了”,鲁迅说得太明白了。
“五四”一代人或者说“五四”之前的仁人志士,把中国失败的原因找到了船坚炮利,后来发现不仅是船坚炮利,又找到文化上,这等于是此一时彼一时地翻烙饼,对文化传统和整个世界局面的理解始终是在一个相对主义的层面上,偏一下,正一下。我觉得整个一百年来,中国人缺乏一个对整个世界的理解能力,要么就说洋人特别好,要么就说我们自己特别好。
我听前面几位老师的发言,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儒释道,包括乡村理想主义、理想国、乌托邦,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当然是同意的,但是我也有一个担忧:最后你何以对面世界?这还是一个问题。
酪奴堂深刻地隐喻了中国百多年来愈挫愈勇,靠植根于我们的文化,同时又善于向别人学习,才走到了今天这个局面。我觉得“酪奴”代表一个文化冲突,我们应该正视这样一个文化冲突,轻易地把票选在哪一边可能都不是一个正确的语态。当我们被别人打得特别惨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的文化说得一无是处,就奋发,然后又觉得道德沦丧,人欲横流,又觉得我们自己这一套好。我们对历史和文化的认知应该是趋于综合的,是需要有一个像马克思所说的辩证法的螺旋式上升的态度,而不是偏执于一方。当年讲文化偏执论没办法,不偏执就没法冲破旧的文化,所以不得不偏执。但我们今天真的需要一种极端的偏执吗?我自己是没有把握的。但我把它作为问题提出来。滕贞甫在这部小说里塑造了典型的文化人物,一块几平方公里的圣土,在一个来势汹汹的世界性的大潮中(这个大潮也不仅仅是外来的,也包含着包括着我们自己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的内部变化),这样一种文化理想的位置在什么地方?这都是需要考量的。滕贞甫的小说给了我们特别好的思考这些问题的机会。而且滕贞甫的进入,他对小说人物的塑造,他对中国乡村社会这样一个经济关系的想象和描述,在很深的程度上给我们提出了问题,真的是非常深刻。
仓廪足终知礼节,不足怎么办?外部的秩序和礼仪的规驯就特别重要。九里是没有原住民的,都是流民,只有王克笙是有文化的,他的初民管理是带着文化记忆去重建(九里参与议事都是“元老院的贵族”,世袭制,非常像初民的治理),去诉诸那几个家庭,如果没有一种理想化的建构和植入,这个事情是非常难的。但是文学是干什么的?如果这个世界一如既往地贫困、无序、肮脏、混乱、残暴,而我们的文学也一如既往地去肮脏、残暴的话,我们还要文学干什么?所以,一定程度的理想化是应该被我们所原谅和接受的。滕贞甫按照一个作家的想象,根据自己的文化积累和文学能力,给我们拿出这样一部文学作品。我觉得是站得住的,不仅站得住,而且是我2018年非常重要的一本书。
对于《刀兵过》的文化意义,我们可以各抒己见,但是有一点大家应该是认同的,就是它印证了滕贞甫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文学能力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小说的语言,一般写到20万字就撑不住了,就开始粗针大线了,但这部小说,里面的文化含量、器物、规约的那种仪式,细节的考究,都是一个写作者超群的文学能力的表征,没有这种能力是达不到的。
小说写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是既有文学野心,还有文学能力,作家的艺术才华是杠杠的。滕贞甫给我们贡献了2018年年末一部非常优秀的长篇小说。
《刀兵过》的语言非常典雅,正派,稳健,干净。这个干净,不是说情节,而是美学观念,是对小说语言的艺术理解。这部小说的语言没有枝蔓的东西。
此外,小说还有一点是我个人非常感兴趣,我认为也是非常优秀的,就是对人物的处理。比如郭瞎子,这样一个看起来十恶不赦的人物,也有他豪爽精明幽默的地方。滕贞甫的处理不是刀下留人,而是笔下留情。笔下留情不是冬烘、妥协,而是他对世界和人性的尺寸。我不喜欢没有尺寸的事物,走出去,返回来,打出去,能收回来,这是很好的美学、艺术能力的事,同时也表征着写作者对这个世界的基本态度。不是绝对的好,也不是绝对的坏。《刀兵过》有一种暧昧的文化力量,对这种“暧昧”要在一个褒义上去讨论,小说中的人物身上没有负面标签,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的情和义、忠孝节义。我觉得滕贞甫对这个世界和人性理解是有分寸的。这种得小说获得了圆满的成绩。
钱念孙(安徽社科院研究员):
我不是搞当代文学的,当代文学作品我读得少,评价一部作品的好或坏,需要比较,如果读得少,严格讲就没有发言权,不过我也读过一些,比如说《白鹿原》《古船》《最后一个匈奴》。但是读了《刀兵过》之后,我还是很震惊的。
首先是他对百年历史和百年风云的思考。历史无法改变,但是对历史的认识有各种各样的阐释空间。同样是通过乡村来展示百年史,《刀兵过》中王克笙、王明鹤父子和《白鹿原》中的白嘉轩,都是传统文化的化身,但有所不同,这一点显示了作家比较深入的思考。《白鹿原》中,尽管白嘉轩个人的人格形象体现了传统文化的风骨或风采,但是整个描写对传统文化是批判和否定的,令人感到传统文化在百年历史中是必然灭亡和消失的,是无法抵挡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西方文明的冲击,抵挡不了中国的现代化,尽管身上体现了许多优秀的品质,但他还是一个悲剧人物。按《白鹿原》这个路数来写的长篇小说太多,包括《古船》等。
但是《刀兵过》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它翻过来了。
同样是写清末到今天的历史,而且这段历史也正是中华民族历经劫难和沧桑之变的历史,这段历史当中的各种力量,包括义和团的,俄国人的,土匪的,日本人的,国民党的,共产党的,各种文化冲击这里,但九里这个以传统文化来治理的地方,由四户到一百多户人家,它不是衰败的,而是兴盛的,温情的。作家之所以这么写,是对近百年的历史有自己独到的思考。
这个思考,又带出了第二个问题:它是个乌托邦的,在现实当中有没有可能存在?也不能说绝对不能有。这就要说到作品缜密的写实与整体的象征关系。写小说要靠细节,靠细致的描写和动人的刻画来支撑小说的美学力量。小说的充裕性,美学上的跨跃性,在《刀兵过》的整体象征上有很多突破,这是这部小说超跃一般当代小说之处。
它的整体象征有很多,比如碱滩之所以叫“九里”,是因为村庄与道观的距离正好九里,而这个道观是王氏父子的精神寄托之所。
再说传统文化的民间信仰,三圣祠是儒道释三家的东西,也包括民间的东西,还有道观,都象征着中国人的精神,也是对我们近百年来中国社会民间信仰或者说是社会信仰问题的模糊的一种思考。
另外,王氏父子百年中遇到那么多次刀兵,最终顽强挺立。正如滕贞甫在创作谈中所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过刀兵的历史,翻开二十四史,间或总能嗅出血腥气。”我看过一本西方人写的历史书,讲中国有记载的几千年文明史中,平均三十多年就会发生一起战乱。所以说,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就是刀兵过的历史,但是,我们历经劫难,中华民族还能屹立不倒,而且在今天繁荣强盛,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里面起作用,这里面都包含着作者深刻的思考。
在今天这个社会,究竟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现在还在不断重新认识、分析和阐释当中。滕贞甫用自己的小说,用自己深入的思考,对百年历史,对中华民族的历史,甚至超出百年而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和空间上,从人类发展的必然性上来思考,所以推崇了小说中乡贤代表的一套思想与文化。小说除了儒家思想之外,还有很深的道家思想在其中。小说名为《刀兵过》,我认为支撑小说对刀兵的看法是老子在《道德经》中讲的一句话:“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
由于这种缜密的写实和整体象征的关系,所以作品比较有张力,是一个好看、耐看、禁得住品味的小说。能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小说的文化品位,语言晓畅,又有韵味。关键是对古典文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释道文化,包括汉语的韵味,有非常深刻的功力。他的描写细腻多姿,气韵生动,有诗意的叙述,所以很感人。就我读过的小说来讲,包括很多学者写的小说,从小说艺术和文字驾驭表现能力,很少有超过滕贞甫的《刀兵过》的。小说的语言肯定是风格多样的,但有些作品,可能是我的偏见,作为一个汉语的表达,杂质太多,这不是优点。怎样把汉语作为一个小说创作的艺术性的语言,《刀兵过》在这方面有很高的成就,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收获。
虞金星(《人民日报》编辑):
我对《刀兵过》直觉的观感,是古典韵味比较浓厚的小说。一是笔法有力道;二是有驳杂的写作意识。在长篇小说写作中,驳杂不是一個缺点,而是应该有的一个特质。
一是其中有力道,《刀兵过》是有很明确的情节线索的。比如两代王先生要恢复祖姓的信念,比如九里这个小村庄演变的过程。读者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小说在情节之上是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笼罩,这种力量具象化来说,既有大小王先生尊崇的三圣祠、中医和茶中间的道,还有玉虚观两代掌门人的三清全真之道,一种入世的力量,一种出世的力量,在书里时不时以神秘的面貌决定着两代王先生恢复祖姓的努力走向,也决定了九里习俗的形成,以及百年过刀兵的过程中的遭遇。比如几次过刀兵,九里居然是由于三圣祠里供奉的孔夫子和达摩祖师而幸免于难,躲灾的鸽子洞来自塔溪道姑神奇的传讯。如果单从小说的情节上来说,这些都是背逆写作逻辑的,但从笼罩在情节上的道来理解,这些全是合理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这就是义以载道,尤其是与历史相关的古典小说中,情节当然是小说的基础,但是真正主导情节的,是特殊的历史叙述法则。小说情节在整体上会服从、普及这种法则的要求。像《三国演义》里,这个道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脱胎于宋史的虚构梁山水泊这个大村庄的《水浒传》里的道是天数。载道小说适合以宏观整体的全制式角度来取景观照,很容易出现类似于说书人这样的声音。《刀兵过》里没有明确用到说书人这样的角色和叙述方式,但有些细节里面还是透露着这样的痕迹。比如像书的尾部,“马治平就这样当上了九里第一任书记,而且一当就是三十年。后来九里经历的风风雨雨,证明王明鹤的选择高明之至。”这些其实都是说书人的角色。只有从全局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写法才是合理的。还有先天的全知的视角,其实他是与九里拉开了距离的,有一种距离感。
第二点是小说里呈现的驳杂的写作意识。《刀兵过》大概是不只想讲一个乡贤和村庄的故事。我理解大概有三种意识,三种色调。
一是家国历史的意识,讲中国史的意识。小说往小了说是一个小村庄从无到有,从奠基到存续的故事,九里那条青条石在河边的矗立很有历史感;从大的方面来说,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家国一体,所以小说里有远在欧洲的巴黎和会,远在北京的“五四运动”都和九里这个小乡村联系起来了。这两年上映的电视剧,如《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现在在播的《大江大河》,它串联家国历史的尝试和这部小说是很像的。
第二种意识是文化史的意识,小说经常写到一种风俗在九里是怎样形成的,比如写到三圣祠后面的万柳塘,写到玉虚观的修行,从某种意义上有社会学调查和文化史的风味。
第三是传奇的意识。传奇是古典小说的流派,讲神怪,讲侠义。这部小说有通俗文学的基因,尤其是王克笙和塔溪道姑,身上都有传奇的间歇侠客气。单纯从故事发展的角度,从情节推演的角度,这里面很多是闲笔,似乎是古典小说“荡开一笔,话说两头”的写法,但这也恰恰是这部分小说有意思的地方,是它耐读、值得读的地方。透过小说能读到比故事、比情节更为丰富的内容层次,这应该是长篇小说应该有的雄心,它要跃出文学。
我这些年读长篇小说,有时读得很难受。而这部是读得比较过瘾的,尤其是前面的大半部分,因为闲笔更多,因此读得更从容更过瘾。
翟永明(中国人民大学访问学者):
《刀兵过》不是一个外部的历史进程的描写,更多的是它超脱于历史和现实之外的一种精神的力量。人物身上带有儒家的仁、义、礼,比如发乎情止于礼,又包括了道家的文化。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一个是建构一个是解构,一个出世一个入世,但在小说里同时出现了。他是怎么把二者结合起来的?我想是一个“善”字。
“善”在儒家里可能表现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孝悌忠信,那种对父母对兄弟对自然对鬼神对天地的良知,包括外在的笃定,刚毅,隐忍,坚忍不拔,在小说里都有很多表现,是儒家外向的善,对世间苦难产生了非常大的力量;而道家的善更多的是一种道法自然,上善若水,大巧若拙,大悲若喜,大音稀声,大象无形,是这样一种特质,就像那两位道姑,那种世间罕见的纯净无邪,完全超越了俗世,而且对世事是完全洞悉的,是一种内向的善。这个小说最好的点是能将这种外向的儒家的善与内向的道家的善结合,形成更完整的一个善的文本,传达出一种人性的美,甚至是一种带有神性的美。那种美好的感情确实不能逾轨,否则作品所构建出的那种很和谐的秩序或者美可能要被破坏掉。这种美还表现在那种外在的结构上,结构跨度这么大,作家绵绵不绝地控制得这么好,能协调起来,也是源于一种由善结合起来的美。
俞胜(中国作家编辑部主任、作品责编):
滕贞甫的长篇小说《刀兵过》从清朝末年一直写到改革开放之后,小说以王克笙、王明鹤父子谋求恢复祖姓为经线,以清末、民国、伪满等不同历史时期一次次的过刀兵为纬线,编织出一幅20世纪中国乡村波谲云诡的历史变迁图。小说不仅记录了东北乡村的百年沧桑, 也是一部记录乡村人物家族史和心灵史的力作。
王家原本姓“朱”,世代从医,因祖上曾被迫在大周朝任医官而埋下了灭族之患。为了使子嗣绵延,为了使家门免遭涂炭,只得骨肉分离,远走他乡,并易“朱”姓为“王”。当年,王克笙远走白山黑水间时,母亲曾叮嘱:“恢复祖姓,应当从长计议,大周非善朝, 朱家易姓也非光彩事,不到河清海晏之时,不可草率为之。”于是,寻求河清海晏之象就成为王氏父子矢志不渝的追求。清朝灭亡了,民国不见河清海晏,日伪时期更不见,国民党统治时期也不见……不但不见,且一次次的过刀兵让世外桃源般的九里弥漫起战争的硝烟,村民的日常生活遭到战争的蹂躏,人性也在战争的夹缝中被反复碾压、揉搓、重塑。
《刀兵过》中人物形象众多,两代乡贤王氏父子,韵致天成、道行高洁的道姑塔溪、止玉 ,面善心恶的黑木,狡诈、坚忍的“苇地之獾”尉黑子等等,这些人物形神兼备、惟妙惟肖,交织出一组异彩纷呈的人物群像。其中,王氏父子凭借自身的威望、品行、才学让九里有了道德楷模和淳美乡风的引导者。在老先生王克笙、小先生王明鹤两代乡贤的规范和引导下,九里最终成为“世外桃源”,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福地、仁义之乡。村民人人知大义、识大体。小说为两代乡贤树碑立传,也呼应了当下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思潮。
作家滕贞甫潜入民族精神的秘境,揭示宗教和信仰在民间具有多么强大的力量。在九里,“三圣祠”无疑是村民们最重要的精神家园,是村民们的精神依归地。“智仁勇三德,儒释道一家”,因为共同的信仰,三圣祠也庇佑着九里免遭义和团乃至日军的蹂躏。三圣祠流贯在小说的始终,可以说是这部小说的一个文眼。“文革”期間,三圣祠被毁,王明鹤一下子颓废苍老了,甚至患上了阿兹海默症。而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三圣祠终于得以重建,也重建了小先生的精气神,让80多岁的老人“脚步稳健,腰背挺直,完全换了一个模样”。三圣祠的重建也让王明鹤老人感觉终于到了河清海晏之时,于是宣布恢复祖姓。作家滕贞甫以一支游刃有余的笔,既高歌了我们今天的盛世,也潜行进民族精神的秘境中,点触民族精神和信仰的伟大。
行超(《文艺报》编辑):
我看70后、80后写的作品比较多些,因此看过《刀兵过》之后,有受教育的感觉。对比之下,感觉我们这个年龄的年轻作家已经很少有人再去想这方面的问题了——不是说他们能力达不到,而是关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好像已经被年轻一代遗忘了,他们的创作很少涉及这部分。因此《刀兵过》这样的写作非常珍贵。我们应该多读这样的作品。
开始时感觉人物太完美了,身上没有瑕疵。在通常的小说人物塑造中,这样的人物是有问题的,对高大全伟光正的人,我是不能接受的。但越读到最后,越觉得这个人是必须这样的,我反而会捍卫这个形象。我看到山洞那段时特别紧张,我想千万别出事啊,我就特别怕人设到这儿崩了。九里是一个桃花园,是一个超然于现实世界之外的存在,我觉得对这里的生活和历史,对某个人物,不能用现实的逻辑去束缚他们。如果用通常的手法处理,那么一个神性的带有理想主义的人物到这里就崩了,这个我是不能接受的。芦苇荡可能就是一个隐喻,若隐若现,似有似无,如果把镜头推远一点可能就根本看不见芦苇荡中间有人,但他们就存在于缝隙当中,像孙犁写的荷花淀一样,不知道芦苇的缝隙当中有多少生命在生生不息的存在。这样的作家和这样的写作勇气特别值得年轻作家去学习——我们在写作中特别回避和不敢触碰的东西,那些宏大的、人性的、文化的、历史的东西,他是特别坚决地就要写这个东西,这个勇气是特别值得年轻人学习。
(主持: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字整理:吴艳,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8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