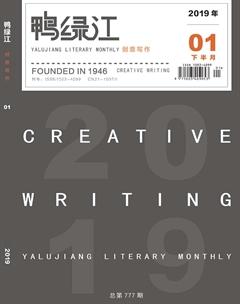创意写作的本相及其对立面
许多初次接触创意写作的人,喜欢从概念入手,在“creative”上生发无穷想象,结果经常掉进自己挖的坑里,还给创意写作带来不必要的烦恼:“难道传统写作就没有创意?”“(如果有)创意写作古已有之!”另有一些从国外回来的作家、学者,亲身接触了国外同行的工作,觉得国外的创意写作与我们国内宣扬、推崇的创意写作似乎不尽相像,因此对国内的创意写作不以为然。还有许多创意写作从业者,按照自己对创意写作的理解,欢天喜地的“埋头苦干”,但也为创意写作的发展埋下了许多隐患。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么,何谓创意写作?作为概念,它如何形成;作为实践活动,它最初因何而生;发展到今天,它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作为一个“革命性”的探索,它的对立面又是什么,等等,种种发问,在中国创意写作如火如荼推进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它进行梳理、回答,以便解除误会,凝聚共识,共同应对中国写作教育的问题。
一、概念的由来
1837年,美国学者爱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在一次题为《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的演讲中,推出了“创意阅读和创意写作”(creative reading and creative writing)概念,并做了阐释。他认为,人们在阅读和写作过程中,由于主动性被激发,因而阅读和写作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而整个文学教育,同样具有创造性。其中,文学研究从属于更高等级的持续不断的文学创造与再创造(re-creation)活动,研究的基础和对象,不應再仅仅是文学作品,而是文学活动(literary act)。
爱默生提供的概念及阐释,为后来创意写作的文学教育、文学研究、文学写作教育、文学阅读等诸方面的展开提供了设想,但最初的创意写作却以“英语写作”(English Composition)的名义存在。直到美国剧作家、创意写作教师威廉·休斯·默恩斯(William Hughes Mearns)的《年轻的创造力》(Creative Youth,1925)与《创意的力量》(Creative Power,1929)先后出版,创意写作才正式指涉一门具体的研究课程。在这两部著作中,休斯·默恩斯公开了自己在林肯专科学校的教学实验,其中包括自己开设的“创意写作”课程。而作为教学/写作实践的“创意写作”首次进入公众视野是在1922年。威廉·斯坦利·布雷斯韦特(William Stanley Braithwaite)在编辑《杂志诗歌选集与美国诗歌年鉴》(Anthology of Magazine Verse and Yearbook of American Poetry)时选入了一首凯瑟琳·科斯马克(Katharine Kosmak)的诗,而凯瑟琳就是休斯·默恩斯的学生之一,创意写作的“作家培养”初现成果,引起了人们注意。次年(1923年),默恩斯借势将学生们三年以来最好的作品名为《林肯诗歌、小说、随笔集》(Lincoln Verse, Story, and Essay)结集出版。这是创意写作教学改革成果的第一次集中展示,根据林肯学校的校长奥蒂斯·考德威尔(Otis Caldwell)在前言中的陈述,出版这部合集的目的在于“全面回应”英语写作课“效果不佳”的抱怨,提供一种“检验诗歌教学成果的方法”。合集的出版收到的效果远远超出了预期,因为读者从《林肯诗歌》中学到了比教材更多的东西。因而也有人将他们将它视为创意写作正式亮相的一次宣言。
二、创意写作的兴起
美国创意写作研究专家迈尔斯(D. G. Mayers)指出,创意写作的兴起与“美国高校中古典文学的式微与英语文学的兴起”背景相关。19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文学教育内容以古希腊罗马文学(即所谓“经典文学”)为主,当代英语文学遭到忽视,教学内容脱离时代生活,那个时候学界普遍认为,除了像荷马、维吉尔这样的经典作家,当代人的作品根本不值一提。这个问题的解决以语文学的兴起作结,然而又带来新的问题。语文学的兴起将英语当代文学抬到与古典文学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是语文学对文学作品的分析照搬了自然科学模式的分析解读,文学被当作语文学和修辞学材料,成为语文学和修辞学的外壳,忽视了文学的艺术本质。这种状况下的“写作”,包括“文学写作”,都从属于语法练习、拼写训练和修辞规则识记。即使在写作作为课程核心的情况下,也着重培养学生在论述过程中的整洁度、敏感度、精确度、正确性及完整性,极尽所能地避免出现错误,不鼓励学生在写作过程中表达自己的观点或想象,写作变成了语言研究的基础。
“英语写作”在此时应运而生。针对传统写作的困境,高校普遍开始开设小说、诗歌写作课程,同时招募大量的作家、诗人进入高校教写作,最初引领潮流的是哈佛大学。1880年,哈佛大学首次开设高级写作的选修课程,写作系的亚当斯·谢尔曼·希尔(Adams Sherman Hill)、巴雷特·温德尔(Barrett Wendell)、勒巴隆·布里格斯(Le Baron Briggs)、查尔斯·汤森·科普兰(Charles Townsend Copeland)等教师,纷纷在自己的写作课程上开始适度改革,部分课程允许学生通过诗歌或故事获得学分。时任哈佛大学修辞与演讲学首席教授的弗朗西斯·切尔德(Francis J. Child)最先尝试给二至四年级的学生每学期布置16篇作文,开设将文学教学的中心从分析研究转向写作实践,逐渐向创意写作的“文学研究最理想的结局,就是文学创作的开始”观念靠拢。切尔德之后,新一代写作教师在修辞学与演讲学课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写作教学的探索,创立了“每日一题”的教学方法。但哈佛的写作改革,包括整个英语写作,却没有把写作教育完整带到创意写作,它们只是创意写作的前身,其功绩是为后者的入场扫清了障碍。温德尔、布里格斯院长、科普兰等人都有某种深刻的道德主义倾向,在他们看来,写作是为了实现个人道德的提升,同时,他们的写作训练主要集中在新闻专业这些“非文学”创作,英语写作已经被改造成了基本能力课程,完全摒弃了创造性自我表达的想法。而在基本能力课上,写作又被简化成了要求学生遵守的一系列外在标准,变成了一种纠正行为的模式。此时,英语写作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甚至成为压抑心灵的工具。
语文学解决了文学教育脱离时代生活的问题,扩大了文学教育的视野,它自身的问题又由英语写作得到部分解决,但英语写作很快就在教育理念、教育内容上陷入僵局,却给爱荷华大学留下了机遇。后者在理念上刷新了英语写作,而在教学内容上,精力主要集中在诗歌、小说等这些虚构类文学写作。
从“英语写作”开始,创意写作就显示出与传统写作的不同之处。第一,在全国范围内,直接开设小说写作、诗歌写作课程,这就恢复了文学的“艺术”属性(而非语文学意义上的材料)。第二,聘请小说家、诗人来教小说、诗歌,实现“行家教学”,也就是我们日后津津乐道的驻校作家的“作家教学”,这就加强了创意写作的专业性。第三,开辟了文学研究的新思路,如温德尔所言:“文学研究的理想终结不是享受诗歌,还包括创作诗歌”,这就坚持了创意写作的实践性。第四,十分重视文学技巧的研究和写作训练,找到了创意写作的抓手。这种思路在创意写作未来的发展中被广泛继承,而“作家可以培养”“写作可以学习”就是建立在“技巧”的教学与学习之上。作为一个教师,温德尔开创并实践了新的教学方法,为美国创意写作教育教学甚至写作水平的提高,做出很大贡献,虽然他只是一个三流作家。
爱荷华大学接过哈佛大学的旗帜,实现了“从英语写作”到“创意写作”的转变,标志是:一,“文学”成为“思想与行动相统一、文本研究与创作技巧相结合的综合学科”,文学以自身为目的。二,开始具有自己独立课程体系、学位进阶体系、评价体系,成为真正的学科。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战后“婴儿潮”、美苏军备竞赛的时代背景下,美国政府大幅增加教育财政投资,创意写作教学也在这期间得到迅猛发展,此处不再多言。
三、创意写作的发展
创意写作作为学科确立了自身地位后,开始走出校园,走向社会,深入社区,广泛介入社会事务,超越文学教育的单一功能。比如大量学院之外的创意写作工作坊,像“未来作家”(Writers of the Future,简称WOTF)、哥谭作家工作坊(Gotham Writers Workshop)、法典作家群(Codex Writers Group)、瓦伦西亚826号(826 Valencia)等组织,继续发挥着创意写作的教育教学功能,或是提供更接地气的创意写作课程、线上线下培训作家,或者通过作家聚集的方式,讨论与出版作品,或是通过提供文学写作辅导的方式,帮助社区居民尤其是外来移民,等等。创意写作进高校、进监狱、进社区、进移民群、进少数族裔,等等,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让它们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一部分,扩大了自己的影响。
创意写作在走出校园同时,也开始走出美国,向全世界传播。它首先在英國落地生根,创建出了自己的学科系统。1970年,东英吉利大学建立了自己的创意写作系统,经过近四十年的学科发展,它不仅成为英国创意写作系统的领导者,也培养出了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石黑一雄、安·恩莱特(Ann Enright)等著名作家,同时,它也为自己所在城市带来了荣耀。2012年5月10日,东英吉利大学所在的诺维奇城正式成为继美国爱荷华城之后的全球第二座“文学之城”。创意写作在英国落地生根后,迅速与英国正在兴起的文化创意产业结合,为英国创意产业的激活,在时尚设计、影像、交互式互动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业、软件服务、旅游、博物馆、美术馆、遗产和体育等领域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创意写作在澳大利亚开辟出了新的路径。澳大利亚政府于1994年发布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明确提出构建创意国家定位(Creative Nation),力推将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结合概念,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并通过创意产业和文化机构来打造澳洲认同与澳洲特色。同年成立了布里斯班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作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直接支持的国家级创意产业振兴机构,这些为创意写作在澳大利亚的发展提供了平台,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文化创意产业紧密结合,并服务于创意国家的定位,是澳大利亚创意写作学科发展的背景和特色。
在亚洲,创意写作也在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港台地区等地推广开来,并迅速与本土文化结合,呈现出了新面貌,其中,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写作体系以及新加坡的探索,更多融入了中华文明和华语写作元素,独具特色。台湾的写作教育更多依靠教育机构与基金会的支持,把文学奖、文学杂志以及其他媒体的参与视为重要支持,文学营、写作营是重要的方式(将另文谈到)。
四、创意写作的培养目标
作为写作教育,创意写作到底要培养什么?这个问题在英语国家也长期存在争论,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念。第一种观念以保罗·道森(Paul Dawson)、简妮·瑟芭(Jane Souba)、格雷迪斯·坎贝尔(Gladys Campbell)、西蒙顿(Dean Keith Simonton)Tan Ai Girl、露拉·B.库克(Luela B. Cook)、安娜·海格(Anna F. Haig)、伯尔·霍格瑞夫(Pearl Hogrefe)、伊丝贝尔· 福特(Isbel O. Ford)、多萝西娅·布兰德(Dorothea Brande)等学者为代表,他们认为,创意写作并非仅仅指文学性的写作,而是包括其他以强调创意为特点的写作类型,是一切“以创意为特点的写作类型”,从文学写作到创意写作,实现了从想象力到创意能力的转变。而作为写作教育,创意写作教学“学生用他们找到的最合适的方式表现他们的所思所感”,主要培养“写作技能”“创造力”“创造性智慧”“自我探索”“积极性”等目标,而作家就是“有创作能力的人”,并非指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家”。第二种观点则以马克·麦克格尔(Mark Mcgurl)、艾伦·泰特(Allen Tate)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创意写作就是“文学写作”,作为一个学科,它主要培养文学作家。创意写作虽是高校(英语)文学的“革命者”,但“大学以及英语系是文学最大的庇护人”。两种观点之间,罗伯·蒲伯(Rob Pope)的观点更客观,他指出:一,创意写作包括各种形式的写作,但是脱离了文学写作的创意写作是无根之木。二,文学可以通过创意写作成为以实践为基础的艺术。三,文学研究、文学理论与创意写作之间存在潜在冲突。其观点三解释了高校文学教育普遍困境所在,而观点二则提供了具体的改革路向,对中国高校中文写作教育改革具有特别的警醒意义,一则对创意写作研究与认识普遍存在的“先入为主”格雷戈里·莱特(Gregory Light)、任意想象现象是一个反拨。
创意写作培养目标之所以难以像其他学科那样被明晰表述,存在着多种原因。一方面创意写作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事实上存在不同的目标和发展模式,正如史蒂夫·梅尔(Steve May)指出的那样,创意写作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它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机制内以不同的方式发展自己,并且拥有多样的目标,导致我们对它的认识难以统一。另一方面,创意写作本身是一个跨学科、跨领域的新型事物,如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Sternberg)所倡导的那样,对它的认识与研究则也要相应的跨学科视角,而实际上,我们对创意写作的认识事实上一直存在着单一、片面的现象。
五、重新理解创意写作
综合考察世界创意写作实践的种种面貌,梳理创意写作的历史进展,同时也综合各种研究对创意写作的理论描述,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创意写作”最初仅仅是指文学写作和文学写作教育,后来泛指包括文学写作在内的一切面向现代文化创意产业、适应文学民主化、文化多元化、传媒技术的更新换代等多种形式的写作以及相关的写作教育。与传统写作相比,它具有如下特点:在对写作的理解上,它认为写作是以创造性思维为主导,以文字、符号等作品为实现形式的创造性活动,创意优先且以创意为本位,并构成文化创意及其产业活动最重要最基础的上游环节部分。在培养目标上,它以提高创意能力、训练写作技巧为指归,可以培养作家,但“成为作家”只是创意写作教育的理想的结果,而“作家”也不仅仅是指传统的文学作家。在学科理念上,它认为人人皆有成为作家的可能和成为作家的权力,坚持大众教育的思路。在学科方法上,它以工作坊方法为基本的、标志性的学科方法,坚持行家(作家/专家)教学,坚持教育教学法研究,专业性是其特点。在教育教学理念上,它认为创意写作是艺术实践,而创意写作教学则是教育科学。创意写作可以教学,但需要科学教学。
六、创意写作的对立面
创意写作在英语国家兴起与发展过程中,其对立面非常清晰且依次出现,在与对立面的交锋与问题的克服中,自身得到逐步发展。但创意写作在中国落地生根以来,情况变得十分复杂。作为一个新兴的、“舶来”的事物,它并没有遭遇到想象中的反对。其一,从一开始,几乎所有最优秀的作家都支持创意写作,而且几乎所有一线作家都进入了高校,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从事创意写作。其二,传统的写作保持了沉默,并未为自己的学科地位激烈辩护,因为它自己的学科地位早已边缘化,急需一场粗暴“革命”。其三,英语国家尤其是美国创意写作的成功,给予中国创意写作莫大鼓励,严歌苓、卡佛、石黑一雄等几乎是免费的励志广告。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创意寫作没有对立面,没有自己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我们注意到,中国创意写作的对立面不是传统的写作教育,传统的写作教育有其合理部分,而是包括传统写作教育在内的教育非专业化、庸俗化及泛化现象。
写作可以教学,作家可以培养,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教学能力,不是所有的教学法都适合写作教育,甚至包括许多大作家,也未必能把写作教好,培育出好作品和优秀作家。我们说,作家教学写作,只是创意写作教育教学的行业要求,而不是说,作家天然就会教学写作。许多作家只熟悉自己的写作经验,只能提供自己的“独家秘诀”,不能提供人类写作的普遍经验,而创意写作提供的恰恰是写作处方,而不是偏方。研究写作规律、创意规律,研究教学教法,是包括作家在内的创意写作从业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和必须完成的课题,但遗憾的是,现在已经出现了急匆匆将缺乏研究准备和教学准备的作家推上讲台的苗头,这既是对作家的滥用,也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中国当然有既在写作上成就斐然又在教学上驾轻就熟的作家,美国当然也有长于写作短于教学的作家,甚至有因为不堪教学重负而退出创意写作的作家,但“作家教写作”,只是创意写作教育教学专业化的前提,远谈不上一步到位。道理很简单,术业有专攻。例子也是现成的,科尔与乔丹,一个是篮球大神、公牛队的大拿,一个是公牛队的跟班,但科尔执教的球队将乔丹(曾经)执教的球队打得找不着北。俩兄弟,一个会打,一个会教。
创意写作要培养作家,创意写作可以培养作家,只是创意写作教育目标的通俗说法,但我们不能把它推至极致,庸俗化。其一,创意写作培养的作家,包括传统文学作家,也包括其他有创造能力和写作能力的作家,不能简单以文学作家为唯一标准。其二,创意写作培养正确的写作方法、科学的写作习惯、系统的写作知识,能激发一个人的创意潜能,提高一个人的写作能力,成为一个能胜任文化创意产业(包括文学消费)链条上写作需要的作家,但并不能保证它一定成为大作家,写出经典作品。如果能,当然喜闻乐见;如果不能,也不必强求,因为成为大作家,写出经典作品是机缘巧合的事情。至于说培养不出“天才”,这个锅创意写作不背,因为创意写作从未说过这样的浑话。其三,创意写作坚持创意优先,这只是对写作现实和写作规律的正确描述,而不是写作的结果,不能保证每一次创作都具有高度创意。如前所述,创意写作改变的是写作观念和写作教育观念,写作观念和写作教育观念的改变,的确能解放写作生产力、创造力,让我们的写作更加自由,但这也仅仅是充分条件,不能保证所有的写作一定比以前的写作更加神乎其技。一定要这样,甚至每一次都这样,否则就是创意写作的失败,这个锅创意写作也不背。
鉴于创意写作在英语国家的成功,以及当下中国写作教育面临的种种问题迫在眉睫,当创意写作引进中国后,中国的“创意写作”似乎雨后春笋,遍地开花。从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大会的规模来看,2015年大约100人参加,三四十所高校有开设课程的想法;2016年则有一百多人,近八十所高校开始做创意写作;2017年参会人员就超过了200人,一百多所高校开始加入这个行列。到了2018年第四届大会时,即使大大限制了人数,也有超过300多人参加会议,这个时候创意写作在高校已经是燎原之势。然而带来了新的问题,许多人做创意写作,只是在抢占新兴事物的“先机”,瓜分新兴学科的“地盘”。一些民间写作培训机构,明明在做“快乐作文”,甚至完完全全的“应试作文”,但一夜之间就改旗易帜,变成了“创意写作”。一些高校,明明缺乏开展创意写作的师资准备、理论准备、教学准备,却时刻准备着“弯道超车”,霸王硬上弓。这种创意写作的泛化现象,必将鱼目混珠,降低创意写作的水准,混淆创意写作的标准,最终让人们失去对创意写作的信任,导致创意写作失去自己的活力与民心。
还有一些“非专业化”“庸俗化”“泛化”混杂的更可怕现象。它们使用了创意写作的一些术语,比如“思维训练”“工作坊”“突破障碍”,借用了一些訓练方法,极力鼓吹解放想象力,“放开写”,越具有想象力越好,越大胆越好。然而,如果这勉强算是创意写作的话,也只是创意写作的第一步:“开始写吧”。但开头了怎么样?有没有更深入的研究文体规律、类型规律,有没有匹配的专项训练,有没有完整的从开头到结尾的系统跟进?等等。更重要的第二步“成为作家”“工坊第二课”,却烂尾了,“梦醒了却无路可走”。一些中小学培训机构借着社会对语文教育的怨气,挟着“反抗语文”的勇气,满地播下“创意写作”的种子,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然而这种行为会严重打乱现有的秩序,被迫让那些参与学习的中小学生,在两个思维频道上不断切换。想想,在应试教育大环境不改变的前提下,这种“大胆”尝试,出现牺牲品恐怕在所难免。
创意写作需要与本土结合,需要向传统汲取资源,需要面向实际,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写作教育的改革可以无限妥协,以致回到老路,或者放任其非专业化、庸俗化、泛化,从而走向自己的反面。正确理解创意写作的本源,理清创意写作内涵外延,是团结更多的写作力量,共同面对中国写作教育教学改革难题的前提和开始。
(文中部分文字选自《创意写作教程》“绪论”部分,这里有改动。)
参考文献
1.David G. Myers, The Elephants Teach: Creative Writing Since 1880,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ew edition 2006.
2.Rob Pop,Creativity:Theory, History, Practice e Routledge, New edition 2005.
3.Tom Kealey,The Creative Writing MFA Handbook, New York ·London,2008.
4.Dianne Donnelly,Does the Writing Workshop Still Work? Multilingual Matters Lt 2010.
5.Joseph M.Moxley, Creative Writing in America: Theory and Pedagogy,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1989.
6.《作为学术科目的创意写作研究》, ﹝英﹞黛安娜·唐纳利著,许道军、王雨萌译,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待出版)。
7.《创意写作的兴起——战后美国文学的“系统时代”》,﹝美﹞马克·麦克格尔著,葛红兵、郑周明、朱喆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8. 《创意写作教程》,葛红兵、许道军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
(许道军,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创意写作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