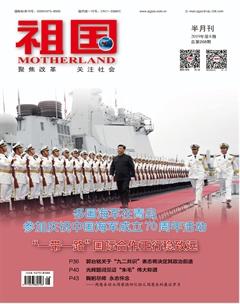人民安全:国家安全治理的逻辑起点与价值归宿
杨华锋
“人民性”的由来
过去讨论人的安全或曰人类安全主要是国际安全研究领域,其旨在对以国家与地区为研究对象的安全研究进行反思,试图提供一种替代性的研究框架,即以人的安全作为分析范式。但囿于国际事务、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格局牵涉众多、影响深远,故始终未能成为普遍接受的分析框架,其中不乏一些学者明确提出人的安全并不具备作为分析框架的基础条件。但随着2014年“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人的安全有了新的内涵与新的发展。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下,人民安全是宗旨,政治安全是根本。如果将国家安全的分析维度分为国际安全和国内安全的话,那么二者的区别是显著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所集中讨论的11种安全议题本质上都是基于国内安全的视角进行阐述的。如果说国际安全主要以民族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那么国内安全就主要以人的安全或者与之相关的议题为研究对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既为政治合法性提供了新的阐述,也为维系与保障国家安全提供了行政层面的实施路径——以人的安全为媒介,通过对人的安全的满足实现人民对政权合法性的认同。
人民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安全感、经济福利改进中的获得感、政治发展中的自由度,是衡量“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政治承诺的实践标准。“人民性”是国家安全的本质属性,人民安全是一切国家安全工作的逻辑起点与价值归宿。失去“人民性”关怀的国家安全话语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人民性”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有持续生命力的国家安全理论与话语体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中心思想其实就是维系与保障人民安全,皆因人民安全关涉领域众多,方才有了涵盖政经文社……各个方面的安全诉求与安全议题。因此,自“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后,无论是国家安全战略布局、国家安全立法,还是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国家安全实际工作,都在努力贯彻落实“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价值要求。如何有效地实现与推进“人民安全”,可以从其需求与供给两个维度进行阐述。
理解人民安全的需求与供给关系
就需求侧而言,人民安全本质上就是三种权利的实践,即人民的生存权、生活权和自由权。这三种权利也基本囊括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所讨论的安全领域。从人民的生存需求来看,经济安全、环境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和核安全均对其生存权构成直接影响;从人民的生活保障上看,社会安全、资源安全和科技安全关乎人民社会生活的安全与否;从人民的自由发展来看,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也决定着其是否享有必要且充分的政治自由空间。
就供给侧而言,尽管人民安全需求的满足包括个体意义上的成长与發展,也包括社群、社区和地方社会的保障与维护,但更多的还是以政府组织为代表的组织化的供给。就政府组织化供给来说,包括政府供给范式、特定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支持、以及具体安全事务领域中的安全产品和服务。政府供给范式说的是政府模式和政府类型,根据行政权的介入与干预程度,政府供给存在无为型、引导型、主导型和掠夺型等范式;从特定的制度安全与政策支持角度来看,政府供给亦可分为攫取型、包容型、发展型等不同制度属性; 具体安全事务中的产品和服务,具有多样性与权变性。
基于国家安全治理的安全供给侧改革
在需求与供给关系讨论的基础上,国家安全的实践环节也就集中呈现为人民安全的供给保障,包括安全的制度供给、服务供给和协同供给。既有政策层面的支持与引导,也有具体安全事务领域的产品服务,同时也不局限于单一供给主体结构,存在政府、企业和社会其他组织及群体的协调合作、协同保障。具体来说:
一是安全观念的变化。当前基于人民安全治理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在理解上仍然存在不少分歧,从观念转变-制度调整-行动规划三者的互动分析框架下,观念的转变是最紧迫的。当下仍存在着将总体国家安全理解为众多安全领域的大合集,各自领域各自部门在回应安全诉求与安全需要时仍然停留在过去的思维框架里,本质上还是一种程式化、官僚化的应对模式。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提出“总体性”时,即为国家安全的总体性、民主性、民本性奠定了基础,之后不论何种言辞都无法跳过这一框定。在我们看来,“总体性”的框定即标志着但凡涉及到安全感知、安全状态和安全能力的问题都可以说是国家安全问题。只是在细分时,我们要讨论哪些是人的安全、哪些是国家的政权安全,同时要厘清不同安全议题或安全情势在不同条件下的互相转化的问题。总体性也就意味着对过去单一性、分散性的一种纠正,安全问题本质上具有系统性、演化性和渗透性,必须在总体性治理的视角下去理解各个领域发生的安全事件。比如响水事件、成都中学腐烂食品事件等,它们都在不同情境下对网络安全、政治安全构成一定影响,必须对其临界条件有着清醒地认知。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一种新型的安全观,其核心思想在于对安全问题的系统性、演化性和渗透性的理解。任何一种安全议题,即便在其“生命周期”中并未呈现出典型的政治安全风险,但不容忽略其内在演化的逻辑,在当下社会中,任何安全风险都有冲击政治安全临界点的可能。因此,必须转变安全观念,传统意义上对安全的军事化、情报化理解是无法满足当下与未来国家安全发展之需要的。
二是注重培育与提升制度框架与政策规划的包容性、开放性和发展性。伴随政府放管服改革的推进以及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要求,人民安全需求的满足也需要与之匹配的政府范式与服务行政的变革。这就要求政府政策供给要更多地体现包容、开放与发展性,避免制度的攫取性与掠夺性。避免再出现诸如简单且粗暴的“清理人口”、“煤改电和煤改气”等机械式政策,在强调中央统一权威性的同时,积极发挥地方的主动性与适应性。
三是在将安全需求进行细分之后,推进安全协同供给实践。国家安全具有“多主体政治与多主体政治安全”的特点,因而在供给方式上,必须调整供给结构,促进供给主体与供给机制的多元化和多样化,提升府际合作、部门配合和公私部门的协调性,系统而全面地理解人民安全需求,并根据需求与供给间的关系做出适当的微观治理安排。这一议题的讨论与推进事实也就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内容。换句话说,人民安全需求的满足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是异体同构的,是从不同视角下对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不同表述。保障人民安全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的中心目标,对人民安全不同维度、不同层次需求的满足既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要求,更是维系与保障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
总之,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功能、类型与能力,既是保障政治安全的关键,也是保障人民安全的必要基础,人民安全是政治安全得以保障的媒介。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是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人民安全”成为一切公共事务治理满意与否的判断标尺。尽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谱系中,政治安全是根本,人民安全是宗旨,但需明确的是,作为政治安全核心内容的政权安全,其安全维系仰赖于人民安全的供给水平。人民安全是其第一要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安全道路的核心价值,保障人民安全利益是国家安全工作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
(作者系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