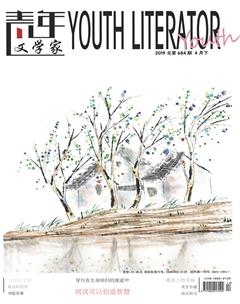《斩首之邀》:辛辛纳特斯的精神特质
摘 要: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文艺创作不能照搬所描写的对象,而是要用陌生化对这些对象进行加工和处理。《斩首之邀》为我们营造了一个荒诞到不可理喻的非真实的世界,将读者带入一种陌生化的氛围之中,其中夹杂着理想、自由等浪漫气息。透过这些浪漫主义和非现实主义的因素我们能看到辛辛纳特斯所遭受的身心煎熬,以及对自由精神之乡的不懈探寻。
关键词:荒诞;矛盾;追寻
作者简介:姜丽娜(1991-),女,汉族,青岛大学2016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外比较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2--02
一、外部世界的荒诞性
纵观辛辛纳特斯周围的环境,到处充斥着荒谬、非现实与不可理喻性:偌大的监狱竟然只有辛辛纳特斯一个犯人;看守他的士兵带着像狗一样的面具,法律要求审判他的法官必须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事实上无法满足这一要求便只好通过化妆来解决;辛辛纳特斯被判斩首,为他辩护的律师又是传统斩首法的倡导者,而且律师也画了兔装;辛辛纳特斯执行死刑前与家人的会面场景也显得如此荒诞,马思全家都来了,家具都搬来了,这一情节描写完全将监狱场景家庭化,分不清到底身處哪里。虽名为探视,但根本没有人关心辛辛纳特斯的死活,妻子马思只顾和情人调情,岳父只管开口大骂,马思的弟弟放声歌唱,马思的孩子各自嬉戏,维克托一天掐死一只猫,监狱中的那只猫也未能幸免,一个孩童的心灵都失掉了原有的童真和善良,反而被麻木与残忍充斥……前一秒还无限嘈杂的囚室,下一秒就陷入一片死寂,这种强烈的对比,产生极大的讽刺效果。
死刑日期来临,这时候一切才渐渐恢复本来面貌:囚室里的蜘蛛竟然是假的,在辛辛纳特斯搬走之后,整个监狱也轰然倒塌,皮埃尔根本不是什么狱友,他才是刽子手!可是这个疯狂的世界却将刽子手奉为偶像,所到之处处处引来尖叫和欢呼。皮埃尔肤色红润,跟在他身后的监狱长和律师形容憔悴,双眼充满粘液,这种对比下存在的关系,不得不令人联想到某些讽刺现实的问题。最后,辛辛纳特斯终于明白了,“一切都欺骗了我”[1],不论是埃米的轻易许诺,墙上的敲击声,还是狱友的友情,甚至连处决时刻的观众都欺骗了他,后面几排的看客竟是画上去的。这是个疯狂的世界,到处都是疯狂的人,辛辛纳特斯感到了自己近于可怜的绝望。
纳博科夫将这些非现实的描写全都塞进《斩首之邀》,通篇小说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冷酷、自认为理所当然的欺骗、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淡漠、对生命的蔑视、死亡仪式感的丧失,而辛辛纳特斯身在其中。在这荒诞的氛围中,辛辛纳特斯对自由的追寻成了整篇小说浪漫温情的显现。
二、辛辛纳特斯自身的矛盾性
灵与肉之间的矛盾。童年开始,辛辛纳特斯活在灵魂彼此透明的世界,而他却是唯一一个不透明的存在,他无法融入周围环境,于是,不得不在半透明与黑色障碍物的夹缝中艰难求生,将自身置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他曾试图寄希望于“古人的迷雾”,但也失败了。成年之后的辛辛纳特斯仍然无法摆脱这种困扰,导致他的行为与意识不统一,乃至相背离。在监狱囚室,他以书为工具,实施自我麻痹,使自己沉浸其中可以暂时忘记与周围环境的矛盾。当看到信中说不能马上与马思见面时,他在罗迪恩面前表现出无比的冷静。然而另一个辛辛纳特斯却哭泣着蜷缩在一只球里,他学会了时刻伪装自己。在监狱里无人时,他摘掉脑袋,摘下锁骨,摘下胸廓……他沉迷于这种对自己的解剖,这种没有盔甲没有面具的时光,但是狱卒一出现,辛辛纳特斯立刻恢复原样,他需要时刻对他者保持警觉。辛辛纳特斯又急切渴望得到他人的理解,哪怕是对于死亡的理解。马思作为辛辛纳特斯的妻子,本应是在心灵上离他最近的那个人,然而事实正好相反,他最终没有得到任何人的理解。辛辛纳特斯一方面自我囚禁,另一方面又渴望接触,这种矛盾的心理不断左右着他。
自身与时间的矛盾。辛辛纳特斯不光与周围的人之间存在矛盾,与永恒的时间同样存在矛盾。由于被判了死刑,他不停追问执行时间,但没有人告诉他确切的处决时间是在哪一天。他想要写点什么,然而,在不知道时间是否充分的前提下他无法提笔开始写作。“如果你对自己说,从昨天开始写时间是足够的,你会倍感痛苦——你又会认为要是我昨天开始写该多好……”[2],辛辛纳特斯因此便总是处于这样一种痛苦的循环中。他觉得自己应该写点什么,或者是留下点什么,因为他的眼睛、听力、嗅觉都是独特的,这充分表现了他对自我的肯定,对自身存在性和独特性的认同。为了肯定自身的独特性,辛辛纳特斯不惜以自己微小的力量与庞大的时间对抗——写作,无论下一秒是否死去,这一秒就着手写作。时间可以杀死肉体,但不死精神。
辛辛纳特斯所面对的对于我们每个人同样适用,放眼整个人类,自从降生那一刻开始就已经被判了死刑,却没有人知道离那一天到底有多远。辛辛纳特斯,包括我们自己,这种与时间的矛盾是不可解的,但辛辛纳特斯却未放弃。
三、对自由精神之乡的追寻
在这个充满荒诞性与不可理喻性的世界,辛辛纳特斯身心处于巨大的矛盾之中,但他仍然不放弃对自由精神之乡的追寻,全书中浪漫主义的痕迹由此开始显现。
从童年开始,就尝试与他人建立联系。成年后,囿于牢笼,意识却不断出走,这是一种充满理想因子的浪漫的出走。从第一章开始,辛辛纳特斯被囚,却在监狱中实现了意识的出走。此后,辛辛纳特斯的意识多次翻越围墙,一路上磕磕碰碰,仍能看到心中所想。每次对马思的怀念也是对家的怀念。“家”相比于外部世界,是一个比较私人的、隐秘的、自由的场所,辛辛纳特斯渴望有一个隐秘的天地,不被监视,行动自由。另外,除了多次提到“家”之外,塔玛拉公园多次出现,这是一个与“家”的概念相对的,开放的场所,却仍为辛辛纳特斯所迷恋,可以看做是辛辛纳特斯自由精神之乡的代名词,也是他对外部世界唯一的希望所在。周围的一切都不可信,唯有公园是他所念。每次意识的远走,都因现实的介入而失败告终。肉体无法离开囚禁他的狱室,即便在意识层面他也要无条件地接受他者的随时介入,并始终不能真正地自由地徜徉于公园之中。那幅画在墙上凹处的塔玛拉公园的远景,仿佛时时刻刻都在嘲笑着辛辛纳特斯。
透过塔玛拉公园,我们看到了他对自由的热切的渴望。因此,当辛辛纳特斯拒不接受监狱人员的示好时,年少的埃米在不知不觉中,于某种程度上却成了最理解辛辛纳特斯最真切的需求的人,并顺利地成为辛辛纳特斯的精神寄托。他轻信了少女的许诺,在谜底揭开后,他却败的更加惨烈,“这就像一个人最近在睡梦中失去了自己在现实中从未拥有过的东西而伤心。或者希望明天又能梦见把它找回来了。”[3]
终于,与现实之间深深的矛盾使辛辛纳特斯不再挣扎,而是选择了自我逃离。辛辛纳特斯对梦和现实有其独特的见解,在他的梦里,世界是活的,迷人的,崇高的,自由的。清醒生活是半睡眠状态,梦才是纯现实。梦境彻夜发出光芒,那里的一切能愉悦灵魂,又充满童趣。从他的梦中我们能看到与荒诞现实之间的巨大对比,此时的梦已不仅仅是梦,是辛辛纳特斯与现实对抗的武器,他以此为盾,守护着自己的自由精神之乡。小说的结尾,辛辛纳特斯在上断头台的那一刻,他坚持要自己走,这是在不自由的环境下能做出的唯一自由的选择。
结语:
在这个荒诞的世界,辛辛纳特斯是一个孤独的旅人,怀揣着放光的梦,以一己的星星之火,给自己周围黑暗的世界,提供一点亮。手捧这点亮,即便在绝望的境地仍然心中依然涌动生的渴望,不灭的是对自由精神之乡的探寻。
注释:
[1]《斩首之邀》:纳博科夫,陈安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8月第一版,第177页。
[2]《斩首之邀》:纳博科夫,陈安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8月第一版,第37页。
[3]《斩首之邀》:纳博科夫,陈安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8月第一版,第177页。
参考文献:
[1]《固执己见 纳博科夫访谈录》:纳博科夫著,潘小松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什克洛夫斯基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
[3]《纳博科夫小说 追逐人生的主题》:王青松,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