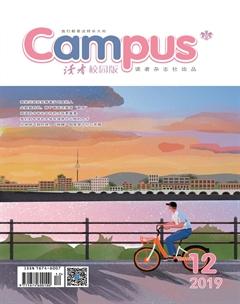那些珍藏在抽屉里的爱与惊喜
文珍
一
儿时总是很喜欢去妈妈办公室,因为翻检她的抽屉时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一进门我就直奔主题,一层一层地仔细翻检。妈妈偶尔试图阻拦,但更多时候为避免我影响她工作,只好舍卒保车。而掠者如我,只觉常翻常新,永远都有彩头:没用过几次的三色圆珠笔;同事送她的旅游纪念钥匙扣;一个和小学生作业簿气质完全不同的牛皮纸笔记本,上面写着“工作手册”……再不济,也能找到几颗快融化的大白兔奶糖。最幸运的一次,是找到一支英雄牌钢笔,还是最新款的。这支笔我后来用了好久,几乎一直用到小学毕业。
从抽屉中缴获这些让人兴奋的、似乎带着妈妈熟悉气息的战利品,是我童年时十分愉快的经历之一。长大后,妈妈才告诉我,其中有些本来就是给我的礼物,她怕直接给了我不以为意,便故意藏在抽屉里让我自己去发现,那样我会更高兴,到手后也会更加珍惜。
她实在是儿童心理学的高手。还有几桩小事,想来都颇令人钦佩。幼年的我一旦不肯早睡,她便把我骗进房间,飞快地把客厅墙上的挂钟取下拨快一个钟头,过一会儿再走进房间告诉我过了睡觉时间。我不信,她便让我出去自己看——一看居然已比该睡的时间晚了半个钟头,顿觉已占尽便宜,困意便当真无可遏制地袭来。待我乖乖睡下,她再把时间调回去。
另一个谎言同样收到了奇效。从小到大,每次开家长会,基本都是妈妈去,而无论成绩好坏,回家我都鲜受惩罚。甚至成绩不太好的学期也是如此。实在忍不住问她老师有没有告状,妈妈总说:“没有——啊,某老师好像还夸你聪明。”我无功受禄,简直不能置信,说这科明明考得不好啊。妈妈若无其事道:“人家老师当然分得出谁是真聪明,只是不用功。”惭愧而备受鼓舞(其实只是虚荣)的我下学期分外用功,该科成绩也就真的上去了。也是成年之后的某天,我才突然福至心灵:“初中那个化学老师是不是从来就没夸过我?”妈妈笑道:“你猜。”
然而最好的母女情也必然在时光流逝中经受考验。上了大学之后,我和她的分歧日渐增多,记得大二有一次和她在电话里大吵,挂断后异常难过,立刻坐下写了一封道歉信,并在没来得及反悔前一鼓作气寄了出去。放假回到家里,我无意间拉开她梳妆台的抽屉,突然看到那信封,顿时如遭雷击,满面通红,飞快地合上了抽屉。
今年回家过年,我竟又在自己房间的抽屉里看到了它。这一次我终于鼓足勇气打开了,开头就是:“我预感自己可能永远都不好意思再看这封信。妈妈你不要笑我。但我实在是很爱你,才会和你如此较真儿……”
时隔十几年,我还是脸红得读不下去。
以上是关于妈妈的抽屉的故事。
二
爸爸在我的故事中,向来缺席,上学时甚至还有同学以为我来自单亲家庭。但是爸爸其实一直都在,只是存在感稀薄——我嫌他当了一辈子顽童,从不像“别人家的爸爸”那么懂事。上小学三年级前我还肯和他一起玩,到三年级后老师开始布置作文,我一动笔他就在一旁跃跃欲试:“要不要我帮你写,写完带你去玩?”
我白了他一眼:“你上次帮我写的那篇,老师说是我所有作文里写得最差的一篇。”
每次我自己写的都是全班的范文,必被当众读之。我每次都得意得要死,又假装鸵鸟羞愧得把头藏进课桌抽屉里,其实虚荣心早已爆棚。大概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我惊觉自己已长大,而爸爸并没有,此后只好和他分道扬镳。
爸爸和外婆这两个斗了一辈子嘴的对头,现在有时会平静地并排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外婆再也不说他了。妈妈和我看到,总是会含笑对视一眼,什么话都不说。
爸爸同样也有关于抽屉的故事。
故事同样要追溯到小学高年级,我和他已经快不做朋友了的年代——有一次学校布置课外作业,要求每个人做一个手工模型,并参加全校比赛。众所周知,本人动手能力极差,因此只得放下身段重新向旧玩伴求助。“老顽童”不计前嫌,一口应允。那晚我被早早打发上床,却一直睡不着,我发现他书房的灯一直亮到半夜。
我明明告诉他随便做个什么只要能交差就行的。
不料到了第二天早上,他给我变出了一个奇迹:49个火柴盒粘在一起做成的抽屉柜!整体刷上了漂亮的红橡木色,每个火柴盒上还贴了一个用金色香烟纸箔做成的拉手!它就那样端正堂皇地立在桌子上,就像真正的抽屉柜,或者一个梦境。现在想来,大概最像的,还是一个迷你中药柜——这大概就是我一直迷恋药柜的起因。
我在那里呆立许久,脱口而出的却是怪他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做了一个不能再拿回来的东西。
最后得没得奖,我早已不记得了,能确定的是,抽屉柜最终果然没有回到我手中。而我至今仍然不知,爸爸是如何在一夜之间,找到了49个空火柴盒和红橡木色的木器漆。
长大后,我偶尔还会梦见那个柜子。在梦里,我又变成了那个八九岁且心高气傲的小女孩,皱着眉看着抽屉柜,陷入交与不交的两难之中。
说起来,我和爸爸不再一起游戏也已经二十几年了。去年他来北京看我,我毫不犹豫地把他带到了中国科技馆。
老顽童果然在里面兴高采烈地玩了一整天,连吃饭都舍不得离馆,就在馆内买了个盒饭凑合。回家后还和我显摆,那里面除他之外,其他成年人就只有带学生来参观的小学女老师们。他带那些小孩尽情体验各种项目,自己也趁机坐了无数次模拟火箭、航天飞船和汽车……还说那些漂亮的女老师都喜欢他。“我帮她们省了多少心!”而他最高兴的,则是可以趁机捏那些小孩子肥嘟嘟的脸,“随便捏,他们都无所谓!”这自然也是恶趣味之一。然而这次我笑嘻嘻地听他说完,没有抢白,没有嘲讽,也没有不耐烦。
童年的遺憾之一,大概就是把那个用火柴盒做成的柜子听话地交给了学校。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重新选择,一切真的会不同吗?
那样,我希望和爸爸的关系比现在更好一点,当玩伴的时间也更久一点。
至少,不必那么着急地长成一个正确而无趣的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