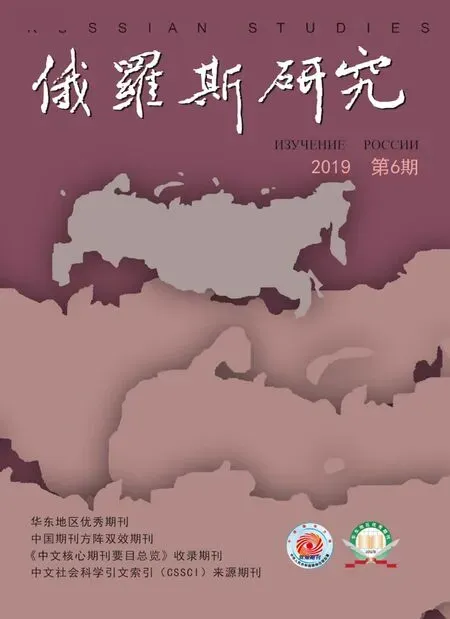反抗与重塑: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对俄罗斯文明的新构想*
郭丽双
政治思潮研究
反抗与重塑: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对俄罗斯文明的新构想*
郭丽双**
俄罗斯文明定位的不确定性,是千百年来困扰其身份认同和国家发展方向的难题,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再次面临这一难题并重新抉择。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在俄罗斯多元化思潮的激荡中脱颖而出,其强大生命力在于,它在文明论和地缘政治学层面上,较合理地回答了俄罗斯文明定位不确定性的难题;并在深厚哲学建构的基础上,提出反抗西方文明普世论和国际政治旧秩序、重塑俄罗斯文明和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新构想。以重塑俄罗斯文化共同体的方式重塑俄罗斯文明,对俄罗斯本国的国家认同是一种建构性力量,但它一旦超越国界就容易引起国家间或区域间的冲突。
新欧亚主义 俄罗斯文明定位 俄罗斯文化共同体 俄罗斯外交
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对俄罗斯文明的新构想新在哪里?这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在其中的贡献是,它以多元文明论反抗西方的普世价值论,以欧亚文明论重塑俄罗斯的国家定位;于哲学和地缘政治学之基整合建构出“第四政治理论”、“新俄罗斯”、“第三类世界秩序”等政治理论,反抗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旧秩序;以重建文化共同体来重塑俄罗斯的欧亚文明定位、国家发展定位,试图重塑世界的文明秩序和国际政治新秩序。根据俄罗斯政界在国家认同和国家文明定位方面的表态,我们可以确定,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在学理层面和政治实践层面使俄罗斯摆脱了几百年来“斯拉夫派”和“西化派”东西方文明循环争论的困局,它完成了从自身欧亚文明独特性出发,为反抗西方价值体系、探寻本国独特发展道路、重塑国际政治新秩序而进行文明论奠基的时代使命。
当前,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提出反抗西方文明普世论和国际政治旧秩序、重塑俄罗斯文明和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新构想,成为俄罗斯学界和政界的热点。它与当下俄罗斯面临的重新选择紧密相关,它为在东西摇摆中的俄罗斯文明定位找到了自己的根基,从学理层面较合理地解决了俄罗斯文明定位和国家身份认同的尴尬。俄罗斯文明定位的不确定性,是千百年来困扰俄罗斯身份认同和国家发展方向的难题。“双头鹰”民族在东方与西方的两极张力间摇摆,是东西方两种精神在俄罗斯灵魂中的斗争,它使俄罗斯的历史发展呈现出间断性和跳跃性。俄国白银时代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Н.А. Бердяев)曾在《俄罗斯的命运》中揭示了俄罗斯文明的这种复杂矛盾性:俄罗斯的自我身份认同在东西方两种文明的碰撞中生成,其理想型的文明定位是代表全人类,其拯救全世界的弥赛亚使命也源于此。[1]俄罗斯的历史事件多次践行了这一使命:彼得大帝西化改革、叶卡捷琳娜二世向欧洲扩张、苏联向其他国家输出社会主义模式等。这种代表全人类的文明定位,使俄罗斯在理论和现实中都遭到惨痛的重创。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独立初期经历了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我们是谁”“向何处去”的“俄国斯芬克斯之谜”再现。[2]急剧的社会转型呼唤新的精神价值基础,俄罗斯的社会思想陷入错综复杂的多元化思潮中。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解决西化派与斯拉夫派的传统争论?俄罗斯的文明定位和国家身份认同何在?正是在回应这些关键性问题中,欧亚主义骤然复兴。在继承古典欧亚主义提出的俄罗斯欧亚文明论之基础上,新欧亚主义完成了哲学、地缘政治学、民族学和地理学的整合性建构,由纯哲学转向政治哲学,进而走向政治实践,开启了该学派的新阶段。[3]它以俄罗斯文明的欧亚性之独特价值和多极文明论反抗西方文明普世论,反抗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旧秩序;以重建文化共同体来重塑俄罗斯的欧亚文明定位、国家发展定位,进而试图重塑世界的文明秩序和国际政治新秩序。
一、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
20世纪末以来,在国家体制变换和改革失败后,俄罗斯社会各界开始了理性反思。“俄罗斯向何处去?”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只有欧亚主义才能拯救俄罗斯”的主张引发了强烈关注,古典欧亚主义被唤醒,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成新欧亚主义(Неоевразийство),对俄罗斯的内政、外交产生重要影响。普京自第三次出任总统以来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等,都与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密切相关。笔者认为,它不仅成为俄罗斯经济战略、外交政策、政治联盟的理论依据,而且是俄罗斯文明定位、国家身份认同的哲学基础。
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首先是从学术界以欧亚文明论立场批判西方文明普世论开始的,它由欧亚主义思潮逐渐发展成熟为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当代欧亚主义哲学家古米廖夫(Л.Н. Гумилёв)、帕纳林(А.С. Панарин)、俄侨哲学家留克斯(Л. Люкс)尖锐地批判了西化派的主张。[4]他们指出,自由主义西化派的观点是乌托邦,因为俄罗斯有自己的文明特点,永远不会变成欧洲国家。[5]自由主义西化派脱离俄罗斯现实,造成俄罗斯严重的对立和矛盾。从1991年起,俄罗斯哲学领域著名的杂志《哲学问题》,刊发了一系列关于古典欧亚主义的学术论文。[6]
古典欧亚主义的复兴、新欧亚主义的再造、“国际欧亚主义运动”的成立、新欧亚主义思潮的传播与发展,都与俄罗斯当代的一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直接相联。此人就是原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现任“国际欧亚主义运动”领导人杜金(А.Г. Дугин)。杜金从1991年起担任莫斯科《要素》杂志主编,他对新欧亚主义思潮的理论建构与传播,对“国际欧亚主义运动”的成立与发展,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997年,杜金出版了《地缘政治学基础》一书,标志着新欧亚主义再造的完成,同时开创了地缘政治学在学术领域的先河,使其成为当今俄罗斯的显学。目前,地缘政治学已成为俄罗斯政治学的教学课程,该书也是俄罗斯政治学的教材。众多的出版与研讨活动,使“欧亚主义”一词频繁出现在媒体上,在俄罗斯掀起了新欧亚主义思潮。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成立了古米廖夫基金会,俄罗斯科学院设立了“欧亚研究中心”;在莫斯科成立了“欧亚主义”出版社,《欧亚主义》杂志也得以创刊。[7]在此影响之下,俄罗斯民众开始认识到欧亚主义的当代意义,将其视为拯救俄罗斯于危难的民族精神。著名电影导演米哈尔科夫(Н. Михалков)满怀激情地对欧亚主义充满期盼:“俄罗斯永远是欧亚国家,在我们这里,如果说有道路的话,我想这就是自己的发展道路——欧亚主义的道路”。[8]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逐步从确立走向发展成熟,其代表性文献包括:《地缘政治学基础》(2000)、《全球化的诱惑》(2003)、《铁幕的真相》(2007)、《第四政治理论》(2009)、《21世纪俄罗斯:今天的日程》(2013)、《相对于俄罗斯的新俄罗斯:新起点还是毁灭?》(2015)、《俄罗斯:重新面临道路的选择》(2015)和《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俄罗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任务》(2017)等。[9]
在俄罗斯新旧历史转换和急剧的社会转型中,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作为古典欧亚主义在当代的重生,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新欧亚主义思潮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是从1989年到1993年。这一时期探讨的主题是俄罗斯文明类型的归属问题,其主张体现在与其他学派代表的论战中。这场争论主要是在当时俄罗斯社会三位著名的思想家——古米廖夫(Л.Н. Гумилёв)、利哈乔夫(Д.С. Лихачёв)和索尔仁尼琴(А.И. Солженицын)之间展开。古米廖夫主张,俄罗斯属于欧亚文明,其文明特征与游牧民族紧密关联。而利哈乔夫认为,从文化起源来看,俄罗斯文化与欧洲文化具有同源性,所以俄罗斯从来就不属于东方,俄罗斯文化是欧洲文化的重要部分,“回归欧洲”从来就是俄罗斯各个时代的强音。利哈乔夫驳斥古米廖夫的观点道:如果俄罗斯文化被确定为介于欧洲和亚洲之间、西方和东方之间的文化,那么,按照这种主张势必推论出俄罗斯文化是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化,而实际上俄罗斯文化对欧洲文化做出过独特的贡献,它不应该被视为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化。[10]对于以上争论,索尔仁尼琴发表演说指出,不应该把俄罗斯简单地划归到欧洲或者亚洲国家,因为从高加索到中亚的穆斯林共同组成了俄罗斯国家的人民,俄罗斯的各民族与东斯拉夫民族一起构成一个整体。[11]俄罗斯只有回归传统才能不被西方所同化,才能有自己的未来。这一阶段的争论虽然没有达到一方说服另一方的结果,但是在俄罗斯文明归属的问题上,不再只是拘泥于几百年来俄罗斯属于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的争论。俄罗斯属于独特的欧亚文明这一观点,引起了俄罗斯社会的广泛关注,古典欧亚主义创立的欧亚文明论,在隔离于故土之外几十年后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12]
新欧亚主义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是从1994年到1999年。这一时期探讨的主题是俄罗斯发展道路的选择。1993年叶利钦总统炮击俄罗斯联邦最高委员会的“十月事件”,引起了学术界对1991年俄罗斯历史道路选择正确性的质疑。很多新欧亚主义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对俄罗斯发展道路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他们努力使新欧亚主义独特的学术思想,转变为对俄罗斯社会发展特殊方式的有力阐释。这一时期形成了新欧亚主义一个创造性的思想——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学说,它提出了在地缘政治博弈进程中的一系列政治学知识。自此,新欧亚主义理论家分化成“文明论”和“地缘政治论”两个不同的研究路向。前者以人类文明的形成、分类、发展与前景为着眼点,揭示了俄罗斯文明形成的过程、文明内涵及其未来发展方向,将其界定为欧亚文明;后者则从地理学、民族学和政治学融合的视角出发,根据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研究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政治行为,揭示了俄罗斯跨欧亚大陆的地理政治现实,认为决定俄罗斯未来发展的必定是复归俄罗斯历史中鼎盛时期的欧亚帝国模式。新世纪以来,俄罗斯新欧亚主义逐渐将两个不同的研究路向相结合:在地缘政治基础上,重塑俄罗斯文明。
新欧亚主义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是从2000年开始直到现在。新欧亚主义思潮按照政治立场的不同,分化为左派、右派和中派。先后出现了“欧亚党”、“国际欧亚主义运动”等以新欧亚主义为主导思想的政党组织和社会组织。在政治实践方面,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成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国际组织的思想基础。[13]新世纪以来,无论在政界还是在学界,新欧亚主义都成为关注度最热的焦点。在对待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态度、俄罗斯与西方文明的关系、俄罗斯未来的发展方向等方面,该思潮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政治立场和价值立场。
新欧亚主义左派的代表人物,包括俄罗斯自然历史学院教授伊格纳托夫(И. Игнатов),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巴什基尔国立大学哲学系教授瓦希托夫(Р.Р. Вахитов),俄罗斯科学院科学与政策分析中心教授卡拉-穆尔扎(С. Кара-Мурза)和俄罗斯国立电影大学教授捷列金(С.М. Телегин)等人。他们的著述和活动大多刊登在《东方》和《红色欧亚》文集中,同时发表在“俄罗斯局势”和“奥伊泽杜林”的网站上。新欧亚主义左派的基本主张是:强烈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民主制、多党制和议会制,认为资本主义是病态的、邪恶的社会秩序,贪婪、消费本能、人们之间的仇恨支配着它;主张所有非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反抗处于“全球资本主义”顶端的西方现代资本主义;主张宗教和共产主义相结合,该派的代表们大多数信教,认为各种“宗教”组织都是平等的,社会主义和宗教世界观及其二者在社会中的角色相容相通。[14]
新欧亚主义右派的代表人物,有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帕纳林(А.С. Панарин)、《我们的同时代》杂志主编科日诺夫(В.В. Кожинов)和乌克兰国家地理协会会长帕先科(В.М. Пащенко)等人。现任“国际欧亚主义运动”领导人的杜金(А.Г. Дугин),他原本是新欧亚主义右派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其“第四政治理论”曾经是新欧亚主义右派立场的典型代表作。但在乌克兰危机前后,杜金的政治立场发生了改变,更倾向于激进的左派,主张诉诸武力解决乌克兰危机,并主张以此作为重建“俄罗斯世界”的开端。相比之下,帕纳林、科日诺夫等,则始终是持欧亚文明论坚定右派立场的代表。该派的主要观点是:主张欧亚文明论,认为俄罗斯的欧亚大陆地理空间这一自然条件,是欧亚各民族相互融合、创造欧亚文明的客观先决条件;欧亚文明是人类文明中独特的一种,是东西方交汇的结果,它不隶属于东方文明或者西方文明;主张文明多极论,认为人类任何历史时期曾出现过的文明都有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不应该以人类进步论和文明进化论的思维方式考察人类各个文明的发展,而是应该以尊重每一种文明类型的思维方式,考察当时当地某一特殊文明样态;主张俄罗斯必须有强大的国家政权,认为恢复强大的国家权力,是防止俄罗斯这个国家灭亡的唯一途径,因为俄罗斯的历史证明,任何削弱国家权力的行为都可能导致该国解体;俄罗斯历史的自然延续是俄罗斯人民命运的发展延续,1812年俄法战争、1917年十月革命、1945年战胜德国法西斯等,都证明了俄罗斯历史的核心是强有力的国家;[15]主张爱国主义是俄罗斯人民意识结构中最高的精神价值原则,它不应被理解为对俄罗斯前社会主义(君主制时期俄罗斯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热爱,而应被理解为对俄罗斯国家的绝对忠诚。[16]
新欧亚主义中派(温和派)代表人物,是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教授科瓦列夫(Ю.А. Ковалев)。他批判杜金以“全球使命”、“俄罗斯世界”等错误观念将新欧亚主义由保守引向激进,挑起俄、乌冲突。他指出,俄罗斯地缘政治地位确实存在客观的矛盾,当前世界明显分化为三个强大的趋势:美国“强迫引用民主”的活动在增强;宗教激进主义分子活动有所增加;杜金“俄罗斯世界”的思想将变成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中心轴”。科瓦列夫认为,悲剧在于三个趋势的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是真理的代言人,因此相互间都不能被说服,无法达成共识。杜金主张通过战争解决这一矛盾是错误的,因为矛盾的根源在于价值观上的冲突,武力无法解决价值认同问题。科瓦列夫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正确方法,是建构三方都认同的新价值秩序,能完成这一使命的,是古米廖夫的大欧亚主义与索洛维约夫的世界意识,二者结合构成的第三类世界秩序,将是矛盾三方达到价值共识的基础。[17]
由上可知,新欧亚主义左、中、右三派的不同在于:左派试图将新欧亚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从宗教的立场出发,认为这是在此岸世界中最好的实践方案;中派主张将斯拉夫主义与新欧亚主义相结合,认为这是解读俄罗斯文明密码的唯一途径;右派则主张将保守主义与新欧亚主义相结合,认为强有力的国家权力,是俄罗斯保存国家不毁灭的必要前提。三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试图重塑俄罗斯文明,反抗西方文明普世论对俄罗斯的侵蚀,主张只有新欧亚主义才能重振俄罗斯的雄威。以上左、中、右三派划分的依据,是对待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态度和俄罗斯传统价值观的立场,这是俄罗斯和中亚一部分学者的观点,这显然带有欧美国家的意识形态划分依据的色彩。目前俄罗斯思想界对于该思潮的研究和派别划分,还没有达成理性的共识,是否能够达成不同于欧美国家的意识形态划分的依据,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跟踪研究的要点。另外,左派将宗教和社会主义相结合,这是看似矛盾的结合,但是在俄罗斯这个富有浓厚东正教传统价值观的国家,有许多学者从宗教的天国在现世的实现,来解读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在当代俄罗斯,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无神论的代名词,俄共也在积极与东正教会展开各种合作。
二、新欧亚主义的反抗与重塑
反抗与重塑,是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从理论贯穿到实践的主题。它在深厚的哲学建构基础上,提出反抗西方文明普世论和国际政治旧秩序,重塑俄罗斯文明和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构想。新世纪以来,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成为俄罗斯学界和政界的热点,它不仅是自由主义改革失败和俄罗斯融入欧洲受阻的应激性反应,而且较好地回答了俄罗斯迫切需要明确的文明定位和国家发展模式等问题。
“在人们投身于改造世界的实践之前,仅仅知道当下所处的世界存在很多问题是不够的,人们还需要知道一个更好的未来世界是什么样子的。”[18]反抗与重塑这一主题,在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的不同时期、不同代表人物思想中,有不同的侧重和表现,但总体上都是以欧亚文明论为基本立场:俄罗斯的文明定位是欧亚文明,是不隶属于东方文明、也不隶属于西方文明的独特文明样式。它在古典欧亚主义思想资源的基础上,用现代地缘政治学、人类学等新方法,批判和反抗西方文明普世论、重塑俄罗斯欧亚文明的独特性。其基本观点是:在文明观上,主张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俄罗斯欧亚文明的独特性,以文明多元论反抗西方普世论;强调本土主义的价值,俄罗斯文明是世界多文明体系的一极,其独立的文化价值在于欧亚性的精神文化。在政治观上,主张在地缘政治基础上的权威主义和强国主义,通过加强国家作用的方式,将民主、法制与强大的国家政权相结合,对内实现团结和维护社会秩序,对外则巩固传统地缘政治利益和扩展地缘政治空间,实现其帝国梦想。在价值观上,主张“新欧亚的民族主义”,高举反抗美国价值秩序和政治秩序的理论旗帜,或基于文明多元论或基于第三类的世界秩序,构造地缘政治基础上的超民族认同,构造反抗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及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新欧亚价值体系。[19]在宗教观上,主张回到原初而古老的宗教信仰,各种不同的古老宗教(正统的东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等)都与现代存在主义哲学中人“在”的这一本真状态内在相连;在人的原初内在生命中形成相容共通的价值观,让人们从内在精神出发去信仰各种古老宗教;在纯粹的精神信仰中找回人的原初本质,找回现代哲学对人形而上存在的遗忘,找回人类存在的哲学本体论和神学根基。
当前,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反抗西方文明普世论、重塑俄罗斯文明的新构想,主要体现在帕纳林、杜金和科瓦列夫等哲学家的理论建构中。
(一)帕纳林的俄罗斯文明欧亚独特性
作为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文明论的杰出代表,帕纳林曾尖锐地指出,俄罗斯的欧亚性与西方在文明类型和地缘政治上的对峙将导致全球危机。在《神秘的铁幕》(2006年)一书中,他预言道,“只有欧亚主义才能拯救俄罗斯”,俄罗斯将像自己的先辈一样,将来要把标志着俄罗斯独特文明的两大元素“陆地和海洋”合而为一。[20]
1. 俄罗斯文明的欧亚独特性是民族、宗教、政治、文化融合的产物
帕纳林在文明共性的基础上考察了俄罗斯文明的特殊性,强调俄罗斯文明可以作为世界文明中的一个样态而存在。“在东西方民族政治和历史文化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欧亚人民国家身份认同和民族宗教包容性”[21],它们造就了俄罗斯文明的欧亚独特性。帕纳林批判了全盘效仿西方的西化派观点——俄罗斯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注定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和自主性,只能跟在西方的后面。帕纳林的观点是,“在构建俄罗斯社会时,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抽象的一般原理,而应是俄罗斯的具体特点,民族的幸福与繁荣”。[22]因此,俄罗斯的发展,只有依靠自己几个世纪以来与游牧民族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独特欧亚传统和价值观,才会有光明的未来。
2. 通过传统的内在精神信仰重塑俄罗斯国家制度的文明基础
帕纳林明确地提出了俄罗斯传统的欧亚主义使命——作为先锋带领弱者反对强者。东正教的救世主义和整个俄罗斯历史,都在践行这一使命。帕纳林认为,社会动荡的根源是精神危机,摆脱这种危机的唯一出路是,促使人们从内在精神出发去信仰正统的东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23]同时他进一步发展了古米廖夫“只有欧亚主义才能拯救俄罗斯”的思想,主张俄罗斯以新欧亚主义的政治定位和俄罗斯文明独特性,应对西方世界的挑战,以回归彼得一世之前俄罗斯的原型,找回已失去的东斯拉夫和图兰成分的统一,重塑俄罗斯国家制度的文明基础。[24]
(二)杜金的“新俄罗斯”构想与“第四政治理论”
杜金[25]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代表,被外媒称作“普京大脑”,并被列为与伊斯兰恐怖组织领导人齐名的人物。[26]原因就在于,他的欧洲大陆主义方案、“新俄罗斯”构想、“第四政治理论”等哲学思想,在重塑俄罗斯文明、反抗欧美主导的世界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欧洲大陆主义方案
杜金把古米廖夫的欧亚大陆发展空间的理论范围和活动范围扩展到了欧洲,他认为,欧洲对于欧亚主义“大空间”具有地缘政治的完整性和战略重要性,其中乌克兰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地缘政治上来看,乌克兰和俄罗斯联盟,是重建俄罗斯欧亚帝国的主要保证”[27]。正是基于这一观念,杜金在乌克兰危机中极力主张东乌克兰必须加入俄罗斯,称乌克兰从历史、地缘政治、文化认同等方面,都与俄罗斯的命运休戚相关;如果俄罗斯失去了东乌克兰,就等于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根基和历史血脉。因此,他被欧美媒体称为俄罗斯帝国主义、扩张主义的鼓吹者。同时,杜金依据独特地理和历史决定独特民族、独特文明的欧亚主义地缘政治理论,将俄罗斯欧亚文明体发展为俄罗斯-伊斯兰大陆联盟。主张联合伊斯兰国家作为最重要的战略盟友,一起反抗以美国为首的单极世界。[28]
2.“第四政治理论”
“第四政治理论”是杜金基于传统价值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从哲学到政治、从理论到实践的政治哲学新构想;是一种从哲学到政治的反抗,是新欧亚主义的一个新理论基点。该理论主张以古希腊哲学、存在主义哲学和宗教神学探寻为思想资源,力图为人类找回存在的本体论和神学根基,以此重塑人类神圣的精神价值,反抗现代工具理性主义和社会主义过度物化对人的奴役。首先,在哲学上以“此在”反抗现代性对人的奴役,找回被人们遗忘了的“在”的意义,实现价值翻转,反抗现代性的旧价值;然后,在政治学上建构新的理论范式、新的意识形态,有力地在政治实践中反抗国际旧秩序。它不仅为多元文明达成价值共识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为现代人反抗工具理性主义的价值旧秩序、反抗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及其政治旧秩序,开启了回归传统论的方向。
杜金认为,现代性导致人类精神维度的扁平化和信仰的迷失,使人类陷于错误意识形态的统治中。传统及其代表的价值在现代性来临之际被推翻,于是“上帝死了”、“世界祛魅”、“神圣终结”,现代性的精神在于用人取代了神、用哲学和科学取代了宗教,用理性和科技的建构力量取代了启示和信仰的位置。现代性精神孕育了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三种意识形态。杜金汲取了法国哲学家阿兰·德·伯努瓦(Alain de Benoist)《反对自由主义》一书中的思想,构建自己的政治学说。伯努瓦批判了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三种意识形态,呼吁人类应该寻找第四种意识形态。杜金结合俄罗斯自由主义改革失败,和2008年以后俄罗斯保守主义声望不断提高的现实,针对20世纪三大主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提出“第四政治理论”。该理论理顺了其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建构的内在逻辑,夯实了其构建保守主义的新欧亚主义基础,补充了最初的“保守主义革命”和“第三道路”理论。他最开始提出的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帝国联盟”,本身是多个异质文明的组合体,是多极文明论的应用,这就需要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价值认同的思想作为支撑。但他并未能给出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帝国联盟”的主导观念,因为俄国东正教的精神传统无法涵盖“帝国联盟”多元文明体系,不能给出统摄不同文明体、不同宗教观的价值认同,这一点成了杜金地缘政治思想逻辑上的缺口。[29]杜金的“第四政治理论”,为完成以上多元文明达成价值共识的艰巨任务,从哲学的源头和未来两个向度上探寻思想资源。
第一个方向,是求索于现代社会之前的古老神学文化、传统价值观、非理性主义的崇拜仪式和传说。向传统以及前现代汲取思想灵感,以此反抗现代社会理性主义和社会主义过度物化的价值趋向,“神学正在回归,并成为‘第四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30]杜金认为,现代性终结了传统和宗教、等级和家庭这些对人至关重要的传统价值,所以对现代性的反抗就必须回归传统及其所代表的神圣价值,这意味着宗教的回归。在这个意义上,“第四政治理论”乃是要找回现代哲学对人的形而上存在的遗忘,找回人类存在的本体论和神学根基。而一旦人在形而上层面找回自己,就必然意味着一个全新等级结构的形成。在这个结构中,家庭、民族重新找到自己的存在空间,在政治层面,这意味着一种帝国秩序的回归。[31]杜金认为,只有将宗教和神学等非理性的精神作为“第四政治理论”的新基点,在人内在生命没有任何限制的深度和信仰的高度上,才能自然地形成相同的价值观,“第四政治理论”也不再是强制性的。“以前神学阶段的那些非理性的宗教仪式和传奇的时刻,向人们显现的所有古老的信仰和精神追求,对于已经被现代观所扭曲的人类来说,更有精神价值和内在说服力,就因为它是古老的价值;古老意味着是良好,而且越古老就越好。”[32]
另一个方向,是求索于批判和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存在主义哲学。杜金赞赏现代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理论主张——被异化的人(被抛的存在者)通过追问“在者”之“在”,找回自己丢失了的生命意义。他选取了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概念,作为“第四政治理论”的主体。杜金认为,“此在”作为兼容性概念,将是“第四政治理论”包容与整合多种异质文明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来自不同文明体的“此在”,从传统宗教观和哲学观中根据不同的文化语境,从哲学层面找回人存在的原初意义,达到不同文明体在原点上的价值共识。杜金明确指出了这种新意识形态的三条主要原则:社会正义、国家主权和传统价值。他也认识到,即使能唤醒各个文明体的传统价值,要统合这些异质文明的世界观也并非易事;但在共同反抗自由主义的斗争中,它们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联合,达到基本的价值共识。
综上所述,“第四政治理论”是以新欧亚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结合,作为代替20世纪三大主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第四意识形态;它以“此在”为主体,在不同文明体中追寻各自丢失的传统价值,最大限度地团结不同文明的价值,共同反抗自由主义。用杜金自己的话表述就是,“请人们反思21世纪的今天和人类的存在方式。希望全体人类共同努力,用自己唤醒传统价值的行动,在21世纪共同构建新的生命形式、新的意识形态:‘第四政治理论’。”[33]该理论是欧亚主义观念的延续,同时也是其向“统一俄罗斯”党的保守主义靠拢的转向。[34]但它在俄罗斯国内与主流的保守主义——“统一俄罗斯”党的保守主义纲领之间,既有相类似的原则,也存在重大差别,本质上并不相同。[35]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反对西方的自由主义,主张以俄罗斯传统价值作为俄罗斯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区别在于,前者主张在俄罗斯欧亚文明论的基础上重塑俄罗斯传统价值观,从哲学到经济、政治全方位地积极反抗西方的价值定位,改变国际旧秩序;后者作为俄罗斯初期自由主义激进改革失败的应激性反应,主张在其自身现代化过程中完成传统的再造,反对激进主义的变革和斗争,主张以传统斯拉夫主义为内核,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实现稳定和改良的发展道路,维护现存制度。
3. “新俄罗斯”思想
世界比较文明论先驱丹尼列夫斯基[36],在批判文明进化论基础上提出的多元文明论和俄罗斯文明独特论,深深地影响了新欧亚主义: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如果能够在历史中完成自身的精神发展,便形成一种文明类型;[37]全世界的十种文明类型各有自己的文明特点和价值,是世界历史舞台上不可或缺的文明类型形式;[38]它们之间具有异质性,不能被孰优孰劣的进化论方式取代;[39]俄罗斯文明不同于欧洲文明,也不同于亚洲文明,它是一个独特的文明类型。“俄罗斯人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和其他斯拉夫人一起创立完整的斯拉夫文明,要么完全失去其独特的历史意义和文化类型,而成为另一个文明的民族性材料。”[40]必须保护俄罗斯文明的特性,不被欧洲文明同化。据此,杜金从俄罗斯文明的独特性和多元文明论出发,并综合古米廖夫追求的“新的俄罗斯思想”和欧亚大陆空间理论,发展出多元文明世界的新理念和重构“新俄罗斯”的思想,以此反抗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每一种独立的文明类型都享有政治独立的权力,全世界存在多种不同的文明类型,那么政治就必定是多极政治格局,这样才是真正合理的世界秩序。[41]
杜金主张按新欧亚主义的地缘政治定位,和俄罗斯欧亚性的文明定位,在俄罗斯文明的范围内重建“新俄罗斯”:在地缘政治基础上重塑俄罗斯文明,以跨区域的俄罗斯文化范围界定,重建“新俄罗斯”的空间范围。[42]在杜金看来,对俄罗斯地缘空间中的性质界定和欧亚性的文明定位,是重建新俄罗斯的前提;只有宣示俄罗斯的历史、文明和主权,真正意义上的新俄罗斯才有可能。他认为2014年的乌克兰事件是俄罗斯现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是俄罗斯政府面对乌克兰亲欧盟示威运动挑战的被动回应;如果失去乌克兰,俄罗斯的大欧亚空间将无的放矢,因此必须明确新俄罗斯的概念。
什么是新俄罗斯[43]?杜金分别从地缘政治、文明类型和国际现实利益斗争三个方面作了具体界定。
从地缘政治方面看,乌克兰和俄罗斯联盟,这是重建俄罗斯作为欧亚帝国的主要保证,也是当代俄罗斯人的历史责任,也是俄罗斯的敌人——美国、北约和西方国家最担心的威胁。亚努科维奇被推翻和其后的一系列事件证明,乌克兰不愿与俄罗斯结成联盟,这将使俄罗斯丧失恢复“欧亚大空间”的可能性,由此出现了克里米亚和新俄罗斯的议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从原来的世界超级强国衰落为第三世界国家,由原来传统地缘政治空间的中心变为苏联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从苏联主导社会主义世界的经历看,还是从俄罗斯弥赛亚宗教政治传统看,俄罗斯都无法接受这一现实。重建新俄罗斯的思想,强烈地表达了俄罗斯力图重返强国、重返中心主导地位的追求:“我们是谁?世界强国?一个区域?或次区域?克里米亚事件表明了俄罗斯对世界区域地位的不满。”[44]重建新俄罗斯可以使俄罗斯重返失去的地缘政治主导地位。
杜金认为,从文明类型方面看,新俄罗斯意味着——觉醒,重塑一个新俄罗斯的世界。新俄罗斯(从敖德萨到哈尔科夫的地区)是俄罗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这个部分使俄罗斯变得更加完整。界定新俄罗斯的文明标准不是种族,而是俄罗斯的历史、文化、宗教和语言。新俄罗斯的历史、文化、民族起源、宗教、自我意识等方面的俄罗斯认同——都是伟大俄罗斯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她(敖德萨到哈尔科夫等地的俄罗斯认同)俄罗斯将不可想象。“2000万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无论他们是什么种族,在思想文化上都是俄罗斯人。很显然,远不只是种族方面的大人(旧称)的存在代表着俄罗斯本身,而且俄罗斯文明范围内的所有人都代表着俄罗斯。”[45]这里,可以看到杜金重塑“新俄罗斯”的主张,有通过共同文化扩大俄罗斯文明认同的倾向。文化认同超越国家认同,容易引起国家间或地区的矛盾冲突。苏联时期说俄语的许多加盟共和国,现在都是独立的国家,尤其是近几年纷纷开始改变自己国家的语言和文字,向“去俄化”发展。对俄罗斯来讲,这是保护“保守价值观”和“保护同胞权利”的愿望,但是对于其他独立自主的国家来讲,则意味着挑战国家身份认同的威胁。
在杜金的理念中,从国际现实利益斗争方面看,“新俄罗斯”是俄罗斯与欧美主导的国际旧秩序的斗争,俄、乌冲突事件成为谁来控制莫斯科的试验:是作为国家利益代表的俄罗斯政府,还是受大西洋势力影响的“第六纵队”(用来讽刺俄罗斯内部的亲西方势力)。这场较量的结果势均力敌,两种势力各自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克里米亚成为俄罗斯的政权,明斯克协议则是“第六纵队”的胜利。俄罗斯不会放弃,因为俄罗斯文明已经觉醒,“如果我们坚持立场,那么现行的世界秩序将崩溃,它将最终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退场;这将是一场精神觉醒——冲断和结束‘文明查理’对世界的统治,并把欧亚保守主义革命扩展到欧洲和美国。”[46]
综上所述,重建“新俄罗斯”,是新欧亚主义者怀着俄罗斯传统主义所固有的弥赛亚救世情怀,在多元文明世界的新理念基础上重塑俄罗斯文明,反抗国际旧秩序的维护者——欧美联盟,建立国际价值和政治新秩序的政治哲学构想。俄、乌冲突是这一构想的政治实践。其中潜藏的俄罗斯文明扩张论,是其致命的弱点。
以上杜金对俄罗斯文明和国家发展道路的新构想,没有停留于政治哲学的象牙塔中,而是通过政党组织和非政党组织向社会各阶层渗透,逐渐实现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力图成为俄罗斯政治哲学的主流。2003年,杜金把“欧亚党”改组为以古米廖夫命名的非政党社会组织“国际欧亚主义运动”,政治上支持普京,从反对党转变为支持派。这标志着新欧亚主义由纯学术理论走向政治实践。[47]俄、乌冲突爆发后,鉴于各方压力和需要,杜金于2014年6月辞去莫斯科大学教授的职务,专门进行新欧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动员工作。“国际欧亚主义运动”向俄罗斯政治高层渗透新欧亚主义的主张,对俄罗斯的国家发展定位、政治、经济、外交等都发挥了直接影响。但在俄、乌冲突后,俄罗斯陷入被动局面,俄罗斯社会各界开始批判反思:杜金重建新俄罗斯世界的主张,是否会走向帝国主义的极端?
(三)科瓦列夫的“第三类世界秩序”论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教授科瓦列夫,是当前俄罗斯新欧亚主义温和派的代表[48],在批判杜金的激进主张中,逐渐明确了新欧亚主义的新观点。[49]
1977年科瓦列夫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博士毕业后,一直在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工作,长期从事俄罗斯文明论的研究。他在批判文明进化论的基础上,确证了俄罗斯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存在的固有矛盾,主张通过将俄罗斯传统哲学与地缘政治学相结合,从理论到实践层面全方位地解决两种文明的矛盾,使俄罗斯摆脱千百年来的文明论困境。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以下的著述中:《21世纪俄罗斯:今天的日程》(2013)、《俄罗斯:回到未来》(2014)、《为了俄罗斯的战斗》(2014)、《乌克兰危机是形成第三类世界秩序的根据》(2014)、《欧洲是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还是俄罗斯VS.欧洲呢?》(2014)、《俄罗斯:重新面临道路的选择》(2015)、《俄罗斯:寻找未来的方式》(2016)和《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俄罗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任务》(2016)等。
1. 批判现代“西化派”与“斯拉夫派”的争论
科瓦列夫在批判当前俄罗斯“西化派”与“斯拉夫派”争论的基础上,发展了古米廖夫“只有欧亚主义才能拯救俄罗斯”的观点。他指出,在当前的俄罗斯只有通过新欧亚主义超越东西方争论,才能为俄罗斯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当前俄罗斯再次遭遇寻找国家发展方向的关键时刻,针锋相对的“西化派”与“斯拉夫派”的立场,恰恰反映了俄罗斯地缘政治地位客观存在的固有矛盾;这两派分别以“俄罗斯的敌人”和“俄罗斯爱国者”两种方式解释了矛盾的一个向度,无法解决俄罗斯发展道路的重大问题。“现代的‘西化派’主张,‘俄罗斯是欧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俄罗斯是欧洲文明;‘斯拉夫派’则反击说,‘不,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应该以自己的方式成长’。现在很明显,这绝不只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理论分歧’,这种分裂直接关系到俄罗斯的前景。”[50]俄罗斯只有选择新欧亚主义的立场才是正确的,才能超越俄罗斯素有的东西方文明的争论,找到俄罗斯正确的文明密码和国家发展方向。
现代“斯拉夫派”的基本观点是,俄罗斯不需要创造什么新的东西,只应该依赖于俄罗斯原有的核心价值观——东正教,一切问题都会在“超人因素”的影响之下被自动解决。所以,东正教应该成为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科瓦列夫认为,现代“斯拉夫派”的主张不符合俄罗斯当前的现实,包含着矛盾。首先,俄罗斯是个多宗教国家。在俄罗斯的永久居民里面有超过1800万穆斯林,佛教徒、犹太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也很多。在俄罗斯联邦的一些地区,“俄罗斯”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很久前,这种紧张关系就被西方国家称为从高加索到中亚的“软肋”,它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这客观地说明,某些国家已经把俄罗斯视为穆斯林世界的组成部分,并利用这一点消解俄罗斯的国家身份认同。如果把东正教当成国家意识形态,那么将会导致剩下的几千万人口成为“二等公民”的不良后果。其次,社会是否真的具有“东正教复兴”的基础,还是不能确证的问题。今天,俄罗斯人中的60%-80%“认为”他们是东正教徒,但积极参加宗教活动的虔诚信徒为数不多。据俄罗斯的社会学家分析,对于很大一部分自称东正教徒的俄罗斯人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种文化自我认同而已,而入教只是表面现象。列瓦达中心的调查显示,2014年复活节前夕,俄罗斯72%的人口“保持正常的饮食”,而“完全尊重禁食”的只有3%。对于信徒数量“夸大数字”的做法毫无意义。最后,当前俄罗斯东正教仍然不能实现在科学和宗教之间的有效对话,没有解决“信仰与理性”的矛盾,每一方都觉得自己比对方更有价值。[51]这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宗教大法官》里,有关天上面包和地上面包的矛盾。在没有解决好这一矛盾的前提下,如果按照斯拉夫派所主张的,俄罗斯完全“依靠东正教”,使东正教成为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那么俄罗斯很快就会被人们从理智的现实世界中开除出去。因此,“斯拉夫派”以东正教复兴为根据战胜“西方派”的结论不能令人信服。东正教是虔诚信徒生活中的道德和精神“动力源泉”,但它不可能成为整个俄罗斯社会的“动力源泉”,东正教不能被视为俄罗斯复兴道路上的“万能工具包”。
俄罗斯现代“西化派”的立场是,俄罗斯是欧洲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要再谈“俄罗斯的特殊道路”,而应该在俄罗斯发展民主和个人自由的思想。科瓦列夫指出,这样的主张听起来令人振奋,但是当我们清楚了解这些价值观在欧洲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后,就会发现它同样不符合俄罗斯当前道路的选择。从文明类型和历史上看,俄罗斯不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从社会现实看,西方的这些民主自由价值观本身,在西方世界已经矛盾丛生。欧洲人比较成功地通过“自力更生”的方式,从“超人因素”控制效应中走出后,“市场民主”体制和整个国家运行系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西方世界已经出现价值和市场的僵局。俄罗斯“西化派”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错误地把已经耗尽创造潜力的发展方式推荐给俄罗斯,这绝对不是俄罗斯所期望的路径选择。
2. “第三类世界秩序”
科瓦列夫在批判以杜金为代表的新欧亚主义激进派主张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类世界秩序理论。他认为俄罗斯选择新欧亚主义是正确的,但不是以杜金为代表的新欧亚主义激进派主张,而应该是古米廖夫的大欧亚主义与索洛维约夫的世界意识,二者的结合,将构成俄罗斯特有的第三类世界秩序。杜金错译了俄罗斯文明密码,其激进主张挑起俄、乌冲突,使俄罗斯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科瓦列夫对新欧亚主义激进派的批判,引起俄罗斯政界和学术界的强烈关注,由此于2016年在圣彼得堡召开了国际研讨会,探讨俄罗斯在困境中如何做出新的抉择。
科瓦列夫使用“综合”(синтез)理论,对西化派观点进行了批判分析。该理论是在19世纪后期由俄罗斯哲学家索洛维约夫(В.С. Соловьёв)提出的。索洛维约夫是现代意义上俄罗斯哲学和东正教神学的奠基人,他在理性思维的统摄下对俄罗斯哲学进行了客观唯心主义的改造,使俄罗斯哲学摆脱了文学抒情式和神学神秘式的表达。科瓦列夫着重分析了索洛维约夫思想并综合中世纪和近代对待神的两种错误观点,进而提出寻找现实生活的精神基础、建构精神世界完整性的主张。索洛维约夫的观点是,中世纪人们热衷于基督教,把上帝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有损于人的物质世界和人自身的价值;但是启蒙运动以后,又把人的位置摆得过高,甚至超过上帝,这也是不科学的;所以索洛维约夫提出神人类的概念,将二者综合,这是人和神乃至万物的大一统[52],是为人类现实的生活寻找到的完整的精神基础。科瓦列夫借用了索洛维约夫的这种批判反思,汲取批判对象中的积极因素,再进行综合。“综合”理论是指各种参与社会运转的因素,参与到类似于植物光合作用的综合活动中,而各因素的运行性质决定了世界秩序的类型。[53]科瓦列夫运用该理论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种世界秩序。
科瓦列夫认为,第一种世界秩序的类型是2000年前开始在西欧出现的,在基督教基础上以极权主义的方式形成,它通过基督教强制性的教义信条管控个人信仰来实现。第一类世界秩序的“核心”是,只有上帝才有真正的价值;人的一切都取决于他,地上的人的生活,其实只不过是给最后审判准备的素材。显然极权制度没有给人类自主性留有独立空间,这成为它自身发展的阻碍。因此,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另类替代的复合体。启蒙运动的理念为:是否对上帝有信仰只取决于个人选择,因为上帝在实际生活中不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人必须一直靠自己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54]
人类精神自主性的“独立”,为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开辟了道路。但因为不再虔诚地信仰教义的信条,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彻底变化了的情况下控制人们?如何形成新的有效机制?16世纪在欧洲开始出现市场民主国家,它们是根据理想模式在“制衡”制度的基础上而建成的,市场使人们非常有效地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带来高品质的商品和丰盈的服务。这样就出现了第二种类型的世界秩序:相互独立的立法权、政权和司法权,确保如工业团体、政党等政治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理想中);确保民间社会独立于政府的权利,确保非国有媒体在完整社会系统中的特殊作用;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承认个人利益相对于国家利益具有绝对优先性的基础上,同时也确保了每个人都可以在法庭上挑战行政机关和立法系统的权利,每个人都具有平等的权利,任何个人都没有优于其他人的特权和优势;“市场的无形之手”(理想中)在平等生产者的公平竞争基础上有效地规范生产。[55]在实践中,这的确产生了相当积极的成果。例如,“制衡”系统为民间社会创造了有效地控制政治权力的条件。但目前西方的这些机制产生了一系列自由、平等的悖论,市场经济在促进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同时,与道德、自然和国家利益产生矛盾,导致资本、市场对人的剥削与奴役。
在对前两种世界秩序的利弊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加上对以杜金为代表的新欧亚主义激进派的批判,科瓦列夫提出了“第三类世界秩序”。他认为,现代“斯拉夫派”和“西化派”的主张,都不适合当下俄罗斯对发展道路的重新选择。那么是否有适合俄罗斯目前道路选择的方案呢?科瓦列夫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这种方案是存在的,就在索洛维约夫的“第三类世界秩序”与古米廖夫的欧亚大陆方案的结合中。
索洛维约夫曾确信“第三类世界秩序”一定会出现,它会作为已经存在的前两个世界秩序的综合。该综合的要素是:中世纪欧洲以物质世界为代价而依赖于“天上”的世界(这里泛指各类宗教中的彼岸世界);启蒙运动文化以“天上”的世界为代价而激发人和物质世界的独立性。“第三种类的世界秩序”是以上两类世界秩序的新的组合。索洛维约夫认为,俄罗斯文明是开创“第三类世界秩序”最为适当的“工具”,它会在一个新水平上继续基督已开创的工作。[56]
科瓦列夫进一步指出,俄罗斯文明的密码应该是古米廖夫的大欧亚主义与索洛维约夫的世界意识,二者的结合将构成俄罗斯特有的第三类世界秩序。俄罗斯文明使命在索洛维约夫这一新秩序的机制中,包含着两个关键点:首先,基辅罗斯接受东正教(10世纪);其次,大俄罗斯的出现(13世纪末),即俄罗斯超民族本身的出现。任何超民族(文明)都可以视为一个巨大的人类社会。俄罗斯的“文明代码”是独一无二的,按照俄罗斯的传统原则——“天上的”总是优先于“大地的”,那么俄罗斯文明代码,就是索洛维约夫“聚合性”统摄之下的古米廖夫大欧亚;二者不是外在的绑定,而是以俄罗斯文明使命为内在精神的一体。
3. “大欧洲”理念
“第三类世界秩序”确立后,那么俄罗斯文明代码与大欧亚的追求,如何在实践中实现综合呢?科瓦列夫的回答是:通过“大欧洲”的理念。他将古米廖夫的大欧亚空间转换为“大欧洲”的理念,这不是俄罗斯文明范围的继续扩大,而是“第三类世界秩序”的实践。
科瓦列夫指出,当前世界明显分化为三个强大的趋势:美国在加强“推行民主”的活动;宗教激进主义分子反西方的活动在增加,穆斯林要求重返“祖先生活和信仰的方式”;重建“俄罗斯世界”的激进思想将变成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中心轴”。目前情况的悲剧在于,三个强大趋势的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是真理的代言人,相互间都不能被说服,无法达成共识。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很可能会挑起一方为实现“自身价值”的新世界大战,造成人为的世界灾难。因此,我们的时代使命就是,呼吁人们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解决真理与意见(可能对,也可能错的观点)的纷争。
从价值观的分析看,美国民主扩张活动的增加,是基于“启蒙的文化”:只有个人选择确定相信或不相信上帝,在实际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自己;伊斯兰极端活动的增长,是基于“只有真主才有真正的价值,人的一切都依赖于他”的原则;欧亚主义激进派将俄罗斯文化扩展为“俄罗斯世界”,试图成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心,它是基于一个全人类的使命——创造一个公正的社会,以替代“西方价值观”。科瓦列夫基于“综合的逻辑”(其中心是俄罗斯的全人类使命),主张三方理论家应该通过对话来“调和”这三种互不认同的价值观。对此,他提出了一个具体方案——“大欧洲”方案。这是一个“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洲”(大欧洲)的想法。这个想法的实现,将意味着一个新的地域和文化共同体的创建。这样,属于不同族群的人,将会形成共同的超民族认同(如超欧洲人),以此消除领土冲突和不同文明间的价值冲突。比较成功的案例是,在苏联时期,作为超民族共同体的“苏联人民”这个概念。对克里米亚的居民来说,“苏联人民”是他们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统一,因此半岛是否属于俄联邦已不重要。建立“大欧洲”的理念,不是机械地把“欧洲价值观”延长到太平洋,或把“俄罗斯文明”(东正教)扩展到大西洋。[57]为消除俄罗斯和西欧彼此间在价值观方面的对立,只能通过把“大欧洲”作为综合区——第三类的世界秩序来实践,在政治外交中实施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欧洲项目。科瓦列夫认为,当前俄罗斯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在价值观综合的基础上,为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洲概念奠基。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个俄罗斯公民看到自己的精神价值,让任何生活在俄罗斯领土上的人,感觉到俄罗斯是“自己生存的保障”。
可见,科瓦列夫的“大欧洲”理念,是第三类的世界秩序在现实层面的实践方案,不仅仅是指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地理概念,而且是文明重塑后的跨区域、跨国界的俄罗斯文化共同体。
苏联的命运表明,没有“意识形态框架”,文化共同体就不可能存在。但在当下的俄罗斯,要建立这种“框架”将面临的巨大障碍,就是原苏联共和国和东欧国家的现代意识状态。苏联模式“意识形态框架”的毁灭,导致了原苏联共和国面临文明分裂的困境。在文化共同体的重塑过程中,这些国家的大众意识分裂为两个方向:“欧洲价值”的支持者,和保持俄罗斯传统价值的人。[58]
丹尼列夫斯基是世界文明多极论的奠基者(但多年来被人们所遗忘),古典欧亚主义和新欧亚主义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观点,将俄罗斯文明定位为独特的欧亚文明,它不从属于西方,也不从属于东方。杜金的“新俄罗斯”理念和科瓦列夫的“大欧洲”理念,是对这种多极文明论的两种发展。“大欧洲”理念主张的是跨区域、跨国界重塑俄罗斯文化共同体,意味着一个新地域和新文化社区的创建,形成超民族的认同。科瓦列夫指出,“形成真正的多极世界需要有多个系统区域作为必要条件,俄罗斯建立欧亚中心区(МЦЕ)将面临严重的阻碍,领土冲突已经让俄罗斯痛苦不堪: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南部、顿涅茨克河沿岸、格鲁吉亚、千岛群岛。因为当前‘冲突’每一方都坚持自己的‘真理性’,普遍都诉诸‘双重标准’和‘对历史的抽样性表述’,如果停留于此,历史将进入无解的死胡同。”[59]这些问题涉及欧洲、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的价值观冲突,或者简化为: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这需要在超越异质文明之上找到一个基点,来解决共同面临的困境。如何找到这样一个基点,是人类成功解决文明冲突的必要前提。如果伊斯兰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都基于自己的价值观,返回自己文明的原初价值,重塑内在价值的道德生长点,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文明间的对话,将是解决文明冲突和领土争端的起点。即只有通过跨文明的对话才能解决“文明冲突”的问题,而跨文明的对话只有在超文明(宗教原初价值)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三.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影响与评价
新世纪以来,欧亚主义从哲学理论变为政治思潮,并通过政治实践将其影响力扩展到俄罗斯政治高层和社会民众,欧亚经济联盟、俄乌冲突、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等举措,是新欧亚主义重塑俄罗斯文明的新构想从哲学扩展到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实践。这在普京执政理念变化、近年来瓦尔代会议[60]的主题内涵、国内外学者对其评价等方面都有所体现。新欧亚主义是否有成为俄罗斯主流政治哲学的倾向?这是极具争议性的论题。笔者从对当代俄罗斯五大社会思潮的研究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新保守主义思潮与新欧亚主义思潮的融合,将是俄罗斯社会思潮未来的主流方向。[61]
从俄罗斯总统普京20年来的执政理念看,他对俄罗斯文明定位、国家身份认同、经济外交策略等问题,也曾在东西之间摇摆过,但是最后选择了欧亚主义的国家定位。从第一个任期里的国家定位——俄国是个欧洲国家;过渡到第二个任期——俄罗斯历来就是欧亚的桥梁,俄国是欧亚国家;到第三个任期的说法——欧亚文明并没有因为俄罗斯帝国的结束和苏联解体而停止存在。[62]在2013年的“瓦尔代”俱乐部国际会议上,普京表示:“欧亚一体化,这意味着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有机会成为全球发展的一个独立中心,而不是欧洲或亚洲的边缘。”[63]这被俄罗斯学者视为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学说,在普京执政理念中的突出体现。
从“欧亚”概念看,“欧亚”不是纯粹的地理概念,而是哲学和地缘政治概念。一般意义上的“欧亚”概念界线不明晰,大致有三种理解:一是指大欧亚——欧洲和亚洲;二是指“后苏联空间”;三是指“欧亚思想的基础”。在2015年之前,学者们对普京欧亚战略的解读是第二种和第三种的结合,是排除西欧和东南亚、以欧亚中心区域为基础的原苏联空间。但从近几年欧亚经济联盟的推进看,普京的欧亚战略是包括东南亚在内的。[64]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名誉主席、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创始人卡拉加诺夫(С. Караганов)2016年的发言佐证了这一点。他指出,普京总统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希望借此加强各方合作,“大欧亚地区涵盖区域包括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东盟、伊朗、以色列和埃及。”[65]正如我国年轻学者封帅副研究员所指出的:“欧亚空间,作为俄罗斯权力的区域映射,欧亚空间塑造了俄罗斯,也被俄罗斯所塑造。”[66]笔者尝试延伸此“欧亚空间”的含义,它绝不仅仅是地理学和历史学的概念,它被赋予了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政治认同的含义后,就变成了为政治权力斗争和重塑区域秩序,提供合法性话语基础的哲学概念、政治概念。
从近年来瓦尔代会议主题的延续和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国家政治诉求与本文“反抗与重塑: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对俄罗斯文明的新构想”的关联度。2013年瓦尔代会议的主题是“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2014年的主题是“世界秩序:新规则还是无规则?”;2015年的主题是“在战争与和平之间:跨越冲突的逻辑”;2016年的主题是:“未来始于今日:塑造明天的世界”;2017年的主题是“创造性破坏: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将从现有冲突中产生?”;2018年的主题是“俄罗斯:二十一世纪的方案”;2019年的主题是“东方的黎明和全球政治秩序”。这些主题表明,俄罗斯近些年所关切的是,重塑国家身份认同和重塑国际政治新秩序。而这个新认同和新秩序,都需要新的哲学价值基础。笔者认为,新欧亚主义正是能够从文明论和地缘政治学方面,为此提供理论支撑的哲学基础。对于2019年瓦尔代会议的主题,我国俄罗斯问题专家赵华胜教授发出疑问:“瓦尔代年会都是以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或俄罗斯发展为主要议题,这次为何突然转向了东方”?[67]追问后得出结论是,俄罗斯的国家定位是欧亚国家,是欧亚主义的定位。
新欧亚主义是不是欧亚经济联盟、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的理论基础?这又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攻击自己对手一定要切中要害,也许从批评新欧亚主义的众多声音中,更能看清这一密切联系。俄罗斯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科诺别里(А. Кнобель)在“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前景和障碍”一文中,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大学的尼基京(А.И. Никитин )教授在“欧亚安全架构变化趋势”[68]一文中,莫斯科大学世界经济系伊诺泽姆采夫(В.Л. Иноземцев)教授在“欧亚经济联盟:在空间中的损失”[69]一文中,不约而同地批判了新欧亚主义者是后苏联一体化的激进支持者,是欧亚经济联盟理论和实践的推动者,是造成俄、乌冲突的思想推手。
新欧亚主义将引领俄罗斯向何处去?是战争?还是和平?尤其是在俄、乌冲突后,人们更加注重批判、反思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建构的负面作用。它是否只是维护俄罗斯文明和民族尊严的应激性反应?是否有走向自身反面、走向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对此,俄罗斯和国外政界、学界有不同的评价。
从总体上看,俄罗斯、欧美、中亚政界和学界,对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的关注度较高,主要聚焦于新欧亚主义意识形态、俄乌冲突和欧亚经济联盟等问题。相比之下,我国的关注和研究则略显薄弱,主要聚焦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等问题。
在俄罗斯政界层面,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和采纳,集中体现在它对普京执政理念和国家决策的影响。在国家身份认同方面,自总统的第二任期开始,普京的思想有明显转变,以前他多次表示“俄国是个欧洲国家,我们信奉的是基督教。”[70]而在他第二次担任总统后不久便发表了题为《俄国:新东方前景》一文,很明确地指出,俄国是欧亚国家,俄国是连接亚洲、欧洲和美洲之一体化的独特交接点。普京的第三任期以来,将新欧亚主义的思想应用于经济和外交领域。2012年普京重登俄罗斯总统宝座的“王者归来”,被杜金称为“欧亚主义象征”。[71]在2013年9月的“瓦尔代”俱乐部国际会议上,普京进一步明确了欧亚经济联盟的定位。
与政界不同的是,俄罗斯学界对新欧亚主义的评价较低。除新欧亚主义学派本身的自我肯定外,只有部分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代表主张将其与自己的学说相结合,探索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新道路。大部分学者对古典欧亚主义评价很高,但对新欧亚主义却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如,当代俄罗斯传统哲学代表、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霍鲁日(С.С. Хоружий)教授就尖锐地指出,新欧亚主义在当前俄罗斯政界影响很大,但是它就像皇帝的新装一样,很多政界人士根本不理解新欧亚主义的思想实质,只是为他们自己的职业生涯增加一个噱头而已;该派的代表人物杜金正确地指出了当今人类复杂的文化都来自古代统一的文化传统,但是他无法给出这一传统是什么,因为在他的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中没有严肃、严格的学理论证。[72]再如看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斯米尔诺夫(А.В. Смирнов),在接受笔者提问时表达的观点。第一个问题:是否可以说欧亚主义和十月革命都是超越俄罗斯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争论,一个是理论上的、一个是实践上的超越?回答:可以说欧亚主义和十月革命都是超越俄罗斯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争论,一个是理论上的,一个是实践上的。这个问题不简单,认同你的观点,欧亚主义者认为十月革命是必然的,部分地认同苏联实践了欧亚主义超越东西方道路的某些主张,但反对压制个人自由。第二个问题:新欧亚主义与古典欧亚主义相比,加入了地缘政治和民族因素,21世纪是古米廖夫的时代,但是否可以认为这种尝试更加有力量,更加容易变为政治实践?回答:不同意新欧亚主义已经成为俄罗斯政治哲学的主流。新欧亚主义在俄罗斯社会的反应很敏感,对古典欧亚主义的继承性我们应该做出自己的客观评价。不要上了新欧亚主义的当,他们的观点很少能经得起批判,没有一个能与古典欧亚主义的创始人特鲁别茨科伊的观点相提并论。[73]
欧美政界、学界极其重视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的政治实践,尤其在俄、乌冲突后,重视新欧亚主义激进派对普京执政理念的影响。主要的基调是,认为杜金的新欧亚主义激进思想“成为今天俄罗斯对内对外政策的基础”,对俄罗斯政府的政治及外交政策的激进走向,起到了促进作用。从各国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到这一点:法国《新观察家报》把杜金称为“普京时代的拉斯普京”,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称杜金是普京的“大脑”,土耳其媒体则称其为“俄罗斯的基辛格”。[74]2014年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将杜金评为2014年度的全球思想者,并和叙利亚的恐怖主义组织(ISIS)领导人巴格达迪(AbuBakral-Baghdadi)、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圣战者约翰”(Jihadi John)等人并列[75];认为杜金一手策划了俄国扩张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俄、乌冲突的理论根源。
我国政界、学界对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的认知,主要表现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与俄罗斯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方面。其基本立场是构建“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友好关系。2015年5月8日,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共同签署并发表了《中俄两国关于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倡导合作共赢的联合声明》《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在中俄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和顶层设计下,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成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2016年6月,普京在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宣布,与中国正式启动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的计划,我国在政界层面积极认可和回应。但就具体内容来说,还未涉及其实质性思想内涵的对接与合作。正如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赵华胜教授指出的那样:“中国认知中的欧亚通常是指原苏联地区,中国还没有成型的欧亚观,更遑论大欧亚观。较少有人谈中国的欧亚政策,对大欧亚这一新概念也还没有官方明确表态。”[76]但中国一直是欧亚合作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如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6+1”等。中国学界对新欧亚主义的研究和评价,主要集中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展开了深入而有效的研究。但中国哲学界对该学派的研究略显薄弱,即使俄罗斯学界高度评价的古典欧亚主义,在我国的研究成果也寥寥无几,还没有深入到其理论对当前俄罗斯政治和外交的影响。我国著名的俄罗斯哲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安启念认为:俄罗斯哲学传统精神的内在实质,是关注俄罗斯以及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但是今天,这样的俄罗斯哲学死了”。[77]我国著名的俄罗斯宗教哲学专家、俄罗斯联邦普希金奖章获得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百春则指出,对于当代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哲学,特别是杜金的哲学理论,我们的研究明显不足……这位学者对新欧亚主义文明论和地缘政治学建构都着深厚的哲学基础,我国学界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综上所述,新欧亚主义从人类文明构成的大视野,探讨俄罗斯作为跨欧亚国家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地缘政治的欧亚空间、文明类型的欧亚独特性、俄罗斯东正教弥赛亚使命的现代延续等。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对俄罗斯文明的新构想,聚焦在“反抗”与“重塑”这两个关键词上。它提出的是反抗西方文明普世论和国际政治旧秩序,重塑俄罗斯文明和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新构想。新欧亚主义之所以在当下俄罗斯备受关注并对国家产生重要影响,其现实生命力就在于此。正如别尔嘉耶夫的评述,古典欧亚主义最值得称赞的是,以文化高于政治并主导政治的价值原则反抗欧洲文化和政治的垄断。[78]古典欧亚主义从诞生之初,就具有反抗欧洲文化和政治垄断的基因。新欧亚主义将其继承,并在地缘政治学和民族学等方面发展壮大,使其从哲学走向政治实践。因此,新欧亚主义的思想实质,不是复兴俄国亚洲地区的独立文化价值,而是重塑俄罗斯文明定位和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价值基础,以反抗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及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重振俄罗斯明确方向和道路。即,为俄罗斯反抗西方价值体系、从自身文明性质出发,探寻本国独特的发展道路,进行文明论的奠基。
The uncertainty of Russian civilization orientation has been a puzzle for Russia’s identity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hundreds of years. As soon as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d, Russia had to once again face this problem and make a new choice. The neo-Eurasianism political philosophy stood out among Russia’s various thoughts. Its strong vitality lies in that it rather reasonably answers the question of uncertainty in Russian civilization orientation from perspectives of civilization theories and geopolitics. Meanwhile, on the basis of profound philosophical construction, it puts for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reshaping Russian civilization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 resisting the universality the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the ol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 To reshape Russian civilization by reconstructing Russian cultural community is constructive for Russia’s own national identity building, nevertheless, once it transcends national boundaries, it is highly likely to cause conflicts between countries or regions.
Neo-Eurasiansim, Russian Civilization Orientation, Russian Cultural Community, Russian Diplomacy
【Аннотация】Неопределённость пози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цивили- зации является проблемой, которая преследует самобытность и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тысячелетий.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Россия вновь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с данной проблемой и делает новый выбор. Неоевраз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выделяется из множества направлений идейных теорий в России, её жизнеспособность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она может разумно ответить на вопрос неопределённости пози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на уровне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х учений и геополитики; на основе глубо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выдвигает новую концепцию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универсализму западн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и старому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у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у порядку, а также перестрой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и нов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орядка. Изменение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путём изменения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ной общины является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ой силой дл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но как только она выходит за пределы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границ, она может вызвать конфликты между странами или регионам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Неоевразийство, позиционирование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русское культурн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1] Бердяев Н.А.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Шевчук , 2000. С.4-5.
[2]郭丽双、汪力平:“俄罗斯古典欧亚主义的文明论建构及其当代意义”,《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3] 新欧亚主义相较于古典欧亚主义的“创新”之处,请参考本文的姊妹篇“俄罗斯古典欧亚主义的文明论建构及其当代意义”,此处不再赘述。
[4] Люкс Л. Россия между Западом и Востоком. сб. статей. пер. с нем. М., 1993. http:// lib. co.ua/philosophy/lyxl/rossijamegduzapadomivostokom.jsp
[5]张建华:“新旧俄罗斯的相遇与歧路——欧亚主义视野下俄罗斯复兴之历史思考”,《学习与探索》,2006年3月15日。
[6] 肖金波:“俄罗斯欧亚主义发展史的启示与反思”,《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1期。
[7]张建华:“新旧俄罗斯的相遇与歧路——欧亚主义视野下俄罗斯复兴之历史思考”。
[8]Мы---Евразия. Беседу с Никитой М ихалковым ведет поэт Эдмунд Иодковский// Континент. 1992. No.70. https://lj.rossia.org›users/bruno_westev/2049.html
[9] Панарин А.С. Искушение глобализмом. М.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Эксмо, 2003; Панарин А.С. Правда железного занавеса.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Эксмо, 2007; Дугин А.Г. Основы геополитики.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РКТОГЕЯ-центр, 2000; https://www.e-reading.club/book. php?book=20827; Дугин А.Г. Четвёрт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Пб.: Амфора, 2009; http://konservatizm.org/konservatizm/theory/140309014819.xhtml; Дугин А.Г. Новороссия---крах или взлет для России//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15. №.9. http://dlib. eastview.com/browse/doc/45325859; Ковалев Ю.А. XXI век. Россия. Расписание на сегодня. М.: РИОР, 2013. https://iphras.ru/uplfile/root/image/institut/admin/Kovalev_2013. pdf; Ковалев Ю.А. Россия: снова перед выбором пути//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15. №.6. C.201-209; Ковалев Ю.А. Новая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реальность и вопросы идеологии. 2017; https://iphras.ru/uplfile/root/image/institut/admin/Kovalev_doklad_19_04_2017.pdf
[10] 胡键:“普京之治论析”,《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11]Асанбеков М.К.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этап развития евразийской идеи. http://easttime.ru/anal ytics/tsentralnaya-aziya/sovremennyi-etap-razvitiya-evraziiskoi-idei/7184
[12]古典欧亚主义者大多是十月革命后“哲学船事件”中,被苏维埃俄国列入反动文人行列而驱逐出境的知识分子。由于苏联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古典欧亚主义学说被隔离于苏联民众视野几十年,只有古米廖夫在本土默默无闻地进行这个方向的研究工作。
[13] Антон К.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доктрина Путина и классическое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Евразийство: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й потенциал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е приложения». 30.12.2015. http:// eurasian-movement.ru/archives/1126
[14] Вахитов Р. Кто такие евразийцы?//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Левых Евразийцев. Уфа, июль 2003. http://redeurasia.narod.ru/krasnaya_evrazia/index.html
[15] Кожинов В.В.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вчера, сегодня, завтра.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90. https://ru.b-ok.org/book/3292663/a153b8
[16] Кожинов В.В. О русском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 сознании: Избр. ст. о наиболее актуальных вопросах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 2002. http://www.hrono.ru/biograf/bio_k/kozhinov _vv.php
[17] Ковалев Ю.А. Россия: снова перед выбором пути//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15. №.6. C.201-209.
[18]罗骞、刘礼:“卡尔·马克思:自由之子——大卫·利奥波德博士访谈(之一)”,《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19] 郭丽双:“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政治实践”,《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4期。
[20] Панарин А.С. Тайна железного занавеса. М., 2006. С.243.
[21] Лушников О.В. Предпосылк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евразийской идеи: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2006. http://lib.udsu.ru/a_ref/09_11_001.pdf
[22][俄]维·费·沙波瓦洛夫:《俄罗斯文明的起源与意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页。
[23] Панарин А.С. Тайна железного занавеса. М., 2006. С.243.
[24] 郭丽双:“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政治实践”。
[25] 杜金是最著名,同时也是最具争议性的新欧亚主义代表人物,西方世界批评他是俄罗斯对外扩张政策的理论来源,而在俄罗斯国内对他的学术成果和政治实践也存在争议。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他思想自身发展也存在变化,本文概括介绍了他的这三个理论,其中存在不同的理论倾向。“第四政治理论”是杜金向保守主义靠拢的一种理论尝试,而欧洲大陆主义方案、“新俄罗斯”思想则明显带有激进的左派倾向。所以笔者认为,杜金在新欧亚主义内部派别的分化中不能作为右派的典型代表人物,其近几年的思想更能代表新欧亚主义左派的理论倾向。
[26] 孔元:“普京‘大脑’杜金的地缘政治观:欧亚主义的回归与全球革命”,《文化纵横》,2015年第5期。
[27]Дугин А.Г. Новороссия---крах или взлет для России//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15. №.9. C. 244-248. http://dlib.eastview.com/browse/doc/45325859
[28] 郭丽双:“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政治实践”。
[29]孔元:“普京‘大脑’杜金的地缘政治观:欧亚主义的回归与全球革命”。
[30] Дугин А.Г. Четвёрт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2009. http://konservatizm.org/konservatiz m/theory/140309014819.xhtml
[31]孔元:“普京‘大脑’杜金的地缘政治观:欧亚主义的回归与全球革命”。
[32] Дугин А.Г. Четвёрт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33] Дугин А.Г. Четвёрт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34]孔元:“普京‘大脑’杜金的地缘政治观:欧亚主义的回归与全球革命”。
[35]荆宗杰:“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思潮中的‘第四政治理论’评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2期。
[36] 丹尼列夫斯基是19世纪俄国自然科学家、哲学家、世界文明史的先驱,是“后期斯拉夫主义者”和“乡土派”的代表。其著作《俄罗斯与欧洲》是其比较文明论的代表作,比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早50年。
[37]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Я.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Составление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Ю.А. Белова/ Отв. ред. О. Платонов. М.: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008. С.5.
[38]Там же.С.6.
[39] Там же. С.7.
[40]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Я.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С.8.
[41]郭丽双:“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政治实践”。
[42] 同上。
[43] “新俄罗斯”是杜金在俄、乌冲突前后用来指称那些发动抗议、试图脱乌入俄的地区和城市,如从顿涅茨克到哈尔科夫、敖德萨地区,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等城市。
[44] Дугин А.Г. Новороссия---крах или взлет для России//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15. №.9. C. 244-248. http://dlib.eastview.com/browse/doc/45325859
[45] Там же.
[46] Дугин А.Г. Новороссия---крах или взлет для России.
[47]张艳杰、于大春:“转型期俄罗斯民族主义与新欧亚主义理论之契合”,《学术交流》,2011年第12期。
[48] 笔者之所以将科瓦列夫作为新欧亚主义温和派的代表,是基于近年来他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都是立足于中派立场的基调,同时也写信求教了我国著名的俄罗斯哲学专家安启念教授。
[49]郭丽双:“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政治实践”。
[50] Ковалев Ю.А. Россия: снова перед выбором пути//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15. №.6. C.201-209.
[51] Ковалев Ю.А. XXI век. Россия. Расписание на сегодня. М.: РИОР, 2013. https://iphras. ru/uplfile/root/image/institut/admin/Kovalev_2013.pdf
[52]这个“综合”并非东西方的综合,并非亚洲和欧洲的综合,而是基督教意义上的综合观念。科瓦列夫在此处是借鉴了索洛维约夫这种综合的思维方式。
[53]Ковалев Ю.А. Россия: снова перед выбором пути.
[54] Там же.
[55] Там же.
[56]此处转引自Ковалев Ю.А. Россия: снова перед выбором пути.
[57] Ковалев Ю.А. Россия: снова перед выбором пути.
[58] Ковалев Ю.А. Новая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реальность и вопросы деологии. 2017. https: //iphras.ru/uplfile/root/image/institut/admin/Kovalev_doklad_19_04_2017.pdf
[59]Там же.
[60] 瓦尔代会议(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是俄罗斯自2004年起每年举办一次的最高层次的国际政治学术会议,创立初衷是为普京“正名”。其宗旨是“形成一个国际专家平台,使外国学者有机会从俄罗斯精英代表那里得到有关俄罗斯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最权威、最可信的信息”,希望以此有效改变西方媒体和精英对普京出身安全机构、进而就认定其行事私密而专横的负面印象。普京每年参会并直接与各国专家学者互动交流,因此,“瓦尔代”常被外界贴上“普京的智库”标签,瓦尔代会议被认为是观察俄罗斯思想动向的特别窗口。
[61] 郭丽双:《当代俄罗斯社会思潮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78-280页。
[62]Ковалева А.О.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Путь К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му Суверенитету. http://eurasia forum.ru/content/295
[63] Антон К.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доктрина Путина и классическое евразийство. http://eurasian- movement.ru/archives/1126
[64]郭丽双:“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政治实践”。
[65] 胡晓光:“瓦尔代俱乐部年会‘中国’成热词”,《参考消息》,2016年10月28日。
[66] 封帅:“世界历史中的欧亚空间:源起、建构与衰朽”,《俄罗斯研究》,2019年第5期。
[67]赵华胜:“俄罗斯还需要秩序吗——瓦尔代会议侧记”,澎湃新闻网,2019年10月18日,https://pit.ifeng.com/c/7qrpMuQDwBs
[68]Никитин А.И. Тенденции изменения архитектур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Евразии. 2015年“中国与欧亚:新机遇与新挑战”国际研讨会的参会论文。
[69]Иноземцев.В.Л.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потерянные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ПОЛИС.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4. №.6. C.71-82.
[70]高懿洁:“中国专家看瓦尔代会议:俄罗斯的身份认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13年9月25日,http://sputniknews.cn/russia_china_relations/2013092543873083/
[71] 粟瑞雪:“列夫·古米廖夫的欧亚主义学说及其对当代影响”,《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年第6期。
[72] 霍鲁日:“展开人学的原则与概念:人的建构的三个类型”,2019年6月6日于北京师范大学讲座。
[73] 斯米尔诺夫:“古典欧亚主义:俄罗斯‘全人类的’设计规划”,于北京师范大学的系列讲座,2018年4月19日。
[74] 荆宗杰:“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思潮中的‘第四政治理论’评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第2期。
[75] 转引自孔元:“普京‘大脑’杜金的地缘政治观:欧亚主义的回归与全球革命”,《文化纵横》,2015年10月。
[76] 赵华胜:“大欧亚伙伴关系︱中国的回应”,澎湃新闻,2017年12月15日。
[77] 安启念:“俄罗斯哲学的现状和未来”,《求是学刊》,2017年第7期。
[78]郭丽双、汪力平:“俄罗斯古典欧亚主义的文明论建构及其当代意义”。
D851.2;D837.2
A
1009-721X(2019)06 -0110(33)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反启蒙与新文明: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当代启示”(项目批准号:18AZX017)的阶段性成果。笔者由衷地感谢《俄罗斯研究》杂志匿名审稿人专业性极强的修改意见,这对本文的进一步完善非常重要。
**郭丽双,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肖辉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