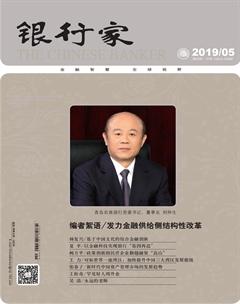反思全球金融危机应对当前金融形势
杨知澎
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风暴对当前全球金融体系及金融监管模式在理论、政策和实践上提出了根本性挑战,同时亦促使全球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重构国际金融秩序和金融监管框架,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值此金融危机发生十周年之际, 面对中美贸易酣战、民粹主义盛行的多事之秋,回顾和反思金融危机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还对于当前中国及全球金融和经济形势具有重要现实应对价值。
应对危机的财政、货币政策和监管改革
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世界各国根据自身情况,各显神通,应对危机。危机爆发后,美国通过注入市场流动性、救助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稳定了金融市场信心,避免了挤兑出现。在传统货币政策无法有效应对金融危机的前提下,美联储在救市中创造性地使用了非常规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促使美国率先在发达经济体中走出危机。中国政府在2008年底推出的四万亿投资一揽子刺激计划,以保证经济增长,促进就业,维护社会稳定。
在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应对危机,维护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同时,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更是通力合作,完善监管框架,重构监管秩序。2010年7月21日, 奥巴马政府正式签署《多德-弗兰克法案》,拉开了美国重构和强化金融监管序幕。该法案核心内容主要包括:设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对威胁美国金融系统稳定的风险建立预警机制;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以减缓和消除金融市场的欺诈、滥用等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制定沃尔克规则,提高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要求;建立中央对手清算制度,加强衍生品、互换和证券化监管。
危机后欧盟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点:一是改革监管架构,设立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负责宏观审慎监管,建立欧洲金融监管体系,由欧洲金融监管局负责微观审慎监管;二是强化金融市场和金融機构监管,提高金融业资本要求,加强衍生品和对冲基金和信用评级机构监管;三是建立以单一监管机制、单一处置机制和存款保险计划为三大支柱的银行业联盟,欧洲央行被赋予直接监管银行的职能。
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层面的监管改革在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的主导下迅速推出了一系列的监管标准和建议。这些成果重点涵盖三个方面:微观审慎监管、宏观审慎监管、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危机中迅速推出的“巴塞尔协议Ⅲ”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成果的集中体现,其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强化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一是恢复普通股(含留存收益)在监管资本中的主导地位,同时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建立了两个超额资本要求:留存超额资本缓冲用于吸收严重经济和金融衰退给银行体系带来的损失;逆周期超额资本缓冲用于经济下行时期吸收损失,保持信贷跨周期供给平稳。
第二,引入杠杆率监管标准,作为资本充足率的补充。2018年正式纳入第一支柱框架。
第三,建立流动性风险量化监管标准。一是流动性覆盖率,用于度量短期压力情境下单个银行流动性状况,目的是提高银行短期应对流动性中断的弹性。二是净稳定融资比率,用于度量中长期内银行解决资金错配的能力。
中国此轮全球金融危机中相较于发达国家的损失要小,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政府应对危机冲击的手段和效率,同时以政府监管为主导的中国式金融监管模式也起到了相当强的抵御作用。根据我国当时“一行三会”监管体系在危机及随后发展中存在的监管重叠和监管空白并存以及监管效率低下的问题,2013年8月,国务院正式确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2017年11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正式成立,旨在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2018年3月,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正式成立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适应银行业和保险业新的发展要求,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金融稳定。
后危机时代经济金融形势
弹指一挥间,危机已过十年,旧的危机影响尚未消除,新的危机幽灵又若隐若现。当前,除美国经济在表象上呈一枝独秀之外,包括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巴西、土耳其等新兴市场经济,仍然处于缓慢恢复和问题偶发的交替之中。例如,2009 年开始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随后向“欧洲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蔓延,沉重打击了脆弱复苏中的欧元区经济。近来,集中发生的巴西、阿根廷和土耳其债务和货币危机更让我们担忧是否又将世界拖入另一次重大危机之中。
诚然,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在应对危机中采取的财政、货币和监管改革措施,对维护全球经济稳定,恢复金融秩序,提振市场信心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重要政策和措施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也日渐显现。例如,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避免了通缩出现和金融系统的崩盘,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甚至还产生了诸如加重经济脱实向虚,损害货币政策自主性,强化了金融机构“大而不倒”逻辑,推高政府债务等诸多长期和深层次问题。
除了经济领域的巨大的影响外,美国救市措施和量化宽松政策对政治和社会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恶化了收入分配状况, 诱使财富差距进一步增大,致使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盛行,形成当下特朗普总统致力推行的“美国优先”政策的民意基础。当前,从主要经济和金融指标看,美国经济仍然表现强劲。然而, 随着美联储加息周期的开启以及美国政府债务规模的不断膨胀,美国经济可能也很快进入下行阶段。
中国政府2008年底推出的四万亿投资一揽子刺激计划促使中国经济在危机中迅速实现“V”型反弹,但从长远来看,其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四万亿投资虽然挽救了危机中经济快速下滑的趋势,却加剧了企业和地方政府过度负债,致使金融风险积累和投资环境恶化,损害了长期增长潜力。在经历了“V”型反弹之后,从2010 年第2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滑,呈现“L”型走势,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中国经济“新常态”既是经历长期高速增长、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自然放缓的结果,也与四万亿投资政策透支了经济增长潜力有一定关系。
目前,中国金融体系正处于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关键期。经济金融经过了上一轮扩张期后,进入下行期。在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金融风险的源头在高杠杆” 的明确判断。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实体经济的主要风险,将集中体现为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产能过剩、企业困难加剧和失业率上升等。为此,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引导资金脱虚向实是关键。而引导资金脱虚向实,仅仅依靠从金融侧去杠杆倒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效果并不明显,更重要的仍是提高实体经济效率,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当前金融形势的启示
2017年2月,特朗普总统甫一上台就签署命令废除代表強监管思想的《多德- 弗兰克法案》的部分条款。2018年3月15 日和5月23日,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先后正式通过《多德-弗兰克法案》修正案, 旨在放松金融监管(尤其有利于中小银行机构),促进经济发展。这意味着在危机中达成的强监管共识随着经济增长恢复、金融市场发展以及利益攸关各方博弈力量的此消彼长逐渐让位于放松监管的要求。
金融监管改革、监管规则调整总是伴随着金融危机发生进行的,甚至可以说金融危机是推动金融监管和监管规则完善的重要力量。在新一轮监管改革完成和监管规则完善之初,依据新规则确立的监管目标和测算风险水平基本反映真实经济和金融状况。随着金融市场的复苏,金融机构的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又随着各种形式的创新活动的增多而增大,于是在新监管规则下从事监管套利的动机和压力又逐渐增强,这又势必进一步激发了金融机构热衷于各种形式旨在进行监管套利的创新活动。显然,旨在套利的创新活动由于缺乏历史数据,其潜在风险更加难以准确评估和测算,甚至被人为操纵和低估。这些被忽视和低估的潜在金融风险,因为没有有效监管而得到系统的防范和化解,累积到超过金融和经济体系承受的水平,势必就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一方面给经济和金融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同时也推动了新的一轮金融监管改革的开始。这在政策层面上意味着以下几点。
其一,监管机构在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不应将监管目标与金融机构的经济目标对立和隔裂开来,监管机构应本着从维护被监管者合理利益和股东权益的角度,承认不同金融机构的异质性和特殊性,加强与它们交流和协调,将监管目标最大可能融于被监管者的经济目标中。
其二,监管的手段和技术应随着被监管者的内部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而同步增强和完善,改变被动和事后监管模式为主动和预见性指导、交流和合作监管模式。
其三,监管的核心和重点不应只放在监管目标是否达标方面,而是更应该放在制度建设健全和激励机制完善上。毕竟监管的唯一目标是为了保证经济和金融系统的整体性安全、防范系统性经济和金融危机发生。
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是监管技术和手段,金融机构内部风险管理水平,还是基础社会信用环境,与先进国家和地区相比都还存在差距。当前,我国主要的金融风险将集中体现为杠杆率攀升、债务负担加重和不良资产增加,强监管是可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金融监管主导思想。诚然, 监管不足会导致危机发生,但监管过度则会制约银行业等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甚至诱发监管套利行为大量涌现,并最终影响经济和金融系统的稳定,这一点在今后中国推进和完善金融监管过程中尤其值得关注。
(作者单位:中国青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