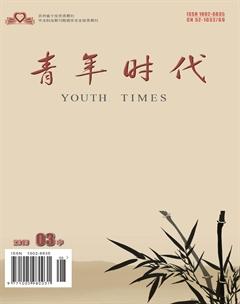浅析王安忆《白茅岭纪事》中的劳改女性形象
谢彤
摘 要:中国当代都市文学史上书写女性故事女性情怀的作家不在少数,却没有像王安忆这样独特的,以女劳教作为叙述对象,她的文字中个人情感不多,却能引发读者的无限深思。在她的《白茅岭纪事》一文中,塑造了许多鲜活新奇的,能够代表上海都市中不同文化精神的女性形象,既实现了对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的都市女性写作传统的接续,也实现了海派小说写作的创新,为世人展现出了不一样的上海故事及其中女性寻找、争取话语方式的途径。
关键词:王安忆;女劳教;都市女性
王安忆在中国当代都市文学史上固然是占据着不动如山的一席之地的,她写上海,不用特殊环境和特殊人物,不用过多的材料,也不用风格化的语言,不要特殊性。不特殊,便无法使读者识别到作者特有的写作风格,可也恰恰是这份不特殊,造就了王安忆写作的成功——她写的日常太能引起共鸣,尤其她对女性的叙事。自19世纪上海“开埠”以来,城市发展,阶层变化,上海女性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她们或许顺应时代潮流改变自我,或者坚持己见偏安一隅,但无论如何,时代的变化总会潜移默化地使她们做出选择:不是这个人,便是那个人;不是这一代,便是下一代。本文通过关注王安忆的经典作品——散文《白茅岭纪事》,浅析其笔下的劳改女性形象。
散文《白茅岭纪事》是王安忆散文集《男人和女人 女人和城市》中篇幅最长的一篇,记录了作者到白茅岭劳改农场采访上海女犯人的历程及采访期间的有感而发。白茅岭劳改农场有另一个名字,叫作白茅岭监狱,前者的称法大概是为了使说法委婉一些,但它确实是作为一个主要接收改造罪犯和劳教的场所,具体地址在安徽省郎溪县境内,距上海市约274公里,是上海市的外移基地。如果不是通过作者的笔触,我们实在无法想象在如此单调的土地上还集中了如此多有故事的、不同寻常的女人:“流氓”、“偷窃”、“诈骗”,也有女人会犯,并且不少是惯犯。这里有作者想要找寻的“米尼”,但她们又不仅仅是“米尼”,她们的人生经历或许有重合之处,但凑在一起却迥然不同,要么则是融成一个新的故事。
第一位接受采访的是一名“使人感到头痛”却文雅清秀的女劳教,她时常被怀疑是神经病。作者将同一个问题“你劳教的原因?”以不同的表达形式反复问了她四遍,女孩从头到尾都答不知道,可她最后一次的回答却恰恰暴露了她内心的不平静:“我正想请你们帮我去问一问,我到底是为什们进来的!我还想请教你们,究竟什么是劳教?”她接着还多次要求得到一本法律的书。此处的不甘与无奈似乎积压了许久终于爆发出来,哪个教养好的女孩子会不自尊自爱,主动去犯偷窃和流氓罪呢?这其中有无冤假错案暂无定论,然而我们能从她身上看到看到这个时期的女性是孤独而无助的。对自由和公平的渴望使她把希望寄托在未完善的律法上;试图以不配合劳教洗刷冤屈却被当作神经病;没有力量挣脱劳改却坚决抗争到底而最终被送去精神病研究所做鉴定……这是女劳教群体中认为自己蒙冤入狱并以自己的方式反抗的一类。
劳教大队中也不乏“被卖淫”的女性。其一是家中男人窝囊懒惰而又势利,偏偏风气如此,只好带着无限的心酸和对孩子的爱,通过与较为富裕的男性发生关系来获取日常所需物资,提高生活质量。亲身经历使她认识到脱离男性自己也能够独自存活,甚至能将孩子抚养长大,所以跨出了这个时代的许多女性不敢跨出的一步——与丈夫离婚并争取孩子的抚养权。然而这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觉醒,她并没有主动地产生独立自主意识,只是生活的压迫使她一步步地做出这个决定。最关键的是,风气使她将卖淫和淫乱与女性的自尊自爱隔绝开来,我们很难想象脱离丈夫后她能够重新找到一份独立而体面的工作来供养她和孩子的物质需求。其二是家境贫困,以柔弱身躯扛起家中生计的坚强的女孩。从另一层面来讲这并不能算是坚强,她被家庭束缚,察觉到生活的无目的性却没有想过要努力去改变现状,浑浑噩噩地任由生活摆布。其三是被冤枉卖淫的女性,每次发生关系不都是她自愿的,即便如此,她仍认命地配合劳教,希望出来之后重新开始人生,可却屡遭意外,三入监狱最终心态奔溃,对人生绝望并产生报社心理。劳改期间,她不要家里寄钱,也不寄去探亲条子,因为不忍60岁的老母亲辛苦奔波。她对母亲充满爱与怜惜,对父亲却是十分憎恨的,憎恨他对妹妹的绝情与残酷。重重苦难的压迫使她心理扭曲,但因为身处劣势只能屈服于现实的爪牙之下,她是可怜而可悲的。据后文作者与同伴所查,她所犯过错都记录在案,无法为她开脱,说谎有几分现实基础也就另当别论了。
作者采访的女劳教中还有一类特殊群体——女同性恋,她们同性相吸的原因或是生性偏向强势的一方,受不得比自己再强势的人的压迫;或是因为长期以来受到男性的奸淫虐待,对男性已经失去希望。前者往往成为女同性恋中处于男性地位的A角,不仅性格,而且在发型穿着、言行举止上也向男性靠拢;而后者往往成为处于女性地位的B角,在双方交往中仍处于被动劣势的地位,却多了几分对同性的兮兮相惜。同性恋在那时也是一种过错,虽然现今我们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已经提高很多,但就时论事,成为女同性恋的双方都是可悲的,A角充满反抗意识,在外表、内心都以男性为标榜,实则失去了自我,即使变得相对强势,也没能摆脱“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B角对伤害过自己的男性产生阴影,有厌恶和不满,可她们最终的选择不是走向独立而只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依附。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受访女劳教是众多女劳教中的清流——她们自尊自爱,对生活充满希望。其一是由表现较好又有能力的劳教担任的“民管”,她为了做生意“结交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时常往返于上海与广州之间”,因为款项上的纠纷被公安部门以卖淫定处,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了。在采访中,她坦言被丈夫之外的拥有美好品质的三黄鸡店老板所吸引,情不自禁去帮他,然而又舍不下对自己不错的丈夫和年幼的女儿。人类的情感是复杂的,女性内心情感细腻而又丰富,对丈夫以外的男人产生欣赏暗恋之心态,也是人之常情,凌淑华的《酒后》中的女主人公想尝试一下在婚姻生活中爱慕第三者的感受,她以主动的姿态,向丈夫之外的异性表达爱慕之情,与女“民管”一样将女性的欲望开诚布公,只是增多了一个征得丈夫的同意的前提罢了。女性的欲望并不比男性的欲望少或者差,她们也需要一个自主的、表露欲望的机会。婚与恋可以紧密结合,却也可以各据一方,对交往的双方来说,婚不一定恋,恋不一定婚,在适当的尺度内,二者并不矛盾。不勉强自己情感的输出,不压抑内心深处的欲望,这是人生而往来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其二是气质最高贵的劳教,她因为与情人长期姘居而被判劳教。事情远远不止表面看上去这么简单。在此之前她还被判过一次劳教,原因是出于慕恋而做出了主动追求的行为,未免有些不可理喻,然而初恋带给她的力量是巨大的:“假如不是遇见了他,我的生活也许就和大多数女孩一样,结婚,再生个小孩……”。然而这一次的劳教却给她带来了刻骨铭心的体验:她的情人,那位已婚的,对她的父母好,也对她有感情的老板,在她三十二岁因他们的关系被判劳教时承诺对她负责。虽然结果未定,但已能够预见路途的坎坷:“在香港,离婚是件复杂的事,财产,房子……”这不知是那老板舍不得现有的利益而搪塞她的借口,还是她安慰自己的理由。然而我们能从中看到这个时代女性的进步:敢于敞开心声,果断地主动追求恋慕之人,为自己创造机会,而不是听从命运的安排,与熟悉的陌生人结婚生子。然而也有其时代局限性:认为情人好是因为他对她的父母好,这极大程度上是出于对父母的孝顺而不是对情人本身的爱情;在交往中处于劣势的地位,不但情人对她、社会对她也是不公平的,情人将她的青春消磨到三十二岁却仍没有给她真正意义上的保障,而社会对于情人姘居,只会把劳教判给弱势的女性一方,她寄希望于情人的离婚,却没有想过为自己找好退路。
王安忆许多作品关注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而这种塑造正是通过世俗生活得以体现。《白茅岭纪事》这篇散文,表面上是完全从第三者的角度看女劳教们服刑前后的人生,然而我们能从诸多描述性的文字从中看到身处大城市的作者同样因不为他人所理解、融不入身边人而孤独落寞的内心。在白茅岭劳改农场接收的女劳教中,有的不甘伏罪而拼命挣扎,聪明的成了令管理员们无可奈何的刺头儿,老实一点的便成了亟待认证的“神经病”;有的因为外面的世界充斥着太多欲望、诱惑、利益纷争所带给人的压迫与痛苦,反倒喜欢上了这个可以暂时逃避现实的、生活充实的地方;还有的满怀着对生活的希望和对羁绊的眷恋,战战兢兢地配合勞教,筹备出去后过上新的生活……她们能直面内心欲望,违抗常伦我行我素;也能逃避现实卸下斗志,抛弃独立依附他人。她们无一例外的经历过生活坎坷、情感波折,尽管内心向往彼岸世界却注定走不到或仍未到达。她们在都市的边缘徘徊,或者前进,或者后退,总有无数种选择的可能性,因为在上海这样一个繁华的大都市,繁华背后必定有阴暗的角落,公平不可能照耀到每一处,也正因为如此,才创造了那么多的可能与不可能。当命运已经发生,只有踏步向前,哪怕荆棘遍布,最终也能收获一份坚韧的温情。
参考文献:
[1]赵欣.上海都市文化与上海女作家写作[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0.
[2]王安忆.男人和女人 女人和城市[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3]王安忆.米尼[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1996.
[4]姚玳玫.中国现代小说细读[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都市女性自爱力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