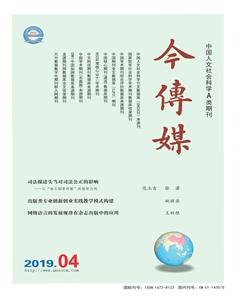《金陵光》的个性特征与办刊抱负
战涛 姚璐
摘要:对金陵大学创刊于清宣统元年(1909)的《金陵光》的主办者、编辑出版概况、办刊抱负与宗旨,以及传播内容作初次历史考察。其将校刊的功能概括为一校之“公共日记”“一台透视社会病原的X光机”、指点迷津的“一座灯塔”的说法极富个性。其刊名所寓意的“旭日东升之晓光今出矣”,以及“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的宣示,将一校之刊的使命和愿景提高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显示了办刊者的高远追求和抱负。同时,认为该刊是我国文理综合性大学学报的典型代表之一,并引领了五四以后大学期刊向校刊主新闻、学报主学术、学生刊物主作品格局的演化。
关键词:金陵大学;《金陵光》;中国高校期刊史
中图分类号:G25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9)04-0115-05
一、主办者
金陵大学原为一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私立大学,始建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它是国内历史悠久、规模较大的著名教会大学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由政府接办,改建为公立金陵大学。到1952年与南京大学合并为止,金陵大学共有64年历史。它由三所书院于宣统二年(1910年)合并而成:其一是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在南京成立的汇文书院(NankingUniversity,1888年-1910年),书院设博物馆(文理科)、医学馆(医科)和神道馆(神学科),是金陵大学最早的源头,《金陵光》(TheUniversityofNankingMagazine)即由其创办,并被金陵大学所继承;其二是由美国教会基督会传教士美葛斯(F.RankE.Meigs)于(1891年)在南京创办的基督书院(NankingChristianCollege);其三是美国教会长老会传教士贺子夏(美籍)于(1894年)在南京创办的益智书院(ThePresbyterianAcademy)。
合并之初的清宣统二年(1910年),美国人包文(A.J.Bowen,1862-1944年)任校长,文怀恩(J.E.Williams,1871-1927年)任副校长,以美国大学教育制度为蓝本,逐步发展成为一所具有一定规模的综合性大学。与此同时,在南京成立董事会。之后,董事会增加了同学会(校友会)的代表,于是便有了中国董事。如任驻德公使的黄荣良、任绥远省实业厅长的韩安、国立东南大学教授陶行知均以校友身份担任董事会的董事。“五四”运动后,在中国爆发了一场基督教运动及由此而引发的收回教育权运动,迫使教会学校在大发展以后进入了改革时期。1927年7月,国民政府收回教育权,同年,金大理事会在上海开会,文理科科长、化学家陈裕光博士当选为金大校长,是国内任教会大学校长的第一位中国人。其初期,先后设文学院、理学院、农学院和医学院。新中国成立,金陵大学获得新生。1951年9月,断绝与美国教会的联系后,李方训任校长,私立金陵大学与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原金陵女子大学)合并为公立金陵大学。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金陵大学等西方教会大学撤销建制,金陵大学文学院、理学院并入新南京大学(南京大学保留文、理学院,其余部分院系分出),成为南京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编辑出版概况
《金陵光》,创刊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12月,是金大第一个问世的全校性刊物。初为英文版,名TheUniversityofNankingMagazine,两月刊,后改为季刊。1913年改为中英文合刊,4月刊行第1期,以后每学月出版一期,全年计8期。刊头“金陵光”三字寓意“旭日东升之晓光今出矣”,初为张謇所题,后又用北京政府教育部长范源濂的题字。
如同《约翰声》等早期刊物,《金陵光》亦为金陵大学第一份学生期刊。其经理、编辑乃由学校全体师生“公举”,组织设编辑、经理二部,以主其事。改为中英文合刊后,编辑部复分为中英两种,以总编辑总其成,顾问员中中西各一位,亦由全体公请,均一年一任。著述除编辑员担任外,备有征文简章,同学可自由投稿,再由主笔评定,被选者按文奖赏,以资鼓励。全刊分导论、论说、译著、传记、文苑、记事等栏目。1913年时的《金陵光》职员为:总编辑刘靖邦;中文编辑,徐养秋、刘佩宜、张枝一、陶行知;西文编辑,胡天津、陈义门、童家炳、都振华;总经理卢先德;经理员,陈裕光、吴守道、凌旭东、卢颂恩;中文书记,冯武云、王海云;西文书记,黄宗伦、卓景昌;中文顾问员王东培;西文顾问员:恒模。其英文职员有FacultyAdvisers(顾问教授):HuHsiao-shih(胡小石);WuChing-chao(吴景超);HwangChi-kang;H.S.Bates;L.S.C.Smythe;T.C.Tomson.等等。
《金陵光》改为中英文合刊后,中文主笔陶行知,英文主笔刘静邦、张謇,内容有关于哲学、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及医学、农学等方面的专著,并发表大量诗、词、散文、游记、剧本及名人传记、同学会消息等。改为中英文合刊之后,其读者更多,发行范围更广,内容也更其丰富,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重要之刊物。
《金陵光》显然为“一校之刊”。金陵大学第一任中国人校长陈裕光即称其为“吾校之刊”[1],《金陵光》中文版创刊之时,《缘起》也指出“本校自有英文报,迄今已四载,……安可不有规模更大之学报”[2]。宣统元年(1909年)创刊之初,《金陵光》为英文版。按陶行知的回忆,1913年2月开始出版中文版。时为三年级学生的陶行知于1913年8月始任主笔,并针对“醉心欧化,蔑视国文”的积弊,提出了“借西学之长,济己之短”[3]。
《金陵光》于1928年初停刊。此间,学校以金陵大学学生会主办的《金陵周刊》取代之。1930年,在全校师生一致呼吁下,《金陵光》复刊,陈裕光校长特撰《藉与共勉焉》一文,指出:“《金陵光》遽行停刊后,代以其他刊物,如周刊、季报等,而以传播校问闻,研究时事为主要目的,虽也有其相当价值,但具有深远历史,极负有相当声誉之学术刊物,不宜长此停顿,则举校师生皆同有此感。今金陵光又重行于此矣,深原主其事者,一本以前之精神,以发扬思想,研究学术为惟一之旨,使社会人士对《金陵光》……”[4]然而,《金陵光》复刊后,仅出1期最终永远停刊。其原因主要是学校对全校出版物作了重新规划:以《金陵学报》主学术,以《金陵大学校刊》载新闻,一般学刊发表师生一般作品,由各院系主办,介于校刊和学报之间,各有侧重,办出特色,提高质量。1930年11月28日,学校出版委员会主办的《金陵学报》半年刊正式创刊,主要刊登高水平学术论文,辟有论者、讲究、时伴、谭丛、纪略、评论、调查等栏目,专设学报编辑委员会,由学校各学院院长推荐教授3人组成,文学院为胡小石、刘遁敬、李小缘,理学院为陶延桥、余光娘、伊礼克,农学院为戴方澜、陈方济、胡昌炽三先生。李小缘任主编。学报有时亦以专号分别编辑出版,除“文史专号”外,还有“理科专号”“农业专号”等。当时,不少著名学者,如王重民、向达、闻一多、常任侠、陈梦家都在学报发表学术文章,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一份深具影响的重要学术刊物。1940年在抗战中停刊,共出刊11卷,約22期。
据1933年6月金陵大学刊印的《金陵大学出版物目录》记载,当时校内各类出版物计有159种,分四类:一为专著,二为规程及报告,三为杂志,四为小册子。其中,科技期刊主要有农学院1924年创刊的《农林新报》《农学院通讯》,1932年创刊的《农情报告》,1925年创刊的《农林科通讯》等50余种出版物。
三、办刊抱负
《金陵光》创刊之初的清末,国内风气犹属闭塞,出版品殊不多见,而以发扬思想学术研究,如《金陵光》者,殆寥晨星。民国以来,国民思想猛进,刊物风起云涌[5]。在解释《金陵光》中“光”的含义时,其《宣言》指出:“学报奚以光名乎,曰天地之大,万物之繁,吾人所持以别上下高低、大小方圆、正斜黑白、动静美恶者,光而已矣,无光则虽有天地万物,奚由辨别乎,学校之宏,学生之众,吾人所赖以知兴衰进退,勇怯知愚贤不肖者,报而已矣,无报,则虽有学生、学校,奚由表见乎,故报所以别天地万物之形,报所彰学生学校之迹,报与光之功用既同,则名报为光,不亦宜乎。且吾人为学业,必求进步,吾人进步,必期速捷,万物流行之速,孰有过于光者乎,风卷不足概:电流莫能喻,瞬息万里,莫可纪极,吾愿以光流行之速,率为吾同学进步之速,复以同学进步之速,率而为金陵大学进步之速,率光乎,进步乎,吾愿一言以祝之曰,学校与学生,进步如流光,或问曰,光之为物,亦繁矣,日光也,月光也,电光也,磷光也,灯塔光也,爱斯光也,下至萤雪,火之细,莫不有光,天然之光,光也,人造之光,亦光也,《金陵光》,安居乎。曰,‘太阳信深仁,哀气□有托,此杜少陵元冬登飞阁之诗也,可见光由热生,热随光至,可以御寒振衰,世有厌世之流,悲观之派,昧爱人之宗旨,忘牺牲之大道,谓热心为好事,谓力行为有求,彼既寒心而凉血,吾《金陵光》,则以随来之热,力曝其心,温其血,祛其寒,振其衰,使其共跻于热忱乐为之学子,如是则冬日之效收,而光之用神矣”[6]。
学生们对《金陵光》寄予殷切希望:一说“月临席上,绮文依而愈妍,吾同学之造业,虽不必待《金陵光》而进步,而同学之成绩,必待《金陵光》而彰明,游子负笈他乡,或千里跋涉,或重洋骇渡,谁无父母,独不一念及吾辈之学业交游与夫学校之现象乎,家函不过道其大略,《金陵光》则详之”,此处指“同学之造业”“必待《金陵光》而进步”“同学之成绩必待《金陵光》而彰明”,连接“学业交游与夫学校之现象”的“家函”必待《金陵光》“详之”,实为对大学刊物功能的重要拓展;二说“当夫黑云蔽天,两大昏晦,月未出而日遮蒙,霹雳一声,使生物得复明辨彼我者,电之光也,倘不幸而有人焉,惑于外物,狎于弗义,大道不明,天良澌灭,必不得已,欲《金陵光》一闪其雷鞭,则亦直闪之耳”,此处显然将《金陵光》视为照亮黑暗昏晦之光、霹雳之光和鞭辟入里、切中时弊之光;三说“金陵光,吾同学之公共日记也,同学既有公共之日记,则固有之精神可以保存,已具之精华有所托属,其中之一举一止,一言一行,咸足以备他年之考据,以作来者之前鉴,虽事已呈,迹已邈,而此公共日记,直能闪烁其彩色,以至于无穷”,此处将校刊的“保存”“托属”“考据”“前鉴”功能概括为一校之“公共日记”的说法,实闻所未闻;三说“吾辈青年为学,正如日暮浮舟险峡,邪说淆听,瓦裂之怪石也,跛行冒善,云翻之豪湍也,是非莫别,安危一发,吾《金陵光》则作船工之塔灯,明其径途,所以佐迷津者之造业焉”,在此,《金陵光》又成为“日暮浮舟险峡”的一座灯塔;四说“世之金玉其外,而败絮其内者,岂鲜也哉,心疾不治,太丧随之,《金陵光》于此则射其爱斯之光,察其肺腑,烛其心肝,病原既得,而后可施针砭也”,此处《金陵光》又成为一台透视社会病原的X光机;五说“吾辈青年,能为左丘明弥尔通之徒,谁能入门墙登堂奥而无所用其光哉,是故囊萤借萤之光,映雪借雪之光也,人至习业至于囊萤映雪凿壁亦可谓无奈之至矣,然三贤必出于囊萤映雪凿壁之计者,何哉无光即无以造其业耳,吾《金陵光》既已佐同学造业自任,则请之为萤、为雪、为爝,皆无所不可也”,此处的《金陵光》又成为奋发于学业之“囊萤映雪凿壁”的照明之源;六说“日日曰月曰电,限于行所言,日磷曰雪曰萤,天然之光也,曰爱斯(X)曰爝火,曰灯塔,人造之光也,兼天然人造而有之者,《金陵光》也,《金陵光》随学生天演之进步,自然发生是之谓天然之说,天下本无《金陵光》,有《金陵光》,自金陵大学学生始,是之为人造之说,《金陵光》之为天然,为人造,姑无论,而其目的则一,目的为何,曰‘李杜文章在光艳万丈长,此光《金陵光》之目的也,曰,然则《金陵光》之作为可得闻乎,曰,‘青华易过,韶光不闲,此光字,《金陵光》用以勉励同学,及时努力,勿使徒伤老大也,‘利剑光耿耿,佩之我无邪心,此光字,《金陵光》用以警醒同学,避不善如蛇蝎,勿以恶小而为之也,一勉一瞥,莫非欲吾同学就草切磋,蔚为国器,对于《金陵光》,便怀有盛世黎民嬉游于光天化日之感,由感立志,由志生奋,由奋而扦国,而御侮,戮力而同心,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则《金陵光》之责尽,始无愧于光之名矣嘻,自帝更声尽,阳台曙色分,《金陵光》之第一号,即旭日东升之硗光今出矣,吾同學曷速兴起耶”[7]。这最后的“六说”,概括了之前的“察肺烛心”透视社会病原的X光机、“囊萤映雪凿壁”之光源、“日暮浮舟险峡”的一座灯塔说,提出了“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为《金陵光》之责的远大理想和抱负,将《金陵光》的社会功能和愿景提高到了一个崇高的高度,显示了办刊者的高远追求和抱负。
四、《金陵光》的办刊宗旨
一是“保存国粹”,即认为“自西学中输,西学派之醉心欧化,蔑视国文也久矣。殊不知腐儒鄙弃西学,固属偏见,而新进蔑视国文,尤为忘本。夫国文之用,所以表示一国人之思想,记载一国人之行动,以互相传达而特异于外人者也,故国界一日不消除,则国文一日必留存,未有国而可弃其国文者也。国文有缺点,吾当补缀之,国文有窒塞,吾当贯通之,国文衰暗,则当改良之、光明之。其事实难,然吾辈青年学子所不可放释之责任也。同人有志于此,爰增刊中文报,以磨练作国文之才,而唤起爱国文之心。能作能爱,而后可言保存,能保能存,而后可言光明”[8]。
二是“灌输学术”,即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泰西学术,实高出吾人之上,何妨借人之长,以济己之短,然徒有英文学报,不过将我之所长彰之外人,而对国内学子反不能尽其介绍之职,殊为憾事,故加入中文以承其乏。凡关于学校学生足为吾辈学子研究之助,本报即译之,虽才有未足,力有未逮,然泰山不让细尘也”[8]。陈裕光进一步指出:“以发扬思想,研究学术为唯一之旨”[1]。
三是“推广规模”,即认为“世间事物不能无进步,即规模不能无推广,本校自有英文报,迄今已阅四载,而此四载之内,三公会联合,三书院统一,学校有进步,学生有进步,成绩日多,精神日旺,安可不有规模更大之学报,与学校学生平行进步,以宣导其磅礴,记载其成绩,而鼓舞其精神哉!”[8]。
该刊曾一度停刊2年,复刊之后,学校主政者仍给予极大希望,要求保持原有的办刊宗旨,并希望:“主其事者,一本以前之精神……使社会人士,对《金陵光》已具有相当之认识者,此后得益加称许而乐于赞助之,视与其他一般通行刊物不同,庶足以保既往之光荣,增吾校之声誉也,斯望以后之主编斯刊物者,亦能本此精神,继续不懈使《金陵光》得与吾校同其始终,为金陵之光,为学术界之光,斯不仅一二人所甚盼而已也”[9]。
简而言之,《金陵光》如同《约翰声》《学桴》一样,均为早期学生编辑和作者为主、学校校长支持的“一校之刊”,但到了五四以后,为了提高学术权威性、反映一所学校真实的学术水平,学校刊物逐渐分化,形成了如同金陵大学那样,校刊主新闻、学报主学术、学生刊物主作品的格局。像1924年的《清华学报》、1930年后的《金陵光》等,均逐渐被以师生合办和最终以教师为主的“学报”、以纯粹的学术论文为主的办刊模式所取代。但是,晚清民初,以学生为主办学术论文与文学作品兼而有之的学报模式及其媒介组织形态,仍有其桥梁、交流、史册、联谊的积极意义,对于养成像陶行知、张謇这样的一代英才仍然发挥了积极作用,即便百年以后看来,仍有许多可兹借鉴之处。
参考文献:
[1]陈裕光.序[J].金陵光,1909,1(1):1.
[2]编者.《金陵光》增刊中文版之缘起[J].金陵光,1913(1):1.
[3]章开沅.校报也应“以生为本”——从陶行知编《金陵光》说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54.
[4]陈裕光.藉与共勉焉[J].金陵光,1930(1):1.
[5]《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中卷)[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404.
[6]陶行知.《金陵光》出版之宣言[M].《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學史料选(中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402-403.
[7]陶行知.《金陵光》出版之宣言[M].《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中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402-403.
[8]编者.《金陵光》增刊中文版之缘起[J].金陵光,1913(1):1.
[9]《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中卷)[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