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载飞逝,再访乔迪·萨瓦里
2013年3月1日,草长莺飞,正值早春时节,刚刚结束了菲律宾旅行的我从马尼拉直飞香港,一下飞机便直奔位于港岛中环的香港大会堂,在音乐厅休息室采访了西班牙古乐大师、维奥尔琴圣手乔迪·萨瓦里(Jordi Savall),第二天晚上在大会堂音乐厅欣赏了他的个人独奏音乐会。之后,我的访谈实录文章《与乔迪·萨瓦里促膝而谈》就发表在了《音乐爱好者》当年5月的杂志上。
2019年3月24日上午,春雨淅淅沥沥,一早便得知乔迪·萨瓦里要在长沙举办音乐会的我,在他下榻的酒店与他如约再度相见,并对他进行了第二次专访。
2019年是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而3月23日,正值哈耶克逝世二十七周年。近几日,我正在重读哈耶克的传世名著《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此番刚与乔迪·萨瓦里在酒店会客室双双坐定,忽然想起六年前在香港采访时他曾说起有一个叫做“The Routes of Slavery” 的录音出版计划,翻译为中文也是“奴役之路”。于是,我灵机一动——话题,就从这里开始吧!
● -王士昭 ○ -乔迪·萨瓦里
● 乔迪,刚刚见到你之前,我还在哼你十多年前用维奥尔琴演录的一支曲子呢,叫《落地的绿袖子》(Greensleeves to a Ground)吧?旋律太好听了,感觉就是英国民谣《绿袖子》的精彩变奏呢,维奥尔琴的泛音真是太美了!
○ 哦,正是这首啊,谢谢你喜欢!
● 你知道经济学家哈耶克吗?二十七年前的3月23日他去世了,但他的杰作《通往奴役之路》将在大家的心中永存,这些天,全球有很多人都在纪念和谈论他。我知道,你如六年前计划的那样录制出版了一套名为《奴役之路》的唱片,这套唱片不仅关乎音乐,更关乎文化和历史。虽然哈耶克的书名与你的唱片主题在字眼上并不完全相同,他所说的人类政治经济制度意义上的“奴役”(Serfdom)也与你唱片主题中的美洲“黑历史”意义上的“奴役”(Slavery)含义不同,但用中文翻译过来字面上就很相似了。你是出于怎样的想法和构思来策划创作这样一套唱片的呢?
○ 音乐是一种能够通过人类固有的情感把人们带入历史思考的奇妙力量,所以在策划构思《奴役之路》的时候,我先从我所熟悉的音乐开始,再通过历史研究逐渐增加思考的深度。其实,你们可以把《奴役之路》视作一部音乐历史剧,其剧情来源于1444年对黑人的第一次大规模掠卖和奴役。为了用音乐阐明这段历史,我问自己:“当初奴隶们劳作时都会唱些什么?那些奴隶的后代今天又在听些什么、唱些什么?”当然,现在的我不可能确切地知道这些人在五百多年前唱的是什么。我们从1600年左右开始记录音乐,但是对一些口传心授的传统音乐,我们必须妥协,所以在某些情况下,我会选择在传统音乐中插入一些新创作的音乐。这个项目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至今仍在继续。2017年11月,在纽约和蒙特利尔举行的“奴役之路”音乐会上,我们又加入了一些北美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汤姆叔叔的小屋:卑贱者的生活》、北美奴隶歌和福音書(Gospel)等等。


● 策划和制作《奴役之路》的过程,于你而言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 当你听到《奴役之路》中那些奴隶歌曲的时候,当你回味歌曲中蕴含的那些黑人文化和思想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强烈而奇妙的灵感。我认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音乐是他们用来沟通与交流的唯一一种语言,音乐可以直接触摸和抚慰人的心灵,它能比一座冰川更有效地平息暴烈的争端,它能做得更感性,这一点是毫无异义的。回想美洲与非洲之间的奴隶贸易历史,想想那些从非洲被贩卖到美洲变成奴隶的黑人,是音乐让他们保留了这种关联——与他们自身传统文化的关联,与家乡的关联,与家庭的关联,这种关联促使他们要歌唱,也促使他们在困苦中留存着希望。你知道吗,音乐中有思考,音乐中有感叹,当这样一个黑人屈身于运奴船中在海上颠簸飘摇时,音乐必然就是他最好的疗心圣药。当你研究这些音乐的时候,你会情不自禁地唱起那些美妙的歌曲,感受到音乐无穷的魔力。
对我来说,《奴役之路》除了音乐,也记载和呈现了一段人类的历史,一段与数百万黑人相关的历史。针对这段历史,没有人说过“我很抱歉”,更没有人为他们的贩奴行径付出代价,所有到美洲的黑人都成为了奴隶,他们被频繁地贩卖交易。甚至直到今天,如果你是一个黑人,那么你会比白人更有可能面临警察的枪杀,你在校园里可能会面临种族歧视和与之带来的不公。可以说时至今日,“奴隶”仍然存在!
● 你是不是认为美洲历史上的奴隶贸易本身就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原罪”(Sin),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刑事罪行?在把黑人从非洲大陆贩运到美洲的漫漫海途中,他们被关押在狭窄的船舱中忍饥挨饿、衣不蔽体,甚至有相当一部分黑人在海途中因病困而死,根本无法看到“新大陆”。
○ 是的,我同意你的说法。要知道,这些原生于非洲的黑人在历经磨难后被运抵美洲大陆,被迫面对另一个世界,被迫面对另一种繁重的劳动和奴役,更被迫面对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文化。1865年以前,他们都是黑奴,在当时黑奴是合法的。从1865年开始,黑奴才是非法的。但是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黑人仍然遭受着严重的种族歧视和不公正的对待:黑人不能与白人在同一所学校就读,不能与白人乘坐同一辆巴士,不能与白人乘坐同一列火车。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黑人才享有了和白人一样的权利,在巴士上享有一样的座位,但仍然有白人讨厌黑人。
● 那么关于《奴役之路》,你将它视为一个文化研究项目多过于音乐项目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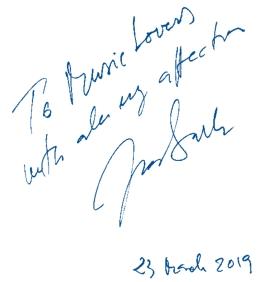
○ 是的,应该说我把这个项目当作一个集音乐、文化与黑奴历史反思的合成品。其中,有西班牙语的宗教歌曲,还有黑人歌手从西非国家马里(République du Mali)带来的传统音乐。他们的音乐听上去像欧洲的一种节奏舞曲,他们唱着非常传统的土著歌曲,也发行自己的录音,流露出他们对非洲传统文化之根的珍视。唱片中的很多歌曲来自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以及美洲大陆上的黑人歌手。在非洲,我有像巴拉奎·西索科(BallakéSissoko)这样的老朋友,他是一位出色的科拉琴(Kora)乐手。我找到一些通过音乐讲述故事,并且描绘他们本国文化的非洲游吟诗人,他们都是很棒的歌手和音乐家。
● 我能感受到你不仅仅是一位音乐家,还是一个文化思想者、一个历史研究者,更是一个身体力行者。你通过自己的音乐项目实践在这些领域做了很多工作,包括促使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人反思在历史上他们的先辈对其他种族做过些什么,他们自己又正在对其他种族做些什么,促使他们“道歉”并做出补偿。
○ 我觉得,当人类社会发生革命的时候,应该反省在历史上发生过什么,如果你不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那么你也不可能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如果你在年轻时犯过一些错误,那么你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如果你年轻时犯了错,年老了还犯同样的错误,拒不认错,拒不纠错,这样的人生是可怕的。
● 你所创立的Alia Vox唱片公司的录音项目从巴尔干音乐(Balkan music)、南美音乐到中国音乐,涉及的面越来越广。迄今为止,你们已经录过多少国家的传统音乐呢?
○ 那可有很多!比如巴尔干音乐吧,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这些国家的音乐都有。还有土耳其音乐、凯尔特音乐(Celtic music)、爱尔兰音乐、苏格兰音乐、犹太音乐、阿拉伯音乐和南美音乐等等。
● 你喜欢做田野采风和田野录音吗?
○ 是啊,我很喜欢田野录音。比如在中国,有朋友带我到民间寻访,我喜欢听民间乐手弹琵琶,弹筝,听他们演奏很传统的曲子。
● 说到中国音乐,这是你第三次来中国了,记得六年前我们在香港见面时你曾说你正在策划一个有中国音乐家参与的录音项目,现在这个计划实施了吗?
○ 是啊,我们已经做好了!(随即他用手机给我看Alia Vox唱片公司官网上相关唱片的介绍页面)
● 我收藏了很多Alia Vox公司的唱片,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唱片包装里除了精致的柯式印刷的CD碟片以外,还有一本厚厚的印制精美、图文并茂的小册子,看上去就像是一本书,信息量很大。
○ 是的,在录音和CD之外,我总是试图通过多种语言向购买它的人传达一些相关联的历史与文化信息。对了,你知道Super Audio吗?
● 你是说S A C D吗?多声道的 SACD?
○ 对!除了普通格式CD,我对SACD也很有兴趣。(他拿出钢笔,在纸上画录制SACD的录音麦克风定位)这里一支麦克风,这里一支麦克风,这里一支,这里又一支……要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多声道的錄音,SACD更能抓住他们的眼球。更重要的是,SACD的声音质量要比普通CD好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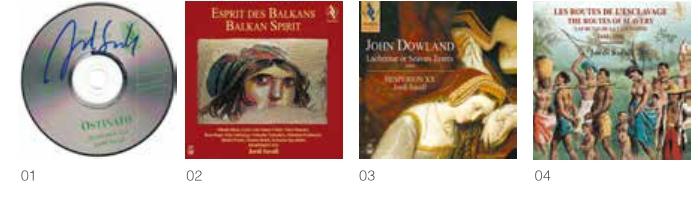
● 那么除了录音,你每年大概有多少场演出呢?
○ 不是太固定,有时候四十场,有时候五十场,有时候六十场。
● 可是你今年已经七十七岁了,按照中国的习俗,你已经算是一位七十八岁的老绅士了,你不会觉得疲累吗?
○ 不会啊,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在音乐中得到了很多快乐。
● 也就是说,你很享受巡演!
○ 是的,我喜欢访问不同的国家,接触不同的音乐,每一次演出都是一次新的体验,是与不同类型人物的有趣接触。音乐不是一种工作,而是乐趣。当你感到累了,音乐会令你愉悦,尤其是当你刚刚完成或者正处于繁重的体力劳动时,音乐会令你自然而然地喜欢上它。音乐家就像一个演员,一个电影演员。当电影演员完成一部电影的表演与拍摄工作时,也许身体上很疲劳,但他精神上的愉悦是不可描述的,音乐家也是一样。而且与此同时,音乐能给我带来能量。我不否认,有些时候,在演奏会之前,我的身心也会感到疲劳,但演奏会一旦开始,我的精神就会马上感到十分愉悦,我的身体也瞬间不再感到疲劳。而且,我演奏的音乐能使观众感到愉悦和快乐,他们的反应对我来说同样是一种富有能量的激励。
● 有些音乐家在结束自己的音乐会之后,乐于和台下的观众们进行交流与问答。比如,每一届香港艺术节的演出之后都有一个叫作“演后艺人谈”的环节,艺术家们就在舞台上,手持话筒,和台下的观众们进行自由随意的问答与对谈。你也喜欢这种形式吗?
○ 是啊,我也喜欢这种交流方式,并且身体力行。演出后的这种交流气氛很好,观众对古代音乐与乐器很有兴趣,我可以一边试奏一边讲解,甚至让观众上台来用我的维奥尔琴演奏。
● 听说这次你没有带来亲自创建的“晚星二十一古乐团”(HespèrionⅩⅪ),而是与三位独奏家一同前来?
○ 是的,加上我自己,一共四位演奏家。编制中有两把维奥尔琴,除了我,另一位维奥尔琴手是洛伦兹·杜夫施米德(Lorenz Duftschmid),演奏长颈诗琴和吉他的是夏维耶·迪亚兹-拉托尔(Xavier Diaz-Latorre),麦克·贝林杰(Michael Behringer)则演奏羽管键琴。
● 欧洲古代弦乐器,尤其是提琴类乐器常使用羊肠弦,那么现在欧洲古乐团还使用羊肠弦吗?
○ 现在的古乐乐师都不用羊肠弦了。羊肠弦诞生与应用的时代,制琴材料几乎别无选择,羊肠是相对合适的制弦材料。你要知道,羊肠取自羊的体内,不仅完整度难以保证,处理制作的过程也极其麻烦复杂,而且制成后的羊肠弦依然是一种物理性状十分不稳定的材料,受环境的影响很大,音准稳定性差,难以有效地承担演奏旋律的任务,若需要拨奏的话,则更加难以胜任。现在的古乐师都用金属弦了,现代技术完全能够满足演奏者对琴弦的音色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