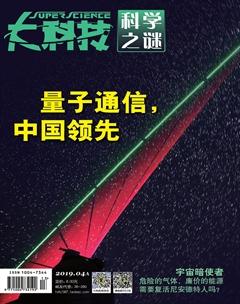《理性的思辨》连载①序言
这本书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著作”,因为当时并不是把它当成一个“作品”来写的,实际上这是一个由原始森林中的一些思考所整理成的笔记。
我在1970年春到1973年秋,有三年半的时间在长白山森林中“插队落户”,得到了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能在尚未被破坏和污染的大自然的怀抱中自由而且清静地思考各种问题。
当时我大学毕业已超过十年,如果从小学算起,到写完这本笔记时,正好经历了三个“十年寒窗苦”(那时的经历确实相当“苦”)。
我大学毕业后在东北师范大学物理系图书资料室工作,整日与书籍为伍,因此看了不少书。我的一生从小就是颇为曲折复杂的。抗战时,父亲是国民党将领,但实际上是在周总理、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的指导下为党工作,故全身心投入抗战救国,抗战期间没有和家人见过一面!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在日寇统治下的上海过着隐姓埋名的“城市平(贫)民”生活。抗战胜利后仍然很曲折,先是家父以“接收大员”的身份接收伪满首都长春,任市长兼警备司令。当时“国共合作”尚未正式破裂,共方代表是伍修权同志。家父后又故意当了解放军的“俘虏”,以便向中央汇报。因为他是蒋经国“最好的朋友”,得以交换俘虏,回到上海,仍与蒋经国密切交往。
1948年秋淮海战役开始前,国民党上层纷纷将家眷迁往台湾,家父也将我们送往台湾,实为人质,使蒋介石不怀疑他。他一人留在上海,坚持到上海解放前的最后一架飞机去香港。
我在台北成功中学念的初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借助军统上层关系,我们全家离开台湾到香港。几个月后,1950年春,我们回到北京定居下来。但从1948年离上海,经台湾、香港,到北京,我们没有见过父亲一面。他在香港为党工作,只在1951年夏回北京在家住了几个月,再次见面就是1955年“肃反”之后了。当时,因潘汉年案(已平反)和孙立人案(在台也已平反)的牵连,父亲已不适合做以前的工作,于是离开了香港进入政协。与此同时,我则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被“哈军工”清出来,转入东北师范大学。由于东北师范大学在长春,而家父是第一任伪市长。从此我就以“伪市长狗崽子”的身份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这使我获得了比兄姐更丰富的经历。因为他们在北京,享受“民主人士子女”的保护。家兄赵展洋更享受过一段“干部子弟”的待遇:高二在“师大附中二部”念书,高中毕业于101中学。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三十来人,同学中多为中央干部子女。不论冬夏都穿发给的灰制服,无特殊化,以后也没听说有人腐败了。因此,我在“插队落户”时,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人生阅历,为写这本笔记打下了一点基础。
对于40岁以前复杂艰苦的经历,我一直持一种乐观的态度,而且存着一种“感恩”之心。我真心感谢上天给予了我比同龄人更丰富的经历。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我更是深怀感恩之情。在老年能看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为人生之大幸事。六十年大庆的盛况,使我深感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光荣和自豪。我怀着感恩之心,回忆起十年前曾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五十年大庆观礼的盛况。我深感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之伟大和来之不易。对当前的“科学发展观”与“建设和谐社会”等国策深怀敬意!真乃国之大幸!民之大幸也!
本人是从事自然科学的,因此,对于将“科学发展观”作为国策,更是感到由衷的钦佩!
本书的基本思路也是以科学发展的观点来分析宇宙、生命和人类的演化发展之规律。
在“文革”前,我只对理论物理和先进科技感兴趣。“文革”开始后,大学实际上停办了,没有什么正经的工作了。而我作为年轻的“小黑帮”得以和校领导、大教授等“大黑帮”一起被斗,一起改造,因而有了和他们交谈接触的机会。这使我对“社会科学”中的学问开了窍。1970年春下乡“插队落户”前,我有时间、有机会看了不少“社科”和“文科”方面的書,并经常向这些“反动学术权威”求教。这使我在“插队”到长白山原始森林中后,不但有了思考的时间环境,也打下了思考的基础。
我“插队”的地方自然环境实在太好了:农民兄弟为我一个人盖了一栋小房子,还有一亩地的院子。我的院子处于村子的边缘,几十米外就是有点名气的“二道白河”之上游,河水清澈,可以直接饮用。过了河就是真正的原始森林,冬季封冻后随时可以走过去。由于在我到达之前十年,那里还是没有人类居住的地方,所以当时原始森林尚未被破坏(可惜后来几乎被破坏光了)。
在这个远离尘世的美丽清静的地方,自由自在地生活了三年,使我有机会思考了许多哲理性的问题,并写下了几百页笔记。
1973年春,我接到东北师范大学回去工作的调令。别人一接到调令,赶紧回城上班,但是我却拖了半年之久。首先,我不敢把这几百页笔记带回去,因为万一被发现其中有“反革命言论”那可不得了!但我又舍不得毁掉这些思考的心得。于是,我把这些杂乱的笔记进行了整理,而把原始笔记毁掉(有些挺可惜的,比如进化论方面的)。另一原因是舍不得马上离开“上海知青”的女友(现在的夫人潘叶虹)。我非常感谢她,当时看得起我这个比她大15岁的“右派反革命”,而且顶住了很大的政治压力和我好。
当时按照“四人帮”的政策,我因为和“知青”谈恋爱而被隔离审查……
本手稿得以保留,今天能够出版,我也非常感谢夫人潘叶虹。是她在此后的近二十次搬迁中将这本手稿完好地保存了下来。那时的困难是当代年轻人无法想象的。比如,1973年我刚调回东北师范大学时,住在地下室,冬天时,门是被冰冻上的,每天都要用力弄开几次!1980年底我前去香港“定居”时,因为没有钱(家父将一切献给党,我去香港时只给了我五千港币),夫妇二人住6平方米,还要爬8层楼(无电梯),每天只供3小时水,还得让房东先用。而且在“港英”统治下,处处受到歧视。我在1978年改正错划后,即担任改革开放后第一届研究生指导教师,但当时香港不承认我的学历,认为我连当小学教师的资格都没有!所以只得“弃学经商”,是夫妇二人配合做(跑)国际贸易起家的。
我在1980年去香港前,写了一本《相对论导引》(1982年初吉林人民出版社第一版;2002年清华大学出版社重版)。我是以“浅出”方式写的,但内容还是包含了广义相对论的数学理论,当时除了译自国外的以外,可能这还是国内讲到广义相对论理论的第一本正式出版书籍。但我是怎么写成的呢?我儿子1980年2月出生,我和夫人借住姐夫的一个房间。我夫人在床上照顾儿子,我在旁边姐姐的钢琴上完成了这本《相对论导引》,因为没有桌子!也几乎没有参考书(所以该书后面没有参考书目)。幸亏姐夫、姐姐当外交官出国去了,我母亲给他们看房子,否则我连这个条件也没有!
我写这些是为了让阅读本书稿的新一代人了解一点老一代的事。现在回到本书稿。因为我是搞理论物理的,因此在思考哲学、美学等“社科”问题时,仍难免带有“数理思维”的痕迹。读者看起来可能会有点别扭,但为了保持1973年“文革”中手稿的原貌,我还是不作修改。
顺便说一句,本书附上部分手稿的原因是说明此手稿确实是1973年完成的原稿,未作修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份“历史资料”,并不针对当前社会的任何具体事物。稿纸因年久已经变黄,但在每一页的左下方仍可看清下列字样:“北京电车公司印刷厂出品七三·三”,说明原稿是笔者在1973年末调回东北师范大学工作前,用1973年3月出品的稿纸写成的。
本手稿得以出版,我首先要衷心感谢我的夫人潘叶虹。除了她36年来精心保存了这份手稿外,这次决定出版它也是夫人的提议。
同时要感谢额的老友,天才的画家、书法家、作家肖大风先生。
吉林人民出版社的邢万生总编,亲自为我审阅全稿,修正了一些标点和用字、用词,主要是修改了涉及外国的个别用词,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但是对这本36年前手稿的原貌、原意均无任何改变。我非常感谢邢总编亲自为我的手稿花费了宝贵的时间和智慧。
我同时要感谢关心本手稿出版的王亦军、波音和何钢军等各位同志。
2009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