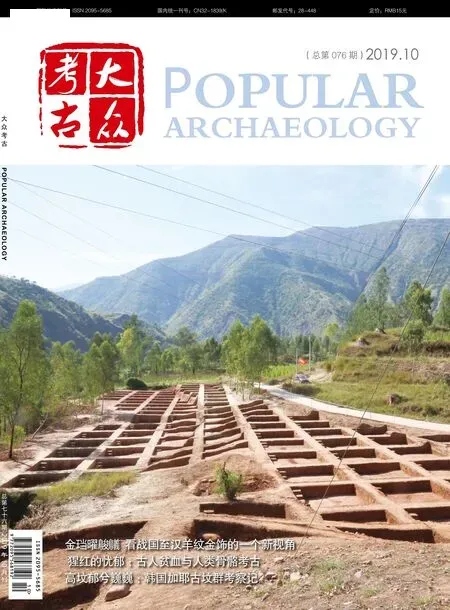山东背屏式造像圆形执物小考
文 图/张潇
山东地区出土的背屏式造像中,有一种特殊的造像形式,其背屏身光后雕刻有手持圆形执物的人像。对于这种圆形执物的性质,前人做出了可能为日、月二天神托举日月形象的推测。经过对比中国古代文物中所表现的日、月神形象,可能未必如此,比对古代印度佛教造像以及中国石窟造像中的乐器图像,此圆形执物可能为供养人持物或膜鸣乐器。
佛像背光是佛教诸尊像背后的光圈式装饰图案,一般出现在佛、菩萨的头部和身后,包括头光和身光。背光是佛“三十二相”中“长光一丈相”的体现,是佛本体的一部分,从不单独出现。背屏式造像则是以背屏的形式来表现佛与菩萨的背光,这种形式最早起源于印度,经由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扶南国(今柬埔寨)传到中国的南方。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山东青州、广饶、临朐、临淄等地多次出土成批的北朝背屏式造像。1996 年青州龙兴寺遗址又出土了以北朝为主的石造像400 余件,其中有大量的背屏式造像。在众多的背屏式造像中,有一种特殊的造像形式,其背屏身光后雕刻有手持圆形执物的人像。这种执物到底是什么,背后有何含义,相关造像组合是什么,都未有明确的结论。
考古实例
目前发现的这种特殊背屏式造像共有三种类型:背屏式三尊像、背屏式单尊像、背屏式三面造像碑。每种类型根据持圆形物人像的不同造像方式,又可分为两身左右对称和六身左右对称。
背屏式三尊像
全部为两身左右对称,共三例。

韩小华造像,碑高55 厘米,宽51 厘米,厚10 厘米


广饶阜城店造像,佛高120 厘米,佛光宽120 厘米

孝昌三年邑义造像,高202 厘米,宽115 厘米
北魏永安二年(529 年)韩小华造像出土于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现收藏于青州博物馆,为背屏式三尊像,石灰石质地。本尊为佛装,跣足立于覆莲座之上,高肉髻,佛头后有莲花。两胁侍皆为菩萨装,跣足立于覆莲座上,头冠已残,前额梳三圆形发饰。佛和菩萨的身后刻有统一的舟形火焰纹身光。身光后部雕两人像,手持圆形物体,左右对称。碑下部为长方形基座。基座左右刻“乐丑儿供养”“韩小花(华)供养”,各有一浅线刻的跪姿供养人。中为二尊护法狮子。
北魏广饶阜城店造像出土于山东广饶阜城店村,现收藏于山东省博物馆,为背屏式三尊像。本尊跣足立于覆莲座上,头部发髻已残。有同心圆式头光,最外圈为缠枝花叶纹,向内为多重阴刻线同心圆,最内圈佛头后有莲花。衣着细节与韩小华造像相似。右胁侍菩萨可辨认出宝缯垂肩。佛和菩萨的身后刻有舟形火焰纹身光,身光尖顶部、头光之上雕有一龙。身光两侧各刻有三尊飞天。身光后部雕两人像,手持圆形执物,左右对称。

图①广饶百册造像,通高276 厘米,宽95 厘米 图② 临淄西天寺造像 图③广饶皆公寺造像,通高254 厘米,宽138 厘米
北魏孝昌三年(527 年)邑义造像出土于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现收藏于青州博物馆,为背屏式三尊像。本尊跣足立于覆莲座上,头部已残,有同心圆式头光,同心圆最内部佛头后有莲花。双手已残。佛装细节以及胁侍菩萨造像均与韩小华造像相似。佛和菩萨的身后刻有舟形火焰纹身光,火焰纹内两侧各刻有三尊飞天。身光后部雕两人像,手持圆形执物,左右对称。
背屏式单尊像
根据持圆形执物人像的造像方式不同,又分为两种:两身左右对称,共有两例;六身左右对称,共有两例。
广饶百册造像征集于山东广饶李鹊镇大张庄村外,现收藏于东营市历史博物馆,为背屏式单尊像。整石呈碑形,身残高135 厘米。造像形式与韩小华造像相似。身后有舟形火焰纹身光,火焰纹内两侧各刻有三尊飞天。身光后部雕两人像,手持圆形执物,左右对称。
临淄西天寺造像残件出土于山东临淄西天寺,现收藏于临淄石刻馆,为背屏式单尊像。佛像跣足立于覆莲座上,头部已残,有同心圆式头光,最外圈为缠枝花叶纹,向内为多重同心圆,最内佛头后有莲花。身后有舟形身光,身光上部已残,火焰纹内左侧残存飞天两身。火焰纹内为兽衔莲花草叶纹。身光后左侧残存人像一身,推测应手持圆形执物。
广饶皆公寺造像出土于山东广饶南赵村,现收藏于东营市历史博物馆,为背屏式单尊像。佛像跣足立于覆莲座上,头部已残,有同心圆式头光,最外圈为缠枝花叶纹,向内为多重阴刻线同心圆,再向内为轮光,最内圈佛头后有莲花。双手已残。佛衣细节与韩小华造像相似。佛身后刻有舟形火焰纹身光,身光后两侧各雕人像三身,中间一人像手持圆形执物,左右对称。

广饶段家造像,残高140 厘米

背屏式三面造像碑,高159 厘米,宽77 厘米
广饶段家造像征集于山东广饶段家村,现收藏于东营市历史博物馆,为背屏式单尊像。整石呈长方形,上顶倾斜,通高221 厘米。碑自中部断裂,断面中心上下各有108 厘米榫眼。造像形式和细节与韩小华造像相似。佛身后刻有舟形火焰纹身光,火焰纹内两侧各刻有三尊飞天。身光后两侧各雕人像三身,中间一人像手持圆形执物,左右对称。

山东特殊背屏式造像统计

方相氏与羲和、常羲擎日月图
背屏式三面造像碑
背屏式三面造像碑仅见一例,出土地点不详,现藏于青州博物馆,为背屏式单尊三面造像碑。主尊佛装,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头部已残。有同心圆式头光,最外圈为缠枝花草纹,向内为多重同心圆,最中心浮雕二佛并坐。值得注意的是该头光并不在佛头的正后方,而是位于佛头之上。身后有舟形火焰纹身光,火焰纹内两侧各刻有四尊飞天。身光后部雕两人像,手持圆形执物,左右对称。基座与题铭不详。
日月天神说
对于出现在背屏式造像身光后的这种圆形执物,佛像出土时的发掘简报都对其有所关注,并进行了描述。王思礼先生最早注意到这一情况并进行了自己的阐释,但并未展开讨论。他称:“……在佛光上部边沿上雕有人物六,有的手持一圆形物,佛之周围刻火焰纹……”
《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清理简报》:“……背光略向前倾,使其与造像碑左右形成两层三角形的空间,此空间分雕日、月天神。二天神仅刻出头部,分刻左右手,手中分别执日、月……”将这种情况描述为日、月二天神手执日月,但没有阐释推测的依据。
后《东营市历史博物馆藏佛教石造像》中称“……上顶两角高浮雕日神、月神各一身,分别手擎日月圆盘……”,也采用了日、月二天神的描述方法,但也同样没有阐释推测的依据。可能是受到了前文的影响。
笔者看来,将这种圆形执物认定为日、月二神分别所执日月的形象,似乎值得商榷,其原因有三。

犍陀罗造像(四川省博物馆)
首先,日、月的表现方式。《淮南子·精神训》云:“日中有骏乌。”高诱注:“骏犹蹲也,谓三足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张衡《灵宪》云:“日者,阳精之宗,积而成乌,像乌而三趾。”现根据出土的古代陶器、画像石、画像砖、墓室壁画、马王堆帛画、铜镜等文物资料,日神所托举的太阳,其表现方式多为日中有鸟或三足乌形象。
《太平御览》卷四引《春秋纬演孔图》云:“蟾蜍,月精也。”《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张衡《灵宪》载:“嫦娥,羿妻也,窃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嫦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唐代徐坚《初学记》引《淮南子·览冥篇》亦云嫦娥:“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月神所托举的月亮形象中,一般有玉兔、蟾蜍和桂树等。
内无动植物形象日、月图像的确认,则需要其托举形象为人首蛇身。如《洛阳新发现一组汉代壁画砖》中有日、月形象,为蛇身的羲和和常羲所执。但就以上几例背屏佛像所保存下来的圆形执物来看,执物本身并无雕刻或纹饰,皆为素面浮雕,与中国传统的日、月天神所托举的日、月形象有所差异。
其次,日、月同时出现的形象也有三种表现形式。一,三足乌、蟾蜍等共同出现于同一圆形中。二,为上文中所提到的人首蛇身所托举。三,如莫高窟壁画中所出现的“指日月瑞像”。孙修身在《莫高窟佛教史迹画内容考释(七)》称:“……右臂高举向上,五指伸张,持一球状物,内绘金乌一个。此球状物即我国古代所说的太阳。左臂下垂,五指直伸向下,手掌下面,也有一个球状物,内画鲜花、野草诸物,当是表现我国古代所说的月亮。瑞像侧旁无榜题,而临近的栏框内,则有‘指日月像’的榜书。参照其他洞窟里所见的此种画面,考其内容,我们断定此瑞像为‘指日月像’。”
据考证,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所见这一瑞像图,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嫡子罗睺罗的画像。一手擎日,一手指月,表现了他生时的景状和其名的含义。显然背屏式造像中的圆形执物与这些表现方式的差异十分明显。
第三,就几例背屏造像中持圆形执物的人像的造型来看,并非全部为左右对称的两人。广饶皆公寺造像和段家造像中,此种形象为三人一组,左右对称共六人像,中间一人手执圆形执物。如果此人像确系为日、月天神,似乎不太可能出现三人成组的形象。另外执物人像的造型,其发式和帽子并非汉人所有,发式可能来源于西域。而广饶皆公寺造像中身光后左侧最下方一人像,所带尖顶帽为胡帽。如果圆形执物为日、月形象,执物的人像不大可能为西域或胡人形象。这似乎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日、月二天神的推测可能需要斟酌。

广饶阜城店造像细节

犍陀罗造像
推论新解
根据背屏式造像中所出现的这种圆形执物的形象、位置以及持此圆形执物的人像服饰、人物组合等,拟对此物的性质做出如下两种推断。
供养人执物
四川省博物馆藏犍陀罗造像是一件典型的犍陀罗佛教造像,左侧第一位供养人左手中正持有一件圆形执物,侧身向佛站立。对比背屏式佛像中的执圆形物人像与此供养人像,我们发现,虽然背屏式佛像中的执物人像只雕出上半身或头部,但两者具有一些惊人的相似性。首先,发饰和帽子相似,都戴有这种向上变窄的尖顶帽。其次,圆形执物的托举方式相似,都为单手侧身向上托举。
观察整个造像整体后发现,虽然造像左侧残损,但根据右侧供养人推测,左侧供养人应该也有三人,而手持圆形执物供养人恰好处在中间的位置,这似乎与背屏式佛像中三人一组对称、中间一人持圆形执物的形象具有相似性。
膜鸣乐器
与其他造像飞天位于身光之中,而持圆形执物的人像在身光外不同,广饶阜城店造像中持圆形执物的人像与伎乐飞天出现在同一雕刻空间里,都在身光的后部。这样的造像组合对判断此圆形执物的性质功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在犍陀罗造像上出现的这种圆形膜鸣乐器——鼓,与背屏式佛像中出现的圆形执物非常相似。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的第13 窟东壁上层天宫伎乐中,也出现了这种手鼓的形象,其制扁平,伎乐左手持鼓,右手击打。与伎乐飞天出现在同一造像空间里的圆形执物可能为手鼓,这就为背屏式佛像圆形执物也为鼓提供了推测的依据。
综上所述,山东背屏式造像中出现的圆形执物应为供养人手持物或膜鸣乐器——鼓,并非为传统意义上的日、月神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