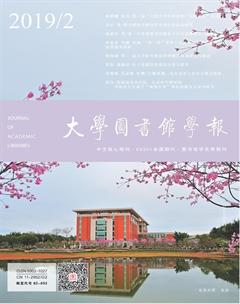考阅读之源,辨阅读之流
摘要《中国阅读通史》系统梳理上古至民國的阅读历史,勾勒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日常生活对阅读发展的影响。以阅读串联中国历史,挖掘源远流长的阅读文化,描述中华文化的知识形成及发展与阅读的亲密关系。知识来源于阅读、发展于阅读,可以说阅读在改变着世界,作为第一部多卷本的阅读通史,《中国阅读通史》的编撰有着多方面的开创性贡献。
关键词《中国阅读通史》阅读理论阅读制度阅读技术阅读生活
分类号G25
阅读堪称人类最重要的能力,文字、书籍出现以后,知识由言传身授转向学习语言文字,以书籍为对象的阅读发展起来,创造了灿烂的印刷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阅读推动了世界的发展。20世纪后半期电子文明的出现促使研究者反观印刷文明,触摸阅读的漫长历史。在阅读的转折点上,阅读史研究兴起了。与西方阅读史研究相比,中国的阅读史研究相对滞后,成果零星分散,蕴含的能量一直未能得到有效激发。当然,这是王余光主编的《中国阅读通史》出版之前的情况。中国阅读通史的编撰打破了这种尴尬局面,在阅读史研究的诸多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书写了中国阅读史研究的新篇章。
研究阅读需要关注谁阅读、怎么读、读什么这些发生性的问题,即人们如何通过阅读习得知识的问题。这极为复杂,很多研究者表达过研究的困惑。但也并非无迹可寻,法国社会史、思想史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探寻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过程中创立了“知识考古学”,对要探寻的问题进行考古式研究,考察具体知识得以形成的那些条件。福柯进入历史的方式是对话语(discourse)进行分析,研究经验、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挖掘社会表象背后的关联代码。如果把福柯的话语分析置换为阅读研究,便能生成一种实践性很强的“阅读考古学”,经由阅读而使知识得以传承的那些问题也就有了探寻的路径。如此一来,阅读史研究在实践中便是阅读的考古学研究,《中国阅读通史》的编撰即是对中国阅读历史的一次学术考古,尘封的阅读场景得以浮出历史地表,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呼应西方的阅读文明。
1探索阅读史研究的本土理论体系
法国年鉴学派的“新史学”以社会史、经济史、人口史等领域的卓越成果,主导着二十世纪上半期史学界的研究方向。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文化史崛起,带动史学界的“文化转向”。新文化史从文化的角度阐释历史,以“深描”和“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呈现出“微观历史”的面容。新文化史的对焦点是被大历史遮蔽的普通人,“他们能够而且已经改变了文化和历史的形成。”[1]这种实践史学也把目光转向历史中的阅读者,彼得·伯克(Peter Burke)认为:“在实践史学中,最受欢迎的一种形式是阅读史。”其重点在于“研究读者的角色,研究阅读习惯的变化,研究印刷的‘文化用途。”[2]代表人物有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阿尔维托·曼古埃尔(Alberto Manguel)、史蒂文·罗杰·费希尔(Steven Roger Fischer)、林·亨特(Lynn Hunt)等。隶属于新文化史的阅读史是年鉴学派“书籍史”研究在文化领域的拓展,即关注书籍与读者的关系。没有读者的参与,书籍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要建设一个研究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让与文本的形式相关的历史和阅读史、读者史以一种辩证关系结合起来。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一位读者总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这一共同体与他分享着与书写文化有关的同样的基本关系。”[3]在历史长河中探寻这样的关系通常有两条路径,一是运用年鉴学派的计量手段对阅读数据进行整理,得出宏观的或长时段的结论;一是对具体的阅读现象进行微观分析,探讨阅读对人生或时代的影响。二者各擅其长又各有其短,数据统计缺少丰富的细节,难以呈现动态的阅读场景;微观分析则是细节丰富,但难以从特殊概括出普遍的阅读风貌。基于此,探索既有阅读数据又有阅读生活的第三种述史方式,扬二者之长,避二者之短,才能真正从读者的角度把阅读的历史勾勒出来。
考阅读之源,辨阅读之流/杨敏Tens of Thousands of Rivers Return to Their Birthplaces
/Yang Min
考阅读之源,辨阅读之流/杨敏Tens of Thousands of Rivers Return to Their Birthplaces/Yang Min
王余光主编的《中国阅读通史》就选择了第三种述史方式。全编共计10卷,首卷为理论卷,依次为先秦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两宋卷、辽西夏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两册)、民国卷,最后为图录卷。署名编著者13位,约380万字,爬梳整理了上古至民国的阅读历程。其首要特色在于,综合年鉴学派书籍史研究和新文化史阅读史研究的长处,结合中国阅读发展的历史实际,探索了一套具有本土特色的阅读史理论。《中国阅读史·理论卷》及其周边著作《中国阅读文化史论》(王余光,2007)、《阅读史导论》(王龙,2017)共同呈现了中国阅读史的理论面貌。中国阅读史理论从八个方面研究历史上的阅读问题:阅读文化、文本变迁、社会环境与教育、社会意识与宗教、学术变迁、文人生活和阅读传统,这种述史理论没有照搬西方阅读史的理论模式,充分认识到中国阅读史的特殊性质,是根据阅读实际概括、提升出来的有效理论。
西方阅读史的理论建构主要在三个方面用力,一是阅读本体研究,借助文学接受理论突出阅读的主体地位,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等论证了作者、文本、读者、阅读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文本的意义只有在阅读中才能产生,个体阅读、群体阅读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样的理论把阅读带入了历史之中,所以罗伯特·达恩顿如是说:“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书的反应,是完全可以做历史性研究和理论性的总结的。”[4]二是阅读权力研究,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西方阅读史上拥有至高的权力,既推动了阅读的发展,又管控着大众的阅读行为。在某些历史时期,行政还会积极辅助宗教进行阅读管制,读什么书和怎么读书(朗读或默读)要由宗教权威来决定。三是阅读载体研究,西方书籍史的物质形态由羊皮、莎草发展到纸张经过漫长的时期,期间印刷出版技术的更新与其相伴随,到18世纪印刷工业来临,书价大幅下降,阅读由精英向大众普及,迎来平民阅读的时代。这些西方阅读史上重要的理论性问题至少后两者与中国的阅读历史有极大差异,即使是神圣阅读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以世俗化的面目呈现,而且从未超越居于主流的儒学阅读。另外,中国书籍载体从竹帛到纸张的变迁及其对阅读的影响走的也是另外一条道路,这充分说明建构中国阅读史理论的必要性。
西方阅读通史编撰常把西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国别性的阅读史则多为断代史。古里耶默·加瓦罗(Guglielmo Cavallo)和罗杰·夏蒂埃主编的《西方阅读史》(1999)、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的《阅读史》(1997)、史蒂文·罗杰·费希尔的《阅读的历史》(2003)等属于通史性质的著作,以介绍西方世界的阅读为主,顺带讲一下东方世界的阅读,选取重要事件铺陈长时段的阅读状况。艾伦(James Smith Allen)的《透过大众的眼睛:现代法国阅读史(1800——1940)》(1991)、沃尔夫(D. R. Woolf)的《英国现代早期阅读史》(2000)等属于国别断代阅读史,研究某个国家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阅读现象。二者比较一下,国别体阅读通史的编撰就成了紧要的事情。
把视线拉回中国阅读史的研究空间也能看到通史编撰的紧要。海外汉学研究中,何谷理(Robert E. Hegel)的《中华帝国晚期插图本小说的阅读》(1998)、虞莉(Yu Li)的《中华帝国晚期的阅读史:1000—1800》(2003),台湾学者潘光哲的《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1833—1898)》(2014)等,属于断代或专题阅读史研究,与内地学者的中国阅读史研究状况相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余光、徐雁、王龙、来新夏、曾祥芹、张怀涛、王波等图书馆界的学者和史学界、文学界的铁爱花、张仲民、赵普光等人,或涉足阅读理论,或就历史上某些阅读问题展开研究,或搜集整理阅读史料,也都可以看作是断代、专题研究。因此,王余光主编的《中国阅读通史》既是中国第一部阅读通史,同时也补足了西方编撰阅读史时极度简化中国阅读历史的缺憾,而且在整个世界阅读史研究领域,也贡献了极其完备的国别体阅读通史,对世界各国阅读通史的编撰具有实际的参考价值。
考虑到编撰第一部中国阅读通史,理论的奠基性和指导性不言而喻,其意图不仅仅在于一部书的编写,还指向更广阔的领域,如断代和专题阅读史研究、阅读文化的传承与推广、东西方阅读文化的交流等。就上文提到的八个板块来说,如果要作一个概括的话,就是一个从外到内的逻辑结构,仿佛如剥洋葱一般,层层推进,抵达核心的阅读本体。首先是时代的社会政治,然后是文化技术,最后是阅读的主流与支流(阶层、群体、个体),以及阅读理论的探讨。这种严谨的理论架构,正是阅读史学界一向缺失的。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理论的严谨当然是学术质量的保证,从知人论世的思路说,也是对中国传统学术理论的现代传承,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增强了理论活力。
2勾勒社会政治力量形塑阅读文化的过程
从抽象层面说,“阅读文化是建立在物质和社会基础上,受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制约而形成的阅读价值观念和阅读方式。”[5]制度、意识形态等社会政治力量对阅读文化的规训和塑造是阅读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决定了阅读文化核心密码的编制方式,决定了在具体的时代中,能产生和传承什么样的知识。《中国阅读通史》系统阐述了社会政治力量形塑阅读文化的全过程,清理出以儒学阅读为本、学而优则仕、勤学苦读、耕读传家的阅读文化传统,对辨析、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大有裨益。
中华文明史上,政治力量更迭频繁,民族政权此消彼长,先后出现过多种政治力量形成的政权组织形式,看似繁乱无章,其实有迹可循,这条线索就是阅读文化的串联。上古三代,文字阅读主要是王室贵族的事情,阅读(占卜、记事)直接服务于政治活动。周朝后期,大一统的政权逐渐解体,“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下移、官学没落、私学兴起,以及新的社会阅读群体——士阶层的兴起,书籍在社会中得到传播,同时有较多的人通过私学接触到书籍,书籍也由早期的王室独占逐渐向全社会扩散,由盟俯机构不断流入民间,阅读开始成为社会现象。”[6]在私学传播中,先秦儒家学派脱颖而出,此后不断强化的儒学主导了两千年的政治制度建构和阅读文化选择。
儒学崇尚礼乐和仁义,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和人性的自我修养。孔子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先秦典籍,成为后世读者基本的阅读书目。出于政治的需要,漢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官学,儒学阅读支撑了中国阅读文化的半壁江山。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长期处于分裂和动荡的状态,政治集团互相争斗,社会秩序失去有效控制,文化管控松懈,社会价值取向出现多元化,儒学与玄学、佛学、道学处于既抗争又融合的状态。即便如此,儒学仍为官学的正宗,教授“五经”(《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之学,发展儒学教育。魏明帝曾下诏曰:“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7]政治上的提倡保证了儒学阅读的主导地位。
隋唐首开科举取士,在制度史上是极为重要的举措。从“察举制”改为“科举制”,促进了阅读风气的社会化。科举以“九经”、“三史”等为必读书目,巩固了儒学的正统地位。“科举成为成千上万家庭从子弟童蒙修学开始就精心策划应对的一个社会活动,熟读规定的经史典籍自然就成为叩开科举仕进之门的隆重开端。”[8]这无疑培养了一个巨大的社会阅读群体。
经过五代十国半个世纪的割据分裂,赵匡胤重建统一中央政权,于是偃武修文,倡导文治。太祖下令修孔庙,制定尊孔崇儒国策。范仲淹作《上时相议制举书》,提出“夫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9]宋朝开国以后大兴学校,广开科举。“政府以科举来控制士人的阅读内容,并以此刺激、推动社会的阅读活动。所以,以科举为中心的阅读活动具有明显的政治和功利色彩。”[10]宋代科举对农家开放,带动了耕读传家、诗书继世文化思想的传播,这是阅读所带来的积极作用,成为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在宋朝的西部和北部,先后存在着辽、西夏、金、元不同的政权,这些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虽然建制各不相同,存在时间长短有异,生活方式各具特色,但在汉字阅读上都有相同的取向,在推广本族文字阅读的同时,极力引导本国人对汉字文籍的阅读,学习汉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王龙概括了各少数民族政权依靠政治力量推行阅读的特点,其中“(1)无论各民族自己创制了什么样的文字,儒学典籍始终是他们最主要的阅读内容。(2)无论有多少个民族进入中原,汉族读者始终是社会阅读的主体。(3)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典籍始终是统治民族的思想来源和文化基础。”[11]由此可见,儒学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后,汉人的经济、文化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明朝立国即着手恢复传统文化,尊孔崇儒,大兴理学。在思想文化领域官方推崇的理学与民间崇尚的心学双峰并峙,加上经济繁荣带来的通俗文化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大众的阅读兴趣,阅读的大众化渐成气候。明代书籍数量增多、内容世俗化、阅读走向大众,依据这些条件,《中国阅读通史》将明代的社会阅读定位成“阅读革命”。清朝立国后承袭明制,又强化了儒学的权威地位,清世祖在顺治十四年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圣祖在康熙二十三年祭祀曲阜孔庙时手书“万世师表”,高宗五次前往曲阜,曾谕旨:“国家崇儒重道,尊礼先师。朕躬诣阙里,释奠庙堂。式观车服礼器,用慰仰止之思。”[12]帝王的举止行为具有典范的意义,清朝也是最后一个把儒学作为政治资本的朝代。一方面儒学发展到顶峰随政治的昏暗逐渐衰落,一方面本土和西方的民主思想愈益焕发生命力,至1905年停止科举,失去政治庇护的儒学核心地位旁落,传统阅读开始了现代转型。这是又一个阅读的大变革时代,“这个阅读变革酝酿于晚清,成形于民国,是中国古典阅读范式的终结和现代阅读体系的开始。”[13]
由以上综述可知,历代王朝均尊儒学为官学,儒学阅读成为连接中国历史的一条红线。两千多年来,儒学不仅支撑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架构,还形塑了古人的价值伦理观念和人格修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而优则仕”等儒学阅读思想,是世界阅读史上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文化现象,积累下的丰富的阅读文化遗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3论析科技发展对阅读的深远影响
文字载体的变迁是阅读史上的重大转折,读者的多寡、阅读量的丰俭、读物的可选择性、文化的繁荣程度等人文现象其实都与科技的发展密切相关。《中国阅读通史》采用传统朴学的考据方法和西方新史学的计量方法,以事实和数据论析科学技术对阅读产生的革命性影响,全面统计了历史上与阅读相关的数据,这样的考证当得上是一部信史。筚路蓝缕之功,史心可鉴。
上古象形符号作为汉字的前身只能刻画在岩洞里面,符号既简单,载体又不可移动,只能供居住者直观阅读而不能有效传播。距今约4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文”(刻在陶器上的符号)初具汉字雏形,也具有了可移动性。之后的甲骨文由于载体的轻便,可以编串在一起,其可阅读性更强。参照《尚书》的描述,“惟殷先人,有典有册”[14],带有文字的甲骨便是中国最早的书籍了。与刻在陶器、青铜器(金文)、岩石(石刻)一类载体上的文字相比,对甲骨文的阅读不再是往观,而是可以携来了。笔者以为,从阅读革命的角度来说,这算是中华民族最早的技术性阅读革命,此后阅读载体的变迁,只是随着这个路子使得书籍越来越轻便。简册和帛书是第二次技术性阅读革命,其书写方式由刀具改为笔具,载体与书写工具共同发生了变革。王充《论衡》有言:“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15],《晏子春秋》有“著之于帛,申之以策”[16]的说法,简牍与帛书在春秋战国时期并用,据孔子的“韦编三绝”来说,他读的即是简册。简牍与甲骨相比是可以串联成规则的书册,便于书写,能够卷叠,可携带性强,而且是真正的书写,舍去了刀具。更轻便的是帛书,其质地轻薄柔软,书绘皆宜,展卷即读,合卷乃收,可随身携带,方便流转。以上几种书籍,共同的特点是制作成本高,产品数量少,只流通于上流社会。纸张的发明及技术上的改进是第三次技术性的阅读革命,105年,东汉蔡伦采用新原料改进造纸技术,使得书籍以抄写的方式得到传播。
秦火以后,汉代要做的一件大事是搜集整理散落的典籍,得益于书写材料的改进,汉代学术得到了空前发展,汉文知识体系也得以建立。刘向的《别录》、刘歆的《七略》奠定了最初的知识体系,从《七略》中我们了解到自有文字以来到汉代,人们都读了些什么书籍,产生了哪些专门性的知识。《七略》收录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为读者的阅读选择提供了依据,也使得阅读群体突破贵族官宦,增添了缙绅和部分平民。魏晋南北朝的造纸技术进一步提高,“活动帘床抄纸器”的发明降低了纸的生产成本,纸张的推广使用带来了书籍数量的增加。与前朝相比增量极为明显,汉代班固统计书籍有“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而曹魏官藏书籍已有“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南朝宋则统计有“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说明知识的传播速度加快,阅读量也增多了。
第三次技术性阅读革命是印刷术的发明使用,知识的传播由手写改进为印刷复制。唐代贞观年间雕版印刷出现,“印刷术的推广应用,使图书的生产社会化和产业化,图书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从而带动书籍编辑业务的进步、装帧样式的革新和图书广告的产生。”[17]唐代书籍的数量达到28569卷。书籍的诸多变化最终指向对读者的召唤,加上隋唐建立科举制,确立四部分类体系,士人的读书热情高涨,文化出现了繁荣。延续到宋代,雕版印刷术得到广泛应用,官刻、家刻、私刻形成出版界三足鼎立的局面,据估算两宋刻本当有数万部。宋代编撰了四部重要的书籍,《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为士人读书治学提供了便利,也显示了帝王好读书、兴文治的气象。宋代很多文献记载太宗赵匡义日读三卷《太平御览》,大臣以为太过劳神,太宗则说:“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不以为劳也。”[18]这是“开卷有益”的出典处,至今仍被当作劝读的经典话语。上行下效,阅读风气达至农家子弟,耕读传家的思想便在宋代普及开来。
宋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经元代王槙改为木活字使用,书籍印刷更为便捷,雕版、活字印刷在明清时期攀上古代书籍出版的顶峰,阅读的大众化时代随之到来。“据《明代版刻综录》所錄,明代至少有5257家出版单位。再根据其他材料估计,明代所刻印的书应在3万种以上。加上无数的手抄本,它们共同成为明代阅读活动存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条件。”[19]这股出版热潮在改朝换代之后很快接续上来,且出版的书籍多于前朝。清代印刷出版业有三件事情至关重要,一是编修《四库全书》,著录之书共计3457种,79070卷;存目之书6766种,93556卷。还衍生了一批目录学和考据学的书籍,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书成之后,乾隆有谕旨:“兹《四库全书》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20]二是自然科学类书籍首次达到出版高潮。中国古代重视人文知识的传播,自然科学一直未有长足的发展,清代算是补上了这一课。受西学东渐的影响,西方自然科学书籍得以在中国出版,同时也刺激了对中国自然科学书籍的整理,诸如天文学、数学、化学、物理学、医学、生物学、地理学、工艺及技术等自然科学领域书籍的出版,使得现代知识体系初具雏形,为民国时期知识的大转型奠定了基础。三是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可称为古代最后一次技术性阅读革命。进入19世纪,凸版铅印技术、平版石印和胶印技术、凹版雕刻铜版技术相继引入中国,新技术不仅能出版精美的图书,还能印刷大版面的杂志、报纸,印刷纸张开始进入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阅读随处、随时即可进行。
清王朝最后的一段时期,出版印刷业的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跨到民国以后书籍报刊的出版印刷真的可以说是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印刷出版的繁荣带来了知识体系的大转型,以科学为导向的现代知识体系建立起来,传统的四部之学被拆解,一种新式的、具有现代色彩的阅读范式形成。“这种新的阅读系统以大众阅读为核心,具有多元性的价值取向,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现代公共性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21]
科技改变了阅读,一部阅读史也是一部科技发展史。处在当下新一轮技术性阅读革命——电子阅读的时代,更能看清科学技术给阅读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这是一次颠覆性的技术性阅读革命,数字阅读快速渗透进人的日常生活,纸质阅读受到极大冲击。“这是读书人生活的一场真正的革命,不能不让人反思。对中国阅读史的研究,正是基于对现实的一种历史反思。”[22]
4还原历史长河中的读书生活场景
阅读史研究的本体是丰富多彩的阅读生活。中国是尊崇读书、热爱读书的多民族国家,如何更真切地还原历史场景,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中国阅读通史》在处理阅读生活时,采用与制度、科技分析使用的自上而下和计量统计不同的方法,以新文化史擅长的自下而上的方式,寻找动态性的阅读细节,串联出不同时代相同的阅读场景,描绘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阅读画面,理清了阅读文化的来龙去脉,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豪感和文化向心力。
中国古代阅读心理有功利和非功利之分,为求取功名而寒窗苦读有明确的外向性目标,为修持身心而徜徉书海有明确的内向性目标,无论哪一种,都反映了古代尚文崇古的文化心理。文在古汉语文化里有丰富的内涵,既代表了德行、智慧,文雅和美善的风范,又是良好社会秩序的外化。崇古从孔子时代就已开始,他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3]这样典范性的话语,后世研习儒学者,均以持守尧舜禹、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自居,因而得到人们的景仰。
上古时期王公贵族拥有阅读权力,其子弟有资格接受教育,《白虎通》《大戴礼记》均记述儿童八岁入学读书,学习六艺等知识。刘向《列女传》载有上古阅读事迹,可参阅。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兴起,阅读群体开始下延,《庄子》中说:“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24]读书明(道)理的思想形成于先秦,孔子、孟子、荀子等多次阐述过这样的道理,孔子有“士志于道”“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的说法,“儒家士人的道德行为取向包含了两个方面:就家庭而言,个体行为须符合孝、悌、慈、友的要求;对国家而言,个体行为必须体现仁、义、礼、智、信、忠的要求。”[25]概括起来就是“内圣外王”之道,为古人追求的理想境界。
汉代书籍增多,阅读者亦众。《汉书》记载淮南王刘安的事迹,“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數千人,…时武帝方好艺文,以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26]描绘了刘安组织士人读书、编书的生活场景。东汉时,光武帝麾下不仅文臣,而且武将也多研习儒术,“如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有子十三人,使各守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为后世法。”[27]读书习艺,明理修身,由此可见汉代家庭生活与阅读的亲密关系。
魏晋风起云涌,生活跌宕,清谈超越之风大兴,一时谈玄论道、率性而为者被目为名士,且吹进内帷,“谢弈女道韫,王凝之妻也。凝之弟献之尝与宾客谈议辞理,将屈,道韫遣婢白献之曰:‘欲为小郎解围。乃以青绫步障自蔽,申献之前义,客不能屈。”[28]这一日常小景说明谢道韫不仅有咏絮之才,还有明辨之智,均是从阅读中学习积累的才华。
隋唐首开科举,促成了诗书教子的文化传统。甘州张掖赵孟武母亲劝其弃猎从学,后中进士。济南林氏丈夫早逝,子侄七人均在林氏劝导下勤学成名[29]。宋代科举向农家开放,使得诗书教子的生活进入农家。“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灯下苦读的少年身旁,常常有母亲的陪伴、督促。日常生活中的阅读,并不仅仅是寒窗苦读,也有温馨愉悦的场景。宋代赵明诚、李清照夫唱妇随的读书、藏书、编书生活,已为阅读史上的佳话,是把读书融入生活的典范。夫妇二人皆出身书香官宦之家,自幼浸淫于书香墨海,皆文才风流。《金石录后序》记载他们在青州归来堂安贫乐道的雅致生活,“每获一书,即共同勘校,整集签题。…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30]能做到阅读生活化的人,其生活必获得艺术化的提升,阅读与生活浑然无间,杨万里的《读书》一诗亦呈现如此的意趣:“读书不厌勤,勤甚倦且昏。不如卷书坐,人书两相忘。兴来忽开卷,径到百圣源。说悟本无悟,谈玄初未玄。当其会心处,只有一欣然。此乐谁为者,非我亦非天。自笑终未是,拨书枕头眠。”[31]
古人重视读书,在家族观念上强调世代相传,是中国古代家训的特色。历史上不乏世代相传的书香世家,不仅男子读书,女性自幼也接受教育,到明清两朝,一家女性皆读书的所在多有。叶绍袁之妻沈宜修和三位女儿纨纨、蕙绸、小鸾均负诗名,常常诗书唱和。山阴祁氏家族世代书香,祁彪佳夫人商景兰,儿媳张德惠、朱德蓉,女儿祁德渊、祁德茞、祁德琼亦读书好学,工诗能文。这就是典型的书香门第,文化传承源远流长。
传统中国以农业为本,农耕文明获得长足发展,事农与读书合流是必然的事情。上古即有舜耕于历山,伊尹耕于有莘的事迹,三国时期诸葛亮曾“躬耕于南阳”,晋陶渊明《读山海经》有“既耕亦已种,时还我读书”的自述,耕读合一在宋代扩散开来,明清时期发扬光大。“耕读不仅是中国古代读书人主要的生活方式,而且体现着他们对人生价值的理解,对生命意义的体悟,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对读书与生活的实践,对学术文化的传承。因此,耕读就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的重要特点。所谓‘带经而锄亦为美丽的田园风景平添了一道亮丽的色彩。”[32]晴耕雨读、昼耕夜读也是平民大众的生活方式,弭氏教导儿子谢惟馨说:“吾家赖以为生者,不过读与耕耳。君于读书之暇,何不于田省耕,劝戒勤惰,以望有秋,以办两税之需,以赡一家之养。”[33]由于历史的原因,耕读传家的优秀传统已然难以为继,20世纪90年代物理学家杨振宁回忆童年生活,记忆犹新的是春节贴的春联:忠厚传家,诗书继世。环顾当今,已经没有人在门楹上贴这样的对联了。楹联的对照,显示了当前传承阅读文化、推广全民阅读的重要性。
司马迁《报任安书》说,人有郁结之处,欲以疏通,故述往事,思来者。《中国阅读通史》可谓异曲同工,“21世纪以来。电子设备和网络普及,阅读,特别是传统意义上的阅读等相关问题备受关注。我们应该怎样认识阅读和阅读文化的含义、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如何弘扬阅读文化……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阅读文化与阅读史研究就是对阅读传统的总结和对现实阅读状况的反思,对于我们继承优良的阅读传统,推广社会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提升整个社会的文化品质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亦将有所裨益。”[34]所谓知古才能鉴今,通观全书,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
《中国阅读通史》从起意编撰到出版发行历时13年,是“第一部以中国阅读史为研究对象的多卷本通史类著作”[35]。唯其是第一部,在取得诸多开创性成就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些不足,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第一,文体、风格不尽统一,各卷内容轻重有别。第二,史料选择缺少章法,有的堆积过多,有的稀少奇缺。第三,阅读场景的还原有所欠缺,阅读传统的勾勒不甚清晰、连贯性不强。这当然是瑕不掩瑜,但可以提醒我们在史实、史鉴的把握和叙述上注意统一的文体风格,在尽可能还原历史场景的前提下选择有机的材料,描画动态的历史场景,勾勒生生不息的阅读文化传统。
新世纪以来,阅读推广研究如火如荼,阅读史研究则不温不火,热与冷不相调和。时下阅读推广研究几乎没有阅读史的学术基础,产出的学术成果大多为推广案例的收集和整理,偏于阅读推广方法的介绍。《中国阅读通史》体现的学术精神、提供的学术方法,对于扭转阅读史和阅读推广研究的轻飘与散乱,确实大有助益,相信会带动学术研究的良好风气,产生更多的厚重之作。
参考文献
1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非凡的小人物:反抗、造反及爵士乐[M].王翔,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2.
2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M].蔡玉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70.
3罗杰·夏蒂埃.过去的表象:罗杰·夏蒂埃访谈录.沈坚,译.//李宏图.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134.
4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M].萧知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32.
5王余光,王琴.中国阅读通史·理论卷[M]. 王余光,主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8.
6徐林祥,张立兵,张积.中国阅读通史·先秦秦汉卷[M]. 王余光,主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110-111.
7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94.
8黄镇伟.中国阅读通史·隋唐五代两宋卷[M]. 王余光,主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7.
9李勇先,王蓉贵.范仲淹全集上册[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237.
10同8:216.
11王龙.中国阅读通史·辽西夏金元卷[M]. 王余光,主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7-8.
12索尔纳等.钦定学政全书校注[M]. 霍有明,郭海文,校注.武漢: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238.
13许欢.中国阅读通史·民国卷[M]. 王余光,主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1.
14李学勤.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26.
15王充.论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194.
16晏子春秋.//二十二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581.
17同8:123.
18同8:239.
19王龙.中国阅读通史·明代卷[M]. 王余光,主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184.
20何官峰.中国阅读通史·清代卷(上)[M]. 王余光,主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41.
21同13:22.
22同5:1.
23孔子.论语[M].长沙:岳麓书社,2000:22.
24庄子.//二十二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84.
25同6:128.
26汉书·卷四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62:2145.
27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M].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90.
28同20:212.
29同8:96.
30李清照.李清照集校注[M].王仲闻,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78.
31同8:343.
32同19:320.
33同19322.
34同5:6.
35王波.不忘本来,文明互鉴:我看《中国阅读通史》的学术价值[N].图书馆报,2018-04-02[3].
作者单位:阜阳师范学院图书馆,阜阳,236037
收稿日期:2018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