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已经消亡,机器人成为唯一的幸存者
蒯乐昊

Prada荣宅 GOSHKA MACUGA “我曾为何物?”展览现场 图/Alessandro W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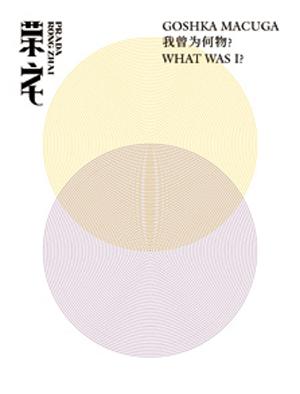
“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面临全球退化的风险。”
“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站在过去,凝望着镜子里消逝的未来。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站在我们创造的大屠杀中,但我们再也看不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人类已经消亡,上海荣宅的主人,一位机器人正在对虚空发表演说,他在循环背诵由人类历史上众多重要演讲摘录构成的独白,这些独白曾经作为预言而存在,而现在早已经成为结语。
这座记载着昔日荣光的府邸,闹中取静,位于上海静安区陕西北路186号,是清末民初中国富商、“面粉大王”荣宗敬的家宅。现在PRADA接手了这里,在经过六年细密的整理修葺之后,作为PRADA艺术基金会的展览场地对外开放。“在我们接手这座房子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间不易被发现的内室,里面甚至还留有一个当年的保险箱。”谨慎起见,他们在摄像机的公证之下打开了保险箱——发现里面秘藏的并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一沓当年上海滩的旧报纸。
这段小典故几乎可以视作荣宅这次新宅“我曾为何物”(What Was I)的现实版预演:当时间流逝,人物流散,保留下来的是文字和文明的碎片。
Goshka Macuga是这次展览的主角,这位1967年生于波兰华沙的女性艺术家目前生活在伦敦,正如博尔赫斯被认为是“作家中的作家”,Goshka也被称为“艺术家中的艺术家”,这是因为她的创作长期以来总是呈现出某种学术的纯粹性,在艺术家本人身上,似乎也可以看到这种本能的诚实。
Goshka Macuga的大部分作品都在关注开拓性课题,比如时间、起点与终点、坍塌与复兴。What Was I似乎是那三个著名的哲学终极问题的变体,这也是玛丽·雪莱小说《弗兰肯斯坦》里的追问。在Goshka的构思中,后世界末日的人类纪时代,科学发展到了崩溃边缘,技术成果成了毫无价值的工具。最后一个被遗弃的机器人,作为“类人”的存在,居住在荣宅之中,不断自言自语,对着虚空抛出自己的语言和思想,试图交流。
“我有一种重要的灵感来源,它是一个数学上的概念——奇点。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它意味着如果事情发展的路径一直延续,会达到一个爆发点,这个点是难以预计的。通俗点儿说,当某一个人工智能的程度已经超过人类的时候,可能就是奇点到来的时候,人类似乎就没有必要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上了。”Goshka的重点并非勾画人类文明的末日,她更想问的是,我们能否应对这一可能的未来,以及,我们是否还具备重建世界的能力?
而在这种如迷宫一般的旧式府邸之中,每个房间都布置着人类文明的遗留物,那是Goshka从PRADA基金会的收藏中选择出来的,从1950年到1970年之间的作品——来自德国零派、意大利抽象主义的艺术家在这里错落有致,成为这些房间里静默的存在。

Vincenzo AgnettiOltre il linguaggio, 19702 emulsified canvasesCourtesy Fondazione Prada

Goshka MacugaDiscrete Model No 006, 2018paper collageCollection of the Artist, London

Salvatore ScarpittaCairn Sled, 1974bandages, wood, mixed media图/ Roberto MarossiCourtesy Fondazione Prada
在整场展览中,Goshka的角色,既是艺术家,也是策展人,她选择这些作品,是因为这些作品中都流露出相似的特性:一种面向未来的实验性,更加抽象,更加不受限于时间的艺术形式,它们是不诉诸文字的语言,似乎更容易被未来的观众解读。
在这所安静的房子里,机器人回响着的演说是唯一的声音,Goshka将这件作品起名为《致吃掉书卷之人子》,这个典故来自《旧约》里的“以西结书”。以西结是耶路撒冷的祭司,后来也成为流亡途中的预言者。机器人的外观呼应了这种宗教感。
“当我想要做这个机器人的时候,我花了很长时间思考如何去呈现它的样貌,我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确定它到底应该是男是女,或者要不要用一个历史上已有人物来作为原型去塑造这个机器人。”任何一种设定,都会被认为带有深意,但是现在,这个机器人是白人,但样貌中带有以色列或阿拉伯人的特征。Goshka在日本完成了机器人的制作,日本精湛的技术赋予了他不可思议的真实感:他不但可以自如地转动头颈、手臂,连皮肤和毛发的触感也跟真人别无二致,他的手指灵活地作出各種手势,他甚至可以眼波流转,当他发表演说的时候,那清澈的眸子会突然注目过来,与你对视,眼睛背后似有灵魂,让你身上轻轻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Goshka Macuga 图/Francesco Pizzo
“最后我用了我身边一个朋友的容貌作为原型制作了这个机器人,我把这位朋友视作了我的缪斯。”她没有给机器人穿上衣服,这样可以裸露出那些带有电子配件的关节部位,如果用衣服遮挡掉这些部分,你会以为面前正在说话的就是一个真人。裸露带来了另一个问题:虽然机器人是按照人类的外貌设计的,体格也仿佛是男性的体格,但他却没有更多的性征了。他正对着观众的坐姿,让他的性带恰好面向正前方,Goshka坦荡地做出了这一切:那里空无一物,吃掉书卷之人子没有性别。
“虽然我给他做了胡子,这是为了让他看起来像一个尊贵的、睿智的人,在不同的文化里面,胡子都是一个容易被解读的身份象征,但是我并没有赋予他明确的性别。我不了解中国的性别文化,但我自己居住在伦敦,你知道,在那里,流动性别乃至无性别都是接受度非常高的文化,所以我有这个性别开放度。在未来,我们的性别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的性别会怎么进化?这些确实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啊。”长得像纯情女生的Goshka穿了一套男式的黑西装,一双手粗大得像个男人,指甲修剪得很秃,她因为这个话题笑了起来,笑得相当雌雄同体。
所有的这些尝试,都让这场展览变得像科幻、像哲学、像寓言和神话,当你从一个房间游荡到另一个房间,一种幽闭而循环的幻觉渐渐盘踞你的脑海。出口处的荧光字母What Was I 发出幽幽的冷光,语法里确凿无疑的过去时态,好像在提醒你:
未来已经发生。
编辑 杨静茹 rwzkhouchuang@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