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导演徐童人活一口气
徐琳玲 张玮钰 唐慧敏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在上海一家不起眼的书店兼咖啡馆里,一场小范围的内部放映活动正在进行中。一楼早已满席,楼梯上、阁楼层,挤挤挨挨坐着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影迷。
当天放映的,是纪录片导演徐童的两部新作——《赤脚医生》和《两把铁锹》。
片尾曲结束,徐童走上台前。他戴着一顶牛仔帽,看上去放松、健谈,讲起对摄影器材的摸索、拍摄技巧、剪辑手法、配乐心得滔滔不绝,恨不得一口气把毕生经验都倾囊而出。“想让年轻人们少走一些弯路。”他自个打趣说,“年纪大了,一开心就爱唠叨。”
十年里,这位60后导演把镜头对准生活在城市边缘的“游民”——按摩女、小偷、算命术士、流浪艺人、乞丐、孤独老人这些野草般的存在——也用浓墨呈现出一个鲜活、生猛的“底层江湖”。
他拍摄的“游民”系列——《麦收》《算命》《老唐头》《四哥》《挖眼睛》,摘得过国内外电影节多个纪实类奖项。有“中国第一编剧”美誉的芦苇也是他的粉丝,称赞他的作品“具有史诗风格”。
十年的纪录片生涯,在这条北方糙汉身上留下了斑驳的风霜。如同《麦收》里耕耘的农夫,他如今也在等待麦子黄了的季节。
“赤脚医生菩萨心”
纪录片《赤脚医生》是徐童第一部镜头不对准底层游民的作品。
片中主角孙立哲曾是中国最有名的医生,“知青偶像”,在特殊的年代一度被推向暴风眼的中央。
1951生的孙立哲来自北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父亲是清华大学教授。1968年,17岁的孙立哲投身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大潮。
在延川县关家庄插队时,他吃惊于当地缺医少药的现状,于是跟好友史铁生学医,开始为老乡们行医看病。在土窑洞里,这个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北京知青进行了三千台手术,奇迹般无一失手,成了当地百姓心目中的“活菩萨”。
他的事迹被层层上报,后和邢燕子等五人被定为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典型,并成为当时“赤脚医生”路线所树立的一面旗帜,一时“红得发紫”。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孙立哲被审查,后又被平反、释放。不久,他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辗转定居于美国。
纪录片一开头,就是孙立哲回国、回陕北“探亲”的场景。听闻他回来的消息,延川县老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迎接这位三十年前的“救命大恩人”,隆重得如同庆祝当地庙会。他们扭起了大秧歌,敲起腰鼓,吹着唢呐,用陕北的信天游颂扬这位“菩萨医生”当年治病救人的事迹。
镜头跟随着孙立哲坐火车、回乡、走访故人的脚步,采访了他青少年时的同学、朋友,一同在陕北插队的知青伙伴,被他從“生死线”上抢救过来的延川老乡们,短暂交往又一同被审查的昔日女友,以及当年响应国家政策、带头做结扎手术的村干部。
在墨西哥题材电影配曲《弗里达》的激烈变奏声中,孙立哲回乡探亲之行、片中人物的口述回忆、历史资料片还原,三四条时间线交错并进,再现了一个“知青偶像”的青春生命史——他的青春萌动,他的“菩萨心肠”,给老乡们治病、做手术时发生的各种幽默的段子,如何被卷入政治、被利用又被吞没……
在激烈的戏剧冲突和华丽的音乐动效中,《赤脚医生》呈现出一幅历史的复杂面相,充满着各种吊诡、巧合、反转,以及阴差阳错、啼笑皆非的故事:
人道主义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年代里的“错位”;青年男女之间谈情说爱如何上纲上线为“政治问题”;对“赤脚医生”制度的反思、对“一刀切”式政策执行的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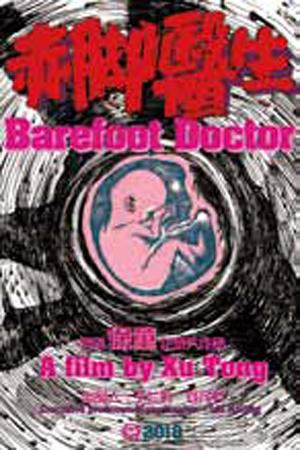
相比过往的“游民”小叙事,徐童承认《赤脚医生》是他一个更有企图心的作品。他有一种特别的迫切感——要用纪录片把这段历史记录、保存下来。
“我希望,通过这个片子,让人们特别是年轻人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人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回关家庄探亲时,孙立哲无论走到哪里,都被老乡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着。除了叙旧,有许多人是来找这位当年闻名乡里的“菩萨医生”看病的。镜头里,一位老妇抱着生病的小孙儿在人群中挤了一整天,怎么都凑不到孙立哲面前。
徐童一直都很认同欧洲资深电影人、曾执掌柏林电影节主席之职长达18年的科斯利克(Dieter Kosslick)推崇的一句话:“个人的,即政治的。”这也贯穿了他拍纪录片的始终。
“我相信记录下的个体经验,是对社会最有力的检验,它彰显了一个社会对个体生命尊重的程度。而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的遭遇可能被忽视,可能被遗忘,甚至有可能被篡改,但一旦被记录下来,那是不可磨灭的。这就是纪录片的意义所在。”
“没有乐趣,人就不活了么?你这话,太无情”
徐童出身于北京一个导演家庭。
他的父亲徐真,是新中国第一代科教片编剧、导演中的佼佼者,专长于动物题材的纪录片,曾多次获得国内外电影节重要奖项,代表作《灰喜鹊》《鸽》。在徐童的童年记忆里,父亲常年扑在秦岭山区、原始森林里拍片,一走就是一两年。“每次走前人干干净净的,等回来时就是胡子拉碴的,活像个野人。”
小男孩都崇拜父亲,徐童从小就模仿着父亲的一举一动,摸过他从电影厂带回来的各种镜头、胶片、摄影器材。那时,他拿着父亲的海鸥相机学拍照,跟着学洗胶卷、放印照片,是学校里有名的摄影小记者。因着家庭熏陶,1983年,徐童考进了北京广播学院(简称“广院”)电视系新闻摄影专业。
1980年代,国门刚刚打开,来自世界各地的哲学、文学、艺术和各种人文主义思想一股脑儿地涌入,青年人中兴起一波跟着一波的“读书热”、“思想热”。
“那时候,我们都流行读大部头的经典,读尼采、福柯、萨特的哲学,小说就是读《百年孤独》这些来自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一直到卡夫卡,从古典主义到现代派这150年左右的文学经典。”
他对世界、对周遭人事秉持的态度和价值,也在那个时代定下了基调——“就是那些最硬核的东西,关于人道主义,社会公正,以及自由、平等、博爱、法治这些关键词,深入骨髓。”
在崇尚文学、艺术的年代,这个年轻人对未来有一个清晰又模糊的志向——“一定要做一个艺术家。”
当时,他是系里的高材生,专业课拔尖,常跑在外头拍片子。临近毕业分配,北京电视台到广院招人,挑中了三个,他是其中之一。
毕业前夕,一封匿名举报信寄到了教导处,揭发了几年前的一桩代考事件。徐童和同专业的一位师弟双双受处分,代价是不予毕业。
对一个刚刚20岁出头、未经历世事的年轻人来说,这不亚于一场“灭顶之灾”。像南美丛林里一只蝴蝶偶尔扇动了翅膀,这桩小事一步接着一步地改变了徐童的人生轨迹。他默然接受了惩罚,并第一次感受到人性的复杂:“即使看上去很单纯的同学,人心有时也是不可测的。”
和他一同受处分的师弟叫李明。1990年代创办了后来名声大噪的小马奔腾广告公司,并涉足影视投资、制作、发行,一度是国内最有实力的影视公司。2014年,李明盛年之际突然离世,留下旷日持久的债务和公司控制权纠纷。

年幼的徐童和父亲徐真

1985年,在广院读书期间的徐童
“情义,情种,情怀”是徐童对这位师弟的评价。这三个词,也是他自己的写照,贯穿了他处世、为人和做艺术的道路。
1992年开始加速的市场经济,给从体制里脱离出来的人留下了生存的空间。为了谋生,徐童搞过印刷,办过广告公司,写写、画画、做设计,不时帮在电视台工作的大学同学拍个片子。他成了腰上最早别着BP机的人之一,有了自己的房子,在生意上赚过,也血本无归过,一路兜兜转转,起起伏伏。
为了省钱,徐童一直租住在北京东郊的城乡结合地带,邻居、街坊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乞丐、小偷、妓女、流氓。他结识了许多人,和一些人成了朋友,一起喝酒、聊天,也听了很多故事。那段忙于生计的日子,他保持着做笔记的习惯,“因为怕自己把这些故事淡忘了。”
2007年左右,刚迈入40岁的徐童正处于人生的一段低谷。忽然间,那个一直被按捺着的理想越来越强烈地涌动着。
“为什么一定要做艺术家呢?因为80年代种下的那种见地太强烈、太深入骨髓了。你除了要表达自己之外,还有一种焦虑,包括所有历史上留下的作品都给出一个这样的激励——人要不枉活此生,你要把来过一遭的痕迹留下,也就是你应当把对社会周遭、对人的这种所谓的感悟、感觉诉说出来。”
他几乎一气呵成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珍宝岛》。这是一部非虚构基础上的虚构作品,以一名警察为主角,“张冠李戴”地串联他在近二十年里见过的、听说过的许多人和故事。
2013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珍宝岛》。北京一家影视公司买下了小说的影视版权,徐童和芦苇合作担任编剧,芦苇完成剧本的第一稿,阿城做指導,最终在他手中完成了终稿。目前,正在走后期流程。“相信会是一部在院线上映的作品。”这位一直坚守在纪录片领域的导演说。
小说和文字,远远承载不了迫切需要找到出口的表达欲。他干起了“老本行”,用一台家用级小摄像机开始拍纪录片。这是他当时唯一能摸得着的机子,“当时想着赶紧拍,上战场就顾不上挑拣枪了。”
那时,徐童住在北京东郊的高西店,每次外出或去农贸市场都要经过一条街,街上开着几家洗头按摩小店。来来回回走得多了,他和按摩店小妹们混了个脸熟,其中一个叫苗苗,20岁。“第一眼看到苗苗,就觉得她很特别,爽朗、天真,完全不像做这一行的。”
在和苗苗的攀谈中,徐童得知她的老家在河北农村,一个有着大片大片麦田的农业区。这个意象吸引了对乡土有浪漫情结的徐童。6月麦子黄了,他跟着苗苗回了老家,见到了她的家人:患重病的父亲趴在炕上输液,母亲出门赶集,弟弟年幼,已出嫁的姐姐也自顾不暇。在外打拼的苗苗,是这个家庭唯一的“顶梁柱”。
“这是一个很辛苦的女孩,为了养活一家人一直在奔波,这种奔波是以出卖自己的身体为代价的。”徐童回忆说,“我那时就想一定要把苗苗的故事拍出来。”
连着几个月,他每天都在苗苗所在的按摩房里“蹲点”,只要不影响她的工作,就在一旁候着。他拍下了苗苗和小姐妹们的闲聊:骂老板贪财无情,数落讨厌的客人……他跟着她们去KTV唱歌、找乐子,谈恋爱。
和《珍宝岛》一样,《麦收》的拍摄和后期完成得非常顺利。2009年,徐童又认识了在燕郊算命的厉百程。厉百程双腿残疾,幼年父母双亡,被兄长虐待,很早就离家流浪。每天摆完摊后,他回到破败的出租屋,照料着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石珍珠,这是他的智障媳妇。两个孤苦伶仃的人相依为命。寒冬来临,他带着石珍珠从燕郊回到老家,也等待来年的机会。
《算命》采取了中国传统小说章回体的叙事结构,镜头跟着历百程从燕郊到老家清龙县,再到石珍珠老家,记录下小人物在不同时空里颠沛流离的人生,以及其中的人情世故。
“残酷又温情。”——一位影迷如此形容徐童的作品。
观看徐童的作品,让人一边为这些底层小人物的命运感到难受、悲伤,一边又感慨于生命的生猛与顽强。当你刚刚被片中流露出来的片刻温情感动着,措不及防中,又目瞪口呆于导演猛地撕开他们的另一面——那些不那么光彩、甚至有点不堪、却压抑不住的灰暗和人性欲望。
这些镜头记录下的真实,会让在顺境中长大、习惯了主流社会教养的年轻人们感到眩晕和失语。

《赤脚医生》放映中,有几分钟,好多女观众低下头或别过头去,也包括我。四五年前第一次看“游民三部曲”时,我和朋友中途几次低下头,同时又为自己感到羞愧——觉得这种躲避,是对那些镜头里的人物的一种不尊重。
在现场,一家书店的老板有点激动地谈起自己的感受。“我们可能要比他们幸运一些,没有生活在他们那种处境下,但是那种情感、感受,在某一瞬间都很相似。”
有段时间,他逢朋友就安利徐童的“游民三部曲”,因为相信“多看这样的作品,会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一些的人”。
3月底的上海,我和徐童、唐小雁一同行走在老法租界的法国梧桐下。路上,我提到每次看到他的片子,都有“一种世界观被摇晃”的失重感,需要花上大半天才能平复被搅动的心绪。
这让徐童听了很高兴,“这就是文学和艺术的意义和魅力所在——让一个人脱离他有限的、狭窄的生活轨道,去感知、理解甚至去活一次他人的人生。”
十年跟拍底层游民,也逼着徐童反思自己生命中的“轻”与“重”,思考“活着”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拍《算命》时,他看到大冬天夜宿街头的乞丐,问出了一个知识分子气十足的问题:活得这么辛苦、这么没有乐趣,干嘛还活着呢?
“没乐趣就不活了么。你这话,太无情!”厉百程第一次朝徐童发了一通脾气。
“活着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不光是爱情这些东西赋予的。”经历了前半生的起起伏伏,徐童曾说是苗苗、厉百程这些人救了他,把他从灰暗和恐惧中拉了出来。
这些年,他甚至有了一点点“自虐”倾向——特别愿意去体会人在困境和逆境里的那种分量感,“因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和命运抗争的那一口气。”
“零”和距离
看过徐童作品的人,都会惊诧于他和被拍摄对象之间近乎为零的距离。
《算命》中,摄影机的镜头从上到下俯拍,几乎贴着唐小雁的头,近距离地拍下她用针穿红绳扎肚皮、以求来年转运的举动,看得人肉痛起来;《老唐头》里,家庭成员们正为家事吵得不可开交,忽然大姐扭过头来,“徐童,你来给我们评评理”,仿佛镜头完全不存在。
徐童说自己很认同北京电影学院的老教授、有“中国纪录片之父”之称的司徒兆敦说的一句话,“所谓纪录片,就是陪一个人过一段日子。”
这种长时间的相陪、相处,甚至吃、住在一起,使得他和被拍摄者成为真正的朋友,是那种带着江湖情义色彩、必要时可以两肋插刀的。
拍《算命》时,徐童认识了常来找厉百程算感情运的按摩店老板娘唐小雁。这是个16岁就离开家乡出来闯荡的东北女子,经历坎坷,性格凌厉泼辣。她找厉百程讨教破解“孤单命”的办法,一转身又以过来人姿态告诫手下的小妹——“男人是什么东西呀?”
在被仇家举报后,“干女儿”供出了她的名字,唐小雁进了拘留所。接到唐小雁托人打来的求助电话后,人在云南的徐童立刻赶回北京,因为手头紧,他抵押了自家的车凑足了7万块罚金,把她“捞”了出来。当时,两人相识仅两个月。
从拘留所出来后,唐小雁對他一字一句说:“徐童,你让我干任何事都行,就是要我的命,我都能给你。”
2009年,徐童到黑龙江探望关了店、回到老家的小雁,见到了她的父亲唐希信,一个年过八十依然生猛、鲜活到“疯魔”的孤独老人,他和儿女们相处得磕磕碰碰,对过往拧巴又矛盾。唐希信成为徐童下一部纪录片《老唐头》的主角,接着是唐小雁的四表哥(《四哥》)。在《老唐头》中出场过的唐家老三,一个沉迷于诗歌小说、蹉跎大半生的文学爱好者,又成为《两把铁锹》的主角。
看着很粗犷的徐童说自己是一个“怪人”。和他接触过的人,会觉得他温和内敛,知识分子和文人气很重。但实则“内心很狂野,有江湖气”。“所以我和小雁他们很合得来,打起交道来毫无障碍。”
我们聊起著名纪录片导演周浩的作品《龙哥》,以及一个纪录片导演究竟该和被拍摄人物如何相处的话题。徐童由衷地欣赏周浩那种冷静的思辨力,称他为“解剖大师”,“像一把手术刀,以及和人物始终保持那种审视、静观的距离感,镜头处理拿捏得特别准。”
相比周浩,他说自己似乎无法保持这种冷的距离感,“好像拍什么,就掉进什么里了”,自然地和对方捆绑在了一起。“这容易带入作者的一些情绪,失去了距离感,会产生某种失真感。”
“但是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由于我跟人物完全站在一条战线上,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所以,人物对镜头的信任感是特别强烈的,会把他不曾说过的话,在别人那里不曾表露的东西,在你的镜头前面表露出来。因为(你)是他同伙,他没有顾忌,也更加敞开。这样,镜头可以拍到人物很真实的东西。”
原罪:“被表达”和“被看见”
“纪录片是有原罪的。”纪录片导演、金马奖得主周浩曾坦陈:“做这个职业,就要去承受它的原罪。”
伦理问题,也是徐童被质疑得最多的——为什么要把这些小人物不够体面的、灰暗的部分记录下来?为什么这么残忍,去撕掉他们最后一丝尊严?以及把这些故事拍出来,这算是一种对个人隐私的侵犯么?
非议的口水多了,有时也让徐童很生气——“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他们愿意向我敞开自己,让我记录下来。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障碍。”他也碰到过麻烦,是在某个片里出场的一个次要人物,这成了他不愿意提及的一块“心病”。
《老唐头》完成后,徐童曾用电脑把片子放给唐希信看。老头儿看完后,还对他有了一点不满——明明片名叫《老唐头》,他才是主角,凭啥要把这么多镜头分给其他人?
徐童也有自己的原则。《麦收》里的苗苗后来结婚、生子,离开了北京。他有意不去打搅她现在的生活,《麦收》不再公开放映,删除了网上所有能找到的片源,“但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发现又有人上传了。”

2011年,徐童在拍摄《老唐头》
让他真正感到陷入道德和法律困境的,是2013年拍攝完成的《四哥》。四哥是唐小雁的表哥,是一个职业小偷,曾多次入狱,同时也非常具有江湖中人的“魅力”。徐童用黑白影像记录下四哥的“日常江湖”和他回忆的狱中岁月。
《四哥》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电影节做了一次首映后,就再也没有放过。徐童决定今后再也不碰这一类的禁忌题材,“太难,太纠结了。”
相比四哥、苗苗、厉百程、老唐头,唐小雁是徐童的“游民”系列里最为特别的存在——“相比他们,她更有个人的自觉,有主动性。”
“因为她的阅历、她十多年曲曲折折的人生经历——从老家出来当服务员,到过珠海,后来又到北京,做过夜总会的伴舞小姐、被性侵过,自己又开过按摩店、当过黑煤窑老板,经历过很多很多,她有倾诉的欲望,愿意把自己作为一个样本从人群中抽出来,让大家看到。这是我觉得她最不一样的地方。某种意义上,她已经成为她那个群体的一个代言。”
“如果我不去讲我的这些遭遇,不去拍我家的这些故事的话,那我们这样的人的生活可能就永远不会被人知道。”在一次和观众的交流中,唐小雁吐露自己的心声。碰到放映有关自己和家人的片子,她常常躲开,“因为一看就会哭会流泪。”
上海当天的放映现场,当身着驼色大衣、戴着眼镜、扎着发带的唐小雁现身时,人群中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竟然有机会看到小雁姐真人,比看到女明星还激动。”一位影迷说。
如今,唐小雁拥有数量不少的粉丝,大部分是女大学生。每次交流现场,都有女孩上来要加她的微信,然后会在网上向她倾诉各种人生问题,包括恋爱。
十年间,徐童和他的纪录片也改变了唐小雁的人生轨迹。自《老唐头》起,她参与的程度越来越深,已成为徐童的重要合作伙伴。最近四部片都由她担当制片。在《赤脚医生》的片尾,打出了一行字幕——“摄像 唐小雁”。
徐童用“聪明”来评价这位搭档。每次参加国内外电影节、影展和重要的放映活动,他都会带上她。2013年,两人一道做客窦文涛在凤凰卫视主持的“锵锵三人行”。
徐童一直留意观察着小雁身上微妙的“变”与“不变”。他早有计划完成一部以唐小雁为主角的纪录片,片名叫《小凤》——那是唐小雁在老家的小名。
“但我老觉得还没拍完,因为后面路还长着,她还在走着呢。可能等年纪再大一些,再有个十年甚至二十年的跨度,到时把它们剪辑在一起就成了。会是一个超长的纪录片!”
编辑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