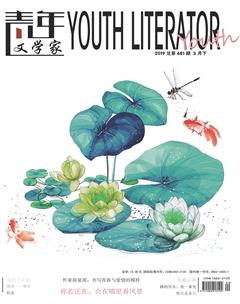浅议文学与治疗
成季耘
摘 要:文学作为艺术门类的一种,主要是由作家通过运用精致独特的语言艺术构建的一个美丽舒适的精神花园,在文学的世界里,人们可以“兴观群怨”,可以通过阅读欣赏文本中细心雕琢过的语言,精心安排的情节,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来舒缓人的情绪,治疗人的身心。本文重点是通过对文学治疗这一概念的整体论述,来研究在文学活动中文学是具体通过何种途径来治疗人类的身心,并同时探讨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治疗的方式是否存在着某种困境。
关键词:文学治疗;途径;困境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9-0-03
引言:
在中国大陆,文学治疗作为学术问题被获得关注是由叶舒宪教授于1998年发表了两篇文章:《文学治疗的原理及实践》和《文学与治疗一一关于文学功能的人类学研究》而始。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治疗的这一问题本身是到现在才出现。自从文学被划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关于文学的研究也越来越精细化,专业化。特别是在雅各布森提出“文学性”这一概念之后,关于文学的研究则开始逐渐地只关注文本自身。在此种情况下,文学功能的研究只能被不断地划定为认识、教育、审美这三个传统的范围内,而关于文学治疗的问题则一直是处于被搁置与遮蔽的境况。此后文学治疗重新被提出是因为在现代性危机引发的文化寻根思潮与后现代主义交织的语境中,全球思想理论界出现了东方主义、原始主义和生态主义三大转向,这给文史哲专业带来一场后现代文化寻根运动。在这样一个思想文化背景的影响下,文学也被重新放置于一个新的语境,这也使的诸多学者重新反思文学的含义,包括文学的功能。在这之前对于文学功能的探讨大多是基于宏观的社会层面来评述的,后来随着人类学的不断探索研究,叶舒宪在《文学与治疗——关于文学功能的人类学研究》明确提出:“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借助于人体象征性动作的仪式行为发生在先,借助于语言符号的文学发生在后。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把文学象征的世界当作仪式象征世界之延伸或置换。从历时关系着眼,史前社会中仪式表演(萨满、巫医等法术)乃是文学滋生的温床和土壤。到了文明社会之中,仪式表演转化为戏剧艺术,仪式的叙述模拟转化为神话程式,仪式歌辞转化为诗赋,巫者特有的治疗功能也自然遗传给了后世的文学艺术家。”所以文学治疗作为文学的一种功能它并不是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逐渐展现出来的,而是在文学的起源时它就已经存在了。
本文重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讨论人为什么需要治疗的问题,从“治疗”这一概念入手,分析人类需要治疗的真正原因。第二部分主要讨论在文学活动中文学治疗的具体途径。第三部分则针对当下文学治疗社会实践运用的困境来专门论述文学治疗自身存在的问题。
一、人为何需要治疗
在理性主义的大旗下,科学技术被神话到似乎是可以解决人们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也似乎是在科学技术的改变下人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在这个物欲横流,信仰崩塌的时代,由人创造出的“理性”却越来越不受人的控制,每个个体的价值越来越低廉,精细化的社会分工也使得每个人就像这个社会大机器的一个小零件,存在感极其微弱,而“批量生产”的方式更是让人们有一种随时可能被替代的危险。没有安全感,没有归宿感。高速运转的社会,越来越优越的物质条件却让每一个现代人“无家可归”。很多人都认为是现代性危机与现代性风险迫使人们开始去思考如何去解救和治疗现代人千疮百孔的心灵。可这只是一个从当下的时代背景来探讨“文学治疗”重新被获得关注的原因,并不是人需要“治疗”的真正原因。正如学者曾宏伟学者曾写到:“根据人类学的观点,文学是基于治疗而发生的,或者说文学最原初、最基本的功能便是治疗功能,而非认识功能、教育功能或审美功能。”因此不论是在原始社会还是文明社会,“治疗”都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在探讨“文学治疗”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探讨人为什么需要治疗?同样对于人需要治疗的原因也不能只简单的归结为时代所致,或学术研究潮流的影响。
对于一个概念的意义我们可以通过去反观它背后那个概念的意义来把握。谈起“治疗”这一概念我们能想到的无非是“疾病”,因为有疾病的存在,所以治疗才有存在的可能。古往今来人们对于“疾病”这一问题的敏感不是没有理由的,佛教曾说过人生而有“四苦”,即生老病死。而“疾病介于生死两者之间,既关涉到生,也牵连到死,它是生与死的相邻母题。”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巫术中为什么有很多咒诗都是和治疗疾病有关,也会理解为什么“疾病与治疗”会是文学中永不衰落的母题。
而当“治疗”这一词汇褪去科技与医学的伪装之后,把它放置于一个切身的关于“人”的命题之下时,有关治疗的领域则不应该仅仅只局限于科技与医学所能达到的人的生理与心理的方面,其精神性与超验性应该是我们更要去关注的问题。因为从根本上说人类不仅仅是个动物性的存在,同样他也是个精神性的存在,所以人类往往在追求生理满足之后还需要心灵与精神的安顿。因为人类大概是唯一一个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终会死去的物种,所以很多时候人这一生所做的种种就像是一个不断治疗自我,填补永恒缺口的过程。
因此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理解因为疾病,因为人天生的脆弱与永恒的不完满,所以治疗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不应该是个陌生的话题。
二、文学治疗的途径
(一)文学治疗功能的概念
“文学治疗功能”这一概念在中国大陆最早是由叶舒宪教授提出的:“文学是人类独有的符号创造的世界,它作为文化动物——人的精神生存的特殊家园,对于调节情感、意志和理性之间的冲突和张力,消解内心生活的障碍,维持身与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健康均衡关系,培育和滋养健全完满的人性,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叶舒宪教授基于文学文化意义上所做的阐释。在这个定义中叶舒宪主要是从文学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出发来说明文学具有治疗人类心理疾病,维护人类心理健康的可能。学者曾宏伟也曾尝试对“文学治疗”做出了定义:“所谓文学治疗,是指罹患心理疾病的审美主体通过各种审美实践活动(如从事文学阅读与鉴赏、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与研究等),缓解、消除自身心理压力或偏差,解除心理困扰,恢复内在精神生态系统平衡,最终实现身心健康的心理治疗行为与方法。”在曾宏伟所论述的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文学治疗”的理解更多的是从文学活动的主体出发。而后来的学者章米力对“文学治疗”做了一个更为全面的概括:“文学治療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文学治疗是由心理医师指导的,通过引导性的语言、舒缓的音乐、自传式的倾诉、专业化的技术手段,包括催眠、冥想、绘画、团体分享等,从而帮助病人激发联想、缓解压力、补偿欲望、确立自我价值。广义的文学治疗浸透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依靠着文学手段调整内心的平衡。”章米力学者直接从“文学治疗”本身出发,将其分为广义和狭义,这使得“文学治疗”的概念更加具体全面。
以上是对于“文学治疗”这一概念的简单论述,下面将对文学治疗的具体途径展开论述。宫爱玲在《现代中国文学疾病叙事》中对于文学治疗的途径主要分为三种:文学创作的治疗、文学故事的治疗以及文学审美的治疗。而笔者在这里则将会从文学活动的两个大的方面来论述:创作者治疗与接受者治疗。因为在文学活动中,文本作为一种媒介沟通着创作者和接受者并同时对他们发生着作用,所以谈及文学的治疗途径应从创作者和接受者两方面入手。
(二)文学治疗的途径
1.创作者与文学治疗
文学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从生理角度来说,人天生就有表达的能力或意愿,不论是用语言、音乐还是线条或色块,这都是人的一种表达方式。表达是人的天性,因为人是社会性动物,而表达就是为了使得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相互连结而存在的。其中文学创作就是人类表达方式的一种。
古人云:“不平则鸣”,“发愤著书”,在文学活动中,创作者往往是通过语言文字将自己心中的情绪表达出来,在这种外化式的表达中,创作者很容易就能将自己心中的不平和郁结表达出来,而同时因为语言与现实所产生的这种距离感使得创作者能够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重新审视自己所表达的故事或抒发的感情,也会对于自己所面临的境况来进行积极的思考。
(1)自医:古往今来文学史上病患作家太多太多,杜甫、鲁迅、史铁生、张海迪、尼采、卡夫卡、拜伦、海伦·凯勒、伍尔夫等等。这种现象并不仅仅是因为上述所提到的文学叙事具有外化式的性质,能够对人的负面情绪有宣泄功能,而更是因为文学具有使人回归社会秩序,重新构建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可能。正如袁愈祯关于叙事治疗的论述:“叙事治疗就是指治疗师通过倾听来访者带有问题的故事,运用适当的方法,使问题外化,追求一种‘将问题和人分开的理念,进而帮助来访者找出被主流故事压制而遗漏了的生命闪光片段,引导其通过拾缀这些闪光碎片来重构积极故事,以唤起其人格发生改变的内在力量的过程。”
当然,病患选择文学叙述来宣泄情绪,舒缓抑郁也与文学自身的安全与隐匿有关。因为文学是虚构的,它来源于生活,但同样也超脱于生活。对于文学的世界里时间、人物、情节等都不可像历史记载一样可去考证与调查。而这就恰好给予了创作者更多的安全感,不用局限于现实世界里的个人身份,使他们可以尽情在文学的世界里抒发情感。
(2)医人:在文学史上有很多作家不仅仅是病患,同样他们在更多的情况下扮演着“医生”或“拯救者”的形象。如中国作家鲁迅、沈从文、老舍等等。这类作家在治疗自己的同时,往往无意识或有意识地去治疗着别人,这首先是因为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始终都伴随着“隐含的读者”存在。它是相对于现实的读者而存在,是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文本问世后可能出现的读者的一种预想和期待。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本身就会有一个潜在的倾诉对象,所以作者在宣泄情绪,寻求自我满足之余还会注意到他者的存在,也就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尝试与他者沟通,并可能会从他者的角度出发,与其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其次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创作者最初的目的就是专门为了治疗他人而书写。这类作家敏感细腻,且富有人文关怀,他们能发现并关注到生活中需要“治疗”的人,然后从他们的角度出发进行文学创作,最终达到治疗的效果。作家鲁迅、沈从文、毕淑敏都曾有过这样的创作动机,七十年代末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也都是通过暴露和反思“文革”对人们所带来的伤害从而达到治疗的效果。
在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医人”和“自医”并不是完全对立分裂的,很多情况下在同一部作品里其实可能都存在着“医人”和“自医”这两种情况,笔者在这里所做区分只是为了更好的分析两类情况的各自特征。
2、接受者与文学治疗
文学文本除了“隐含的读者”之外还有现实的读者,这是真正把文本内涵可以具体化的读者。读者即文学文本的接受者,他们在阅读过程中通过不断去感受作者的情感变化,情节的跌宕起伏,人物的传神逼真来寻找和作者的共鸣点,这也是接受者的情绪不断外化的过程,通过阅读接受者潜在于内心的情绪或者郁结因所产生共鸣而被调动出来,并随着文本情节的发展而被宣泄和净化,最终达到治疗的效果。而无论是在创作者那里,还是在接受者那里文学所带来的宣泄与满足都是存在的。两者不仅都可以通过文学语言进行一个平等的沟通,同样也可以在文学语言所建构的文学世界里获得补偿性的满足和情绪宣泄的快感。
同时接受者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不仅仅只有情绪的宣泄和释放,文学治疗在很大一部分是体现在培养新的价值观方面,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读者阅读优秀的文本除了能产生共鸣,达到情绪的净化之外,还能在此基础上通过思考领悟到新的人生哲理,感受到不同的生活方式,并以此来对我们当下生活的困境给予指导和帮助。
但我们也要意识到文学对于人意义的建构并不是适用于所有人的,因为不一定每个读者都能明白文本深处所蕴含的意义,并通过文学来建构自己的精神花园。可这也不意味着文学治疗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就是无效的。正如王旭峰他们所提到的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传统叙事可能是更为有效的治疗方式,因为“通过在文学中回归传统,回归稳定的文化和身份认同,找到稳定的价值评判体系,人们往往能够从容的应对突发事件,抚平突发事件或灾难带来的心理创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们通过文学文本来进行沟通可以打破时空的界限,可以与古老的过去和遥远的未来直接展开精神性的对接,这使得人类在漫长的时空里获得了归属,而不再是一个无过去可依赖,无未来可追寻的原子。所以说通过阅读文学文本不仅可以达到情绪的宣泄,培养新的价值观,同时还能巩固我们的身份认同,满足我们的社会性需求。
三、文学治疗的困境
关于文学治疗应用的困境已有部分学者在这方面做了相关的研究,但所谈及的都是关于文学治疗在社会具体实践运用中所遇到的阻碍和困难,但对于文学治疗本身是否存在困境却少有人涉及。鲜有人提及不代表问题就不会存在,因为海明威、川端康成、海子、三毛的自杀无一不提醒着我们是否应该去认真考虑文学治疗的可靠性。
毋庸置疑,通过以上论述笔者认为文学治疗是肯定存在的,首先文学可以解除压力,并以艺术化的手法来发泄和满足人的欲望。其次通过文学阅读,接受者能获得更多的社会归属感,上文中提到的“回归传统叙事”的治疗方法正是如此,因为文学文本自身就是一个可供交流的场,在这个场中我们可以打破时间空间的局限,不仅能感受到自己,更能感受到他人。
但就算文学治疗有众多优点与长处,很多文学治疗失败的案例也使我们不得不清醒面对这个问题,而且大部分被治疗失败的人都是文学作品的创作者。首先,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治疗”这个词并不等同于“治愈”,“治疗”侧重于过程,而“治愈”侧重于结果。文学治疗也只能是提供一种疗愈的可能性。其次,我们在那些自杀的作家中可以发现相同的一点:当写作再也不能维持他生命的意义的时候,他们能选择的只有自杀。对于那些细腻而又多愁善感的作家来说,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感触和我们普通人是不一样的,可这种与众不同也造就了创作者的孤独,有些文学作品问世后也许是无人问津的,那么创作者的交流系统就会呈现一个关闭的状态,长期以往创作者的自杀便会成为一种可能。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创作者对于自己“江郎才尽”的恐惧,如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却选择了自杀。其实对于作家来说失去写作能力是最为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这就相当于运动员失去了双腿,歌唱家失去了嗓子一样,当用于维持生命意义的一种可能,或者说是唯一的可能被毁灭掉的时候,也许能留下的就只能是绝望。
作家在创作中更多的是在表现情绪,这是一种极为感性化的表达方式,它能将情绪宣泄和抒发出来,达到一时的内心安宁与平静。但却不能解决问题所有的问题,因为人不仅仅是感性动物,同样也是个理性的动物。所以仅仅依靠感性的方式去解决人生的所有困境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人不仅仅是需要艺术,也同样需要宗教和哲学的原因。在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中艺术也只能是作为回归绝对精神的一个阶段,但卻不是终点。所以大部分作家的自杀的原因都是因为过度投入感性世界而发现无果,只能走向毁灭与死亡。
人是复杂的动物,是多纬度的存在,想要真正维持一个心灵的自由与健康就不能仅仅只是停留在某个单一的领域之内,应通过情感、信仰和理性等多方面的滋养来达到人体生态的健康与平衡。
参考文献:
[1]崔荣艳.文学治疗研究述评[D].华东师范大学,2015,3.
[2]王立新、王旭峰.传统叙事与文学治疗——以文革叙事和纳粹大屠杀后美国意识小说为中心[J].长江学术,2007(2).
[3]武淑莲.文学治疗作用的理论探讨[J].宁夏社会科学,2007(1).
[4]袁愈祯.文学叙事治疗理论与实践[D].陕西师范大学,2014,5.
[5]叶舒宪.文学治疗的民族志——文学功能的现代遮蔽与后现代苏醒[J].百色学院学报,2008(5).
[6]叶舒宪.文学与治疗——关于文学功能的人类学研究[J].中国比较文学,1998(2).
[7]叶舒宪.文学治疗的原理及实践[J].文艺研究,1988(6).
[8]章米力.疾患的表达及文学治疗的生命力[J].百色学院学报,2013(3).
[9]曾宏伟.文学治疗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J].学术界,2009(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