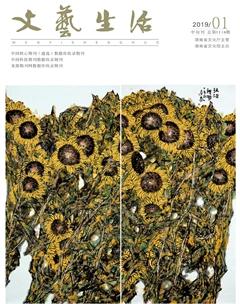传统戏曲和传统曲艺的融与通
刘延璐
摘要:戏曲和曲艺是中华民族艺术的的两大瑰宝,同时也都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人们都习惯上喜欢将这两种艺术称之为姊妹艺术。数百年来,这两种艺术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曲艺与戏曲之间有着相同的发源地,并且这两种艺术在发展过程中也在相互之间不断的发生交流和渗透,进而形成了如今各自之间都具有联系但是却又相互独立的表演艺术。文章主要对戏曲和曲艺区别,相互借鉴与融合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戏曲;曲艺;区别;融合
中图分类号:J805;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9)02-0134-02
一、前言
戏曲与曲艺在表演过程中不断相互借鉴,进而使得人们对曲艺和戏曲之间的区别从感性层次提升到了理性的层次,有助于曲艺和戏曲在综合方面的异同得到界定。融,任何戏曲都可以成为曲艺的题材,通,任何曲艺的形式都可以成为戏曲的借鉴。在对这两种艺术协调创作、表演、欣赏等关系进行确定过程中,可以针对性的吸收这两者之间的艺术成果,并且也能够对其进行参考。
二、曲艺与戏曲的区别
(一)呈现角色的人称不同
戏曲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连贯的戏剧冲突,剧中每一个人物角色都是以第一人称出现的。随着情节的展开和戏剧冲突的发展,观众看到的悲欢离合都是每个角色的直观呈现。《打金枝》里面的皇上、公主、郭子仪、郭爱,每一个人物都是“专职”的第一人称,“公主挨打”、“郭爱受绑”、“皇上讲情”,每一个剧情的发展也都是这个“专职”角色本人来推进的。而曲艺则大不同,往往是“台上一人,能演一群”;“台上哥儿俩,千军万马”。曲艺是以第三人称叙述为主,人物身份可以跳进跳出,讲到什么地方,需要以何种人物身份出现,全由台上一两个人表演。侧身刚刚还是猪八戒,扭头己变成了孙悟空;上一句还是岳元帅的语气,下一句己成了金兀术的声音。所以一部《杨家将》有名有姓的几十、上百人,刘兰芳自己分身有术,均能演绎得栩栩如生。
(二)演员对服装服饰的要求不同
曲艺不像戏剧那样由演员装扮成固定的角色进行表演,而是由不装扮成角色的演员,以“一人多角”(一个曲艺演员可以模仿多种人物)的方式,通过说、唱,把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各种各样的故事,表演出来,告诉给听众。曲艺的唱地域性更强,故属于小众。戏曲的服装是直观的定性,戏曲的唱超越地域性,故属于大众。为了更好地表现人物本质,戏典服装应该正确掌握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关系,在服装的穿戴上,服装的色彩运用上,可以与原来生活中的情况有某些区别,这种区别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面脱离生活的真实性,而是要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加工改造,使之更典型,更有代表性、能更深刻,更真實的表现人物。为凸显每一个角色,戏曲表演中对服装服饰、脸谱化妆以及场景设置的要求是很严格很考究的。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身份,甚至不同的性格,他们的穿戴装束都迥然不一。在传统戏曲中,同为蟒袍,皇上穿的须是黄色且多为盘龙;同为朝服,文官着袍,武将扎靠:同是净角儿,曹操要煞白,关羽则赤红。现代戏曲的服装道具更是具体细化到一副眼镜一支烟上。因为只有这样,戏曲才能更好地完成其“情景再现式”的艺术表演。曲艺往往没有这么繁琐,对服装道具的依赖性较小。相声演员穿一件大褂儿上台演出,提起苦守寒窑十八载的王宝钏了,把手绢往头上一扎,这就是女性人物;说到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将纸扇一举,这就是表现的劳动工具。二人转演员的着装算是和戏曲里的“行头”有些接近了,但它的作用也更主要的只是演员的演出服。因为从上台到下场,整段儿演出下来,不管中间“跳进”过多少角色,变换过多少身份,演员绝不会因为情节的变化和人物身份的不同而在装束上进行改变。
(三)即时性不同
曲艺在即时性上有较明显的优势。说唱艺术,“说”字当先。体现即时性这一点,也主要在“说口儿”上。人物角色的变换,情节行进的快慢,主要靠“说”来掌握。由于“说”的时候不需要伴奏、布景等多方面的配合,演员就可以常常根据现时现地的情况灵活地加进或变换一些临时的新内容,以达到更好的演出效果。相声表演中的“垫话儿”以及其它许多曲艺曲种中时常出的“现挂”都是演出即时性的表现。戏曲表演讲究有板有眼,有固定的程式,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台词,从起始到结束都是不能随意更改的。这是因为作为综合舞台艺术,戏曲表演的完成需要众多人员、多个环节的密切配合,每个演员的任何一处表演都关乎到整个剧情的起承转合,不允许有临时性的改动,这样一来,整体的灵活性和即时性自然也就稍弱了一些。
三、戏曲与曲艺表演手段的差异
(一)曲艺的“说”与戏曲的“念”、曲艺的“唱”与戏曲的“唱”
在曲艺中,其中的“说”往往显得比较口语化一点,也就是说,其在贯口、诵诗方面的发生比较口语化,只不过在原来基础上进了适当的加强其节奏感。戏曲中的“念白”主要可以分成为“韵白”以及“本白”两种方式。“韵白”用中州韵吟诵,“本白”用地方话表达。戏曲中的“本白”一与曲艺中的“说”相比之下,往往在归韵以及拖腔调方面需要花费很大力气。也就是说,与曲艺中的“诵诗”比较而言,“本白”在韵律感方面非常强。
不管在戏曲中还是在曲艺中,其中的“唱对五音四呼有着非常大的讲究,并且也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依字衬腔的特点。但是在语音以及旋律方面,戏曲与曲艺比重方面则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在对曲艺进行演唱过程中,往往有着字重腔轻的特点,而在戏曲中这种“唱腔”的特点则要显得比较明显。
曲艺以及戏曲在发展的过程中,在对唱腔的发展中都是通过咬字发音的方式,也就是所谓的“依字行腔”的方式。但是如果论道投入的方面。则戏曲的投入远远超过曲艺的投入,而曲艺将主要的重心放在了咬文嚼字方面。这也就会使得戏曲给人感觉有一种“似说似唱”的感觉。当然,戏曲在唱的过程中也有着不少差异性。架桂娟认为曲艺在演唱的过程中可以有两种方式,其中主要包括“唱书调”以及“说书调”。他认为前者属于“唱着说”而后者则属于“说着唱”。但是也戏曲中整体的演唱风格相比之下,“说书调”以及“唱书调”之间有着比较明显的共性,这就体现了一种较为典型的“说”的色彩。
曲艺中的“唱”和戏曲中的“唱”其实都是一种表演的方式,他们在服务的时候,都是具有一定的目的。两种方式由于目的不同,进而在其手段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在曲艺中,“唱”则主要是对讲述着进行客观上的叙述,在这中间也穿插了不少对人物进行摹拟的抒情方式;而在戏曲中“唱”主要的作用是为给角色进行服务,虽然戏曲中在“唱”的过程中,也穿插了一些叙述的成分,但是其主观色彩并没有失去。
曲艺与戏曲在这方面的不同之处,表现了出发点不同则其规定性也就不一样。仅仅就拿唱强来说,在相同的地区,曲目以及剧目中共同占有同一个曲牌的现象非常普遍。但是在对曲牌的使用方面,曲艺和戏曲之间还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他们在叙事以及抒情方面侧重点不相同。
(二)曲艺的“做”与戏曲的“做”、“打”
在戏曲中,其程式化体系以及行当化体系往往比较庞大。如果将程式化比作是“经线”,将行当比作“维线”,那么他们之间许多交叉的“点”就比作为“做”、“打”等。
戏曲表演程式中一共有9个系统,其中包括:基本程式系统、抒情程式系统、生活程式系统、武打程式系统、舞台调度程式系统、板式唱腔和念白程式系统……这9中系统中,前四种系统主要通过“做”、“打”等方式建成,而后面的5个系统,则主要为了给“做”、“打”提供给系统性支持。
中国戏曲里中,舞台上的每一個角色其实都是行当中人,所以而程式在戏曲中的作用是主要用来塑造每一个角色的基本语汇。在每一个行当中,每一个“本工”在制定喜怒哀乐中都有着自己的一套方式,并且其中的每一个动作甚至每一个招数都有非常明确的规范。由于不同规范在行当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所以在动作、表情、造型方面也非常的丰富多彩。所以相比之下,曲艺表演在这些方面有着很大差别。在古时候,艺人们说书时,总要念上一段“西江月”作为定场词,一世上生意甚多,惟独说书难习。紧鼓慢板非容易,千言万语须记”在念的过程中声音不仅要洪亮有力而且也要抑扬顿挫。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说书是一门很难学的行业,但是与戏曲的复杂性相比起来,在其形式方面还是简化了很多,尤其是一个人常衣素面“一台大戏”,显得非常淳朴。
四、戏曲与曲艺表演的相互借鉴与融合
以南平的南词曲艺与南词戏曲为基础相互融合的南词轻喜剧《公民张二狗》为例。在该剧中,不仅将音乐、灯光、舞蹈以及人物造型等融为一体,还增设来南词曲艺说书人这一特殊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是将以南词作为同一创作基础的曲艺与戏曲有效融合在一起,取得了相得益彰的文化艺术效果,也为南词艺术的探索和发展开创了一条成功之路,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一方面借助南词说书人的说唱演艺方式,实现南词戏曲场景变换之间的衔接,并在不闭幕的表现形式基础上,将说书人设定为该剧整场表演的组织者、事件的解说者和前后场的串联者,不仅让受众在同一时间内同时感受南词曲艺与南词戏曲的艺术文化魅丽,还能感受到南词戏曲与南词说书人相互融合的别样艺术表现形式。
另一方面,通过说唱艺人的表演帮唱和表演伴唱或道白等表演形式、方式,不仅彰显了南词曲艺的形体表演与唱腔,还充分体现了南词戏曲在细腻刻画人物面部表情和心理变化的特殊表演风格,更重要的是同南词为母体却以不同表演艺术为表现形式的南词曲艺和南词戏,在该剧中以有效嫁接、取长补短的相互融合方式实现了珠联璧合的效果。
另外,在该剧中,南词说书人在九段唱腔中除了使用传统的鼓作为曲艺音乐,还使用了失传已久的板作为与鼓协作的曲艺音乐,并根据该剧剧情的需要和曲牌的风格,使用了板与鼓的不同伴奏结合方式,或先板后鼓、或板鼓交错、或强弱倒置。板与鼓的完美配合和精美设计,不仅为南词说书人的说唱表演增添了显著的艺术感染力,也为该剧的剧情发展和人物表演助添了一份别样的艺术渲染力。
曲艺和戏曲虽然在艺术表演方式各有不同,但两者在很多方面却存在很多同气连枝、相同或相似之处,例如,二人转的鼓点与京剧的鼓是有共性的,主要乐器也相同,因而可充分借鉴彼此的长处和优势,寻找两者在表演艺术上的共性和相同点,并在此基础上,可有效创作出符合人们对艺术审美新需求和高要求的新型表演形式。
五、结语
从上面的情况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对去曲艺进行规范时,其流程也要比戏曲能简单很多,并且曲艺中的许多讲究都是来源于戏曲。所以正好验证了前面的观点:曲艺中与戏曲之间存在非常多的交流和渗透。如果说,戏曲在形成过程中源于曲艺向戏曲中渗透,那么当戏曲变得成熟的时候,则更多的是曲艺对戏曲的元素进行了吸收和借鉴。在清朝,由于扬州地区在南北方向的交通比较发达,所以当时民间的活动演出非常频繁。很多昆曲演员开始弃“戏”从“书”,开始做起了评弹行业,这对当时的说唱行业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
但是,曲艺在吸收戏曲元素的过程中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虽然在表面看来,只是把握了其中的“度”,但是从深层次来看,却体现者这两种艺术之间存在的区别。
因为曲艺演演员主要是通过单三人称的口吻进行讲述故事,所以演员在表演过程中主要通过口头阐述,必要时还会加一些肢体语言。曲艺表演过中,对人物性格的描述更多是建立在客观讲述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戏曲在表演过程中主要通过表现一个角色的主观言语以及行动进而展现人物的形象,甚至在刻画人物的心里活动时,也通过人物的肢体动作来反应。所以对唱、念、做、打过程中的情绪化以及性格话极为重视。曲艺在表演过程中主要对事物展开叙述,在必要的时候也会穿插一些代言,所以很多演员在作“功”过程中具有非常明显的辅助性,所以其难度系数比较低,同时在对基本功以及日常化的训练过程中也并不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