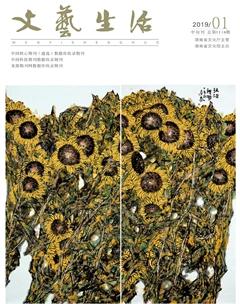谭延闿的“崇古”书法观
吕建凤
摘要:谭延闿书法早年学翁同龢,中年参以钱沣笔法,后上溯到颜真卿,同时广临诸帖,终自成一家。而崇古思想是谭延闽毕生坚持的书学理念,它是谭延阊书学研究的一条主线,也是指导谭延闿书法实践最根本的一则书学思想。
关键词:谭延闿;崇古;书法观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9)02-0020-01
谭延阎书法崇古不仅仅是技法上的追根溯源,他更崇尚的是古人书法中的“意”。前人关于书法古今之辩,常有“古质而今妍,之谈,至于孰优孰劣历来都是众说纷纭。南朝宋书法家虞龢在《论书表》中提出的“古今观”较为中肯。虞稣论钟、张与二王是古与今,二王父子之间又是古今,由此论推出二王书法相对于钟、张书法是妍,王羲之书法相对于王献之书法是质。然而钟、张、二王之书优劣既微,同为终古之独绝,百世之楷模。所以虞稣认为古质与今妍并非孰优孰劣,而是书法传承之规律。
明代项穆在《书法雅言·古今》篇中批判了世人较为极端的书法古今观,指出世人学书的两个弊端:其一,学书仅宗秦、汉,此为学古太过者:其二,书技只取式于宋元而不上溯,此为学古不及者。他认为尚古太过或者不及均不可取。
察其谭延闿书法崇古思想的内涵与虞、项之论不谋而合。谭延阎尝言:“观古人用笔,乃知今人之非,则艺进矣。”并且他认为学书与学诗多有相同之处,他常以学书与学诗之道相互为用,如:
作诗与写字同,宁涩毋滑,宁拙毋俗,宁苦毋易。
《诗话》有云:
‘唐人用字用韵,皆极平淡,一经点梁,遂成绝唱。犹之园蔬囿彘,经良庖烹治,即成异味,初不必山珍海错。宋以后凿险缒幽,转为多事云云。大意如此,其言亦未为无理。孙过庭论书云:‘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能平正,乃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窃以为诗亦宜然。
这两处言论,其一是从审美与鉴赏的角度来论述作诗与写字的相同点,其二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论述学诗与学书的相同之处。此类言论在谭延阎的日记和手札中并不少见,他这样阐述言论的目的显然是让自己的论据更加充分,论点更加形象化,却也反向印证了谭延闿的某些书学理念与其诗学观念相通,这一发现给谭延闿书学思想研究提供了论据。
谭延闾的书法崇古观并非是强调追根溯源,以秦、汉为尊。就以谭延阎的书法实践来看,其书法早年受翁同龢和刘墉的影响,到中年以后又参以钱沣笔法,他从1914年开始临习《麻姑仙坛记》,此后半世不曾懈怠。但是他在取法唐颜真卿的同时并未否定或摒弃翁、刘之法,如1926年他在致友人和庆善函中说:
刘、翁、钱、何为有清四大家,不可不观其通。今以所印何临《道因》残帙奉赠,足医重坠之病。何书不易学,然不可不知也。
此语中,谭延阎对刘、翁、钱、何有清四大家的书法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未拘泥于时代的先后与早晚,可见谭延阎崇古并无过之或不及,用合乎时宜来形容他的崇古观应当不为过。如前文所述谭延阎认为学书与作诗有相同之处,另外,我们从谭延阎的诗论中也能发现相似的观点。
就以“取法”为例,在相关文献中未曾见到谭延阎明确阐述学书的取法观,但他却不止一次地论述过作诗的取法观,如:
故当以学古人为第一,且必须学唐以前,久之放笔,自写胸臆,自然与宋贤合,所谓取法乎上也。
今人论诗,宗宋人,不甚以湘绮为然,其实从此法门入手决无轻浮浅俗之弊,犹学书先当作九宫楷书也,若学成以后,放笔为之,虽自成一家亦可,何必拘拘唐宋之见乎。
以上两段论述,其一,谭延闿主张学诗如果要学成高深的境界,就必须“当以学古人为第一”,并且明确指出目的是要取法乎上。当然取法乎上之语并不是谭延闿首次提出,其原句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此语出自《易经》,此后这句话常被喻意为学习上的取法乎上。如宋代詩词评论家严羽在其《;仓浪诗话》中,曰:“学其上,进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
其二,谭延闿对学诗以湘绮先生入门予以肯定,他认为湘绮得古法,所以学湘绮入门不会有轻浮浅俗的弊端,就如同学书之初当先学“九宫楷书”,入门之后,再放笔为之。
这三段论述可以看出谭延闿对于学诗的取法观非常明确,而这种取法观与他的书法实践也是吻合的。谭延阎的书法宗颜,但他早期也深受翁同龢和刘墉的影响,所以说他学书是从翁、刘上溯到颜真卿。这一学书过程与他所论及的学诗过程可谓异曲同工。还有一则言论更进一步证实了谭延阎的书法取法观:
眼高手低是一病,然恒不自足之心,亦即进步之一端。日计不足,岁计有余,不仅良吏为然也。吾书不足学,学之徒增习气,仍以学古人为宜。
1925年谭延闿的书法已经大有名气,但是他仍劝说友人:“吾书不足学,学之徒增习气,仍以学古人为宜”,足见谭延闿将取法乎上作为习书至关重要的原则,也表明他的崇古观念是非常牢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