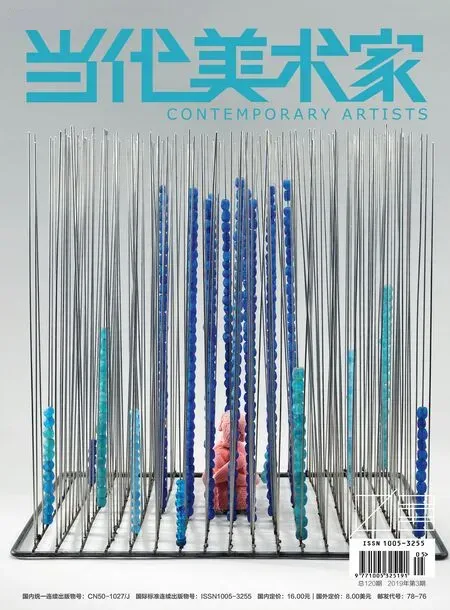塞尚的“实现主义的还原”
——以乔纳森·克拉里的塞尚研究为中心(下)
Su Hang

1 塞尚马尼岛附近的屋子63cm×79cm约1888
3. “实现主义的还原”之意涵
3.1 还原之不可能
胡塞尔、柏格森、梅洛-庞蒂和克拉里笔下的塞尚都共享了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碎片化的理解,并且都处于20世纪的机器视觉王朝彻底重置的背景。差别就体现在对待分心和分散的注意力的态度上,胡塞尔和柏格森对此都采取了拒斥的态度。而在二者之外,梅洛-庞蒂与克拉里达成了某种一致性1。
克拉里在塞尚那里发现了一套和《物质与记忆》中的知觉动力学完全不同的理论。克拉里认为塞尚发现的是在场的不可能性,是一种“去主体化的运作”。克拉里认为,抓住可见世界的做法是在无休止地经历失败,这种效果是最原始的眩晕经验,眩晕是混乱的自行运动2。
这与梅洛-庞蒂所强调的身体是在“自然中的肉体”是一致的。在梅洛-庞蒂看来,这种自然乃是粗野的自然,一种谢林所谓的“野蛮原理”,或者胡塞尔所谓的“不转动的大地”。而“肉体”提供一种场域,使得所有的感觉可以浮现、交织。在此场域中,单一的可见者、可触者都被所有的可见者、可触者所环绕3,进而形成了某种可逆性:感觉者与被感觉者的相互交互。但在这种交互过程中,却蕴含着明确的意义的模糊性与不可能性,“我们应该适时地强调一种总是临近却事实上总是未实现的可逆性”4。因为这里的每一个单一感觉都有着多个层次的模糊(比如能触者已经包含着被触者、能见者、他人的触摸等),这些模糊蕴含着不能收拢的裂口和开放5。
正如克拉里指出的,这种模糊性最后导向了另一种节奏的空间/时间,导向了那样一种事件的无限漂浮时间。这一事件“只知道速度,不断地划分那种早已存在的东西,亦即某种与此同时尚未存在的东西,同时太早与太晚的东西,某种即将要发生又刚刚发生了的东西。”6克拉里自然引入了对“身体”的分析:塞尚的作品是“身体研究”的产物。他不由自主地,将注意力投向了身体,投向了它的脉冲、它的暂时性,投向了身体与一个不断转化中的世界7。
3.2 朝向“还原之根本不可能”的还原——“激进统一”的可能性
克拉里的塞尚研究其中一个重要洞见在于:塞尚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许多作品是对综合本质的一种激进的再思考。克拉里认为塞尚的作品提出了一种专注的固定,塞尚不会从投向视域的一瞥或眼睛的前后扫描开始(这是胡塞尔做的工作),而是耐心地观看一个视域的局部区域8。一旦眼睛停止运动,一种潜在的、反复无常的情境便产生了。各种视觉固定与静止的经验,向他揭示了再现世界的那种常规的绘画实践的不充分性9。世界只能被理解为一个正在生成中的过程10。
“统一”是绝大多数画家和哲学家最后都要做的工作。彻底的解构和对统一的排斥是与绘画和现象的本质相悖的。绘画之为绘画,就是对动态世界的抓取,不论抓取的是碎片,或者声称抓住了整体。这样,在绘画的定义上,就蕴含着解构的彻底不可能。所以,塞尚提供的是一种新的“观看方式”,与重置的视觉机制与碎片化社会相吻合。
这种“综合”是从两个角度展开的,其一是“还原对象”与“主观创造对象”的综合。“还原对象”即将艺术写实还原为其展现出来的样子;而“主观创造对象”则指的是以个人的主观情绪为尊,来高于甚至脱离自然万物而进行的绘画创造。但这两点显然都不是塞尚采纳的。有学者在分析“艺术乃与自然平行之和谐”一句时,强调“实现其感觉”与“复制对象物”的综合,才是塞尚此言的要义所在11,与此处讲的“综合”大体意涵近似。
其二,综合是将碎片化借助绘画形式,综合为具有统一“意义场域”的“一幅图”。正如学者所着重强调的,绘画必须要“立”,而不能只有“破”。“破导致了全部架上绘画的终结12”。这种综合是所有绘画所坚守的,而这里想指出的是,塞尚是通过第一重综合,来达到第二重综合这一目的的。
对第一重综合分析最为出彩的是弗莱,尤其是其中对《通往黑色城堡的路》分析的一段,笔者初读此段,深深被弗莱敏锐的领悟力所震撼:
“他在被选中的色彩之键上转调,就像音乐家一样自由。他不再像过去那样从大自然中接受精确的暗示,而是接受其变化的暗示,然后根据感知范围的延伸,再将它们描绘下来。13”
如果仅仅是对自然万物进行再现,实际上只是沦为了自然的奴仆,这也是艺术家强调主观创造之自由的原因。但是如果仅仅强调主观的智识或感觉,创作则毫无根基,反而沦为玄想或空洞的呼喊。真正的实现主义式的综合,应该是自由地接受大自然变化的暗示,然后根据这种暗示,去运用感性或知性得到暗示背后的“统一”。这种暗示也许往往是碎片化的,但却不是毫无秩序与章法的。如果用中国哲学或绘画的术语,所谓的“暗示”即“象”。“象”在中国哲学话语中,其实就是由无法察觉的微小变动引生的某种整体的变化趋势,以及这种趋势在认知主体中产生出的无法归约为具体感知的意味。“象”与成形的物相比,又因始终保有丰富的趋向和可能性而更为能动和积极14。
克拉里的分析就在这种“综合”的语境下展开。克拉里指出,观看方式不再是被感知的世界内容的聚拢(柏格森式的),而是想要进入不稳定的不断运动中。塞尚试图在知觉空间内重新建构一种“力”15,作为对“重心”排除的“离心力”。只有在意识到这种不稳定的复杂性之后,心智才有可能建构概念并加以创造16。
这种不稳定的力,正是上文提到的“象”或弗莱所讲的“暗示”。这种新建立的注意力,进入了与世界的主观交接更加强有力的再创造状态。而视觉本身乃是“一座变形与置换的真正剧场”17。在各种关系所构成的星系持续出现与解体中,我们建立了一种感觉和身体性的注意力。这种重新建立起来的注意力是万物自身运动变化的显现,是万物本来的样子,万物“实现了自身”。

2 塞尚咖啡壶旁的女人(La Femme a la Cafetrere)130cm×97cm约1895
3.3 “实现”的意涵——普遍性与个体性区别的消解
将克拉里的塞尚解读放入“实现主义”这一语境下,我们会发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推进对于塞尚作品的理解。首先,实现的核心是万物自身的显现,是作为被给予者的“万物”的主动活动。而人所做的,正是抓住自身显现过程中的种种明确的形体与无形的暗示(即“象”),表达或实现万物自身的综合统一。这方面并未脱离现象学的语脉(虽然是一种激进的发展),另一方面将绘画艺术放入了更为广阔的哲学背景之内(不论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本文并不准备就这些哲学背景进行详尽分析,但仍需要勾勒一些基本的框架。
首先,将绘画作为万物自身的表达,并非是我们强加给塞尚作品的解读。塞尚就曾明确说过:“是风景在我身上思考,我是它的意识。”不过,塞尚的这一想法恐怕还需要后世学者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剖析。弗莱对此的分析是,塞尚并不是去“匹配”自然,而是揭示他如何在对物像进行简化的基础上,致力于“通过一种持续变化和调整的肌理来表达它们。18”表达的种种方式,是弗莱最为关注的,而克拉里在此基础上,更加关注“表达的可能性问题”。而我们在此文中所讨论的“实现主义的还原”,正是对这一问题提供一个可能的回答。
对“实现”重要分析之一当属亚里士多德。他在《形而上学》Θ卷第六章讲(1048a30-32):“实现活动是事物的显现”(energeia is the thing's obtaining[or existing, or being present: ὑπάρ χ ε ι ν]not in the way which we call δ υ νάμ ε ι)19。“ὑπάρ χ ε ι ν”的字面意思是“在下ὑπά,开始άρ χ ε ι ν”,即“开始有,始有”,在此处作名词,所以被翻译为“存在,显现等”。整句话比较恰当的翻译即“实现活动是万物的显现”。这里翻译为“实现活动”的energeia,简言之指的是“目的在其自身的活动”。目的在此处意涵即“完成”,也就是说,这种实现活动并不是去创造某种还未出现的东西,不是去完成某种还未达到目的的活动,而是“显现出这个事物或东西本来的样子”。而这正是绘画活动(乃至全部艺术)的意涵所在。真正的实现活动,就是呈现必然的潜能与倾向。也就是“真实的存在”。“塞尚的艺术不断地追求趋近现实、实现真实的精义”大概就在于此20。
其次,万物在绘画艺术中的显现,一定是带有绘画者浓烈的个人色彩的。绘画者的自由一方面体现在上文所讲的“实现真实”上,另一方面体现在个人色彩上。所以,“实现主义的还原”解释不仅不与夏皮罗的精神分析研究相冲突,而且是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
“当我们将他笔下的静物对象与其同时代的或者后来画家笔下的静物对象加以比较时,他的选择带有十分强烈的个人色彩,而不是偶然的,这一点才显得更加清晰了……在塞尚的所有静物画中,苹果都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习惯性母题,而在其同时代其他画家的作品里,它们却是偶然的……”21
绘画最令人惊叹之处,就在于普遍性与个别性。绘画者力图用绘画来把捉世界的整体、世界的真实。但在塞尚眼里,世界只有被当做不断去中心的不确定序列,把握世界的定点或中轴已无可挽回地消失后,才是可以被认知的22。克拉里反复提醒我们,塞尚并不是在累积同一个统一区域的不同或多样角度下所看到的东西,而是我们个体对多样性的不断把握重新组织整个世界23。这种重新组织后的世界,是真实的?还是个别性的创造?或者,这是一种仅仅属于个体的真实,抑或真实地创造?恐怕很难有坚实的答案,我们只能看到这些作品敞开的一个世界,并且看到他将自己分解为“无数震颤,全都在从不间断的连续性中相互关联着,全都彼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在各个方向上移动,就像布遍一个巨大肌体的战栗一样”24。
结语
行文至此,在开头部分对本文章的期许已经基本达到。一方面克拉里的研究并未脱离现象学(梅洛-庞蒂)、精神分析(夏皮罗)与形式分析(罗杰·弗莱)太远。另一方面,通过提出了一种“实现主义的还原”,提出了以还原的不可能为核心的“激进的综合统一的可能性”。最后,笔者想引用克拉里与弗莱对塞尚“线条”的分析作为结语,以稍微弥补本文对具体绘画案例分析的不足。
绘画的构成维度“线条”是释放“绘画深度”的重要环节。这一点克拉里对《松石图》的分析尤为清晰,他提醒我们观察右下方那块岩石,它的体量不是通过立体造型的技法,而是通过轮廓线来暗示某种不安的气息。很显然这个轮廓线是不连续的:左侧是一个S形,在整幅画的中心,右侧则是不精确的羽毛状的曲线,一直通到右下角,突然转为一个向下的直线,使整块岩石显示出最粗略的“作为岩石的样子”25。
克拉里指出,这幅图中间的带状结构相对于画面其他部分有截然不同的质感和清晰性。岩石发挥着使人“集中注意力”的作用。但当我们试图稳定对岩石的视觉,却因为触碰到了岩石奇怪的线条,而又导向了解体和变形。但我们仍然形成了知觉,达到了“去中心化的,不确定的统一”,无论其轮廓线、色彩多么奇怪,我们仍然知道这是“岩石”。
弗莱对笔迹和线条的强调,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松石图》中的这些徒手线条,能够清楚地告诉我们“某种我们称之为艺术家的感性的东西”。这些线条使得整个画面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中,为一个扁平化的画面,赋予了诸形状的“结晶化”形态。“诸平面相互交织,彼此渗透,共同建立起一个画面,而且复杂性没有危及生动流畅的相互关系”26。岩石、青苔与后面的松树都严整地统一在一张图中,却有着溢出画面的生机与活力。塞尚敏锐地察觉到了自然的暗示,生机与活力正是这些自然事物“本来的样子”,他们借助形状怪异的圆柱体、圆锥体和球体,得以被清楚地呈现出来。在此意义上,我们可能才真正领会了“艺术乃与自然平行之和谐”的意涵。
注释:
1.克拉里对梅洛-庞蒂并不是十分重视。在书中仅仅出现了三次,在第一章的一个注释中,克拉里更是指出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对“注意力问题毫不重视”,笔者谨慎的认为这是克拉里对梅洛-庞蒂的一个误读。
2.乔纳森·克拉里著,沈语冰、贺玉高译:《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第270页。
3.黄冠闵:《触觉中的身体主体性——梅洛-庞蒂与昂希》,载《台大文史哲学报》2009年第71期,第163页。
4.同上。
5.同上,第163-164页。
6.乔纳森·克拉里著,沈语冰、贺玉高译:《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第268页。
7.同上,第229页。
8.同上,第237页。
9.同上。
10.同上,第238页。
11.沈语冰:《图像与意义:英美现代艺术史论》,第74-75页。
12.同上,第79页。
13.罗杰·弗莱著,沈语冰译:《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2-153页。
14.杨立华:《气本与神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二章。
15.乔纳森·克拉里著,沈语冰、贺玉高译:《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第235页。
16.同上,第237页。
17.同上,第235页。
18.转引自沈语冰:《图像与意义:英美现代艺术史论》,第66页。
20.同上,第75页。
21.迈耶·夏皮罗著,沈语冰、何海译:《现代艺术:19与20世纪》,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34页。
22.乔纳森·克拉里著,沈语冰、贺玉高译:《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第284页。
23.同上,第280页。
24.同上,第283页。
25.同上,第264页。
26.罗杰·弗莱著,沈语冰译:《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第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