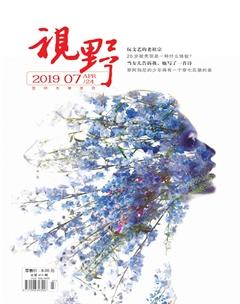致那一瞬间的光芒
程则尔
在什么场合,你会害怕成为被选中的“幸运儿”,并受到全场关注?大概是在集体聚会时,主持人意犹未尽地询问“哪位观众愿意给大家表演个节目”时吧。
通常这样的时刻,气氛明明还没从火热中降温,但除少数有才艺的人有资格淡定地昂着头外,其余人早已把眼神躲向某个角落,心底如同黑云压境。看到主持人朝自己走来,惊惶如笼中鸡兔,或看到主持人正从箱子中抽出一个号码,那两根手指拈起的仿佛是自己的心。直到某个不幸的家伙被抽中,并被掌声和嬉笑声强行推到人群中间时,才终于松了一口气,仿佛刚躲过一场枪林弹雨。
是的,作为没有任何才艺可登大雅之堂的我,曾无数次经历过上述场景;但又偏偏是在那被炙烤的时刻,会不甘心地想那束光明明可以打在自己身上。
小学时,如果不是因为一次一鸣惊人的表现,或许直到毕业之后我也不会注意到坐在我右后方的女孩。她戴很大的黑框眼镜,几乎遮去小半边脸。她不爱说话或走动,每天都在纸上写写画画一些奇怪的东西,是班级里可有可无的存在。
有一次上作文讲评课,语文老师露出惊喜的神色:“这次有篇作文写的是古体诗,我非常喜欢。”说完便向全班分享了这篇佳作。虽说诗中的“明月”“黄沙”“美酒”等意象如今看来稍显平淡,但在当时,的确让我们这群小屁孩惊艳了一番。
这首诗,便出自右后方女孩之手。雷动的掌声中,略显羞涩不安的她,在我心目中瞬间从毫无存在感的角落少女,升格为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古风才女,就连从前的沉默寡言,如今看来都是一种温润如玉的内敛含蓄。
人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审美与想法,也有着不同的信仰与追寻。在为一首诗的魅力而惊艳的稚嫩年纪,我觉得诗人真是一个耀眼的头衔,并且也想成为一名诗人。
我不会写诗,能想到的方法就是不停背诵很多古诗,当一个“不会作诗也会吟”的才子。
那本诗集是我从柜子里“刨”出来的,早已沾满泛黄的时代气息。每天晚上,我都要倚靠着床头翻开它,背一首新的诗词。父母推开房门,难得没有训斥我“超过十点还不睡觉”,而是轻轻退回去带上门,脸上是满意的神色。
不过,这个习惯并未持续很久,后来,就没有后来了。少年的想法不知天高地厚,总是忽略掉日积月累的含义,以为多比别人掌握几首诗词就能成为文艺大咖。当我尴尬地发现,会背几首诗并不能给我带来什么短期收益,甚至无法以具象的表演形式呈现在公众场合时,便又把诗集塞回了柜子深处。
如同我的情怀一样短寿,那个女孩突然享受到的榮光,并没有持续多久,片刻的掌声很快变得稀稀疏疏,将她连同在班级小范围掀起过的诗词热潮,送回沉寂的角落。甜冰棒、游戏机,更多新鲜有趣的事物,源源不断地涌进我们狂放的青春。无人记得那次作文讲评课上的惊艳一刻,也无人想过要将那份惊艳延续下去。
也有过无限趋近那束光的时刻,只差一点,就能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才艺的人。
我已不太记得,当初是怎么与笛子产生联系的,好像是初一某天放学后,我在学校大乐团门口等参与排练的同桌。
这是一个光荣的团体,他们经常在额上点上小红点,胸前佩戴大红花,高调地出现在学校的各种盛会上。当我在走廊上踮起脚,透过窗户看到一群同龄人熟练地用二胡、琵琶、古筝等乐器进行合奏时,感受到了一种神圣并投以羡慕。
学一门乐器吧。这个想法如同西瓜一样,“咕噜”一声从内心深处滚落出来。经历一番自我选择与跌跌撞撞之后,我落到了笛子这个坑里。
从前只知道玩游戏,毫无艺术细胞的我,忽然开窍想学吹笛子了,父母自然乐见其成。然而他们忽略了,我想学乐器的初衷并非热爱音乐或想以此来陶冶情操,而是为了能享受加入大乐团的虚荣,以及一股少年特有的心血来潮。在门类众多的乐器中选择笛子,也只是觉得这种乐器既廉价,又易上手罢了。
其实,一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接触笛子后才知道,这支冷冰冰的竹管子,本身并不能发出悠扬动听的声音,一切都要靠贴在出风口的笛膜的振动来完成。这种脆薄的小纸片极其珍贵,踏遍县城所有乐器店均无出售,竟要远赴省城才能买到。
周末下午,从省城回来的父亲推开门,拍拍裤管上的泥,把一盒被体温焐热的笛膜交给我,连声音里也带了几分倦意:“既然选择学吹笛子,希望你能坚持下去,父母会尽可能为你创造条件,接下来的一切就要看你自己了。”
我的第二个“原以为”,是以为笛子的学习是一个短平快的过程,稍微努力几周,就可以在人前卖弄了。结果单是学会怎么把笛子吹响,就耗去了几天时间。
那时,县少年宫没有笛子老师,父母几经辗转,终于托朋友在川剧团里寻了一位老笛手给我当师父。每个周末,我都要去找师父接受一对一指导。
学吹笛子,从吹单调的音阶开始,先吹上一百遍“哆来咪”,倒过来再吹上一百遍。在少有人烟的三层旧楼里,充斥着荒凉萧索,充斥着我断断续续、错漏百出的吹奏声,以及师父恨铁不成钢的责骂声。
秉承师父教诲,从前玩心颇重的父母,周末时轮番留在家中监督我练习吹笛子。当听到房中已长久偃旗息鼓时,他们总会第一时间警觉地推开房门,看看我是不是又在偷懒。看着令人眼花缭乱的谱子,我在叫苦不迭和后悔不已中,早把加入大乐团的愿望抛到了九霄云外。
在学习了半年以后,我终于不再仅仅重复单调的音符,开始接触一些成形的乐曲,也终于到了父母千盼万盼可以在亲戚朋友面前露上一手的时刻。
一切都是一场预谋。从母亲的几个朋友逛完街经过楼下,被母亲硬拉着上楼坐坐,到端着茶杯的父亲装作不经意地说“我家孩子学吹笛子以后懂事了不少呢”,再到母亲催促我“快给阿姨们表演一曲”,他们耗费心血想要获取的荣光与体面,终于快要瓜熟蒂落。可惜,我那点可怜的“造诣”,只能磕磕绊绊吹完一曲《少林寺》。在阿姨们勉强的鼓掌与称赞中,父母脸上写满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