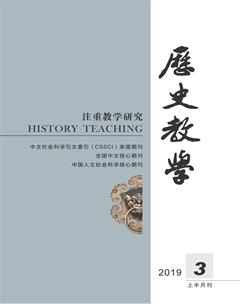革命与暴政的悖论:暴君挑起革命、革命抛弃暴君
编者按:17世纪英国史充满革命的话语,这是英国史上难得的独特现象。这百年间,英国发生了数次内战、审判国王、创建共和、摄政独裁、王朝复辟与宫廷政变等一连串轰轰烈烈、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通过内战和革命,英国掀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在恢复混合君主制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从主权在君(王)到主权在民(议会)的转变,为现代代议民主政治开辟了道路。尽管这场绝无仅有的革命早已走入历史,但它的影响并未尘封,而且还留下了许多悖论,至今让人着迷。诸如:为何挑起革命者既不是下层群众、也不是上层议会反对派,而是专制国王?为何克伦威尔既充满神圣的清教理想、又具有反专制的革命热情,却走上了军事独裁的不归路?为何1688年宫廷政变既孕育于暴力之中、又带有暴力性质,却被称为“光荣革命”?对17世纪英国革命史的研究,中国学界从未停止,但是在对这场革命性质的认识上,长期以来没有变化,即从专题论著到一般读物,从大学课本到中学课堂,只采资产阶级革命一说。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困惑。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英国史研究在不断深入,并取得了许多有深度、能体现中国学者话语特色的新成果。为了及时、充分反映这方面的新进展,本刊从本期起,将连续三期登载南京师范大学姜守明教授关于17世纪英国革命史的专题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作者将这场革命放入16~17世纪社会转型、民族国家建构这个长时段加以考察,把17世纪中叶的革命和1688年“光荣革命”看做是同一场革命的前后两个阶段,详细探析了17世纪英国革命史所呈现出来的三重悖论,即革命与暴政的悖论、革命与独裁的悖论、革命与妥协的悖论,进而得出了关于这场革命同时具有清教革命和宪政革命双重属性的结论。这不仅为我们进一步理解英国革命史提供了观察问题的新视角,也为我们揭示了英国在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过程中追求传统与变革之间平衡的政治文化奥秘。
革命,本意为革故鼎新,通常指是由下层群众发动的、反抗上层统治者政治压迫的暴力运动。暴政,顾名思义,特指统治阶段的残暴施政。17世纪的英国革命,包括17世纪中叶的革命和1688年的宫廷政变,不是由英国广大的普通民众自下而上发起,而是由斯图亚特专制君主以武力形式挑动内战、自上而下开始的。也就是说,17世纪英国革命的发生,并没有依循常规,而斯图亚特专制君主的暴政是引发革命的直接诱因。革命爆发后,议会反对派作为广大民众的代言人,扮演了被动应战者的角色,但他们为了捍卫自古就有的自由与权利传统,就宗教信仰自由和国家主权归属,即究竟是主权在王还是主权在民的问题,与专制君主展开了殊死的较量,最终战胜了暴政。
关键词:革命,暴政,专制君主,议会,自上而下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5-0003-07
一、主权在王与主权在民的争端
主权,即国家主权,是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最高权力,所以现代民族国家又称主权国家。早在16世纪启蒙时代,法国学者让·博丹就在《国家六论》①一文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国家主权的基本理论,并明确提出了主权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主要标志的观念。主权国家,客观地说,对内应当拥有至高无上的司法管辖权,对外则享有独立平等的发展权。在“民族”“国家”观念淡薄的中世纪,如果说存在主权观念的话,那么在教权主义的支配下,基督教世界认同的仅是主权在神的信条,这就排斥了民族国家存在的可能性,也就谈不上平等独立的主权国家。中世纪晚期,民族意识不断增强后,基督教普世主义观念日益受到挑战,人们开始以神权君主取代神化上帝,并用皇权主义代替教权主义,因而主權在王的主张就必然地成为了民族国家形成时期“新君主制”(New Monarchy)的题中之意。
新君主制,即专制君主制,源于中世纪的等级君主制,发轫于15世纪后期,是一种新型的国家体制。②在追求民族国家潮流的过程中,都铎王权已成为国家政治向心力的目标指向,诸位君主前后一致,均集行政、立法与司法大权于一身,不仅享有至高无上的专制地位,③也实现了与国家利益的巧妙结合。都铎王朝的新君主制,在追求专制主义过程中,适应了英国社会转型的现实需要,实现了与民族国家的利益趋同,因而具有历史的进步性。苏格兰的詹姆斯承袭都铎王位后,不列颠岛出现了两王国共一主的局面。这样,英格兰和苏格兰间40多年来争论不休的英格兰王位继承问题暂告一段落。④不过,这也埋下了日后英苏两国正式合并的伏笔。⑤
詹姆斯一世上台后,置英格兰的经济、民生和民族国家利益于不顾,去强化过时的专制主义。都铎朝时期,专制主义既是君主追求私利的手段,也是巩固新兴民族国家的工具。然而,斯图亚特君主不懂此一时、彼一时的道理,严重脱离实际,强力推行专制统治,日益激化与议会的矛盾,逐渐将英伦三岛拖入了多事之秋。早在13世纪初期的大宪章时代,英格兰已形成了国王与贵族联合治理封建国家的混合君主制传统。中世纪盛期,由国王、上院和下院共同组成的议会,作为一种混合君主制模式,构成了英国的等级君主制。及至中世纪末期近代早期,随着启蒙思想出现和民族国家形成,等级君主制发生转向,开始朝着君主专制和议会民主制的方向转变。这种转向不是悄然或平稳进行的,它引发了上层统治者之间的权力斗争,导致了国王与下院关于国家最高权力即国家主权归属问题的争论。斯图亚特君主詹姆斯一世对过时的专制主义的追逐,是17世纪英国关于主权在君(国王)还是主权在民(议会)争论的触点。他不但迷恋中世纪经院神学家阿奎那的“君权神圣”说,还“以一种神学家的自傲和一个国王的自命不凡”,⑥相信上帝的赐予是其作为一个外来君主统治英国合法性的根基。⑦对此,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评论说:“当他被承认为国王以后,他就认为他的君权是神授的。凭这个理由,他以‘神圣的国王陛下自居。”⑧除了论证其承袭英格兰王位的合法性外,詹姆斯他还想通过神化王权的手段来强化其专制统治。他对内实施看似宽容、实则接近天主教的宗教政策,对外追逐所谓的和平主义,实际上是对国际天主教势力的屈从。这不仅违背了中世纪以来英国形成的“王在法下”“王在议会”的混合君主制传统,也严重伤害了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英吉利国家利益。诚然,他暂时平息了与议会之间的争执,但矛盾并没解决,直至日后酿成的内战与革命。
17世纪英国革命的起因,表面上,是斯图亚特王朝这个外来因素偶然作用的结果,实际上,则是都铎朝末期以来英伦社会矛盾积聚与激化的产物。准确地说,它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就是反传统与维护传统的两股力量相互较量的结果。从理论上讲,詹姆斯继承都铎王统顺理成章,而问题在于,他在推行专制统治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现象;尤其查理一世在处理宗教、征税、外交等事务以及偏袒宠臣方面,不但狂妄固执,独断专行,还严重背离了都铎朝以来君主倚重贵族、国王与议会联合统治的混合君主制传统。如果说詹姆斯在奉行专制主义时是理论上的巨人和行动上的矮子,那么可以说,查理在推行大陆式的绝对专制主义时,不遗余力,完全是个莽撞的“实干家”。一方面,他利用高教会派国教徒推动所谓的宗教“革新”政策,过于纵容国内的天主教徒,残酷迫害遍布朝野的清教徒,严重伤害了国人的宗教情感;另一方面,他从不想召集议会,除非为了财政拨款的目的,又不得不求助于议会。欧洲“三十年战争”爆发后,议会动用财政审批权来反制查理,只批准了一项14万镑的拨款让他用于海外战争。虽然作为一种安慰和补偿,下院赋予查理为期一年的关税征收权,还是拒绝了他提出的终身征收关税的要求。①1625年8月查理解散了处处掣肘他的议会。在议会的召集与解散问题上,查理激化了专制王权与议会的矛盾。到40年代初,这种矛盾终于以极端的形式爆发出来。
二、议会反对派与王党的殊死较量
英伦的内战是斯图亚特君主专制和议会反专制的力量之间相互较量的结果,它作为17世纪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以下一些鲜明特点:
第一,宗教热情与政治主张相结合。英国著名法学家白芝浩指出:“如果没有受到宗教理论的推动的话,单单政治原因在当时是不足以激发人们对国王进行这样一种反抗的。”②内战爆发时,王党和议会反对派的地域分界和宗教分野都非常清晰。从地域分布情况看,王党力量主要集中在英格兰的北部和西部地区,议会力量则散布于英格兰的东部和南部地区。从宗教信仰审视,凡是国教徒和天主教徒都站到了国王及王党一边,而新教不从国教的清教徒则站在了议会一边。在议会反对派阵营内部,既有不同的宗教态度,又有相左的政治诉求。在神学教义和教会组织方面,长老派接近于大陆的加尔文派,他们要求废除国教会的主教制,坚持由选举出来的“长老”来管理教会;在政治诉求方面,他们提倡精英政治,倾向于寡头治国。③比较而言,独立派要激进得多,他们不承认全国性的教会权威,认为各地的教众都可以自由组成独立的宗教团体;④在政治上,他们不仅主张废除君主制,还置疑贵族统治的合理性。由于各自独立的组织形式和不同的礼拜方式,独立派内部又分成许多宗派,诸如温和而理性的浸礼派、公理派、教友派,⑤激进与极端的第五王国派、震颤派、平等派,等等。宗教倾向和政治理想相对应,这一点看起来很奇特,但并不难理解,因为对各政治派别而言,宗教信仰在革命过程中发挥了意识形态上的重要作用,难怪乎有学者把英国革命看成是一场清教革命。⑥笔者同意这种看法,诚如钱乘旦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英国革命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宗教的政治化,当然政治也宗教化,政治理念都是用宗教语言来表达的”。⑦
第二,政治分裂并不显示阶级区分。在革命中,两个对垒阵营没有太大的区别,对立双方队伍的构成中,各有贵族、乡绅,也有富商和小商人,还有小土地所有者、手工工匠和佃农。从占比情况来看,两个敌对集团的力量大体相当,而这种分裂局面又使阶级分野变得十分模糊,因而很难从阶级的角度去判别这场革命的属性。有人认为它属于一场资产阶级革命,①不过笔者指出,这种看法的不足之处在于无法判明谁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当时正值原始积累阶段,萌芽中的资产阶级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所以“资产阶级革命”说难以成立。②
第三,专制国王扮演了触发革命的角色。从长时段来审视,革命并非英国史的常态,17世纪革命只是一个偶然插曲。如果都铎王位不是由斯图亚特君主来继承,如果詹姆斯一世能像伊丽莎白女王那样把英吉利民族作为其统治的依靠,如果查理一世不固执地效法大陆的绝对专制主义,或许英国就不会发生涉及信仰自由和国家主权归属的严重危机,那么革命也无从谈起。然而,那些假设偏偏能从17世纪初叶英国史上找出凿凿证据,谁都不能视而不见,故发生革命就在情理之中。1642年8月,查理在诺丁汉的卡斯尔山上举起皇家旗帜,宣称议会叛乱,这标志着英王及王党分子正式向议会反对派和人民宣战,③从而拉开了英国内战的序幕。10月23日,激战首先在沃里克郡南部边山附近发生,双方有大约5000名士兵战死沙场。④此后,查理率军进入泰晤士河谷地区,把大本营设在了与伦敦相距82公里之遥的牛津。同年11月,王军占领了英格兰北部五郡,次年5月在康沃尔郡的斯特拉顿战斗中又击败议会军。是年秋,拉尔夫·霍普顿爵士从西部、威廉·卡文迪什从北部、查理从牛津向伦敦进军,东南部形势吃紧。开战之初,议会军之连遭败绩,主要原因在于:其一,战争由国王挑起,拼凑起来的议会军仓促应战,整体实力不及王军;其二,议会军战略目标含糊,缺乏统一指挥中心;其三,议会军疑虑与国王武装对抗的正当性,不敢放开手脚,不敢打败国王。如东部联军指挥官曼彻斯特伯爵就说过,如果我们打败国王99次,他仍是国王,他的后代也都是国王;但如果国王只打败我们一次,那么我们就要被统统绞死。⑤既然清教领袖持这种心态,那就可想而知,议会军在战争初期连连失利并非无以为根由。
不过,革命呈现的形式往往是似急风暴雨,或动力强劲的列车,它一经启动,在强大的动力和惯性的作用下,会向前猛冲,势不可挡,而想要立刻制动下来,几不可能。为了扭转战场上的不利局面,议会党人尝试与苏格兰人结盟。在北方,苏格兰人反抗查理的专制统治,对于英国革命来说,起到了导火线的作用。现在英国的议会党人谋求与新教长老会支配下的苏格兰人结盟,这种举动合乎逻辑。根据1643年8月签订的《神圣盟约》(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苏格兰盟约派应出兵帮助议会党人,英国议会则须向盟约派提供军费每月3万镑,并承诺在苏格兰、英格兰与爱尔兰组建起统一的长老派教会。这个誓约的签订,意味着英格兰人与苏格兰人联手对抗专制国王,也標志着清教在反对国教的斗争中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反对天主教、实现信仰自由,是英国革命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显然,结盟双方是各有所求,正如苏格兰牧师罗伯特·贝利所评论的那样:“英格兰人追求的是建立一个世俗的同盟,我们的目的却是建立一个宗教同盟。”⑥为了制服与盟约派联手的议会反对派,查理便向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寻求帮助。这样,“不仅原来在爱尔兰服役的许多英国兵为他效劳,而且大批爱尔兰人也参加了他的军队”。①尽管如此,战场上的主动权还是由王军渐渐转向了议会军。1644年初,21000名苏格兰士兵从边境上渡过特威德河后,在英格兰北方对王军起了牵制作用。7月初,王军大败于马斯顿荒原大战。次年6月14日,查理和他的外甥、莱茵选侯之子鲁珀特亲王指挥7500名王军,与费尔法克斯爵士和克伦威尔指挥13500名议会军,在纳斯比战役中对阵并遭败绩,而以“铁骑军”(Ironsides)为核心的议会新军对战胜王军发挥了决定性作用。②
三、革命抛弃查理一世的必然性
第一次内战结束后,议会党人、盟约派与他们的共主查理一世进行了数月之久马拉松式谈判,无果后内战再起,王军又告失败,直至查理被押上了审判台。查理之所以被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所抛弃,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苏格兰人对查理的冥顽不化感到极度失望。在内战中,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共同打败了他们的国王,但盟约派向议会反对派提供帮助是有条件的,除了要求把长老会确定为英国国教外,还要求给予参战经费补偿。③内战初期,英格兰人迫于战争压力,接受了长老会色彩浓厚的《神圣盟约》;内战初告胜利后,长老会顺势取得了英国国教地位。此时,苏格兰人对国王还是心存幻想,希望能得到他同样的承诺,以为那样的话,长老会就能在英国站稳脚跟。不过,查理自投罗网、遁入了苏格兰军营,只是想找个临时落脚点,而无意到苏格兰去避难,更不会满足苏格兰人的愿望。在与苏格兰谈判时,他还暗中与法国往来,甚至还希望爱尔兰能向他伸出援手,提供军事援助。但是,苏格兰人已经意识到在他们的国王身上榨不出什么油水,便决定予以抛弃了。1647年2月,查理被交给了英国议会军。
其次,英国的清教独立派和长老派的合作是战胜查理的保证。在与国王谈判时,议会反对派答应恢复查理的王权,前提是他必须接受由威斯敏斯特议会起草的《纽卡斯尔建议》(Newcastle Propositions),其主要精神是废除主教制,惩罚内战中的王党分子,严格实施反天主教法,建立长老会制度,并由议会掌握军事力量、任命国家的主要行政官员和法官。这也是第一次内战结束后议会反对派与查理谈判的条件。查理以为接受这些条件等于束住自己的手脚,他还考虑到议会本身也非铁板一块,因而他想继续利用长老派和独立派之间矛盾,④拖延谈判,以期获得最大化利益。三年前从牛津出逃时,查理就这样说过:“我要诱致长老会派和独立派与我联合,以借此叫两派互相消灭,我是决不放弃这样干的机会的,那样一来,不久我又是国王了。”⑤在反专制问题上,虽然长老派和独立派有矛盾,但他们既合作又斗争,而合作对他们来说都是权宜之策,彼此的矛盾并未消除。当他们打败国王、胜利曙光初现时,他们在如何对待查理及苏格兰人问题上又产生了分歧。独立派深知,长老派与国王、长老派及苏格兰人的共性,远大于他们彼此间的差异,因而特别担心长老派与国王的结盟,也对长老派与盟约派的联手感到忧虑。不论哪种情况出现,独立派害怕他们在战争中的一切成果都将化为乌有。幸好他们还掌握着议会军,由于军队赢得了战场上的胜利,他们就以军队来维护胜利果实。因此,新教独立派和长老派的斗争就主要表现为军队和军队的缔造者议会之间的斗争。8月新模范军开进伦敦,他们以武力占领了议会大厦,导致力量的天平朝着军队和独立派一侧倾斜。此时,独立派领袖克伦威尔和高级军官们都对查理寄予希望,并公布了一份与他谈判的《建议要点》(Heads of Proposals)。由于查理尤为反感关于限制王权、限制主教权威、由军队、议会和国王三者分享国家权力的条款,他拒绝了《建议要点》。
再次,由独立派操控的议会军是反制查理的重要工具。由于宗教信仰有差和政治态度不同,独立派和长老派只有采取联合一致的行动才能迫使国王就范,而一旦王党获得喘息的机会,那就意味着专制王权的回归,那样议会反对派势必前功尽弃,英国将会完全中断四百年来形成的议会传统。但是,高级军官对国王的妥协态度,激化了军队内部独立派与平等派的矛盾。1647年10至11月间,在伦敦西南部的普特尼召开的全军会议,围绕着内战后秩序重建,尤其国体安排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独立派妥协的色彩极为鲜明,他们坚持《建议要点》,主张保留君主制和上院;平等派则提出了激进的政治纲领《人民公约》(An Agreement of the People),他们要求废除君主制和上院,建立一院制的议会。关于选举权问题,高级军官认为财产是选举资格的必要条件,只有财产才能出创造负责任的选民,确保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平等派反驳说,生活在英国土地上的所有居民,包括最贫穷者和最富有者,都应当享有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因而他们主张实行成年男子普选权。①普特尼辩论越来越激烈,克伦威尔眼看无法收场,只得强行予以终止。
最后,查理与苏格兰人的勾连加速了他的失败。高级军官压制了平等派势力后,独立派完全控制了军队。恰逢此时,查理却逃离囚禁地汉普顿宫,逃往了与汉普郡南部海岸相距几英里的怀特岛。这样,他就失去了议会和军队的信任,也促成了独立派与平等派的重新联合。议会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提出四项条件,包括由议会控制陆、海军事力量20年,及议会自行决定休会时间和开会地点等,②但是均遭查理的拒绝。很快,查理又转向苏格兰人,并于12月26日签订《密约》。据此,他承诺将在三年内强行推广长老会教派,镇压独立派和其他异端团体;③苏格兰人同意恢复其王权,还答应将派遣军队帮国王与议会军作战。1648年1月王党在多地发生暴乱,内战再起,参与者有议员、地主、商人,还有伦敦市民和乡民、主教和长老派,以及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等,如此庞杂的成分,这是第一次内战中不曾出现的现象。面对严峻的形势,克伦威尔不得不向平等派作出让步,答应在战争结束后取消上院、审判国王和释放魏尔事件④中被捕的军官。8月17~19日,他率议会军与苏格兰-查理联军在兰开郡普雷斯顿附近决战,并大获全胜,第二次内战基本结束。
然而,议会反对派内部又现分裂迹象。第二次内战尚在进行时,长老派就暗中勾结苏格兰人及王党分子,因而此刻,军队与议会的裂痕更进一步扩大。为阻止议会同查理的往来,軍队再次开进首都,司令部设在了王室白厅宫内的国王官邸。他们还把查理从怀特岛押解到南部海岸的一个荒凉海角,将他囚禁在一间黑屋里。虽然军队要求议会停止与查理的谈判,并将他作为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交付审判,但议会仍与他保持来往。在这种情况下,托马斯·普莱德上校奉军队委员会之命,率军占领威斯敏斯特宫,把140名长老派议员逐出议会。值得注意的是,1640年11月“长期议会”(Long Parliament)召开时,共有议员490名;及内战爆发,过半议员已转投王党阵营;而剩下的半数议员,现在又有1/2遭清洗。这样,议员总数还有不到90名,长期议会竟变成了“残缺议会”(Rump Parliament)。革命是暴力斗争,服从暴力是一切革命的逻辑。英国革命也不例外。“普莱德清洗”事件充分表明,暴力在权力斗争中更有威力。在独立派的主导下,残缺议会声称查理因“发动战争反对议会和英格兰王国”而犯下叛逆罪。①为此,下院决定设立特别法庭,规定该法庭由3名法官和150名陪审员组成,但是上院否定了下院的决议,其理由是国王作为英国的司法之源,是法院的最高长官,不可能对其进行审判。既然如此,下院索性撇开上院,独自特设法庭,组成人员也减少到了135名。呜呼,查理本是革命的发动者,却不得不接受革命法庭的审判,而罪名竟然是叛国罪或叛逆罪。所谓叛逆,本指臣民涉及危害国王的人身安全及其统治权的行为,现在作为一国之君的查理竟然成为了叛逆罪的适用对象。虽然残缺议会因组成人数严重不足而失去了作为代议机构的合法性,但是,它通过暴力手段设立革命法庭,将置合法的君主于死地,并为他们处死查理的极端行为作出辩护:“在上帝之下,人民是一切正当权力的来源;在议会里集会的英国下议院是人民选出并代表人民的,在本国有最高的权力……”②虽然查理认为该法庭不具合法性,并拒绝作自我辩护,特别法庭依然以“暴君、叛徒、杀人犯及国家的敌人”的罪名,于1649年1月30日将英王查理一世推上了断头台。这样,英国革命迎来了第一个高潮。
我们看到,革命发起者不是英国人民,而是斯图亚特专制国王,查理一世成为他挑起的革命的牺牲品,完全是搬起石头打自己脚。查理的受审与受死,不论当时还是后来,都引起了不少的同情。这是事实。然而对他而言,其悲剧根源不在于他是否挑起革命,而在于他非但像他父亲詹姆斯那样笃信君权神授论,他还固执地依据这种过时的理论行事;更为可悲的还在于,他始终都不明白其权力的终极来源,并不是他笃信的基督教上帝,而是其臣民,也就是没有被他放在心中的英吉利民族。最终,革命将他彻底抛弃。这就是革命的威力,这就是暴力的权威,这就是17世纪英国革命的辩证法。
【作者简介】姜守明,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李婷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