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风里
余同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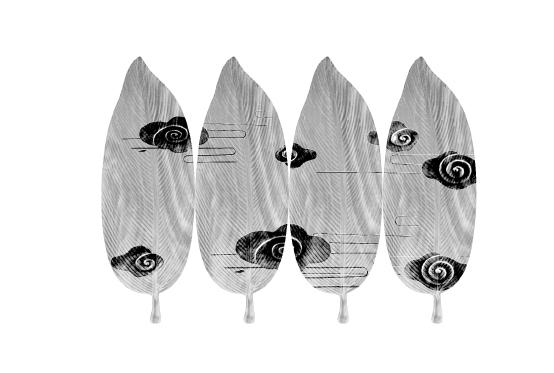
是老甫最先發现那个僧人的。
这天是星期五,按照老甫和小周订立的条约,今天轮到他先使用厨房,等他使用到五点半就由小周接管。五点半刚到,小周就掐着秒冲进了厨房,取下他挂在墙上的砧板、菜刀,拧开水龙头,摆出一副要烧一餐满汉全席的架势。老甫冷笑一声,这个周扒皮不过是故意要把我赶出去罢了,他害不了我,老子早烧好了!他用托盘端着自己才做好的饭菜到了厨房左边一排教室的走廊下,一碟油爆花生米,一盘青椒豆腐干,还有一小碟蒸酱豆,一一摆放在他先前就支好的小课桌上,随后他又从屁股后的口袋摸出了一个扁酒壶,旋开壶盖,把酒倒在壶盖里。还没坐稳当,老甫就迫不及待地喝了一小口,眯着眼,夹了粒花生米放嘴里,嚼了好一会儿才睁开眼睛。
这是老甫一天当中最享受的时刻。他喝一口酒,吃一口菜,闭一会儿眼,再睁一下眼,闭眼时品酒,睁眼时看景,看的什么景?看的是西边的山峰和云彩,一般这个时候,西天上晚霞紫红,把远山近岭映得像一幅画。老甫在县志上看到介绍,说唐朝时候那个叫李白的大诗人曾到过这里,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明镜”指的就是山外的秋浦河,而“屏风里”写的就是这深山景象,所以,后来这一片大山就叫“屏风里”了。老甫一想到这,就觉得自己是个文化人,肚里不光有酒,还有学问,不愧为一名人民教师,不像那个周扒皮,天天捧着个手机看球赛打游戏。哼哼,他扫了一眼厨房里的小周——还有一点为人师表的样子么?
小周在厨房里弄出的动静不小,像打铁一样,但到底厨艺不精,哐里哐当,忙了半天,做了一个青椒炒鸡蛋,青椒还是生的,鸡蛋却已焦糊,下了一碗面,没掌握好时间,面条板结成了一砣面疙瘩。小周瞥见老甫那悠然自得的样子,心里就来火,这个老甫就是《红岩》里的“甫志高”,人民的叛徒。他不想让老甫看见他做的不成功的作品,老甫看到后,嘴角会斜挂左耳朵边上去,一脸的幸灾乐祸,这是绝不能接受的。小周便急速地蹲在厨房里,硬着头皮把那焦糊的菜与面扒到嘴里吞下去,吞得脖子像鸡嗉子哽了好几下。
老甫其实早就闻到了厨房里的焦糊味,他也早就把自己的嘴角斜挂到左耳朵边上去了,活该!你能得像豆子一样呵,你能啊!他把一口酒喝得格外有滋有味,故意嘬出了一阵滋滋响,再抬头去看景。他就是在这个时候看见了那个僧人的。
平常的日子,这深山野洼里根本见不到一个外人。屏风里村拢共六十多户人家,青壮年大多在外打工,常住在村里的不到一百人,其中就包含16个在屏风里教学点念书的一二两个年级的学生,一年级6个,二年级10个。老甫估计等他一年后退休时,一年级恐怕只能招到两三个学生了。所以,每天放学铃一响,学生们的身影消失在山道上后,校园空荡荡的像一口古钟,就差一个敲钟的和尚了。老甫自嘲,这哪是学校呵,这就是座庙。没想到,今天竟然真的来了一个僧人。
屏风里教学点建在半山腰上,视线还是挺开阔的,进山出山的山道就悬挂在西边的山上,一有人出现,立马就会被看见。有时,有些顽皮的学生贪玩,回家时不好好走路,在山道边东窜西跳捉虫打鸟,老甫都会居高临下地看见,就扯了喉咙喊:魏振强,快回家!操礼兵,你明天可想罚站!可是这个僧人像是突然从山林里冒出来的,老甫发现他的时候,已经在两百米开外了。老甫有点奇怪,怎么先前自己望着西天里就没有看到这僧人呢?他难道真的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老甫无聊时,常在山林里走,确实有时会发现走熟了的草地上突然冒出一棵两棵蘑菇,顶着个光头也确实像个拄杖而行的僧人,可那一般是在雨后呵。老甫又想,可能是今天的晚霞太美了,太灿烂了,江山如此多娇,晚霞如此妖娆,糊住了他的眼睛了,让他没有及时发现山道上的人影。
那人越来越近了,这可是个标准的僧人,头皮剃得光溜溜的,穿着青灰色的僧衣,背着一个佛黄色的包袱,胸前还挂着一串大大的佛珠。老甫端起了酒壶盖却忘记了喝酒,“和尚!”他叫了一声,猛地站起来,愣愣地看着前方。
小周这时也发现了那个僧人。在迅速地吞完这餐不成功的晚饭后,他想像往常一样,爬到校园操场边的那棵大枫杨树上去。他试了很多次了,只有爬上大枫杨树,微弱的手机网络信号才最稳定,他得抓紧时间下载昨晚的意甲联赛实况录像,好留着晚上看。他抬起头目不斜视地走过教室走廊,好像并不存在老甫这个人,他不仅关闭了视觉,甚至连嗅觉也关闭了。他不想闻到老甫小课桌上的饭菜香,这个叛徒,菜倒是烧得有点水平,香气到处飘,这不就是想诱惑我寒碜我吗?事实上,关闭嗅觉是比较困难的,你总不能不呼吸吧,这一呼吸,那香味就固执地钻进了鼻孔,怎么躲都躲不掉。小周因此加快步伐,几乎是一路跑向大枫杨树。就在这时,他看见那个和尚飘也似的飘进了校园。他像老甫一样,顿住了脚,张大了嘴。他不由看了老甫一眼,虽然这辈子他再也不想看老甫一眼。
两个人半年来第一次对了一下眼神,又迅速地移开了。他们像两只青蛙样鼓起大眼睛盯着这个突然到来的和尚。
和尚约摸四十岁上下,面色沉静,他口中念着“阿弥陀佛”,双手合十分别朝老甫和小周施礼。
老甫和小周平时也怎么没接触过和尚,不知道怎么应对,慌里慌张地,临时也学着和尚的样子,合掌还礼,不住地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一阵慌乱过后,夕阳落山了,四下里黑下来,黑得有点突然,和尚的面容就隐在了朦胧的夜色里,几只夜老鼠(蝙蝠)上下翻飞。
老甫拉亮了走廊上的电灯,昏黄的灯光雾一样照在操场上。老甫问,“师父,你,来这里做什么?”
小周不等和尚回答,便“哧”了一声嘲笑老甫这个问话好愚蠢,“大师,你是来化缘的吧?可我们这里也没什么吃的呀。”
和尚仍然静静地立着,他又双掌合十道:“不劳烦二位老师,我就是借你们这个操场今晚做一场法事,盼行个方便,可以吗?”
做场法事?老甫和小周的目光再一次碰撞了一下,到这里来做什么法事?可他们俩谁都没问为什么在这儿做,又为谁做。不管是法事还是什么事,这地方好久都没发生过什么新鲜事了,管他呢,他做着我看着,又不收门票,又不费流量,你做吧,做吧。
老甫和小周第一次达成了一致,他们立即同意:可以,可以。
老甫认为做法事那得人越多越好,不就是要个热闹吗,便说:“要不要我再叫几个人来?虽然我只是个小小的老师,但这里的老百姓还是挺尊重我的,我叫他们来他们还是会给面子的。”老甫说到这里,一脸的兴奋,小周都能看见他暗藏的尾巴快要翘到天上去了。
和尚连忙说:“不用,不用,谁都不要喊。”和尚虽然样子很谦卑和善,但语气里有凛然不可犯的意思,看那意思,他是真不想有外人来打扰他。
老甫却坚持着,“不麻烦的,不麻烦,我招呼一声他们都要来的。”
和尚直接将合掌的手势改为摆手了,“老师不用,老师不用,这个法事就是不要人多。”
老甫有点不甘心,准备再劝说一下,却听见小周在一旁重重地“切”了一声。老甫要说出的话便生生地被“切”断了。
小周斜眼看着老甫,他特别看不惯老甫时时处处把自己当一棵葱的样子,这什么德性!自己人生的第一大不幸是到了这鸟不生蛋的屏风里来了,第二大不幸就是偏偏遇到了这货!
小周是半年前到屏风里教学点来当老师的,本来他是应该三年前就来的。
三年前毕业于当地师范学院的小周通过了教师入编考试,分配到了屏风里,当他也是在这样一个黄昏夹起行李来到这个教学点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喝得晕晕乎乎的老甫。
老甫当时穿着肥大的裤衩,袒露着上身,一身肥肉堆在一张课桌椅前,他喝多了,现在想起来,可能老甫是故意要喝多的,他明知道小周那天要去学校报到。老甫一见到小周,立即把嘴角斜挂到左耳朵根子上,“哈哈,”他指着小周大笑,“小伙子,请问,你是因为犯了什么罪被发配到这里来了?”
小周本来就一肚子怨恨,他没想到第一天来到这孤山野洼里,就被一个糟老头这么问,他扔下行李冷着脸说,“因为什么?因为老子杀人了!”
老甫被这句话呛住了,他愣了一下,又喝了一杯酒,笑了起来,“哈哈哈,不错,不错,到这鬼地方,你就是想要杀人,你迟早会杀人!”他笑着笑着,头一歪在小课桌椅上睡了过去,课桌椅太小,放不下他那一大堆肉,他很快就滑到了地上,仰躺在地上睡着了。一群绿头苍蝇在他面前的酒菜上停驻片刻,又降落在他肥大的嘴唇上搓脸搓脚,他也不知道去驱赶,片刻后鼾声如雷。
到屏风里教学点的第一个晚上,小周根本没有睡着,他没想到,县教育局会将他分配到这样一个鬼地方来,听着老甫的鼾声,他干脆连行李都没有打开,第二天一早就下山了。到了县城,他去了教育局人事科,坚决要求改派,人事科长说,“你以为学校是你家菜园门?你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小周狠下心来说,“那我就停薪留职吧,那个鬼地方,我是再不想去了”。小周摸摸口袋里最后的五百块钱,拎着行李,直接买了张去省城的火车票,“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他冲着县城撂下了这句话。
那是辆绿皮慢火车,慢腾腾地行走在初秋的大地上,但小周的心里却像春天一样生机勃发,24岁的他伏在火车卡座上热血沸腾,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想象。
小周觉得自己毅然决然地离开山窝窝里的屏风里教学点实在是太伟大的决策了,在省城做了几个月保安,稳定下来后,小周终于应聘到一家房地产策划代理公司做文案策划。虽然小周读书读的是一所二本师范类学校,但好歹大学四年里一直就喜欢写诗,那些诗总算没白写,这让他的文案总是有股喷涌的诗意,比如,“22度的气温,180度的景观,360度的幸福”之类的屁话,明知是假的,老板却拍手叫好。“说白了,卖房子就是卖想象力”。这是老板的口头禅。公司是个小公司,只有一间办公室,除了老板外,就是一个会计,算上小周就三个工作人员,但老板的口气却很大:“我们要做省城房产广告领跑者!小周,你好好干!”
深得老板赏识的小周干得格外卖力,老板给他发了几个月工资后,对他说,“你是大才,兄弟,我们合伙干吧”。老板让他任策划创意部经理,看着亮闪闪的名片上亮闪闪的头衔,他对老板感激涕零,恨不得对老板磕几个响头。
士为知己者死呵,为了给公司省钱,小周文案也写,接待也做,甚至去印刷厂背广告材料,反正哪里需要哪里去。这天下午,公司为一家客户在户外挂广告牌,本来要请两个民工的,但老板让小周只请一个,另一个吗,不用说就让小周自己亲自上阵。小周二话没说就去了现场,不料,那个从路边请来挂广告牌的老汉,一失足从高处摔落下来,老汉不经摔,当场跌得人事不知。
小周打电话给老板,老板责怪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便把电话挂了。
小周只好把老汉抱起来送到医院。身上一千二百元本来交房租的钱,全部用来垫付了医药费。老板始终不出面,一星期过去,花掉了小周工作一年多来一万多元的积蓄。后来,他留下五百元生活费,把身上剩下的两千多元又全部垫了进去。那老汉被确诊为植物人,病人家属将他们告上法院,小周成为两个被告之一,另一个是公司的法人老板。小周庆幸的是,一审判决中,他被判无过错。但小周高兴不起来。因为看到法庭上的证词后,他发现,那个看起来那么豪氣的老板把所有责任都往他身上推,此前老板负担医药费的承诺,早已绝口不提,小周想不通,自己的所有积蓄全搭进去了,所谓兄弟情义换来的不过是直接对自己不利的证词。等小周再想找到老板时,老板失踪了,那个广告公司的办公室早已经转租给别人了。
小周身上又只剩下不到五百块钱了,和他来省城时一样,等于两年多来,他辛辛苦苦算是白干了。小周不想认输,屏风里反正他是不想回去了。他坚持在省城打临工,打了半年,也只是糊个肚子饱。他发现,原来这个世界诗人还是太多了,再没有哪个广告公司要他这个诗人。忽然有一天好运来了,一个以前做广告时认识的朋友打电话给他,让他去广西,说他们公司正在招聘人才,他已经向老总强力推荐了小周,老总很希望小周去辅佐他,一起创业。小周承认,正是那“辅佐”两个字让他再次热血沸腾,何况,那个邀请他去广西的人,当年落魄时,吃在他那里,住在他那里,算是患难之交。更何况,这个时候,走投无路的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小周又坐着绿皮慢火车,穿越大半个中国到了南宁,那个当年他曾帮助过的兄弟,因为业务太忙没有去火车站接他,通过手机电话一步步引导,将他引到了南宁郊区的一个小院里。那时是黄昏时分了,一轮红红的大大的圆圆的南中国的夕阳挂在院墙外一棵大榕树上。当身后小院的大门“咣当”一声被关闭上锁时,小周突然意识到,他恐怕是掉进了一个传销骗局了。他想喊什么,却喊不出来,那轮红日“咣当”落下去了。
小周在那个院子里待了半年多,终于瞅着一个机会,翻过围墙跑了,在没命的奔跑中,他的一条腿摔坏了,又没有及时治疗,留下的后遗症便是他的左腿比右腿短了几公分,这让他走起路来,总是右腿用力着地向前,左腿迅速地点一下地面,紧跟上右腿,如是往复像是在度量着什么。在异乡的小旅馆里,小周在镜子里看见自己走路的这副模样,禁不住大哭了一场,他彻底灰心了,好马不吃回头草,但他认为自己根本就是一匹孬马,一匹跛脚马还有什么想法呢。他回到了县里,还好,县教育局正愁着派不出人到屏风里,便又让他回去了,好歹算是有了一个吃饭的地方。
小周又回到了屏风里,这是老甫没想到的。老甫那天没有喝酒,他想和这个超级倒霉蛋开个玩笑:“哟,你这是准备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没想到小周却开不起玩笑,阴着脸,拖着那双度量器般的残腿,疯了般扑到老甫面前,什么话也不说,恶狠狠地一把封住了老甫的衣领,勒得老甫翻着大眼睛喘不过气来。
从那以后,两个人再不说话,实在需要说话,就写在纸上,比如,两个人必须共用一间厨房,怎么用,他们就在纸上起草了一个使用协议,详细注明了使用时间、注意事项等等;一学期要去两次镇上中心学校开会,一次是学期开始去领课本、教学参考,一次是学期结束去领期末考试卷子,该谁去,他们早早列好日期,一人一次轮着来。老甫本来是个热闹人,平时就好说个话拌个嘴,他没想到小周这家伙竟然这么倔,倔到就是不跟他说话。老甫有好几次都故意示弱了,没话找话地在他面前递上话把子,小周硬是不接茬。学校本来就冷清,这样一来活脱脱就是古庙里住进了两个哑和尚。
没人和老甫说话,老甫一个大活人也不能让话憋死,他就一个人自己对自己说话,特别是喝了几两酒后,他先是骂自己,你个傻鸟,你活该,你没长脑子,你就不知道那些人说话不算话?你倒霉你活该!他抹了一把鼻涕后,就又骂校长,狗日的校长,你把我卖了,我还帮你数钱哩,你牛逼,你狠!你不得好死!呜呜!老甫越骂越起劲,他索性在操场上转着圈子骂,一般是转到第三圈的时候,他就会骂教育局长,什么鸟局长,你他妈的欺负一个普通老师,你他妈的生个儿子没屁眼!到第四圈,他就会骂一个姓郭的,这个时候,他的嗓子已经有点哑了,骂出来声音像钝刀砍柴,姓郭的,你不就几个臭钱吗?你那些钱都是滴着血的肮脏的黑钱!你讲不讲道理?你们讲不讲道理?呜呜!
老甫骂也骂累了,转圈也转累了,就突然住口,走到校园外一条小溪边洗脸,听到不远处一只哼子鹰发出一声悠长的哼声:哼——哼——他就回屋睡觉了。
小周开始不知道老甫天天骂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后来到镇里开会,才隐约从别人嘴里知道一些情况。原来,老甫四年前还是城关镇小学的一名老师,那一年被抽调到县中参加高考监考。监考程序要求老师拿着金属探测仪探测学生有没有夹带什么电子工具以防作弊。老甫积极地拿着探测仪在教室里转,转到一个考生身边时,发出了“滴”的一声警报。老甫确定是那考生的眼镜有问题,因为仪器一碰上眼镜就叫,于是就拿走了那名学生的眼镜,报告到考场主监那里,主监又报告到考区总监那里。过了半小时,眼镜拿回来了,说是经查验没有问题,又交由老甫亲手退还给了考生。不料,考试结束后,那考生家长把老甫告了,说老甫无故没收了考生的眼镜,严重影响了考生的心情和看题,致使考生发挥失常,要求老甫负责,顺带着,这家长还把学校和教育局也告了。老甫觉得这叫什么事呵,拿着探测仪去探测可是上头的命令,怕什么。可是,老甫没想到,这事不知怎么被媒体知道了,网上闹得热火朝天,县里风向立即变了,最后竟然决定让老甫当替死鬼,处理结果是将老甫的职称从副高降到中级,又调离城关镇,发配到屏风里教学点。我靠!老甫傻眼了。老甫去找校长、找局长,校长、局长苦着脸对他说,那个考生家长是一个姓郭的老板,家里开矿山,势力大着呢,媒体都被他撬动了,他还找到县长那里去了。没办法,暂时让你老哥委屈一下,这么着,你先下去待个半年,风头过去了,我立即把你调回来,直接调到局里教研室任教研员!我说到做到,局长拍着他的肥厚的胸脯说。
老甫只好卷铺盖,悄悄来到屏风里,他指望着局长半年后将他调回去,可是,他待了足足一年,局长也不提这个事,他去找局长,局长不见他,再找,局长已经换了一个局当局长了。老甫足足在屏风里待了四年了,再过一年他就要退休了,老甫憋闷不已,日他妈的,所以老甫到屏风里后见什么都想骂,见什么都要骂他个祖宗十八代。
所以,这当口,老甫听见小周当着和尚的面,从鼻孔里哼出的那声“切”,把他的话头“切”断了,他头发梢子上直冒火,他想发作,想骂人。但看看小周那副好斗公雞的样子,他暂时噤声了,他不想脖子再被这家伙勒一把,这家伙腿是瘸了,手上的力气还在,老甫知道自己蛮干是干不过他的。
老甫只好罢了请村民来凑热闹的念头,但总有点不甘心,便问和尚:“那需要我做什么吗?师父,你别客气,你只管吩咐呵。”
和尚笑笑说:“不劳烦,不劳烦,有需要时再求助二位老师。阿弥陀佛!”
和尚放下背着的包袱,从里面抽出一个小包来,打开,是一个野外旅行帐篷,三两下儿就在空地上支了起来,又铺上了防潮垫。这玩意儿小周以前在省城见人玩过,老甫却大惊小怪地啧啧不已,不时问这问那。和尚很有耐心,不喜不忧不咸不淡地应答着,手上却不停歇。帐篷支好后,他又摸出另一个袋子,里面装的是做法事的器物。一个木鱼,几枝蜡烛,一束檀香。全都整齐地摆放在帐篷前。做好了这一切,和尚盘腿趺坐在帐篷里,轻喝了一口茶,眼睛看着老甫和小周。
破天荒地,老甫和小周不约而同地问了一句:“开始了?”
和尚微笑着说:“没有,十点三十二分开始。”
和尚的神情中有一种肃穆的不可移动的东西,老甫和小周不由得也跟着庄重起来,他们点了点头,选择坐在离和尚不远的地方。老甫坐在操场东头的水泥做的乒乓球台上,他也试图像和尚一样盘着腿,但他太胖了,单盘双盘都盘不起来,只好取蹲坐式。小周还是攀爬到西头那棵大枫杨树上,他一边下载德甲联赛,一边不时瞄一眼和尚。和尚微闭双眼,始终保持着端坐的姿势,一动不动,所谓“老僧入定”大概就是这样子吧,小周想。
于是,屏风里教学点操场上就有点好玩了,一个真实的和尚坐中间,自己和小周分别坐两边,像是两个护法弟子,而且,这两个弟子还互不买账。老甫想到这里,差点要笑出声来,日他妈的,这要能拍个照片发到网上就好玩了。忽然,走廊上的灯光灭了。老甫知道停电了,教学点的供电由山下一个水库的小水电站供给,秋干天燥的时候水量不够就经常停电。
于是,大片的黑暗笼罩在操场上空,笼罩在他们三人的头顶上。哼子鹰偶尔传来一两声悠长的哼叫,秋虫唧唧声如雨般密集,反而衬托得四下里一片大寂静。
也不知过了多久,老甫有点想睡了,他率先站起来,坐到和尚的身边,他问,“师父,要不要加点水?”
和尚欠身說:“好的,那就多谢施主了。”和尚说着,把先前喝茶的口杯拿出来。
老甫从厨房里拎了一只水瓶出来,将水倒在和尚的口杯里,顺势坐在了和尚身边,“你喝,喝完了我再给你倒”。老甫以此获得了在和尚身边合法的居留权。
今天网络信号太差,小周调整了好几个方向,都没能把信号理顺,球赛下载了几分钟就卡住了。他关了手机,滑下了枫杨树。小周在枫杨树下听着老甫和和尚的对话,觉得老甫实在是太可笑了,想凑热闹就去凑呗,非得找个借口干吗呢?没出息!猥琐!虚伪!这样想着,他大踏步地走到和尚前面,坐下来,直截了当地问:“大师,你到底是为谁做法事呢?有什么说法吗?”
和尚愣了一会儿,微笑着说:“说法?佛在灵山曾说法呵。”
老甫和小周听和尚这样说,有些泄气,这和尚明显是不想说吗。
和尚感觉到了他们俩的情绪变化,又笑了笑说:“我可不敢说法,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老甫来劲了,忙拎起水瓶倒水,“大师,你喝水,你喝水”。
和尚闭了眼,像是沉入了另一个时空,他说:“十五年前吧,也就是今天这个日子,下午的时候下起了大雨,铺天盖地的雨,当时你们学校的教室就在操场这个位置,处在两山夹一坞中,突然起了蛟,也就是泥石流山体滑坡,蛟水直冲向教室。当时,值班的老师是个年轻人,他从没见过这情形,当时就吓坏了。泥石流冲过来时,他正站在教室门口,他喊了一声同学们快跑,就只顾自己先跑了。一阵慌乱中,大部分同学跑出来了,落在后排的两个女生却没能跑出,泥石流冲垮了教室,泥石、砖块、山上的树裹挟着两个女生,冲出了几百米远。蛟水过去后,那个老师回过神来,拼命地去扒拉泥石,他扒得两手鲜血淋漓,后来,救援的人陆续赶来,直到晚上十点三十二分,才将两个女孩找到,早已是两具冷冰冰的尸体了。两个女孩都只有九岁。”
和尚说到这里的时候停顿了一下。眼睛又睁开了。
“咦!月亮出来了!”老甫说。
三个人齐齐望向夜空,果真,不知什么时候,原来满天的黑云散去了,露出了白亮的满月来,能看见白月亮在云层里大鱼一样游动。月光如雪般落在操场上,落在他们的身上。山深,月大,这月光好像把他们仨黏合在一起了,将他们与操场之外的世界分隔开来了,或者说,这时,他们自成一个雪白的琉璃世界了。
静了好一会儿,老甫想起了什么,连忙又倒水。
哗哗的水声中,和尚又闭了眼,开始继续说那个故事。“一看到那两个女孩子的尸体,那个年轻的老师受不了啦,他举着两只血糊糊的手哭昏了过去。现场有个省城记者听说了这事,采访了他和学生家长,转天,这个老师就成了名人了,他被称为‘跑得快老师,大家都在网络上铺天盖地向他吐口水,说他在危急时刻只顾自己逃跑,而置学生于不顾,这样的老师师德何在?那老师在被责与自责中,只好离开了学校,不能再当老师了,虽然他其实是很喜欢当一名老师的。尽管后来这事平息了,别人可能也早就忘记这码事了,可是,那个年轻老师忘记不了,这么多年,一到这一天,他就心神不宁。”
和尚再一次睁开眼,抬头看了看天上的月亮。
“所以,”小周说,“他就请你来为亡灵超度了?”
不待和尚回答,老甫抢着说,“是的了,我好像是听说过这件事,没想到就是我们这所学校呵,当年可是条大新闻,好像那个老师的一个手指头还被闻讯赶来的家长一砍刀给砍掉了,你说这家长还讲不讲道理?现在人都不跟你讲道理的!”
和尚摇摇头说:“不是家长砍的,是那个老师扒泥石流时手指受伤感染了,他一直不愿去医院治疗,最后只能切除了事。”
老甫还要说什么,却见和尚看了看天空,站起来走出了帐篷。
和尚在操场空地上画了一个圈,掏出一盒火柴,一枝枝点着了蜡烛,将蜡烛在圆圈内排列起来,等全排好了,小周才发现和尚用蜡烛排成了一个数字“9”。
九支蜡烛明黄的火光闪烁着,像九个跳舞的小精灵。和尚又取了三枝檀香,点燃了,竖立在地上。这香烟像是被一双无形的手操控着,很是听从指挥,三枝檀香分成三股香烟,先是直直往上升,升到半人高时,又忽然各各盘旋成一团缭绕在烛光之上。
和尚做这些的时候,神情庄重,老甫和小周站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出,能听得见彼此的呼吸声。
一切准备就绪,和尚看看时间,又从包袱里取出一件衣服套上。即便是在夜色里,老甫和小周也能看出来,和尚换的是一身很正式的法衣,“袈裟”老甫对小周说。小周很自然地点点头,“嗯。是袈裟”。
穿好法衣后,和尚正了正衣服前后摆,一手托木鱼,一手执木槌,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缓缓地各鞠了一躬。便开始唱起经文来,“南无阿弥陀佛……”他一边唱经,一边有节奏地敲打木鱼,绕着那燃烧着的“9”字蜡烛转圈。和尚的嗓音月光一样明亮,月光下,檀香缭绕,烛光摇曳,和尚的袈裟上像是笼罩了一层薄光,这光是柔和的、清凉的、洁净的。老甫和小周其实根本没听清和尚念的是什么经,但他们俩却觉得能听懂,像是被袈裟上的光牵引着,他们不由得也跟着和尚绕着蜡烛转圈,他们不会念经,就一遍遍念“南无阿弥陀佛”。虽然他们也闭着眼,但是越念,他们就感觉到天上的月亮越明亮,好像每一遍经文都是一块擦洗布,将月亮越擦越亮。
足足一个时辰,蜡烛灭了,檀香也成了灰烬,和尚重重敲打了一下木鱼,戛然止住唱,又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缓缓鞠了一躬。这回,老甫和小周也一同鞠躬了。
直起身时,老甫和小周望见和尚脸上此时一派空明,看不出悲喜,但又分明感觉到,此刻的和尚和做法事之前的和尚似乎不太一样。而且,空荡荡的操场上,也似乎有了和平时不一样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却又说不出来。
和尚脱下了袈裟,归整着做法事时的法器,他好像刚才已经用尽了浑身气力,额头上渗出了一粒粒亮亮的汗珠。
老甫说:“师父,从傍晚到现在你一直没吃饭呢,我们一起吃一点好不?”
小周觉得这老甫总算说了一句靠谱的话,这个建议也正是他希望的,他怕和尚不同意,便热切地说:“大师,吃一点吧,百年修得同船渡呵,和我们一起吃一餐便饭也是缘分呐。”
和尚微笑着说:“那好呵,好呵,只是麻烦二位老师了。”
老甫和小周连忙表态:“不麻烦,不麻烦,分分钟的事。”两人说着,第一次共同去了厨房,也不用商量,就有了明确分工。小周洗菜,老甫掌勺。他们将各自储存的菜贡献了出来,素菜做起来也快,做了四道菜,一个油爆花生米还是当家菜,一个黄瓜段蘸酱,一个青椒土豆丝,一个素炒粉条。
和尚将帐篷里的防潮垫拿出来,垫在草地上,四个菜摆在上面,三双筷子三个碗也摆在上面了。
三个人就在草地上各坐一方,还没动筷子,老甫忽然忸怩作态,把屁股后的扁酒壶在手上颠来倒去倒去颠来,他对着天空上的月亮说:“月下一壶酒,是不是有这句诗?”好像他是在和月亮说话。
小周说:“什么月下一壶酒,花间一壶酒,应该是,你是酒瘾犯了吧?”
和尚却笑了:“一切佛法不离世间法,无花有月也宜饮酒,你们二位尽管喝吧,我且以茶当酒陪你们。”
和尚这一说,老甫和小周“呵呵”地笑了,小碗里斟上了白酒。
“干。”老甫说。
“干。”小周说。
“干。”和尚也伸出茶杯。
月光下,一切东西都闪光,像银器,像水晶宫,他们坐定在草地上,低头喝酒或喝茶,举头望月亮也望山峰。
老甫说:“你们看,这地方叫屏风里真是叫对了,就是一扇大屏风呵。”
“中国屏风,”小周说,“这是个好题目,可惜我现在不会写诗了”。
小周这样说着,突然“呜呜”地哭了,他一边哭一边抹眼泪,举着酒杯对老甫和和尚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干杯吧”。
“干杯!”和尚喝一口茶后,拍了拍小周的肩膀。
也不知喝了多久,老甫和小周渐渐醉了,酒是醉了,心却明的,他们看着和尚一直在陪着他俩,一直听他们说些上句不接下句的酒话。到后半夜,他們俩支持不住了,碗一放,双双倒头在草地上躺下了。身子躺下了,嘴里还没停歇。
老甫说:“你,我知道,你,你我起了个外号,你说我……我……我叫叛徒甫志高,是不是?”
小周打着酒嗝说:“嗯,是……是的,我上课时就是这么说……说……说的。”
老甫翻了下身,四仰八叉躺着,面对着夜空,笑着说:“嘿,嘿,我告诉……告诉你……我……我也给你取……取了个外号,你,叫,周、扒、皮,嘿,嘿嘿。”
老甫“嘿嘿”笑着,笑声刚一停下便立即打起了呼噜,中间没有一丝过渡音。
小周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不,我不是周扒皮,我,不,是,周,扒,皮。”念着念着,渐渐停滞了下来,不一会儿,也睡着了。
秋夜的风吹拂着他们,吹拂着校园,也吹拂着山林和明月,松涛声和着溪涧的流水声隐隐传来。和尚始终面色柔和,结趺而坐,一动不动。这是老甫和小周临睡之前最后看到的。
第二天早上,天色微明时,睡在草地上的老甫和小周几乎是同时醒了。他们翻身坐起,怔忡中,发现那个和尚不见了。
两个人爬起来,发现不仅和尚不见了,帐篷不见了,昨晚的碗筷连同防潮垫不见了,甚至地上的香炷灰烬也不见了,难道昨晚上的一切只是一个梦?他们赶忙去厨房里看,那些用过的碗筷已被清洗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摆放在碗柜里。
老甫和小周默默走到走廊前,伸长脖颈看着山道,想象着和尚穿着他青灰色的僧衣,背着他佛黄色的包袱,在起伏不平的山道上高高低低走远了的情形,他走的时候,想必月亮还大亮着,也好,正好为他照路。
看了好一会儿,老甫忽然对小周说:“喂,你发现没有,他的右小手指没有了。”老甫没有称那个人叫“师父”或者“大师”什么的,也没有叫他“和尚”,而是直接称“他”,好像那个人和他们俩早就很熟悉似的。
小周点点头:“看见了,我看见了。”
朝霞这个时候在东边的天空上烧起来了,烧得一派姹紫嫣红,而屏列的山峰间,从东到西,白雾似的岚气也升腾起来了,一时,群山皆在虚无缥缈间,真像中国画里的屏风了。
责任编辑 楚 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