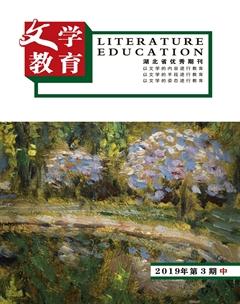抗战时期《文学月报》诗歌初探
宋军如
内容摘要:《文学月报》是抗战时期重庆文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文学期刊之一,而诗歌是其文艺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以《文学月报》刊登的诗歌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相关文献资料,拟就《文学月报》诗歌的特征及意义作具体分析,进而加深对抗战时期特别是抗战中期诗歌的认识和了解。
关键词:抗战时期 《文学月报》 诗歌
一.《文学月报》诗歌概况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重庆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成为该时期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由于战事尚未蔓延至内地,重庆相对安定,文化环境比较宽松,各类报刊杂志纷纷迁入,各类文艺工作者纷至沓来并持续开展抗战文艺活动,使其文化氛围格外浓厚。在此种形势的影响及带动下,重庆本土也涌现出大量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优秀刊物,《文学月报》便是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刊物之一。
《文学月报》为十六开本、月刊,是创作、翻译、评论并重的大型综合性文学期刊。该刊创办于1940年1月15日,由文学月报社编辑,读书生活出版社发行。创刊之初,编委会有罗荪、光未然、戈宝权、力扬、丘琴、罗烽、黑丁等七名成员;在实际操作中,罗荪担任主要编辑,力扬、丘琴参与诗稿编辑,戈宝权负责翻译稿编辑。1941年12月10日出至第3卷第2、3期合刊,被迫停刊。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文学月报》一共出版发行十五期,“发行量曾达到一万册”[1],发行范围扩展至当时的“孤岛”上海,成为抗战时期重庆文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文学期刊之一。
诗歌是《文学月报》文艺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罗荪在《发刊词》中指出,“我们将以广大的篇幅给予诗与画”,且“愿与所有的诗歌青年共同努力于健康的现实的诗风的树立,使新诗能坚实的负起革命先驱的责任”[2],并以此作为《文学月报》的方针之一,网罗了力扬、丘琴、王亚平、鲁藜、曾卓等一大批具有较高文学素养及诗歌造诣的优秀青年诗人作为期刊诗歌部分的撰稿人,还开辟了“诗”、“诗辑”、“诗选辑”等专栏来刊登新诗,涌现了大量较好的抗战诗作,如戈茅《红鼻子和老马的故事》,方然《离延河》、曾卓《受难的山城》、王亚平《血的斗笠》等。此外,《文学月报》还十分重视外国诗歌翻译,“经常的介绍值得我们学习的国际诗人及其作品,以补偿我们新诗遗产贫乏的缺陷”[3],如第1卷第4期设立了“玛雅可夫斯基逝世十周年纪念特辑”。据现存资料统计,《文学月报》一共登载了35首新诗,26首译诗。本文主要是对《文学月报》刊登的中国新诗进行研究。
二.《文学月报》诗歌的特征
(一)情感内容特征
1.时代性
《文学月报》诗歌在情感内容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诗人和文艺工作者首先认识到诗歌应该和民族的抗战现实结合起来,诗歌的社会责任和民族责任成了人们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衡量诗歌是否适宜生存的主要标尺。”[4]罗荪曾提及《文学月报》创刊的缘由:“当时的重庆正处在一个政治低潮时期,文艺界展开过一次对于‘与抗战无关的论战……那时文藝界一部分同志深感需要开辟一个新的阵地……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就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创刊了。”[5]《文学月报》的创办,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扫除“那些颂扬‘为艺术而艺术的歌唱“、清算“那些提倡‘与抗战无关的错觉理论”[6]。《文学月报》诗歌以抗战为主题,内容皆与当时的社会生活紧密结合。这些诗歌,或直接抒写抗战英雄的英勇无畏,如石星的《祭歌——献给我们的队长》讲述了一个游击队长带领战士们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故事;或控诉战争的残酷暴力,如曾卓的《受难的山城》描绘了日军轰炸重庆时的惨烈场景;或抒发对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念和对和平未来的美好向往,如鲁藜的《为着未来的日子》想象着祖国的未来是充满活力的“小女郎”;或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家园的捍卫,如戈茅的《红鼻子和老马的故事》刻画了一个参加过抗战的老人对祖国山河的深情赞美。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月报》诗歌中所颂扬的抗战英雄,并没有仅局限于身居要职、手握大权的风云人物,那些为抗战默默奉献的普通士兵、农民等小人物也是这些抗战诗歌的描写对象。如厂民的《夜织》中,身在抗战后方的纺织女,虽然“辛苦的工作从不被人称道”、“胸前也从不会挂上荣誉奖章”[7],但仍为支持抗战辛勤工作着。
2.战斗性
《文学月报》诗歌在情感内容上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在抗战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理念显然不合时宜,诗歌服务于抗战,担负起宣传、鼓动人民群众团结抗战的政治功利性作用。许多诗歌在书写抗战决心的同时,也积极号召全民族共同抵御外敌。如,在《红鼻子和老马的故事》中,诗人发出呐喊:“四万万五千万和平的人民,/用尽一切力量/要保卫我们肥美的国疆!”[8]
对胜利的坚定信念和对战争的不屈反抗是《文学月报》诗歌主要的情感基调;这些诗歌始终保持着不屈不挠的姿态,传递着乐观向上的精神,清除了一切消极情绪。对灾难的描写,除了表达对战争的控诉,也是为了突出抗战决心和必胜信念。如,《受难的山城》在描述大轰炸之下的重庆悲惨场面的同时,指出:“重庆是炸不毁的,/敌人愈残酷/我们抗战的意志愈坚强!”[9]整首诗情绪高昂,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战斗性。
(二)语言形式特征
1.语言特征:大众化
《文学月报》诗歌在语言上表现为大众化、通俗化。抗战时期,诗歌担负着号召组织广大人民抗战的政治任务,这要求它必须面向大众,拉近与人民的距离;而早期白话新诗具有的“欧化”特质显然与之相悖。正如力扬所说:诗歌语言“不是死了的士大夫的文言,也不是被知识分子自我爱恋着的‘洋八股,而是大众活生生的口语”[10]。在当时诗歌大众化、通俗化的文学语境中,为扩大诗歌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更好地发挥诗歌的宣传、号召作用,诗人们将诗歌语言与现代口语有机结合,使诗歌语言通俗浅显,而又不失鲜活生动,以便于大众的理解认同。如,诗歌《夜行》:“‘走!走向前!/战斗在号召!/祖国在呼唤!/没有忧伤只有勇敢!/走!走向前!/冲破了寒冷与黑暗,/歌唱胜利的明天!/我追着这歌声,/我迈开更大的步子!/我们——三十五个!/又爬过了,/一重山!/两重山!/……”[11]其多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口头语言,没有生僻字,没有过多的书面语,没有多余的形容词,通俗易懂,利于朗诵及宣传。
2.形式特征:自由体诗
《文学月报》诗歌在形式上均为自由体诗。自由体诗指“诗无定节、节无定句、句无定字,有韵或无韵”[12]的诗歌。胡适在《谈新诗》中提到:詩歌的“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13]。力扬对此表示认同,认为“在这暴风雨的时代,诗歌必须是自由的形式,才能容纳了我们民族的可歌可泣的内容与万马奔腾似的情绪”[14]。自由体诗歌不要求固定的形式格律,不拘于诗歌的音韵节奏,有利于表达出抗战时期丰富复杂的时代内容和思想情感,且创作较为快速,更好地适应了战时需要,成为抗战时期主要的诗歌形式。
此外,《文学月报》还刊登了一些长篇叙事诗,如力扬《他们战斗在西班牙》、戈茅《红鼻子和老马的故事》、王亚平《血的斗笠》、李雷《汾河湾上的故事》等。这些长诗善于“刻画英雄人物,富于特定时代特有的生命的力量美”[15],丰富了新诗创作的形式。《汾河湾上的故事》讲述了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带着三个孩子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感人故事,诗歌多用短句,语言铿锵有力,将妇女誓死捍卫家园的凛然大气表现得淋漓尽致,极具震撼力及感染力。
三.《文学月报》诗歌的意义
(一)社会意义
罗荪在《文学月报》的《发刊词》中指出:“文艺不仅是民族的生活与战斗的反映者,而且使民族精神的指导者。不但是历史现实的最正确的见证者,而且是精神领域的伟大的创造者。”[16]这段话恰当地概括了《文学月报》诗歌的社会意义。一方面,这些诗歌虽然不及抗战后期诗歌创作,没有深入反映到抗战时期的方方面面,但也是与时代紧密结合,多角度地展现了战时的现实生活和抗战人民的思想情绪,是时代的反映者和见证者。另一方面,虽然《文学月报》只存在了短短两年,但其发行量曾达到一万册,在当时具有较大影响力。其诗歌在情感内容上所具有的战斗性和感染力,使其很好地发挥了宣传和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参与抗战的政治作用。
对于今天而言,《文学月报》诗歌所处的特殊时代决定了其特殊的社会意义。抗日战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虽然战争已经过去,但这些以抗战为主题的诗歌流传至今,从这个角度讲,这些诗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阅读这些诗歌,有助于今天的人们了解那段苦难的历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从这个角度讲,这些诗歌具有一定的社会教育意义。
(二)文学意义
《文学月报》诗歌是大后方抗战中期诗歌的缩影,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当时重庆抗战诗歌的发展状况。在情感内容上,这些诗歌虽然仍延续着抗战初期对战斗的呐喊和对英雄的歌颂之情,但已突破了初期诗歌口号化、公式化的宣传型创作模式,传递出真挚细腻的感情和较为深刻的思考,更具艺术感染力。在语言形式上,这些诗歌追求大众化、通俗化,将现代口语有机融入其中,缓和了早期白话新诗过于欧化以及疏离大众的弊端。而抗战中期长篇叙事诗的出现丰富了抗战诗歌的形式,为多样性创作潮流的形成以及抗战诗歌创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是,《文学月报》诗歌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局限。抗战时期,“一切为抗战服务”成为社会各界的行动方针,诗歌也不例外。诗人们过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功用,而忽略了对诗歌本身的艺术追求;过分强调诗歌对时代精神和现实生活的反映,而忽略了诗歌对个体自我情感的关照;过分强调诗歌的大众化、通俗化,而忽略了对诗歌思想内涵深度的探索。这导致这些诗歌在内容主题上的单调、内涵深度上的不足,影响了诗歌艺术本身的发展。不可否认,《文学月报》诗歌的社会意义大于文学意义。
四.结语
抗战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救亡图存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一切为抗战服务成为社会各界的方针。《文学月报》诗歌积极响应时代的号召,以抗战为主题,在情感内容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强烈的战斗性;采用自由体的形式,追求诗歌语言的大众化和通俗化。这些诗歌是抗战时代的反映者和见证者,也是民族精神的宣传者和引导者;虽然存在着诸多局限,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抗战诗歌的创作,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文学意义。
注 释
[1]罗荪.罗荪近作[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87.
[2]罗荪.发刊词[J].文学月报,1940,1(1):1.
[3]罗荪.发刊词[J].文学月报,1940,1(1):1.
[4]熊辉.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诗歌观念及其艺术价值[J].重庆社会科学,2009(5):105.
[5]罗荪.罗荪近作[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83-84.
[6]罗荪.发刊词[J].文学月报,1940,1(1):1.
[7]厂民.夜织[J].文学月报,1940,2(4):177-178.
[8]戈茅.红鼻子和老马的故事[J].文学月报,1940,1(1):31.
[9]曾卓.受难的山城[J].文学月报,1941,3(1):66.
[10]力扬.谈诗的形象和语言[N].新华日报,1940-2-24(4).
[11]高兰.夜行[J].文学月报,1940,1(1):33.
[12]陈良运.论自由体[J].文学评论,1984(2):92.
[13]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EB/OL].https://www.douban.com/group/to pic/86858766/?type=like,2018-2-18.
[14]力扬.关于诗的民族形式[J].文学月报,1940,1(3):139.
[15]刘静.抗战时期的重庆诗坛[J].江西社会科学,2005(3):106.
[16]罗荪.发刊词[J].文学月报,1940,1(1):1.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