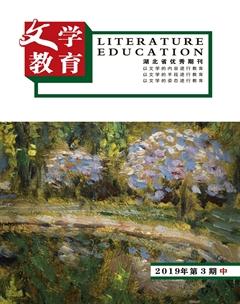柳永俗词研究
内容摘要:柳永是北宋词坛第一位对词进行大力革新的词人,在词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当时不被正统社会认可的柳永,他的词作,尤其是俗词,却有着“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的广泛影响。本文将从柳永俗词中俗之成因、俗之表现和俗之影响等三方面入手,来探讨其俗词之美。
关键词:柳永 俗 《乐章集》
柳永善为诗文,但“皆不传于世,独以乐章脍炙人口”[1]。他的词内容丰富,感情细腻,明白晓畅。尤其是他能将民间俗乐融入到词的创作中,以市井通俗之音调换贵族风雅之曲调,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俗词”。因此,本文将通过研究柳永俗词,从俗词之“俗”的成因与表现等方面来探究柳永对宋词发展的影响,来感受柳词之美。
一.俗之成因
艺术来源于生活。柳永词之俗,其成因有内外之分,主要包括当时社会环境的外在因素以及自身经历的内在因素。
(一)外在因素
北宋建立后,统治者对农业进行革新,通过改进农业生产方式,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刺激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使得粮食产量不断增加,经济也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这一点,从柳永的《望海潮》里“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参差十万人家”看出都市经济的极大繁荣。
经济发展、都市繁华,为宋代市民们优雅富足的生活提供了沃土,享乐之风也尤为盛行。经济水平的繁荣发展,使得生活在这样优渥环境里的文人士大夫便拥有了足够的条件纵情于歌舞声色。与这样的社会风气相适应,宋代的歌妓行业也随之不断发展繁荣。秦楼楚馆的发展,为宋词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带来了宋词的繁荣。敏感多情的柳永在这种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也不禁沉浸其中,动情而唱《倾杯乐》“翠华宵幸,是处层城阆苑”。
此外,柳永时期的统治者对待文臣们相对宽松的政策,通过文化娱乐礼遇文人,大量搜集民间“俗乐。借此缓和与旧贵族的关系”。统治者对“俗乐”的要求,也使得与“俗”有关的各类“新声”因此萌芽。
(二)内在因素
柳永自身也充满了矛盾。他出生于世代儒学仕官的家庭中,本该沿袭家族惯例,踏上由儒生到士大夫文人的道路。诚然,他也曾为此昼耕夜诵。早年的柳永对考取功名充满信心,怀着“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待恁时,等著回来贺喜”的憧憬。然而,多舛的仕途之路无情的打压了他的满腔热情。少年在帝都汴梁度过的繁华如梦的生活,使得他喜欢流连于秦楼楚馆。于是,科场的失意更激发了他生而禀赋浪漫天性和音乐才能,所处的仕宦家族和他个人的天赋在无形中形成了冲突,使得柳永在入世与享乐之间犹豫彷徨,导致了他的人生悲剧。
柳永的独特经历与境遇充实了其作品的内容与情感,为其词别具一格的创作提供了素材。词学大师叶嘉莹先生认为:“词是作者内心兴发感动的产物”[2]。在宋代词坛上,有苏轼尽展雄心壮志的豪放不羁,有李清照尽显清丽柔美的婉约绮媚,而柳永则形成了与这两派截然不同的风格。他致力于词的革新,逐渐打破了文人士大夫词作以晚唐五代小令一为主的局面,推动慢词登上词坛,柳永词作之“俗”也是在这过程中应运而生。
二.俗之表现
(一)题材俗
多情又悲情的词人柳永因屡次落第,流连于市民阶层。这一独特的经历使得柳永在词作中与其他文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而他所处的底层环境也为其词之“俗”发展提供生活素材。他深入“俗世”人心,并抓住了富于特色的生活镜头加以描绘渲染。柳永的取材“俗”不止于生活琐事,琴艺俱佳的歌妓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灵感。
在柳永生活的时代,无论是天子还是庶民,无论是在红墙绿瓦里,还是在街头巷尾见,总有人在吟唱柳永的俚俗词曲,“正所谓‘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3]。
柳永的词作题材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写羁旅行役情怀;一类写“偎红倚翠”的生活及男女之情,一类写都市风光。无论哪一类都取材于生活,贴近生活,契合普通百姓的审美趣味,赢得了广泛的市民受众群体。
(二)语言俗
宋词的语言的来源,不外乎经史子集与市民口语。而事实上,从市民口语中提炼精华,不仅丰富了词的语汇,而且使之具有更多的现实感和生活感,更凸显了词的表现能力。因此,柳永词作收获广泛的听众和读者。这也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语言发展由雅到俗的新方向,由规则化到平民化的特征。柳永,恰好就是这大量运用民间俚语口语创作的第一人。
也许,有些学者认为柳永的词作中不乏典故、也有比兴寄托,但其数量较少,且仍是以俚语口语化用典故,未有过多弦外之音。在他的词中,俚语俗语的运用脉络清晰又明白晓畅,在满足市井民众需求的同时,也受到了歌妓以及市民的广泛歌咏。
如《法曲第二》中“青翼”是一个典故,在当时已经融合为市民群众的口头语,是他们“耳根听熟之语”“舌端调惯之文”[4]。“自觉当初草草”就是一句典型的口头语,此外还有略富文采的“青翼”“香径”,通俗晓畅的“传情”“偷期”,更有“未省”“相将”等一系列俚俗浅白,颇有生活气息的词语。又如《锦堂春》中“是事”“认得”“诮”“恁地”等等,贯穿全篇的浅近的白话使得其词作通俗而富有表现力,有如絮语家常。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倾杯乐》的“朝思暮想,自家空恁添清瘦”;《迎春乐》中的“近来憔悴人惊怪。为别后、相思煞。我前生、负你愁烦债。便苦恁难开解”;如《鹤冲天(闲窗漏永)》“多成破”“则个”“旧时么”“无计那”等,都是柳永将宋代民间的口语融入词作中的体现。还有柳词反复使用的副詞“恁”“怎”“争”等,代词“我”“你”“伊”“自家”“伊家”“阿谁”等,动词“看承”“都来”“抵死”“消得”等等[5]。明白晓畅的语言风格满足了市民阶层的审美需要及语言习惯,也体现了柳永词作中平易而不失个性,个性而富于情感的特点。
其实,引用民间俚语并非柳永一人,但绝大多数人都无其功力。柳永的语言平铺直叙,少精雕细琢,天然似不甚经意,这也显示出他运用俚语的高超技术,因而自然而然也受到市民群众的欢迎。
(三)手法俗
在表现手法上,他用长调突破小令的格局,并创造性地用铺叙和白描的手法提高词的功能。将六朝小赋的铺陈特征运用于词作中,在写景状物抒情中大量采用铺叙的手法。此外,他词作中白描手法的运用也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文字简洁、不加装饰、少精雕细琢又富于感情,在平淡中传情达意。他的词作不似贵族文人的典雅精致,而是贴近生活的简单明白,并在这种纯粹中生动地刻画出人物的细腻情感。
如在《昼夜乐》中,柳永便采用通俗的叙述手法,站在抒情主人公的角度从头到尾叙述其短暂而深刻的爱情故事,以追忆的方式缓缓道来,在平铺直叙中诉说其绵绵长长的懊悔。又如《鹤冲天》姐妹篇的《传花枝》从才、艺、貌三个方面来铺写浪子的风流才调。举“拆白道字”一点,表示其“多才”,是“风流才调”的第一方面;“总知颠倒”,举作词改曲,表现“多艺”,是“风流才调”的第二方面;“表里都峭”寫其身体健美又不失风度翩翩,是“风流才调”的第三方面。通过铺陈叙述,流畅自然地表达其自得情怀。
三.俗之影响
柳永,作为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第一位词人,他对后世的影响甚大。“南北宋之交的王灼即说‘今少年‘十有八九不学刘耆卿,则学曹元宠;又说沈唐、李甲、孔夷、晁端礼、万俟咏等六人‘皆有佳句‘源流从柳氏来”[5]。即使是宋词大家苏轼、开派宗师黄庭坚、一代词宗秦观、集大成者周邦彦等著名词人,也都或多或少收益于柳永词作。
对苏轼而言,柳永词的题材开拓、铺陈直叙、渲染状物、意象选用等方面,都对其作词有着众多启迪。因而苏轼创作,一方面力求有柳词风味,同时自出机杼,又不失浪漫风格。另一方面,又汲取柳词的表现手法和风格语言,拓展诗歌内容,大力革新,开创多样风格,为宋词发展开辟新道路。黄庭坚的俗词创作继承了柳永风调,创作了大量艳词、俚词,但又不同于柳词的细致白描和委婉铺陈,更加直白。此外,秦观受柳永影响,创作了而大量慢词。并将小令中的含蓄缜密引入雅词长调,区别于柳永词的单调浅白,更隽永深厚。周邦彦讲究章法的词体结构,同样也是从柳词学得,近人夏敬观早已指出,“耆卿多平铺直叙,清真特变其法,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故慢词始盛于耆卿,大成于清真”[4]。在柳永之后的苏轼与周邦彦,各成一派:苏轼豪放旷达一脉贯穿,而周邦彦又更加讲究章法,张弛有度。究其本源,皆从柳词分化而出。
总之,柳永作为革新宋词的第一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词作的通俗晓畅,不仅为后代的词曲创作提供了借鉴,开辟了先河,也促进了宋代民间通俗文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赵长征.柳永[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10:10
[2]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
[3]陈师道.后山诗话.柳永词详注及集评[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5
[4]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柳永词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12:34-57
[5]袁行霈.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三版)第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7:36-38
(作者介绍:林夏菁,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本科生;指导老师:吉玉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