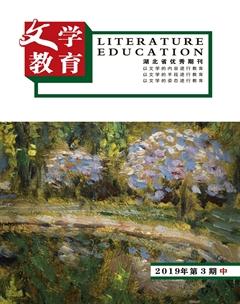鲁迅《药》意蕴探析
周颖
内容摘要:《药》是鲁迅的短篇小说《呐喊》中的一篇作品,主要描写了茶馆主人华老栓为了治好儿子华小栓的肺痨病去买人血馒头的故事,揭示了在旧社会的背景下,底层中国人的愚昧与麻木。
关键词:鲁迅 愚昧 麻木 看与被看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对中国文学的变革,首先便体现在文学题材的选择上。他指出:“古之小说,主角是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五四之后以后的短篇里却大抵是新的智识者登了场。”在鲁迅的作品中,偏重于对社会中下层人民的生活状态与思想进行描写。如祥林嫂、如阿Q都是社会底层人民的一芥。他的作品《呐喊》与《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熟之作。作为《呐喊》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作品,《药》在主角的设置上也鲜明地体现出鲁迅的特点,他将视角聚焦到了中国的底层人民身上,通过对底层人民的描写来映射整个中国社会。华老栓一家,夏瑜及其家人,包括一众“看客”都是在社会中下层生活着的普通人,那时的中国多的是如他们一样的普通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荒唐之事,看似不合理,实则正是中国社会的缩影。
从情节上来看,《药》这篇文章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华老栓买药,第二部分是华小栓服药,第三部分是茶馆议论,第四部分是华母与夏母坟前相遇。
故事的缘由是华老栓的儿子华小栓得了肺痨病,夫妻俩为了治好儿子的病,想到了人血治肺痨的偏方。生病送医是常理,然而华氏夫妇却想通过买人血馒头来治好儿子的病,其迷信思想可见一斑。在那一时期,科学尚未在中国普及,社会上弥漫着迷信的思想,华老栓和他妻子的思想是在整个社会的氛围下造就的。在买药的路上,华老栓偶遇了一场行刑的场面,撞见了一群围观行刑场面的“看客”。对于被行刑的人,他没有觉得丝毫怜悯和同情,甚至也凑上去看。最终,从刽子手的手中,他如愿以偿的买到了能治好自己儿子的病的“药”。文中对刽子手的描写是:“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这个刽子手蛮横、冷漠,仿佛是做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围观处刑的所有人,包括买药的华老栓也好像早已习惯了这种场面,漠视他人的生命变成了一种正常的反应,人性冷漠和自私的一面在此处展现得淋漓尽致。
华老栓带着买来的人血馒头回到了家,夫妻俩对这“救命药”深信不疑,华小栓甚至也相信这东西能治好自己的病:“小栓撮起这黑东西,看了一会,似乎拿着自己的性命一般,心里说不出的奇怪。十分小心的拗开了,焦皮里面窜出一道白气,白气散了,是两半个白面的馒头——不多工夫,已经全在肚里了,却全忘了什么味;面前只剩下一张空盘。他的旁边,一面立着他的父亲,一面立着他的母亲,两人的眼光,都仿佛要在他身上注进什么又要取出什么似的;便禁不住心跳起来,按着胸膛,又是一阵咳嗽。”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馒头,因为蘸了人血而变得无比珍贵,成为了他们眼中的治病良药。他们都期待着,期待着这人血馒头能够治好华小栓的病,殊不知这只是空想而已。“不多功夫,已经全在肚里了,却全忘了什么味”暗示了华小栓的结局。
茶馆的议论是这篇作品的高潮部分。从这一部分中也可以看出社会中下层人民群众的思想面貌和精神写照。在这一段中,各色人物粉墨登场,花白胡子的老人,驼背的五少爷,蛮横的康大叔……刽子手康大叔的到来让整个茶馆都热闹起来,因为华老栓的人血馒头蘸着他刀下的鲜血,众人对于刽子手仿佛带着一种自然的敬畏,对于被他处决的革命者夏瑜带着一种惊人一致的同仇敌忾夏瑜成了茶馆众人的谈资,或嘲讽、或叫好、或诋毁。谈到折磨夏瑜的红眼睛阿义时,驼背五少爷甚至摆出了一副巴结的嘴脸,赞叹阿义的手段高明。花白胡子及一众看客也都觉得夏瑜是发了疯。总之,没有一人对夏瑜的经历表现出一丝丝的怜悯和同情,这是夏瑜的悲哀,也是整个旧社会的悲哀。
故事的最后,华小栓的母亲和夏瑜的母亲在坟地相遇,华小栓与夏瑜的坟地相隔并不远。夏瑜被处决了,华小栓最终也没有摆脱病死的命运,人血馒头没能挽救他的生命。讽刺的是,华母的儿子吃了蘸着夏瑜之血的馒头,而华母一边对夏母表示同情,一边安慰着夏母。而夏母一边怀念着自己的亡女,一边认为她是受人蛊惑才去革命,也没有认可夏瑜的革命行为,不禁让人为夏瑜惋惜。夏瑜和华小栓都死了,夏瑜是作为一个革命者而死的,她接受了民主科学思想的洗礼,希望冲破旧社会的禁锢,为自己的信仰而死。而华小栓死于肺痨病,旧社会中的“药”没能让他活着。两者的死都有一定的必然性,但两者的死意义却大不相同。
在鲁迅的作品中,常常有这样一群“看客”。这些看客,从别人的悲惨遭遇中满足了自己,通过他人的痛苦与不幸,使自己的不幸、痛苦得到宣泄、转移以致遗忘。在别人的痛苦中,悲哀“咀嚼”殆尽,成为“渣滓”以后,就立刻“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这类情感与行为方式表面上麻木、混沌,实际上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忍。在《药》中,围观处刑的人如是,茶馆的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等众人亦如是“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鲁迅将这些围观处刑的看客比作“伸着脖颈的鸭子”,实在是贴切。这些看客的丑态,恰是彰显了旧社会人性的冷漠与残忍。茶馆众人,巴结康大叔的有之,夸赞红眼睛阿义的有之,诋毁夏瑜的有之。在他们眼里,夏瑜做的是大逆不道的事,被处刑是应得的结果;在他们眼里,夏瑜是可憎的。在旧社会中生存,却非要去革旧社会的命,挑战旧社会的秩序,这是为这些看客所不允许的。他们麻木、愚昧,思想受到了禁锢,所以他们毫无同情。在夏瑜眼里,这些人又何尝不是可怜人呢?也不怪乎她在牢中与红眼睛阿义对峙时仍然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夏瑜接受了民主科学的思想,与这些思想陈旧麻木的人存在本质的区别。然而,他的存在是不能为当时的社会所允许的,于是她被处刑,死在了旧社会的刀下。夏瑜成为了被看的对象,被一众看客评判。在这种看与被看的过程中,看客得到了满足,而夏瑜作为被看的对象獻出了生命,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
对于鲁迅而言,他也是个看客: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审视着这个旧社会和这个社会中的群众。群众愚昧而麻木,他一个人清醒,所谓“众人皆醉我独醒”被看的是群众,看的人是鲁迅自己。看和被看是先驱者和群众之间的二元对立。夏瑜和一众看客其实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鲁迅也是个启蒙者。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唤起国人的思想觉醒。在《呐喊。自序》中他描述了自己弃医从文的缘由:“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作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医身容易,医心难。群众麻木、愚昧思想不改变,即使拯救再多病人也无用。所以他投身文学创作,希望借此唤醒民智。
在每一个时代,都存在着“看客”这一群体。《药》所描写的看客,是迷信而无知的,思想长期受到禁锢与限制,他们成为了“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当今时代,“看客”依然不少,他们也许受过教育,懂得科学,但是人性的疏离与冷漠让他们沦为了看客。对于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而言,民主与科学乃是治好他们的良药,而对于现今时代的看客而言,治好他们的良药则是完善的社会体制与和谐的社会风气。只有这时代少一些看客,多一些敢于发声、敢于行动的先驱者,如此我们的社会才能够不断进步。
参考文献
[1]鲁迅.药[M]//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298-310
[2]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7:34-50
[3]吴雨轩.鲁迅《药》中的“看客”思想与现实意义解读[J].赤子(上中旬),2016,No.397,60-61
[4]苏添生.冷眼悲情睿见深——读鲁迅《药》杂评[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3,v.28;No.125,69-70.
[5]曹文生.论鲁迅《药》中的悲剧精神[J].名作欣赏,2012,No.415,48-49.
[6]龙庆荣.“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药》中小市民形象的意义[J].名作欣赏,2010,No.331,73-74+89.
(作者单位: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指导老师:缪军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