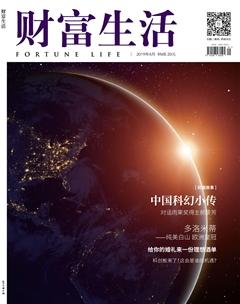对话雨果奖得主郝景芳
科幻究竟是小众还是大众?
写科幻的女作家少,好的女性角色更少?
为什么如今大热的科幻作品不太关注太空了?
相比国外,中国科幻的特色在哪儿?
Q 提到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刘慈欣的长篇小说《三体》以及你的短篇作品《北京折叠》斩获“雨果奖”都被视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作为目前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科幻作家之一,能否请你分享一下对近年来国内科幻文学现状和未来发展的理解?
A 我觉得国内的科幻文学一直都还挺好的。首先是我们的科幻作家都很有才华,然后最近这些年发表渠道也蛮多的,原来基本就只有《科幻世界》,现在其他的杂志也开始发,加上这两年雨果奖之后也有各种新媒体开始发科幻小说,还有老牌的传统文学杂志,包括《大家》《人民文学》等等,现在也发表科幻作品。所以总的来讲,科幻现在的发表平台和创作平台都越来越多了,挺让人高兴的。
Q 虽然发表的渠道多了,但很多人还是会说科幻对中国读者来说是一个很小众的文学类型。
A 其实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科幻都是小众的。在国内的话,我们一般能卖到一万本书就觉得很高兴了;在美国那边,他们觉得能卖五千本就已经很好了。这还都是获奖作家。科幻小说的题材决定了它不会是一个很大众的读物,我个人是一直接受这个现实的。我不会拿它跟现在流行的那些修仙啊、宫斗啊之类的网络小说比销量和热度,既不现实也不敢想。(笑)
Q 但科幻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在票房表现上通常都很抢眼,这种影视和小说的冷热反差你是怎么看的?
A 因为科幻影视从来都是主流的大制作,之前我看到过一些榜单,说影史上最卖座的电影片十个有八个是科幻的。科幻作品的属性决定了它在视觉呈现上会有大场面、大制作,是观众喜闻乐见的大片,但是科幻小说就是小众文学,这在美国也是一样。科幻电影是大众电影,科幻文学是小众文学,这两者的市场状况我们得区别来看。但有一点影响是好的,科幻这个领域的影视改编有了一定的热度后,大家对我们科幻小说的关注度提升了,可能以前卖不到1万本的现在能卖1万本以上,这我就挺开心的。
Q 刚才提到网络小说,其实现在网络文学,比如言情类的也涌现出很多以科幻为背景的作品,但这类作品中“科幻”往往只是一个时髦的元素,那么对于这类创作,你是否认同它们的科幻作品属性?
A 我觉得还是得看科幻设定本身是不是这个故事最重要的核心推动。要是说科幻就只是一层皮,比方说故事讲的是生化危机时代,男女主人公怎样相知相爱,那这个我觉得其实就跟科幻没太大关系,顶多只是赋予了爱情故事一个灾难或者战争的背景。但如果故事是生化危机背景下,人们怎么跟病毒去做斗争,或者是说病毒改变了故事里的某个重要人物的性格、外貌、体能之类的,如何去面对这种变化对他人生造成的影响,那我可以判断它是科幻小说。
Q 你觉得电影《流浪地球》的热度对国内科幻文学的发展会有帮助么?
A 我觉得《流浪地球》是会让很多人都更关注科幻这整个领域,也会关注一些科幻的IP,但是要具体到文学,我觉得还是那样。看科幻小说的人还是会继续看,但以前不看科幻小说的人,就算看了电影还有大刘的原作,也不会说就此养成看科幻小说的习惯。
Q 那么相较欧美作品,你觉得中国的科幻有哪些特色?
A 我觉得我们的作品特色在于会关注到中国社会的形态,中国人的家庭关系,会观察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还有中国未来的发展变化,甚至于中国的历史等等。我们的科幻作品还是很根植于中国本土的。即便是写在20年前的那些校园科幻,也都是写中国的学校里发生的那些事。虽然那时候很多作品的故事有些稚嫩,但是这种本土的融合性从一开始就做得很好,很少有那种完全用外国人做背景的架空作品。反而像是日本的一些科幻作品会有这种(情况),或者是把日本人和外国人融合在一起写。
Q 我们知道《北京折叠》是你长篇小说的第一章,想知道后续全书什么时候能跟大家见面。
A 目前这个故事的后续没列上议事日程。因为题材的关系,我可能一时半会儿不想写它,但是会有别的作品。
Q 听过这样一种观点,科幻小说几乎是“男人的世界”,女性创作者少,有魅力的女性角色更少,那么身为一名女性科幻作家,你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A 其实女性科幻作家一点儿也不少,但因为在大众层面上出名的很少,所以会有这种刻板印象。有这种印象的我觉得应该也不是科幻作品的老读者,假设你问他知道哪些有名的男作家,他估计也只能回答上来刘慈欣这一个名字。但凡是科幻小说的忠实读者,一定会知道无论国内外都有很多挺有名的女作家,光国内我就能数出七八个名字,国外这两年也有很多女作家拿了雨果奖。只是相对来说,女作家写短篇多,长篇少。
至于说特别有魅力的女性角色少,这倒的确是有一点,但这个问题不光是集中在女性角色身上。其实科幻作品在塑造人物方面,和其他一些作品比的确相对偏弱。男性角色往往是一个动作明星的样子,女性就常常是被动作明星所拯救的花瓶,从《超人》那个时代便是如此,有一些动作与冒险相融合的故事。另外一些科幻小说比较偏技术流,这些作品就更加不是很在意去塑造一个丰满的人物形象,还有一些科幻作品,它的主角甚至于都不是一个“人类”。比如说像《超体》这个作品,它的女主角是非常有独特性的,但是她不是正常的“人”;另外还有像《机械姬》的女主角,多么有个性,性格塑造也非常豐满,但它是一个机器人,也不是一个人类。
虽然说科幻小说作家普遍不擅长,或者说不是专注于描写和塑造人物,但因为我自己还是挺喜欢写入的,所以从我的感受来说,觉得科幻小说今后在某种程度上也会跟其他的类型小说或者传统文学结合、靠拢,慢慢地更注重刻画人物。当然,是否擅长塑造人物不能算是评判一部科幻小说的最重要标准,只能说是写作倾向,对于读者来说,根据自己的审美趣味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品阅读就可以了。
Q 你说过薛定谔是你最大的人生偶像,那么他对你的创作或者人生带来过哪些影响?
A 薛定谔对我整个人生观都有着比较大的影响,实际上他整个是把现代物理用比较自洽的一套哲学体系去解释了,形成一个唯心主义的哲学观与世界观。这就影响到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包括为人处世、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等等。
在创作上,我的很多篇作品里都有提到我自己比较关心的一个母题——真实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永远都生活在表象里面,真实世界可能是我们永远看不见的,那么我们如何通过自己所看见的假象去逼近背后的真实?《九颜色》发表之后就有人问我,这九个故事想表达什么?其实我这九个故事都是想表达如何透过表象去看见真正的东西,也就是“表象与真相”这个写作母题。另外还有一个我经常会讨论的写作母题——意识的由来——这也跟薛定谔的哲学观有关,人的意识是怎么来的,人的意识和宇宙之间的关系等等。我在小说里写到人工智能,比如《人之彼岸》就是在写入的意识和机器的意识相比较。这些都是薛定谔对我的影响。
Q 近些年来欧美科幻新作对宇宙和太空的喜爱似乎正在衰退,大热的所谓IP作品似乎鲜少着眼于宇宙和太空;换言之,像《星球大战》《星际迷航》之类的太空主题不再是主流,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这是绝对的主流。你觉得是什么导致了科幻作品的关注点不再集中于宇宙/太空?
A 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大家变现实了。宇宙和太空的尺度要远大于我们原来想象中能够达到的距离。人们曾经以为,按照火车、飞机这样的发展速度,我们很快就能发展出一些能够征服太空距离的交通工具,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比如说现在以人类最快的飞行速度,到达比邻星都要8万年,假如你要想要飞到再远一点的地方,可能得飞一亿年才能飞到银河系的另外一边,那“一亿年”显然就不是一个我们能够去想象的时间尺度了(笑)。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对于太空科技变得更现实了,写这类(太空)故事的当然也还是有的,但那种充满了澎湃激情的想象力可能比起以前就会弱一些了。
Q 你在少儿教育方面投入了很大心力,那么你会推荐孩子们看哪些科幻作品?
A 阿西莫夫的“机器人系列”都挺适合小孩的,挺有意思的。不過要说经典科幻作品的话,其实大多比较黑色,有社会批判性,比如反乌托邦的一些,还有像《安德的游戏》,是反战题材,我不太建议孩子过早地去看这类作品。一方面可能看不太懂,另一方面担心孩子会被故事中一些末世的情绪影响到。我希望孩子们小时候看的东西都是充满希望的,而经典科幻会有绝望的黑暗元素,所以个人觉得16岁以后再去看经典科幻会比较好。
Q 作为科幻作家,你平时是如何保持好奇心不断学习的?能向大家推荐一些深入浅出的科普读物吗?
A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反过来的。我不是为了写科幻才去接触新知识,而是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去学新东西,接触新科技,然后顺便写了点科幻(笑)。即使我不写科幻,我没事的时候都会去学一些新东西。我从小就是一个很有好奇心的人,喜欢去接触不同的东西,我生活的最大乐趣就是学点新东西。不光是科学方面的了,我大概从4、5开始就特别喜欢接触新东西,成长的过程中经常就愿意去学个新乐器啊,看很多类型的书啊,历史的、社会的。
科普读物的话,我建议大家要选择一些像约翰·格里宾这样的作家,他的《科学简史》很经典。为什么说要选他这样的作者呢,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科学工作者,然后又有比较好的语言能力能够去写作,这样的作者可以让大家认识到真正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