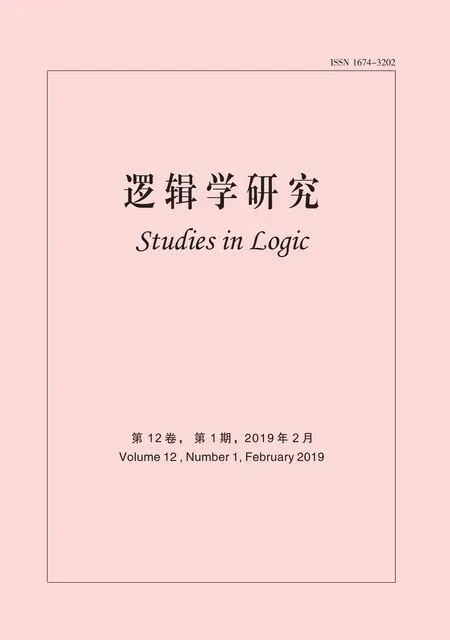因明与连珠体比较研究
王克喜
中国逻辑史的比较逻辑研究始于清末民初,历经百余年的探索和深化,越来越多的研究问题值得我们反思,越来越多的学者看到了中西逻辑和因明之间的共性与个性,也逐渐深入到了三大逻辑源流的本质与特征,比较的对象越来越明晰,共性与个性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人心。
1 问题的提出
在近代思想史上,梁启超较早地把三大逻辑源流纳入研究的视野,从而开创了中国逻辑史研究辉煌的一页。但是,梁启超的研究也留给后人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诸如他特别用力的关于三种逻辑所总结提出的推理形式,意在揭举三大逻辑源流的同异之处,特别是在逻辑共性上下了很大的工夫。梁启超认为,印度逻辑有“以宗因喻三支而成立”的三支作法,西方亚里士多德逻辑有“合大前提、小前提、断案三者而成”的三段论式,墨家逻辑也有相同于三支、三段的推理形式。([13],第104页)
尽管梁启超也清醒地认识到,“墨经论理学的特长,在于发明原理及原则,若论到方式,自不能如西洋和印度的精密”“但相同之处亦很多。”([13],第105页)于是因明三支“以宗因喻三支而成立”,“墨经中之逻辑论式同因明的三支作法的对应关系,存在着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正是两种不同逻辑学有其特殊表现形态的表现。”([13],第 104–105 页)
可以这样说,自梁启超对墨经作如是诠释以后,后世的学者多祖其说,演绎其思想,不仅仅是从事墨家逻辑学研究者如是,从事因明研究者也大有人在。章太炎就认为“辩说之道,先见其恉,次明其柢,取譬相成,物固可形,因明所谓宗、因、喻也。印度之辩:初宗、次因、次喻。大秦之辩:初喻体,次因,次宗;其为三支比量一矣。《墨经》以因为故,其立量次第:初因,次喻体,次宗;悉异印度大秦。……大秦与墨子者,其量皆先喻体后宗,先喻体者,无所容喻依,斯其短于因明立量者常则也。”([11],第222页)在章太炎看来,印度因明、大秦逻辑和墨家辩学的论式完全一样,只不过是次序有些许差别而已。
也有的学者认为“效”“揭示了三段论的基本原理”,“墨辩关于‘效’式推论的论述,反映出三段论式推理的基本原理。其中‘中效式’相当于第一格三段论的结构,‘不中效式’相当于第二格三段论的结构。”([20])
有人认为在中国古代《墨子》一书中所提出的故、理、类和西方亚里士多德所研究的三段论推理如出一辙,例如钟友联先生就认为(断言)下面的“三段论式”为墨学逻辑的一种推理方式:
·大前提——天天有义则治,无义则乱。
小前提——天欲其治而恶其乱。
结论——因此可知,天欲义而恶不义。
·可是依据“三段论式”的定义,上式根本不是三段论文。钟氏称之
为“三段论式”,只是硬套而已。([23])
也有的研究者把因明三支与墨家逻辑的故、理、类进行比较研究,我们来看墨家逻辑对故、理、类是如何论述的:“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三物,指故、理、类。辞,相当于判断,反映了立论过程中所立辞与立辞根据之间的关系,也反映了立论根据的一般性质。理与类,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名辞说等辩说形式互相联结、彼此推演中的一般关系。”([12],第216页)由此可见,把因明三支与故、理、类相比较也是不妥的,毕竟是相同属性太少。
胡适在他的《先秦名学史》中对梁启超、章太炎的《墨辩》中有三段论推理提出了批评,认为《墨辩》中根本不存在什么三段论的推理:“章炳麟先生在他一九一零年出版的《国故论衡》中,认为墨家也有三段论法的学说。他的论点的基础似乎是对我前引有关因果关系的一段话的错误解释。……我的结论是,别墨的演绎法理论不是三段论的理论,基本上是一种正确地作出论断的理论。”([9],第87页)
由于中国古代根本就不存在“三段论”的推理,所以硬要把“故、理、类”比附成三支作法或者“三段论”推理,都是不合思维实际的。即以研究者认为《墨辩》有三段论推理的根据看,这些研究者没有认识到一个推理必须在同一个思维过程之中,如果把两个不同的思维过程中的句子或命题硬排列组合到一起,从而构成一种什么推理,要么这个推理是研究者的既成之见,要么就是拉郎配,而根本不是什么《墨辩》的逻辑推理。一般的研究者都认为《墨子》一书中的《经上》《经下》为墨子所作,而《经说上》《经说下》是墨学后人所作。如果这是可信的话,那么,《经》与《说》就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思维过程,经过了不同的推理的人,无法由《经》和《说》组成一个逻辑推理。即使把《经说上下》与《经上下》都理解成同一个人所作,那么根据《经》与《说》的内容,我们认为《经》是被注释者,而《说》则是解释者,解释者与被解释者无法构成前提和结论,因而也就无法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推理。所以,我们认为中国古代就没有什么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自然也不会产生有关三段论理论的逻辑理论和思想。诚如杜米特留所引著名汉学家马赛尔·格腊内所说那样:“中国人没有三段论的爱好。”([5],第34页)
既然不能把因明三支同墨家逻辑中的故、理、类作比较研究,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与因明三支、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相近似的推理形式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连珠体。
2 因明与连珠体论式上的比较
作为一种逻辑推理形式,连珠体的定义即概念又是什么呢?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定义:(1)《逻辑学大辞典》给出的权威定义为:连珠体是中国古代一种文体,也是逻辑推论的一种形式([14],第48页);(2)《中国逻辑史(先秦卷)》则定义为:连珠是一种表达逻辑推理的文体格式([12],第330页);(3)第三种定义则是沈剑英先生在《中国逻辑史研究》中所给出的定义:连珠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综合性推论的表述形式([16],第250页)。从以上几种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三种定义虽然有些不同,侧重点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通点:连珠都表达了一种逻辑推理的形式。笔者认为连珠并不是一种很系统的逻辑推理理论,而是推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连珠体从论式的复杂性上讲,主要可以分为二段连珠、三段连珠、复杂连珠。
2.1 二段式连珠
二段连珠是扬雄对韩非的连珠格式加以改造创立的,并赋之以连珠之名。刘勰曾称赞道:“扬雄覃思文阔,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26],第363页)扬雄创立的二段连珠留下来的仅一则,虽然其推理性还不是很严格,但是他这种简约的形式却成为了后来学者争相效仿的模式。“虽小而明润矣”,二段连珠虽短小,但是精悍,说理简洁清晰,富有说服力,相比于汉赋琐屑复杂的论说,其效果是不言而喻的。二段连珠可以说是连珠的主要形式,它简约,短小,叙事性强,前后推理结构清晰。沈约曾将连珠概括为“连珠者,盖谓辞句连续,互相发明”([27],第243页)。“互相发明”这四个字清晰地表明了二段连珠的结构特点:连珠推论的前提和结论。二段连珠通常是由这两部分构成,前半部分是前提,以譬喻的形式给出,后面是结论,通常是前提在前,结论在后。有时候为说明某个观点或者结论,也将前提至于其后。但是不管顺序如何,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性质是不会改变的。二段连珠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通常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前提利用譬喻、归纳,类比等等方法阐述一个具有普遍性或者论证力高的观点或者现象,以此为基础,引出与他相关的,具有一定逻辑蕴含关系的对象或者结论。
陆机所作的二段连珠如下:
臣闻:春风朝煦,萧艾蒙其温;秋霜宵坠,芝蕙被其凉。
是故威以齐物为肃,德以普济为弘。([27],第230页)
这则二段连珠是采用了类比的方式来进行说理陈述论说的。“是故”前面的话是前提,包括春风朝拂和秋霜夜降两种自然现象。用春风、秋霜与明君的济德、施威作比,并进而从这两种自然现象归纳出一般性知识,即自然界里无厚此薄彼之分。由于这个道理很明显,所以这个一般道理就被省略了。“是故”以后的话是结论,它是通过与前提事件的类比得到的,即寒暖之于萧艾,芝蕙同厚薄,则明君施威济德于百姓应齐一。在这则二段连珠中,陆机以自然之理类比人间之理,形象生动,简洁通俗地阐明了所要论说的君臣之理。
二段式连珠,都用明显的表示前提和结论联系的词:以“臣闻”开头,“是故”、“是以”引出要论述或者论证的观点,其格式为“臣闻……是以……”这些都说明它们具有了逻辑推理的性质。前提和结论却均非单一事件,而都是具有某种共性的两个事件,因此,往往可以从两个事件中将其共性归纳出来,得出具有普遍说服力的结论来。二段连珠虽然短小,但是仍旧包含了很多的逻辑推理的形式,演绎性的论证,归纳性的结论,以及连类譬喻的比较,都具有很强的逻辑说服能力,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连珠体的推理机制中还会论及。
2.2 三段式连珠
虽然二段连珠是连珠的主要结构形式,但是二段连珠往往是省略了一些不言自明的命题或者语句,因此从其结构的完整性来讲,严格意义上讲三段连珠才是标准格式的连珠。这里我们仍旧以陆机的三段连珠为范例做下深入的分析。三段连珠是陆机为了应付更复杂的推理情况而创立的,可以说三段式的连珠是陆机对于连珠体的最大贡献,可以说三段式的连珠使得连珠的形式结构更加的固定化,也进一步地形式化了,这是古代逻辑学界先哲们探讨命题推理的形式化,将逻辑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最佳代表,对于丰富中国逻辑史的推理类型,扩展我们对于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认识和眼界是非常有帮助的。陆机的三段式连珠主要分为两种基本形式,分别是:第一种“臣闻……何则?……是以……”式,第二种“臣闻……是以……故……”式。
例如:
臣闻:寻烟染芬,薰息犹芳,征音录响,操终则绝。(论题)
何则?垂于世者可继,止乎身者难结。(理由)
是以玄晏之风恒存,动神之化已灭。(喻证)([27],第232页)
这是一首用“何则”和“是以”连接起来的三段连珠。是陆机常用的一种三段式连珠形式。第一段(“何则”前面的话)讲的是具体事例,第二段(“何则”后、“是以”前的话)讲的是一般性道理,第三段是关于人的具体情况。第一段的具体事理是凭借第二段的一般道理而确立的。换言之,第二段是作为第一段的论据出现的,故用“何则?”连接。第二段和第一段之间具有演绎推理的性质。而第二段又和第三段构成省略小前提的演绎推理。第一段和第三段可以看做是类比,也可以把第一段看作是喻例或者是例证。这则三段式的连珠类似于印度因明的三支推论,只不过比喻的喻体有些差别罢了。这是一个标准的三段式连珠,其中有论题,理由,还有喻证构成。这里的连珠论式总是会借助于譬喻、喻证等来引出或者比较出所要阐述的或者表达的观点和结论。
2.3 复杂式连珠
在结构上除了二段式和三段式的连珠之外,还有一种复杂的连珠形式。二段式和三段式连珠虽然简洁,结构清晰,推理思维严密,但是其论证性的力度还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复杂的说理论证的情况,简单的二段连珠或者三段连珠是不能够也不具备其说服力和论证力的。因此,在实际的连珠使用中,往往将多段连珠混在一起使用,既避免了长篇累牍的繁琐论述,同时也保留了二段式或者三段式连珠简明、直接推理、说服力强的特点。
例如:
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假言前提)
其说在:侏儒之梦见灶,哀公之称莫众而迷。故齐人见河伯,与惠子之言亡其半也。(正面例证,列举四则故事)
其患在:竖牛之饿叔孙,而江乙之说荆俗也。嗣公欲治不知,故使有敌。(反面例证,列举三则故事)
是以明主推积铁之类,而察一市之患。(比喻性质的结论,包含两则故事)([12],第331页)
这一则复杂的连珠推论的前提由两个假言命题组成,接着用一系列历史故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归纳,最后以两则故事作结。整个推理过程列举九则故事,每则故事都是独立的,但显然有着内在的联系。“其说在……”中的四个故事和“其患在……”中的三个故事是用来从正反两方面证明概括性前提的,用的是归纳法,是概括性前提得以成立的根据;而从每一则故事与结论的关系来看,又具有类比的性质;再从结论与假言前提的关系来看,又显然是演绎的关系。韩非这里的复杂连珠中有融归纳、类比和演绎于一体的错综的逻辑关系,它把许多事例用逻辑方法串连起来,在语言形式上又“若珠之结排”,形成了架构性非常强的逻辑推理方式,称之为连珠极为贴切。
因明三支也经历了十支、七支、五支、三支和两支论式的演变:佛教逻辑的发展,有着明晰的线索,窥基大师曾在他的《因明入正理论疏》中说:“劫初足目,创标真似;爰暨世亲,咸陈规式,虽纲纪已列而幽致未分,故使宾主对扬犹疑立破之则。有陈那菩萨,是称命世,……匿迹岩薮,栖虑等持,观述作之利害,审文义之繁约,……于是覃思研精,作因明正理门论。”([17],第8页)从窥基的话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三点:第一,佛教逻辑渊源于足目的逻辑;第二,古佛教逻辑的各种形式论在世亲手中得到完成,所谓咸陈规式;第三,陈那针对世亲完成的佛教逻辑之“幽致未分”而创立新佛教逻辑。其实,窥基的这个概括同佛教逻辑论式的发展也是一致的。
在古代印度,佛教内部诸派别之间,佛教与其他教派之间常常展开论辩,而论辩的结果之惨烈又确实令人难以置信。为了辩胜,为了维护教派尊严,论辩者必然要认真仔细地研究论辩的整个过程,必然要强调使用一些方法方式,因此,最初的佛教逻辑的论辩方式也就慢慢地得以成形。
早期的佛教典籍中记载了这样一些论辩过程中必须要具有的一些组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经过反复推敲,反复研究并不断完善,也就成为一种论式而逐渐定型。《长阿含经》在第八卷《众集经》中说道:“复有四法,谓四记论,决定记论、分别记论、诘问记论、止住记论”。这一段话实际上是在传授一些论辩技巧,强调在论辩的过程中首先要把论辩的问题搞清楚,然后在论辩的具体过程中该回答的问题就去回答它,不该回答的问题要保持沉默或不理睬,不仅如此,有时候还要主动出来,采用反问的方式向论敌发起进攻。
《俱舍论》中也论及“五问四记答”的论辩术问题,五问即是指:不解故问,疑惑故问,试验故问,轻触故问,为欲利乐有情故问。四记答和《长阿含经》所讲的四记论内容相同。
需要指出的是,在《阿含经》中已经有关于佛教逻辑论式的萌芽的出现,在《阿含经》中有“知”、“处”、“喻”三支论式的描述。“处”约相当于结论,“知”约相当于小前提,“喻”则约相当于大前提。如《杂阿含经》中就有这样的论式:
(知):当观五阴无常,如是观者为正观,
(喻):正观者,则生厌离,
(喻):厌离者,喜贪尽,
(喻):喜贪尽者,说心解脱,
(处):如果比丘观五阴无常,心解脱者。([22],第20页)
相传为足目所著的《正理经》应该算是佛教逻辑的起点,《正理经》共分五卷十章,在第一卷第一章就开宗明义提出了正理派的十六句义。
在足目及其传人所完成的《正理经》中,五支论式已经确立,具体表述为:
(论题)宗:此山有火
(论据)因:以有烟故,
(例证)喻:凡有烟处皆有火,如灶,
(运用)合:此山如此(有烟),
(结论)结:故,此山有火。
《正理经》已经不仅仅是在具体运用五支论式进行论辩,而且还从理论上定义了“宗”、“因”、“喻”、“合”、“结”五支,例如它对“宗”的定义就是“是被什么证明的陈述”等。
五支作法具有如下一些特点:首先:五支作法(论式)是一个论辩的程式,体现了论辩双方对论题的一个论证过程。“也就是说,最初,因明是一门辩论术,这就是说,因明是耍嘴皮子的工夫,技巧,这样一搞呢,因明的名声就不大好,于是有人就把因明的内涵做了一下扩充,给加上了一个新知识的获得方法,这样一来,因明的范围就大了,成了:因明是立敌双方的论辩方法和对一个命题的论证技术,以及新知识获得的决窍。”([8],第2–3页)“后来佛家又把因明的界定作了扩充,扩成了系统的量论,主要代表著作有公元六世纪初陈那论师的《集量论》以及公元七世纪时法称论师的《量评释论》,这时候因明就不但要承担如何与对手论辩,对一个命题如何论证,如何使自己获得更多的新知识,而且要讲求如何使得别人领悟我自己的观点,所获得的新知识如何成就,如何分类,如何审核等,这实际上已经使因明变为了你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也就是说成了现代哲学的知识论。”([8],第3页)究其实,五支论式为了做到能够“悟他”,它实际的论辩程式应该是如下的格式:
甲:声无常。
乙:为什么?
甲:因为它是所作的。
乙:是所作的又怎么样?
甲:大凡所作的都是无常的,如瓶。而声正好如此(是所作的),所以,声无常。
第二,五支论式是一个论证式,而不是推理式。《正理经》关于“宗”的定义表明五支论式的整个过程都是为了证明宗的,而不是从已知前提推出宗的。《正理经》的宗义是这样的:“已经确立的观点、蕴涵或者假设的观点即是宗义。”宗义就是立论一方所坚持的观点。“而正理派的宗义呢,则包括自己成竹在胸的观点以及还处在假设中的观点,即,只要是在辩论的时候你举出的观点,就叫宗义。甚至说一个观点成立,则随之而成立的另一个观点,也可以称为宗义。比如说,只要成立了无常,则无我也就同时成立了。无我也可以称宗义。”([18],第22页)五支论式与三段论的论式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五支论式既包含有演绎性因素(这种演绎当然是指从论据推向论题,也就是从因喻到宗的思维进程,例如,凡有烟者有火,这山有烟,所以这山有火,因此,宗也就得到了证明),又有类比的因素(灶:有烟,有火;这山:有烟,所以这山有火,也就是说,灶和“此山”在有烟的属性上相同,灶有火,因此可以推得此山有火,也就可以证明此山有火),同时还具有归纳的成分(灶有烟有火,因此,凡有烟者皆有火)。
从事比较逻辑研究的学者习惯于把五支论式同三段论相比较,究其实是因为五支论式和三段论式具有一些相同的性质,如果不考虑论证和推理的区别,如果不考虑思维进程方向的差异,如果不去考虑有效推理和说服论证相异性的话,这种比较具有非常正确的合理性,但如果考虑以上诸因素,我们觉得,佛教逻辑的五支论式可以和中国逻辑史上曾经发展的一种论式——连珠体进行相关的比较。
“连珠者,盖谓辞句连续,互相发明,若珠之结排也。”沈约的这段话实际上点明了连珠体的性质和特征。“辞句连续”是指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一些话语的有机组成,“互相发明”则是点出了这种论式的逻辑性质,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启发,递相启迪的。德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洪堡特曾指出过,在汉语的句子里,每个词摆在那儿,要你斟酌,要你从各种不同的关系去考察,然后才能往下读,由于思想的联系是由这些关系产生的,因此,这一纯粹的默想就代替了一部语法。([10])汉语注重的是“互相发明”,连珠体也注重“互相发明”,体现了汉民族思维过程中浓烈的意会性。沈剑英曾把连珠体同三段论、佛教逻辑论式进行过比较研究,认为:“由此可以看到,这首连珠虽然只有前提与结论两段,但其前提具有归纳的性质,其结论则具有演绎的性质,前提与结论并不具有直接的推导关系,其间还隐含着一个类比的过程,类比的前提原来就是从归纳得出的结论,类比的结论则又作了演绎的前提。而且其类比又是异类相比,与一般类比推理的同类相比显然不同。”([16],第257–258页)
从都具有类比、归纳、演绎性的角度来看,连珠体与佛教逻辑的论式真的是“何其相似乃尔”,如果除去思维进程方向的差异,同是在说理的性质上,连珠体与佛教逻辑论式就是太相似了。
第三,五支论式带有明显的心理因素,是“实践的论证”。我们在前面指出过,佛教逻辑带有明显的宗教感情,这种宗教感情导致了五支论式在论辩过程中必然具有的心理痕迹。这种“实践的论证”既要依靠一定的符合逻辑的“技巧或技术”,又要依靠“俨然有序”的心理过程和浓烈的宗教情感。在为《正理经》进行注释的过程中,富差耶那就把宗、因、喻、合同四种认识方法进行了一一对应,体现了这种论式的心理因素。富差耶那把宗与圣言相对应,把因与推理相对应,把喻与感知相对应,把合与譬喻相对应,个中体现的心理因素实在是显然不过了。
3 因明与连珠体推理机制的比较
对于佛教逻辑论式性质的认识,我国的很多学者有过很多见仁见智的理解和思想,这些理解和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者们对佛教逻辑的认识。
一、演绎说。由于比较逻辑研究的兴起,也由于比较逻辑研究还不够深入,或者说比较的目的更主要的是为了求同,为了寻找出三大逻辑发祥地的逻辑的共性,从事这方面的比较研究往往首先看到的是这一点。
巫寿康在《因明正理门论研究》中指出:“因明史由三种因明学组成,先后顺序如下:古因明学说,陈那因明学说,法称因明学说。古因明学说是或然性推理,陈那因明学说是带有归纳成分的必然性推理,法称因明学说是纯粹的必然性推理。……本书提出的同品、异品新定义,使因明论式又是必然性推理,又满足九句因、因三相、三支中归纳成分的要求。”([21],第15页)这种研究受到了后来的研究者们的强烈反对:“就采用修改《门论》关于异品定义的作法。我认为是不可取的。”([25],第30页)更有甚者,有的研究者认为:“它不是逻辑,现在人把因明用符号操作,就丧失了因明本身的意蕴。”([8],第11页)
其实,逻辑学界对佛教逻辑的论式的研究更多地是拿它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式进行比较,“(1)三段论的法式是思维的法式,三支作法是辩论的法式;(2)三段论法是在演绎断案,三支作法是在证明断案;(3)三段论法是以思维正当为目的,三支作法是以辩论胜利为目的;(4)三段论法不像三支作法留心过失论;(5)三段论法不像三支作法混合归纳法;(6)三支作法的因,不像三段论法备列命题的全形。”([3],第26–27页)正如张忠义在《试论因明的三支论式》中所指出的那样:“国内外学者对三支论式的理解不尽一致。就我所见到的材料,大多学者采用比较研究方法,把三支论式或比为三段论第一格AAA式,或比为充分条件假言推理肯定前件式,或比为由充分条件条件假言推理转化来三段论。”([24])经过张忠义的分析和研究,认为上述三种不尽正确,他认为三支论式应该是“外设三段论”。综观上述诸家,观点虽有差异,理解和分析也有区别,但是,诸家都是把佛教逻辑的三支论式当作是演绎推理的。
二、归纳说。陈大齐曾对佛教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特点作过比较分析。他认为:“因明轨式,宗前因后,其与逻辑,次第不同。立者立宗,若与敌符,宗已有过,不烦更说。必所立宗,敌论不许,立者乃须显示所由。故于因明,宗必在前,因必在后,不可移易。立量轨式,既果先而因后,所寓归纳推理亦须顺此,首先广集宗同异品,次察同品之所以同是否缘于具有此因,又察异品之所以异是否缘于不具此因。因明归纳,自果求因,有关量式,定非偶然。归纳演绎,其在逻辑,各相独立,归纳不必兼及演绎,演绎不必兼及归纳。因明寓归纳于演绎之中,每立一量,归纳一次。此为两者所不同。”([1],第66页)“因后二相即逻辑之归纳推理。逻辑归纳,不呼其宗,因明除之,此为二者不同之点。同品除宗,犹有一利,可免循环论证之讥。逻辑之法,集诸事例,归纳以造普遍原则,继复自此普遍原则,演绎推理,返判彼诸事例之一。论者讥之,谓为循环论证。因明同品既除其宗,能证所证显然有别,自无循环论证之嫌。”([1],第58页)
三、新因明是最大限度的类比推理。郑伟宏在《陈那新因明是演绎论证吗》中指出:
因三相是保证三支作法的演绎论证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同喻满足因的第二相,异喻满足因的第三相,同异喻体不能互推,因而不能缺一;异品若除宗有法与新因明整个体系相矛盾。三支作法虽然避免了古因明无穷类比的缺限,但新因明本身不过是最大限度的类比论证,若把同异品除宗有法表示出来,可以举例如下:
宗 张三有死,
因 因为是人,
同喻 除张三以外,凡人皆有死,如李四,
异喻 除张三以外,凡不死者皆非人,如石头。
一看就明白,这不是演绎论证,因喻符合因三相,但不能必然推出宗。 ([25],第31页)
由于佛教逻辑的组成部分中有喻支,有同喻、异喻,所以,佛教逻辑的三支性质的类比性为大部分学者所首肯。
有的学者并且对三支作法性质的归纳性、演绎性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如汤铭钧就指出:“认为三支作法是演绎与归纳相结合的形式,其结论是必然的,这是国内因明学界长期流行的一种观点。……从归纳的方面说明三支作法不是完全归纳,从演绎的方面说明三支作法不是演绎推理,因而三支推理的结论并不是必然的,三支作法是最大限度的类比推理。”([19],第328页)
有的学者认为,从古因明到陈那到法称的因明史“反映了从或然性推理向必然性推理发展的过程。”([21],第15页)而更多的研究者认为,古因明是没有喻体,因而仅只是类比,陈那新因明增加喻体,还分了喻依和喻体,因而也就成为带有归纳成分的演绎,到法称时代,由于删去了喻支,又把宗、因顺序重新整理,遂成为纯粹的演绎。
其实,不论从古因明学说,陈那因明学说,还是到法称因明学说,也不论是因明十支、因明五支、三支,还是因明二支作法,因明的性质都没有多大的改变,都是一种论证或论辩,而不是一种推理。既然是一种论证,那么论证的可信度就成为论辩双方所高度关注的。论证追求的不是一种有效性,而是一种说服力。追求有效性的是演绎推理,追求说服力的是好论证。因此,佛教逻辑的论式应是论证的模式而不是推理的模式,论证的模式自有其论证的评估标准,而不能用所谓的推理的有效性去评估这么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传承的论证模式。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6],第206页)
此外,佛教逻辑论式的背后还包含有强烈的宗教情感和印度民族的思维模式和世界观模式。在古代印度,不仅仅是佛教,几乎所有的学说派别都是把解脱当作最高真理,而且都强调解脱是绝对真实的。“但是,解脱的情形到底什么样,对个人来说,都不知道,这时古印度的各家学派都表现出一种宗教状态,各家都成立各自的圣言量。各家之间,圣言量各自不同,就有了论争。在自己的学说体系之间,在宗教悲情上所确立的圣言量,该如何再在自己的知识上成立,仍然需要论证,所以它必须回头找根据。”([8],第5页)宗教信仰,圣言量在佛教逻辑的论证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佛教逻辑也被一些学者称作知识论。
古因明论式带有明显的类比性,那么陈那的新因明是不是带有归纳成分的必然推理呢?如果把三支论式同品、异品除宗有法表示出来,可以举出如下例子:
宗 声无常,
因 所作性故,
同喻 除声以外凡所作皆无常,如瓶,
异喻 除声以外凡恒常即非所作,如虚空。
由于佛教逻辑是论辩逻辑,而论辩的起点正在于同品、异品除宗有法,“在共比量中,证宗的理由必须双方共许。立者以声为常宗,自认声为同品,但敌者不赞成声为常,以声为异品。因此,在立量之际,声究竟是同品还是异品,正是要争论的问题。如果立敌各行其是,将无法判定是非。当立取声为常住的同品时,其所闻性因,同品有非有而异品非有,则成正因;当敌取声为常住的异品时,所闻性因于同品非有而异品有非有,又成相违因,出现过失。同一个所闻性因,既成因又成相违因,是非无以定论。因此在立量之际,因明通则,同异品均须除宗有法。否则,双方都会陷入循环论证,同时,一切量都无正因。”([25],第34–35页)正是因为“同、异品除宗有法”,那么同、异喻体的所谓名称实际上还不是一个全称命题,因为“宗”被除外。
也正是因为“除宗有法”,所以,“陈那的因三相理论一方面纠正了古因明容易陷入无穷类推的不足,提高了类比推理的可靠程度;另一方面它又终究未能保证喻体成为真正的全称命题,只有量的扩大,而没有达到质的飞跃。可以说,因三相理论先天不足,它的后二相根据以果求因的原则提出来的,以果求因,就只能把宗有法排除在外。”([25],第43页)
法称对佛教逻辑的论式进行了改进,一种改进是颠倒了宗、因、喻的顺序,把原来最后一支的喻体的部分提到最前面,把原来的宗支置于最后。“这三支按先后顺序分别相当于逻辑三段论式的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这种顺序的调整,就构成了从一般认识应用到个别事例上的演绎推理方式,并与一般人的运思顺序相一致,把思维活动和语言表达统一了起来,这确是一个进步。”([7],第256页)法称的另一个改进是“舍弃喻支,使论式变为宗因二支,如声音无常,所作性故。这是一个极大的改进,把三支论式这一演绎和归纳法掺合在一起的推理形式推向纯演绎法,是对因明推理学说的一大发展。”([15],第25页)
陈那改造古因明五支为新因明三支,法称改造陈那新因明三支为两支,研究佛教逻辑的学者们都认为是改变了佛教逻辑的性质,从类比到含有归纳成分的演绎,再从含有归纳成分的演绎到纯演绎,似乎是符合佛教逻辑发展的历史:从或然性推理向必然性推理进化。这只是研究者的一厢情愿,佛教逻辑到底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应该由佛教逻辑发展的实际去决定,应该由佛教逻辑的性质去决定,应该由佛教逻辑发生发展的文化背景去决定,而不能以对有效性的追求做决定。
我们认为,首先,佛教逻辑的目的不是求真,或然性与必然性在佛教哲学佛教逻辑里并不重要,佛教逻辑的功用是证明佛的观点都是正确的,是为了让越来越多的受众接受这种思想,否则,佛教逻辑就不是佛教宣化的工具而成了一种包袱。从佛教逻辑的观点看,能够成为知识的来源很多,可以是感觉量,可以是推理量,也可以是圣教量,还可以是比喻量,抑或还可以是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探讨。([15])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思维方式会对人们的接受程度带来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佛教逻辑专注的是如何使人们接受一种观点,当然这种观点必须是佛的思想。其次,佛教逻辑是一种论证,而不是推理。论证的过程只要使受众相信并接受,这个论证就是好的论证,它不要求具有必然性。这一点因明与连珠体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打开先秦诸子百家的典籍,在他们的精彩美妙的论辩中,有多少是必然性的论证呢?相反,那些善用譬喻、巧借故事的一个个论证却往往显得通俗易懂,深入人心。再次,佛教逻辑所列的一系列论式的宗都是当时不同教派之间的具有纷争不息、互不相让特点的命题,也正因为是这样,也才有“除宗有法”的要求,如果没有除宗有法的要求,那么,争辩双方就没有相异之处,也就没有了辩论,宗也就不再成为不同教派之间关注的话题了。所以,法称的消去“除宗有法”的限制,实际上是抹去了双方论辩者在观点上的对立,所以,推理是演绎的,论证也是演绎的,但却没有了论辩,也就失去了佛教逻辑存在的价值。
最后,我们还认为,佛教逻辑是一种论辩逻辑,论式的简化,只不过是学理性在增强,丝毫无益于佛教教义和思想的宏大,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在佛教来华以后,佛教几度鼎盛,而佛教逻辑却未曾有过一次兴盛的原因。“从这一层着眼,五支论式向二支论式的发展走的实际上是理论、方法的‘学理化’的道理,有越来越脱离因明创立初衷、越来越疏远信众(听众)的倾向。如果说佛教需要‘大众化’的话,作为其理论和方法一部分的因明,则越来越倾向于精神上的‘贵族化’了。”([4],第284–285页)所以,佛教逻辑的论式的二支化要么是一种推理而不是一种论证,作为为他推理的一种形式:先喻后因,省略宗,这绝对不会是不同教派或者不同观点之间的交锋了,也就失去了佛教逻辑的本真了。关于这一点,沈剑英在《佛家逻辑》一书中给予了正确的评价:“法称可以根据同、异二支分别组成论式,而不需要在同一论式中同时举出喻的两支。据此,我们可知,法称淡化了喻支在论式中的作用,同时也就淡化了因明的论辩特色。”([17],第177页)“法称认为宗‘非亲(直接的)能立’,并更认为其‘传(间接的能立)亦无功能,即宗既不具直接的(‘亲’)能立作用,也不具间接(‘传’)能立作用,所以它是无能的。但我们从论辩的角度看,宗具有标明论争目标的作用,也是能立(论式)的组成部分。从以上的论说我们可知,法称改变了论式支分的秩序,同样使因明的论辩特色淡化了。”([17],第181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法称的理论已渐脱离因明的佛教性质。”([17],第173页)
4 因明与连珠体内在逻辑结构的比较
除了从论式上、推理机制上进行比较,还要注意因明与连珠体内在逻辑结构上的比较,以进一步探析它们之间的同异。
首先,连珠体一二三段甚至复合连珠体的前提之间不构成严格的逻辑关系,既不像三段论那样有大前提和小前提的区分,也不像因明那样具有宗、因、喻、合、结的严格顺序。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因明整个辩式有严格的顺序,而连珠体的前提顺序则相对灵活。譬如陆机的连珠体“臣闻:禄放于宠,非隆家之举;官私于亲,非兴邦之选。是以,三卿世及,东国多衰蔽之政;五侯并举,西京有陵夷之运”([2],第32页),这个连珠体完全可以这样改写:“臣闻:官私于亲,非兴邦之选;禄放于宠,非隆家之举。是以,三卿世及,东国多衰蔽之政;五侯并举,西京有陵夷之运。”也就是说,两个前提的顺序不固定。更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把这一段连珠体加以标号:“臣闻:禄放于宠,非隆家之举[①];官私于亲,非兴邦之选[②]。是以,三卿世及,东国多衰蔽之政[③];五侯并举,西京有陵夷之运[④]。”我们可以整理这个连珠体的推理内在解构是:①→③;①→④;②→③②→④;①∧②→③;①∧②→④;①∧②→③∧④;②∧①→③∧④;……以此类推,如果是三段或者复合连珠体,情况就会更加复杂。通过对连珠体的研究我们发现,连珠体的前提更多使用一个个寓言、故事、传说、历史等案例来增加说服的力量,因此,这些寓言、故事、传说、历史等案例无非是两个效果:第一,增加气势,达到修辞效果;第二,增加聚合论证的证据,达到辩说的效果。
我们在考察多个连珠体的内在逻辑结构时发现,不论是一个人撰写的多个连珠体,还是多个人撰写的不同连珠体,也不论这个连珠体是以演绎性为主,还是以归纳、推类性为主,都可以做这样的理解与分析。
这一点,在因明的辩说中看不到,这也就说明了我们的连珠体还不是纯粹的逻辑形式,还没有完全从文学创作中剥离出来。
其次,从因明和连珠体常常使用的辩说内容上来看,二者也具有明显的差异。中国的连珠体的推理可以构建如下模型:
(上升线代表归纳法,下降线代表演绎法,左右箭头表示推类,尤其是异类相推)
再次,连珠体的深入归纳法的性质与因明归纳性质的比较。因明的归纳性质还是和西方传统逻辑有相同之处的,由“瓶是所作,瓶无常”,归纳出“凡所作皆无常”,而连珠体的推类则是这样的归纳推理形式:
这种推类的形式可以用如下公式表示:
再次,连珠体的内在组成部分重在事理,不强求形式,和胡适所讲的墨家逻辑特征“有学理的根本,而没有法式的累赘”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个特征使得连珠体的“段”或“支”不特别强调顺序,既不像三段论那样有大小前提之分,也不像因明那样有严格的“宗因喻”格式之分,连珠体使用的前提可以自由流动,使用的故事可以移前移后。只要能够达到说理的效果,形式可以随着说理的内容走。例如前述的二段连珠体“臣闻:春风朝煦,萧艾蒙其温;秋霜宵坠,芝蕙被其凉。是故威以齐物为肃,德以普济为弘。”完全可以这样表述:“臣闻:秋霜宵坠,芝蕙被其凉;春风朝煦,萧艾蒙其温。是故威以齐物为肃,德以普济为弘。”三段连珠体:“臣闻:音以比耳为美,色以悦目为欢。是以众听所倾,非假百里之操;万夫婉娈,非俟西子之颜。故圣人随世以擢佐,明主因时而命官。”也可以这样表述:“臣闻:众听所倾,非假百里之操;万夫婉娈,非俟西子之颜。是以音以比耳为美,色以悦目为欢。故圣人随世以擢佐,明主因时而命官。”还可以做其他几种变换。由此可以看出,连珠体的“支式”很自由,也很灵活多变。
- 逻辑学研究的其它文章
- 因三相辩证
- 论集合论的模型
- 《名理探》中对逻辑作为一门科学的讨论